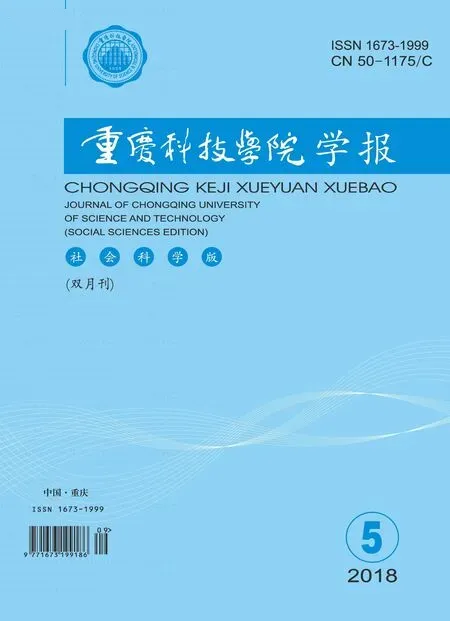近代知识分子革命思想互动的历史考察
——以恽代英与陈独秀革命思想互动为例
凌承纬,刘兴旺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残渣泛起,民国有名无实。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来探索中国的新出路。
一、从自由民主到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多元价值面貌中的最初转向
“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的消息封锁,他们无法得知有关于“十月革命”的直接讯息。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最早讴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他的《庶民的胜利》也明显带有无政府主义反专制、反权威、反阶级的色彩。“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一度对欧美式的自由民主推崇备至,奉为圭臬。他们向往和效仿的仍旧是欧美先进国家,心仪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仍旧是欧美国家流行的改良型的社会主义,而非苏俄革命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使得知识分子对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彻底失望。知识分子对当时北京政府的不满,也在抗议外交失败的过程中愈发加深。陈独秀原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评价极高,称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美国没有在巴黎和会上主持公道,失望之余,陈独秀痛斥威尔逊是专说空话的“威大炮”[1]391。他对威尔逊评价的转变,恰恰说明了世变对知识分子的冲击。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者之前,恽代英尚且只是一位知识青年。跟所有处在纷繁驳杂的“五四”思想解放浪潮中的知识分子一样,恽代英也受到了多种思潮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宣称的唯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是杂糅着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新村主义,亦或是工读主义对新生活、新制度的试验等主张温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专制独裁、卖国媚外的军阀政治土壤中连政权的边都够不到,更遑论民主自由。
从深切的期望跌落到残酷的现实,大多数知识分子跟陈独秀一样,很容易转而接纳批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张东荪就曾说过:“欧战结束前几乎没有人谈社会主义,但欧战结束之后,讨论社会主义成为潮流”。在传入中国的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既有反对改革、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也有反对一切政府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种种理论的主张者相互争鸣,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宣传乃至实践,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渴望社会变革的求变心理,另一方面则增进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理解。当时的苏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理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其所主张的马列主义,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尽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初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重建。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时局,不禁开始思考: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曾是经济落后、政治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但是,俄国在采取马克思主义之后便能面貌一新,那么,中国“以俄为师”则同样有可能从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先进国家。思想界从崇尚欧美的自由民主向崇尚社会主义的转变,直接反映在当时的出版物上。陈独秀和李大钊主要是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来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像《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晨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刊物,它们的立场未必一定是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一支,给予大篇幅的介绍和讨论,也在有意无意间起到了相同的传播效果,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关注和学习的对象。
二、改良还是革命——陈独秀改造社会的路径选择对恽代英的传导
辛亥革命只是颠覆了腐朽不堪的满清政权,中国的政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民国成立后的政治乱象不免让知识分子对是否应该革命产生了困惑。
恽代英早期虽然看到了革命的价值,但其思想更倾向于依靠平民的能力,借由“利群”式的活动来改造社会。流血的革命事业,只是“最后的”,亦是“利害参半的手段”[2]247。 恽代英对革命的理解,在于他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的前车之鉴:要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不在轰轰烈烈的破坏”,也不在蛮横的军阀、无能的官僚、腐败的政党,关键“还在善战无名的建设事业”,而建设事业只有通过普及教育、改造自身、提高觉悟、组织分工与互助的团体来实现。在他看来,彼时对于改造中国的意见,无论是主张切实、根本的实业、教育,还是主张猛烈激进的革命,其实并不存在有不可调和的差异,只是在具体的手段上的分歧,而分歧恰恰要借助协力互助来弥合。
此时的恽代英对革命的认识主要受到了两类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1920年9月至 1921年7月,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华讲学期间,大谈中国不能革命,只能通过平民教育、道德进步来实行社会改良,一时间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其实早在罗素来华之前,他的这些观点就被其拥趸者大量刊登在当时的《时事新报》《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恽代英在翻阅这些刊物后就说:“东荪先生先于共产亦未达,间乃推重罗塞尔之说”[3]654。查阅现存的恽代英日记可以发现,他阅读次数最多的报刊正是《时事新报》和《东方杂志》。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反暴力革命特征的影响下,恽代英认为“吾人所以立国”的根本是“平民之思潮”,“平民商会及其他平民活动,应力兴扶翊”“较不得已而发生武力的革命,稳健而有效力多矣”[3]583。 这一时期除了主张用非暴力的温和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以外,恽代英的主张还杂糅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恽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香浦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3]652。他所赞成的“新村”更加类似于王光祈所设计的“工读互助团”⑴,1920年2月成立的利群书社正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2]311。 由此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中的“非暴力”和“发展资本”在这一阶段对恽代英的影响更为深刻。
到1920年10月的时候,恽代英认识到“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工会罢工,亦非根本良法”[2]244。 这个转变一方面来自于是年年初,胡适与周作人就新村主义辩论。胡适指责“个人主义的”新村生活,主张“一点一滴”“一尺一寸”地改造社会。恽代英对于胡适是颇为崇拜的。在他看来,北京的那些风云人物要么“骄、滑、滥”,要么“弱病”,唯有“适之、漱溟两先生最优”[3]614。 除此之外,工读互助团“不信经济压迫,能力不足”[2]312“用一手一足之劳,想逆经济潮流与资本家争胜”都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只有通过“互助共存”,通过组建一个“进行共产主义的资本团体”,靠着“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2]244。恽代英认识上的转变无疑来自于实际斗争经验的增多和理论修养的不断加深,他逐渐认识到了互助友爱的理想并非先进的斗争利器,脱离现实、脱离革命大谈新村建设、普及教育、发展实业只不过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空想。
在当时,即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知识分子心中公认的启蒙导师的陈独秀,同样经历了从相信自由民主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后传导给恽代英等知识分子。早年,陈独秀把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视为“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乃局何等”[1]99。他提倡欧美式的民主,认为近代文明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对军阀政治下的议会制度本身深恶痛绝。“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尤其是当陈独秀发现经济不平等如同大山一般压在平民大众身上时,他对欧美式的议会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自由的、平等的……相爱互助的”[1]507。欧美式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是人人平等,选举时每人一票,而实际上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是拥有巨大资本的资本家。普罗大众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中还是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境况。
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际强权、政治的罪恶、私有财产的罪恶、战争的黑暗、阶级的不平等”等“黑暗的方面”都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奋斗,利用人性上光明的方面”去改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当做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1]447。可见,在此时,陈独秀是赞成将工读互助作为新社会、新生活的实践方式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刊登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的《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赫然写着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蔡元培等人名。1920年3月 5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的发起人也包括陈独秀[4]605-606。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报告当中。恽代英在1919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更喜欢看见你们的会务报告”[3]624。 可见,陈独秀这时的立场至少为恽代英所熟知和赞同。
然而,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小组大多昙花一现。1920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一组关于工读互助团问题的文章。陈独秀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完全是“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若有上述的缺点,就难保不会失败。所以,“老实说,互助团不能办”。除此之外,改造社会、改造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制度的改造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北京“工读互助团”以为他们是新思想、新制度底(的)产物,便不须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他们便因此失败了[5]54。此时,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制度的改变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消灭掉由私有财产制度和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所以,当时中国是需要国家、政治和法律的。“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只不过“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5]37,这种倾向是陈独秀所不赞同的。“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5]60。
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在第一时间传导给了恽代英。这一时期的恽代英正是通过阅读与新文化的倡导者有了即时性的互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3]624。 所以,恽代英在给王光祈的信中明确指出了对工读互助团失败原因的错误认识,认为“经济压迫,能力不足”才是导致工读互助失败的理由[2]312。在1922年6月1日的《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中,恽代英对他之前所赞同的办实业、办教育的主张有了不同的认识,那就是在“资本阶级”旧势力没有得到改造之时,像“办市政、办实业、办交通事业”等等这一类物质文明的推行,“民众所能受其福利者几何”?还有他一直坚持的兴办教育,在现有制度之下,也不过是给资本家提供的“智识界的一般商品”。这种结果不禁让恽代英产生了改造究竟有“甚么了不起的意义可言”的反思。譬如经营新村事业,创造工读互助团,“以为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事业。然而结果只有挫折与失败”。在不合理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彻底改变旧社会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2]330。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工读互助运动的洗礼,恽代英才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三、队伍、手段、目的——革命道路上的殊途同归
在确定了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后,就存在着对于革命的组成者,也就是由谁来充当改造旧社会力量的认识。恽代英认为,既不能“专靠自己纯粹的血与汗”,也不能“利用别的靠不住的势力”[2]331,可以利用的只有群众的力量。主要原因是:第一,贵族或资本家的利益是靠剥削掠夺而来的,“与平民的利益断乎不能两立”,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天然站在了反对革命的一面。第二,武人对于自身的力量还没有透彻的认识,这显然是由于其“粗暴而浅见”。倘若武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多半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虚荣和私利,亦不能为革命所用。而集合群众的力量并不需要采用理论的说教,群众在经济生活中是受压迫最为严重的阶层,由此而内生的“反动”力量若能集合起来,将是最团结而有力的改造力量。
只是,群众是为着反抗经济生活的压迫、反抗敌对势力而联合起来的。恽代英认为这种联合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类本能,既不需要被煽动,也不可能被阻止。而本能所能带来的后果是无法预计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利用群众、引导群众,让群众本能的力量在理性的、智慧的指导下,投入到“最有效力”的破坏和建设运动中去。
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恽代英的革命观已经十分明确了。他不赞成少年学会的同志乃至年轻人去从事“慈善家、教育家,乃至各种社会改良家”的职业,因为想利用旧势力,也就是贵族、资本家和武人来推翻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设新事业,显然是与虎谋皮。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并不是判断其进步与否的关键所在,工程师、教员等等职业与旧制度的官吏职员相较,并非前者就比后者进步,而仅仅只是具体活动上的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所设定的目标应该是革命运动,而非“不生什么真实效力”[2]333的改良运动。
此外,想要充分合理地发动、利用群众的革命力量,首先,“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知彼”,才能使群众接受引导;其次,“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进化论”。应当熟悉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谋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也就是说建立在“知己”基础上的指导才能有的放矢;最后,“不可不求公民知识的普及”。作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同样需要外界的监督,应当建立培养群众反抗强权的机制而非仅仅将民治的筹码押在领袖的人格上[2]341。
恽代英认为,中国革命的难题在于社会经济落后,工业产业不发达,并没有造就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因此,希望通过阶级觉悟来动员团结工人的设想基本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工人虽然遭受剥削和压榨,但并没有自然形成团体。若无团体,实在难以成为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动员工人参加革命,帮助工人组织运动固然重要,但并非只有无产者才能革命。在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的时候,要注重利用军队和群众的力量来助成民主革命,“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只是恽代英认为,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共产党应当掌握政权⑵,通过改造民党,联合真正的民主人士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的理由简单而充分:其一,“如俄国前例”,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其二,恽代英于1921年10月从武汉赴四川,在川南师范学校任教至此时已一年有余,“四川民党中且有派别,互相水火”,他本人也曾被永宁道尹张英扣押,对军阀假借民主主义之名,实则互相混战可谓有切身体会,所以他认为,有必要设法改造民党,否则“何益于主义之进行耶?”而在革命完成后,首先应当发展交通和各种大工业,经济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势力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其次就是要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选举制。“我们能向这一点做工比勉强在此经济落伍的社会中搜找觉悟工人,经济而有力多了。”建党之初,我党的作风已经相当民主。恽代英在信的开篇即说:“我至今常疑吾党还有一些重大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在于中央命令、政策的制定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上海、武汉等近代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同内陆四川等地势必不能适用于同一政策。虽然“自应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但是仅凭空想,没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就是使得“命令屡不能十分生效”“每有要求是实际无法遵守的”[2]349。 所以,他认为此时中央的指令应当因地制宜,另外,在革命的组成者中,除了工人外,必须要重视群众,重视组建军队。
同一时期,陈独秀认为革命的组成者应该主要是“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和“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5]94。革命不是目的,只是改变现有不良社会制度的手段。革命要的是除旧布新,若发动的是“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只怕革命不成,反而成作乱。时人多用“过渡时代”来定义所处的时期,而陈独秀则用“造桥”来比喻这个过程。虽然现阶段还没能到达“彼岸”,甚至无法断定是否能将“桥”修到“彼岸”,但是今日我们没有陷入到“汪洋”之中,正是因为我们站在“桥”上,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全盘否定前人的贡献,而是要专注于将“桥”修好,“这桥渐渐造的又长又阔,能容大家行车跑马,又架上楼阁亭台,这桥便是彼岸”[5]175。 改造社会不能妄想一劳永逸,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
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本该享受应有的权利,但实际却遭受着困苦。劳动诸君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困苦靠枝枝节节是解决不了的,想从根本上改变,就要做到两点:一是“阶级的觉悟”;二是“革命的手段”[5]170。 劳动者要形成自己的组织,团结成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资本阶级。“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5]174。 陈独秀在论及青年人的志向时,多次引用了“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句话。许多青年或是空喊“主义”而不付诸实践,或是盲目迷信“主义”的万能。“主义”是方向,但实践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社会的进步靠空谈阔论是无法实现的,“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5]93,把旧的制度推翻,同时建立新的制度。
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义和制度是新的,“便不须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5]54,改造社会如逆水行舟,社会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1]91。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没有被彻底改造之前,不论是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这样的团体,还是“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的个人愿望,想要达成单独改造社会的目的,在陈独秀看来“真是痴人说梦”[5]90。改造政治要从改造政党入手。有产阶级组成的,建立在“金力”之上,由“狐群狗党”担负责任的政党,出现腐败是必然的现象。共产党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在理论上要好过有产阶级的政党,不过究竟如何,还是要看改造的结果才能够使人信服[5]174。“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叙(序)不可”[5]177,也就是只有在中国建立起“俄国式的共产党专政”,中国的改造才有成功的可能。
经世济民、上下求索、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民族命运曲折多舛的中国近代史上更显得弥足珍贵。在探索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到了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中,逐步抛弃了对列强的幻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和工农群众潜能的巨大,开始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积极而重要的基础。
注释:
⑴王光祈在1919年12月4日《晨报》上发表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中,把城市中的新生活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认为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需要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⑵学界对于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时间存在有较大分歧,有1921年夏入党说、1921年底入党说、1922年春入党说、1922年8月入党说,但时间均早于他写给施存统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此外,恽代英在此封信的开篇亦称共产党为“吾党”,可见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