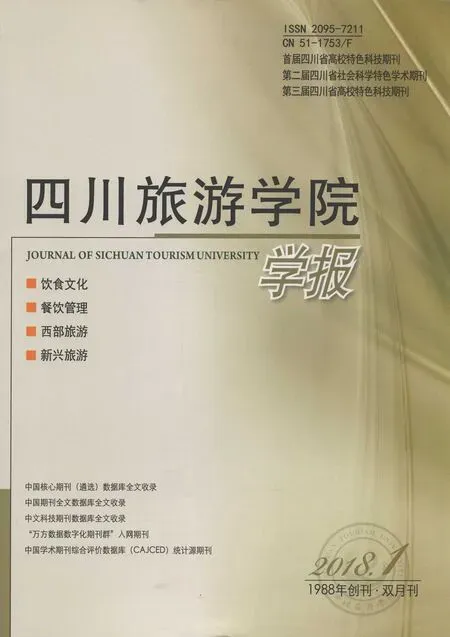论孔子的旅游理想、现实选择及其历史影响※
陈国林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论孔子的旅游理想、现实选择及其历史影响※
陈国林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文章主要研究孔子的旅游价值观及其形成的旅游文化内涵,从文献中关于孔子较为分散的记载入手,论述了孔子旅游理想“游于艺”的核心内涵,并分别从伦理、为政、修身三个方面分析了孔子对旅游的现实选择、原因及其对中国旅游文化的深远影响,对孔子的近游观、山水比德说及游必有方的旅游动机正当性进行了深入阐述。
孔子;旅游理想;现实选择
研究中国旅游文化,孔子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孔子对旅游的态度及认识,对后世形成了极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主要是基于儒家文化理念对旅游的影响,而不是孔子本人的旅游实践对旅游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旅游的理想及其现实选择客观地厘清关于孔子旅游文化现象的历史内涵。
1 孔子的理想追求关乎旅游
1.1 孔子的旅游理想发端
这里所问的,不是孔子关于为政治国的理想,而是他关于旅游的理想。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很多学者把这段文字解读的重点放在了子路身上,当然这一段确实突出了子路勇而当前、勇而少智的性格特征。但一定要注意,孔子所说的“好勇过我”,是把自己作为子路的比较对象。孔子的好勇又是什么呢?“乘桴浮于海”怎么在孔子自我的叙述中就成了“好勇”了呢?“乘桴浮于海”是远离人群、独自漂游于海上,其实就是远离当时的现实,自己找一个清静之地。在孔子看来,“乘桴浮于海”本来就需要勇气,而儒家入世的现实态度,异于当时避世的隐者,因此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了,自己当时所说,只是一时冲动的气话,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勇敢。但显然子路并没有领会到孔子的这一层意思,故孔子批评他“无所取材”。从这段话,我们其实可以窥见孔子旅游理想的一些端倪。
1.2 孔子的旅游理想即是他的社会理想
如果孔子有他自己关于旅游的理想,那这个理想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论语·侍坐章》得到解答,《侍坐章》是孔子旅游理想的生动写照。《侍坐章》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师徒之间展开对话,曾皙有一段流传后世的妙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回答,因为他们所说的也都是治国安邦之法。“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孔子在这里特别指出这是在谈论理想。并说:“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除了对子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外,对于他们的理想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特别认同曾晳的理想而已。
这是一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同时也是一段关于暮春出游的叙写。暮春者,农历三月之谓也,春种已过,农事稍闲,又值春意生发,正是春游时节。春服者,鲜亮之服也。关于“风乎舞雩”中的“舞雩”,一般注释为舞雩台的地名,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1]137、傅佩荣先生的《论语300讲》[2]都持此见。这句话的含义也被解释为在舞雩台这个地方吹吹风。李零先生虽然也持同样的见解,但同时又补充说,雩是祈雨的祭祀,舞雩是用跳舞的方式祈雨[3]。笔者认为这个补充恰是正解,“风乎舞雩”就是随风起舞、祈求风调雨顺。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论及《侍坐章》时说:“政治的目的,不过在求富强康乐,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4]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其实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孔子的理想社会中,旅游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说,孔子的社会理想也包含着他对于旅游的理想。
1.3 孔子的旅游理想是“游于艺”
《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有一个“游”的内涵。我们注意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有先后顺序的,而“游于艺”正好列于最后。是它不重要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它作为道、德、仁的结果,应该列于最后。这句话是讲道、德、仁、艺的次第关系的。
“游于艺”的“艺”,多数学者都解释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先秦时代的六种技艺,“游于艺”的“游”,在此只能解释为游学之“游”。但这样理解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孔子说“游于艺”,而不说“学于艺”呢?如果是“六艺”,用“游”字就难以理解,因为游有漂流不定之意,这是不利于学的。其实,“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真正意思,就是道、德、仁这些美好的思想与修行,需要君子努力实现于普通生活之中,以使百姓之于生活,就如同于诗意之中的旅游。
这个“游”的内涵,在《侍坐章》中有充分的表现。联系一下《侍坐章》中曾晳作答之前的情景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我们就能充分理解,曾晳的回答正好切合了孔子“游于艺”的思想。曾晳所描绘的浴、舞、咏都是艺的具体形态,“游于艺”就是生活于诗意之中。《论语》的体例,一般都比较短小、精练,而唯独《侍坐章》不仅详尽,篇幅还较长。这表明《侍坐章》在整个《论语》中实在是占了重要位置的。笔者认为,就是因为这一段文字,正是特别说明孔子“游于艺”的思想内涵的。
如果孔子有他自己关于旅游的理想,那么我们对孔子之游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了。因为这至少说明,孔子对于旅游的认知是理性的,而不是盲目的。但有一些研究者研究孔子的旅游,冠之以“孔子的旅游理论”。其实无论从《论语》等孔门弟子著述来看,还是从司马迁等人的历史记载来看,说孔子创立了他自己关于旅游的理论,我认为言过其实。其实这些所谓的理论都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总结出来加在这位圣人身上的。
但孔子确实是有他自己关于旅游的理想的。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关于旅游的理想,其实也是他关于未来生活的理想,这就是曾晳所描绘的生活景象。孔子对这种生活景象不仅是赞美的,也是向往的,故当他听曾晳说完自己的志向后,要喟然而叹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在孔子看来,旅游是关于未来的生活图景,或者说,未来美好的生活图景一定与游相关。
2 孔子关于旅游的现实选择及其旅游文化内涵
《周易》有一旅卦,卦辞曰:“旅:小亨。旅贞吉。”孔子晚年喜《易》,为其作传,是为《易传》。孔子虽然有自己关于旅游的理想,但孔子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于旅游的态度,孔子明显继承了《周易》的精神,因此,孔子对旅游采取了十分慎重、务实的态度。有研究者认为:“孔子不仅是我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唯一以垂暮之年游说长征不息的旅行家。”[5]
2.1 侧重于伦理的现实选择及旅游文化内涵
孔子是十分重视人伦之理的,人伦之理就是孔子的治国之礼,而其中“孝”则是这种人伦之礼的起点和核心。在《论语》中,对“孝”的论述多而且重,如《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的观念中,对旅游影响最大的伦理内涵就是“孝”。
《论语·为政》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孝的内涵,其中记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这句看似与旅游无关,但却从心态上制约了儒家对旅游的认识和选择。古代旅行不易,儿子远游最让父母担心,这被孔子视为与孝相违的事情。孔子对旅游基于伦理做出的现实选择,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此外,《礼记·曲礼》说:“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是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必有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无奈的旅行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旅行现实条件的真实反映,这个“一定的去处”所包含的父母之忧成了游子远游时的精神负担。这是儒家文化将人的旅行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对旅游做出的价值判断。同时,古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没有给多数人的旅行提供现实条件。因此可以说,正是现实的条件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使孔子对旅游持一种保守、审慎的态度。
2.2 侧重于为政的现实选择及旅游文化内涵
《论语·宪问》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这与“父母在、不远游”看似矛盾,其实是一致的,都表达了孔子出于慎重的态度对旅游的现实选择。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君子如果留念乡土,没有远大志向,当然就不是君子了,因为这样的君子注定没有天下的担当。孔子的这个观念,与其说肯定了旅游的必要性,不如说从为政的角度阐明了旅游的价值。简而言之,如果说纯粹的外出观光与对父母的孝道产生冲突应该采取“父母在、不远游”的态度,那么,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治国理政需要,旅行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朱熹《四书集注》说:“游必有方,如己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6]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也将“游必有方”中的“方”字译为“一定的去处”[1]43,“方”有“方向、方位”的意项,“一定的去处”这个解释可能是由此而来的。通则通矣,但不一定符合孔子本意。从孔子本意说,唯孝为大,哪怕有一定的去处,如果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这个“游必有方”也是不成立的。这个“方”字一定与志向有关。《周易》坤卦六二的爻辞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其“方”的意思即是“方正”之意。孔子在《文言》中解释“直方大”的含义中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他在《象》中为《周易》的恒卦阐释也有“君子以产不易以方”之句,其“方”均是“方正”“正道”之意。[7]因此笔者以为,这个“方”字理解为“正当的理由和远大的志向”更切合原意。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孔子对旅游的认识,基于伦理的现实选择与基于为政的现实选择,其本质是相通的。君子以孝为本,也要担当天下大义,如果孝义不能两全,游必有方、游必有常则是更具合理性的现实选择。
从为政的角度,孔子还十分注重旅游动机的正当性,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笔者对“游必有方”的见解。《论语·八佾》中述及季氏有一段关于旅游的文字,曰:“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春秋时代,泰山之旅,只有天子与诸侯可以登泰山以祭天,诸侯以下不可以登泰山而小天下。林放为鲁人,曾问礼于孔子,按杨伯峻先生的注释,“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的含义是诘问“泰山之神难道还不如林放知礼吗,居然会接受季氏之旅”。季氏旅于泰山是对礼的僭越,为孔子所反对。
《论语·学而》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周游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了解其为政的实情。我们必须理解,对于今天的旅游,可以是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休闲体验,但在春秋时期,旅游还远没有发展为心情放松的休憩,礼乐崩坏的局面使君子没有更多的闲暇和心情去观光。《礼记·礼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但是需要注意,这段话有一个背景:“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8]这段为政之道,正是在游观的过程中言说的,可以想见,孔子之游,心中常常揣着为政理想与抱负。
以上可以看出,为政是孔子对旅游做出现实选择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也是孔子在旅行过程中高度关注的内容。
2.3 侧重于修身的现实选择及旅游文化内涵
庄子见物而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作逍遥之游,将游览导向了想象世界;而孔子则睹物以思人,将游览导向了他所主张的君子人格。这其实也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借旅游以完善人格的选择,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旅游观深受其君子学说和入世思想的影响。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而后凋也。”看到松柏,想到的是其耐寒的品质,并联系到坚守困境的自身修为。因此对于孔子来讲,旅游其实就是一个修身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孔子而言,最有价值的学习其实就是修身。
当然,从修身的角度讲旅游,对后世影响深远者,莫过于后世所称的“山水比德说”。 “山水比德说”源自《论语·雍也》,全文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智者何以乐水呢?智者应当如水一样,虚心向下,循道而行,不拘一格,以柔克刚,水能解决问题,这是智者之乐;仁者何以乐山呢?仁者应当不动如山,长而久之则显厚重与高大,仁者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要学会坚守内心之仁,这种乐,正如《论语》中所描述的颜回之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此智者是灵动活泼的,仁者是安静内敛的,知者是快乐的,仁者是长寿的。其实要理解这段话,还可参看《论语·子罕》中的一句话“知者不惑、仁者无忧”,智者不惑于外,仁者无忧于内,智者不惑故快乐,仁者无忧故长寿。山水比德说其实开启了中国旅游文化对山水的关注,将自然山水升华为人文内涵,这种内涵的主旨就是君子人格的修养。孔子喜欢而且善于在观览自然景物时将其内化为修养。据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巻五十八载:“《琴操》曰:《猗兰操》,孔子所作。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香兰云。”[9]这种游览观景而自省于修养的观光方式在以后形成了一种传统,影响至今。
山水比德说的实质,其实就是观乎自然、归于人文的旅游文化观。按儒家的旅游文化观,旅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生修养的过程。孔子及其儒家对旅游的文字记述虽然并不集中,但基本阐明了关于旅游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大道仁义的主要内涵和教化天下的重要作用,实质上为中国的旅游文化定下了基调。这个旅游文化的基调对中国旅游的影响至今未曾断绝,自孔子以降,君子人格就是旅行观赏的重要坐标。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的人格化,无一不是对这一深厚的旅游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传承。翻开今天论述中国旅游文化的著述,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已经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论题,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重要内涵,比德的对象也由山水延及到花草树木等更为广泛的自然景物。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旅游只重休闲性、忽视修身是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今天,我们看待梅兰竹菊这些花草,依然应该看到中国旅游文化中的君子人格。
3 孔子的旅游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
马勇在《中国旅游文化史论纲》中将孔子的旅游观梳理为近游观、远游观和比德说三个主要内涵[10],究其实质,近游观就是基于儒家伦理形成的旅游价值观,远游观则是基于儒家为政治国及天下担当形成的旅游价值观,比德说所对应的则是儒家修身与君子人格的价值理念。其实,以上的区别也是人为的,对于孔子而言,伦理、修身、为政(包括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很难截然分开。诚如《大学》所言,修齐治平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因此,从伦理、为政、修身三个方面形成的旅游价值观,其实质也是内涵相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正是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旅游价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观察的社会现象,但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那是一个战火不熄、礼崩乐坏的时代,普遍的、自觉的旅游并不是历史真实。孔子自己周游列国,曾数次历险,他自己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综合考察,对于旅游,孔子其实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矛盾着,矛盾的最后结果,是他做出了倾向于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矛盾,就像他内心深处仕与隐的矛盾一样。作为入世的儒家学说创始人,这样的选择自然在情理之中。重要的是,这种现实选择形成了中国古代旅游一种重要的人文传统,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孔子虽然不是一位自觉的旅行家,但其关于旅行的认识对后世的旅游文化及价值观影响深远。基本可以断定,孔子关于旅游的认识与观念在以后的求仕之旅、游学之旅和宦游之旅中不断得以发扬,从而形成了中国旅游文化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一种典型的旅游文化类型。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傅佩荣.论语300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1:325.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219.
[4]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28.
[5]王淑良.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 [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80.
[6]朱熹.四书集注 [M].长沙:岳麓书社,1985:98.
[7]杨天才,张善文.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31,41,292.
[8]于涌,樊伟峻,付林鹏.礼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97.
[9]郭茂倩.乐府诗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9:839.
[10]马勇,余冬林,周霄.中国旅游文化史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69.
OnConfucius’IdeologyonTravelling,HisChoiceinRealityandTheirHistoricInfluence
CHENGuolin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0, Sichua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Confucius’ values on travelling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developed from them. Based on related literature, the analysis explores the core of his ideology on travelling, his choice in reality and the reasons for his cho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s, politics and self-cultivati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his choice on China’s tourism culture is also expounded, including his philosophy on not travelling far, compar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to human virtues, and having known destinations.
Confucius; ideology on travelling; choice in reality
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应用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6ZS037。
陈国林,男,四川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及旅游文化、旅游文学。
F590
A
2095-7211(2018)01-00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