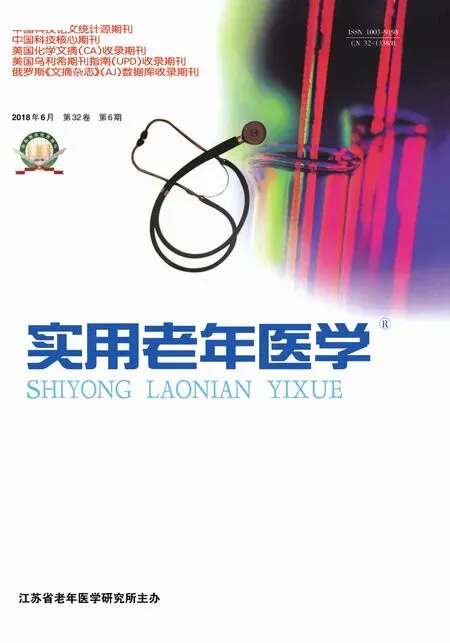老年髋部骨折手术围术期麻醉处理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人因骨质疏松而容易发生髋部骨折。髋部骨折严重影响老年病人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老年病人常并存多种疾患,如何完善围手术期的麻醉处理成为麻醉医师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术前止痛
髋部骨折常伴随着严重疼痛,不予镇痛措施或单独使用阿片类药物止痛均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包括心血管不良事件、谵妄等,增加了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1]。外周神经阻滞可以为髋部骨折病人提供良好的镇痛作用,同时减少阿片类药物相关的并发症。在做好病人术前疼痛评估的基础上,如不存在禁忌证,应立即启动多模式镇痛程序,包括常规给予对乙酰氨基酚、谨慎使用阿片类药物和尽早实施外周神经阻滞,非甾体类镇痛药应避免使用。外周神经阻滞最常用的方法为髂筋膜间隙阻滞或股神经阻滞,一旦髋部骨折诊断成立就应尽早实施。超声引导下髂筋膜间隙阻滞操作简单有效、容易掌握,建议在急诊室内早期开展[2]。硬膜外镇痛同样可以为病人提供良好的镇痛效果,且可为手术提供麻醉,但应注意部分老年病人常服用抗凝类药物,由于骨折造成的血液丢失和脱水等造成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硬膜外镇痛并非合适。解决疼痛最有效的办法是手术治疗,故应尽早实施手术。
2 围术期抗凝药物的处理
老年人普遍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等疾患,部分病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预防治疗,放置冠状动脉支架后需要服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进行双抗治疗,或者因房颤等疾患服用华法林抗凝治疗,这些病人术前凝血功能异常需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术前停用抗凝药物可能增加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而未行纠正凝血功能异常可能带来手术出血增多、椎管内血肿等麻醉并发症。如何调整好围术期抗凝药物的应用成为麻醉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关心的问题。
2.1 维生素K拮抗剂 华法林是其代表药物,主要用于心房颤动、下肢静脉血栓、人工心脏瓣膜术后血栓事件的预防,作用机制涉及抑制肝脏内维生素K依赖的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的合成而发挥抗凝作用。华法林服药后12~18 h起效,36~48 h达抗凝高峰,停药3~5 d后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可恢复至1.2~1.6。使用华法林的髋部骨折病人入院时需监测INR值,如超过1.5需予以纠正。维生素 K、新鲜冻干血浆(FFP)以及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PCC)均能逆转华法林的抗凝作用。补充维生素K逆转华法林抗凝作用对髋部手术病人安全有效。静脉给予维生素K较口服生物利用度高,起效快,1~3 mg静脉注射可有效地使INR在48 h内恢复至1.5以内,故推荐维生素K静脉给药。静脉给药应注意可能发生过敏反应、急性栓塞和华法林耐受等不良反应。FFP含有全部血浆凝血因子,输注前需行ABO血型交叉配血试验,同时存在输血的全部不良反应。英国血液学标准委员会(BCSH)并不建议FFP用于髋部骨折术前拮抗华法林的抗凝作用,仅推荐用于严重出血或维生素K拮抗未达目标的病人[3]。PCC包含Ⅱ、Ⅶ、Ⅸ和Ⅹ凝血因子,可用于髋部骨折病人术前快速纠正凝血功能异常,静脉注射后30 min内使INR恢复至<1.3。PCC和维生素K联合给药有助于稳定凝血功能的纠正和维持INR在合适的范围。目前尚无PCC在髋部骨折病人抗凝治疗方面的临床指南,BCSH建议PCC合并维生素K 5 mg静脉注射,用于大出血的病人或急诊手术的紧急抗凝治疗。如果PCC无法获得,可以考虑使用FFP。
2.2 抗血小板治疗 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是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较新的药物如替格瑞洛和普拉格雷。阿司匹林通过不可逆性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减少血栓环素A2产生,阻止血小板聚集而发挥其抗栓作用,作用时间达7~10 d。2012年美国胸科协会围术期抗栓药物治疗指南指出,对于非颅内、眼内以及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等高危出血风险手术,大部分非心脏外科手术,无论是紧急手术或择期手术,均建议围手术期继续使用阿司匹林[4]。氯吡格雷和普拉格雷均以共价结合的方式作用于血小板P2Y12 ADP受体,不可逆地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功能,停药后同样需要7~10 d等待新的血小板产生以恢复其凝集功能。替格瑞洛直接作用于血小板P2Y12 ADP受体,其作用具有可逆性和剂量依赖性,停药后血液中的血小板功能可快速恢复。对长期服用氯吡格雷等药物的老年髋部骨折病人在其手术时机仍有争议,早期手术的主要顾虑是可能增加术中出血和椎管内麻醉后椎管内血肿的机会。若停用氯吡格雷将造成等待手术时间超过48 h,病人的并发症超过早期手术病人,这些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褥疮、心肌缺血和肺动脉栓塞等。有文献复习了正在服用氯吡格雷的髋部骨折老年病人按常规进行早期手术,结果发现不停用氯吡格雷并未明显增加术中出血,但术中需特别注意仔细止血[5]。也有学者认为服用氯吡格雷的病人出血量更大,早期手术增加出血量,但并不增加死亡率,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双抗治疗病人出血量更多。髋部骨折手术的麻醉方法之一为蛛网膜下腔麻醉,此前对于正在服用阿司匹林的病人实施蛛网膜下腔麻醉可能造成椎管内血肿一直有所顾忌,但目前已有文献证实服用阿司匹林并非蛛网膜下腔麻醉的禁忌[6]。对于服用氯吡格雷的病人,建议停药7 d,凝血功能检查正常后方可实施椎管内麻醉。
3 麻醉方式的选择
老年髋部骨折病人由于其并发症多,病情复杂,宜结合手术方式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目前常用的麻醉方法包括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和周围神经阻滞。尽管有研究显示区域阻滞麻醉比全身麻醉的病人住院期间死亡率和并发症风险更低,但目前仍存在争议。Julia等[7]比较了249 408例全身麻醉和150 964例椎管内麻醉的病人,两者30 d死亡率并无差异,但椎管内麻醉的病人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心肌梗死和呼吸衰竭的风险也明显减少,而肺部炎症的风险2组间并无区别。目前认为椎管内麻醉较全身麻醉病人其心肺并发症、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等发生率相对较低,如无相关禁忌证可优先考虑选择椎管内麻醉[2]。
采用全身麻醉时,由于老年病人的生理和药理学特点,麻醉药物的剂量明显减少,有时仅为正常剂量的1/2~1/3甚至更少。有条件时应监测麻醉深度,维持合适的麻醉水平,避免长时间低血压,减少围术期并发症。麻醉药物尽量选择作用时效短暂的药物如瑞芬太尼、丙泊酚、七氟烷等,便于调节麻醉深度,同时注意合理使用肌松药,或在肌松监测指导下使用肌松药,减少手术结束后的麻醉药物残余作用,促进早期功能锻炼,减少卧床时间过长造成的肺部感染、褥疮和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目前全身麻醉除采用气管插管外,还可采用喉罩通气的方法,如无喉罩使用禁忌证,建议使用喉罩。
采用椎管内麻醉时,由于蛛网膜下腔阻滞起效快,效果确切,若平面控制恰当,生命体征稳定,值得推荐。《中国老年病人髋部骨折病人麻醉和围术期指南》建议在椎管内麻醉实施前患侧先行药髂筋膜阻滞,并推荐首选轻比重单侧腰麻(患侧向上),建议使用0.2%小剂量轻比重布比卡因液(≤5.0~7.5 mg),推注30~40 s,患侧向上体位保持10~15 min[2]。轻比重单侧腰麻对病人的生理功能影响小,但麻醉操作时间较长。笔者对髋部骨折病人采用患侧向上体位进行蛛网膜下腔穿刺,另一助手牵引患肢以减轻骨折处疼痛。蛛网膜下腔穿刺成功后,将0.75%布比卡因液2 mL以脑脊液稀释成近似等比重的0.5%布比卡因液3 mL,根据病人的年龄和机体功能状况,单次注入1~2 mL (5.0~10.0 mg)布比卡因,如使用腰硬联合穿刺针时还可放置硬膜外导管以备用,操作完成后即可翻身摆放体位而无需长时间等待。对于髋部骨折老年病人也可采用硬膜外麻醉的方法,《中国老年病人髋部骨折病人麻醉和围术期指南》建议试验剂量不超过3 mL,并且为防止硬膜外麻醉造成低血压发生而在局麻药中加入麻黄素(1 mg/mL)。若硬膜外导管进入蛛网膜采用2%利多卡因3 mL作为试验剂量时,对老年病人必将造成高位蛛网膜下腔阻滞甚至全脊髓麻醉,严重影响呼吸循环功能,笔者建议利多卡因20~40 mg就可以判断是否发生蛛网膜下腔阻滞,且不会造成麻醉平面过高而带来的风险。至于将麻黄素加入局麻药以预防硬膜外麻醉造成低血压,笔者认为并无必要。一方面若发生局麻药意外血管内注射,对老年病人特别是合并高血压病人,可能加剧血液动力学的波动,另一方面由于麻黄素经硬膜外腔吸收发挥升压作用不及静脉注射快速有效、及时可控,只要麻醉过程中加强监测,及时处理,即可维持血液动力学稳定。
老年病人椎管内麻醉由于椎体的老年性改变和骨折后疼痛导致穿刺时体位放置不当等情况,穿刺成功率有所下降,甚至无法穿刺成功。穿刺困难时不宜反复穿刺,可改用全身麻醉或周围神经阻滞。部分病人因凝血功能或血小板计数异常等椎管内麻醉禁忌证而不得不改用其他麻醉方法,另有部分病人不愿意实施椎管内麻醉亦需改用其他麻醉方法。周围神经阻滞对全身影响较小,手术麻醉过程中血流动力学较稳定,且术后能提供较为完善的镇痛,目前在老年病人髋部骨折手术临床麻醉中的使用渐趋广泛。采用的周围神经阻滞方案包括髂筋膜阻滞、腰丛神经阻滞、腰丛+坐骨神经阻滞、腰丛+骶丛神经阻滞[8]。目前超声引导下的周围神经阻滞定位准确方便,麻醉效果好,并发症少,值得推广使用。但上述周围神经阻滞方案往往并不能阻滞肋下神经外侧皮支、髂腹股沟神经外侧皮支、臀上皮神经,因此需要复合静脉镇痛、镇静药物,才能满足手术的需要。喉罩结合周围神经阻滞的方法,不但为手术提供了足够的麻醉深度,消除了周围神经阻滞范围不足的缺陷,而且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气道管理方式,麻醉对机体影响小,值得推荐使用。不采用喉罩单独静脉辅助镇痛镇静时需注意麻醉用药对病人机体的影响,特别是密切观察和维持老年病人呼吸和循环的稳定。
4 骨水泥植入综合征(bone cement implantation syndrome,BCIS)
BCIS是指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中由骨水泥植入所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包括低血压、心律失常、严重低氧血症、心律失常、肺动脉压增高、出凝血功能改变、哮喘发作等。骨水泥是一种用于填充骨与植入物间隙或骨腔并具有自凝特性的生物材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体系:生物相容性较差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和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磷酸钙骨水泥(calcium phosphate cement, CPC)。PMMA属于生物惰性材料,不能与宿主骨组织形成有机的化学界面结合,另外凝固聚合过程中产生热量、单体的细胞毒性作用而容易发生BCIS。CPC生物相容性良好,固化时热释放效应不明显,很少出现异物反应。植入假体也可分为骨水泥型和生物型,生物型假体避免了骨水泥使用带来的不良反应。麻醉医师有必要了解骨科相关植入材料的特点,以便有效及时处理麻醉手术过程中发生的并发症。
BCIS发生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主要可能与骨水泥毒性、髓内高压、组胺释放和高敏反应等有关。PMMA型骨水泥多为双成分系统,包括粉末状多聚体和液态单体。液态单体的主要成分为PMMA,高浓度的液态PMMA不仅会抑制心肌收缩力,还可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的钙通道,导致血管扩张,血流缓慢、淤积,出现心率增快或者减慢、血压下降等症状。研究发现骨水泥进入骨髓腔后血清组胺浓度上升,同时刺激组织分泌前列腺素,这些因素造成血管扩张和血压下降。对于术前合并心血管疾病和低血容量的老年病人,即使是中等程度的组胺释放都可能引起严重甚至致命的心血管并发症。扩髓操作引起的髓内血管破裂,骨水泥加压形成髓内高压促使空气、脂肪、骨髓、骨碎屑等栓子进入循环而造成肺栓塞,引起肺血管阻力升高、肺动脉高压、低氧血症等严重并发症。BCIS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三级:轻度为血氧饱和度(SpO2)<94%,血压下降>20%,病人神志清醒;中度为SpO2<88%,血压下降>40%,意识丧失;重度为心血管虚脱,需要紧急心肺复苏[9]。临床观察发现骨水泥植入后有近1/3的病人发生一过性低血压,平均动脉压下降幅度为15~40 mmHg。根据影像学研究,临床BCIS的发生率可能远高于麻醉记录,许多轻度且一过性的BCIS并未被麻醉医师所认识和重视。
BCIS的预防主要是改良手术技术,如髓腔清洗、骨水泥植入前充分止血、使用骨水泥枪逆行灌入骨水泥、髓腔引流、短柄假体、轻柔植入假体。使用CPC可减少PMMA骨水泥导致的相关并发症,对高危病人采用生物型假体植入可显著减少此类风险。对于高龄老年病人,术前存在循环容量不足和心血管疾患,假体植入前适度扩容,给予麻黄素提升血压和糖皮质激素,加强监护,预防可能发生的心血管反应。一旦发生BCIS,立即吸入纯氧、补充液体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如小剂量肾上腺素(5~50μg)和快速起效糖皮质激素如甲泼尼龙(1 mg/kg)维持循环稳定。对于存在右心功能不全或周围血管扩张者,α受体激动剂应为首选。全麻手术病人如应用骨水泥后短时间突然发生血压、SpO2和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的急剧下降,应立即按照BCIS来进行处理。
5 术后疼痛治疗
约3/4的髋部骨折手术后有明显疼痛,如术后镇痛不完善容易诱发心肌缺血和心梗、通气功能下降、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同时影响早期功能锻炼,延长恢复时间,降低病人满意度。因此有效地控制术后疼痛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对于老年病人术后的转归有着重要临床意义。
首选神经阻滞镇痛技术,效果较好的方法包括髂筋膜间隙阻滞、股神经阻滞、腰丛阻滞以及以上技术的联合[10]。目前认为闭孔神经联合股外侧皮神经阻滞是术后镇痛有效的阻滞方案,可以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其镇痛效果接近硬膜外镇痛,对老年病人生命体征影响轻微,但存在操作时间延长而增加病人不适感,需要有经验的麻醉医师去完成等缺点。其次选硬膜外镇痛,联合应用小剂量阿片类药物和低浓度局麻药可以明显缓解髋部手术后静息和运动疼痛评分,同时减少了大剂量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恶心呕吐、过度镇静等不良反应,但仍需注意由于剂量过大或个体差异等引起的呼吸抑制、低血压等不良反应。此外,由于老年病人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概率较高,术后早期预防性应用低分子肝素等抗凝药物限制了硬膜外镇痛的广泛使用。病人自控静脉镇痛(PCIA)也是髋部手术后镇痛重要的方法之一,多项研究显示对于老年病人全髋置换术后行PCIA镇痛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对于高龄病人需特别注意阿片类药物的剂量,以免引起呼吸抑制、免疫功能下降、认知功能障碍等不良事件。因此,对于全髋置换术后的老年人进行PCIA镇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切口局部浸润用于髋部手术后镇痛效果不佳,不予推荐[13]。髋部手术后使用多模式镇痛,可在多个不同水平阻断疼痛的传导,改善机体整体的疼痛,同时降低使用单一止痛技术所引起的不良反应,是目前较为理想的围手术期疼痛控制方法。非甾体类消炎药(NSAIDs)在多模式镇痛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NSAIDs药物在老年病人中不良反应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心血管不良事件和肾脏毒性,建议谨慎使用。对乙酰氨基酚相对安全,建议作为多模式镇痛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Morrison RS, Magaziner J, Gilbert M,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 and opioid analges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lirium following hip fracture[J]. J Gerontol A Biol Sci Med Sci, 2003, 58(1):76-81.
[2]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老年人麻醉学组,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骨科麻醉学组. 中国老年髋部骨折患者麻醉及围术期管理指导意见[J]. 中华医学杂志, 2017, 97(12):897-905.
[3] O’shaughnessy DF, Atterbury C, Bolton Maggs P,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fresh-frozen plasma, cryoprecipitate and cryosupernatant[J]. Br J Hematol, 2004, 126(1):11-28.
[4] Douketis JD, Spyropoulos AC, Spencer FA, et al.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antithrombotic therapy: Antithrombotic Therapy and Prevention of Thrombosis, 9th ed: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J]. Chest, 2012, 141(2 Suppl):e326S-e350S.
[5] Soo CG, Dell Torre PK, Yolland TJ, et al. Clopidogrel and hip fractures, is it saf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016, 17(1):136.
[7] Van Waesberghe J, Stevanovic A, Rossaint R, et al. General vs. neuraxial anaesthesia in hip fracture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MC Anesthesiol, 2017, 17(1):87.
[8] 江伟, 赵达强. 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手术的麻醉[J]. 老年医学与保健, 2014, 20(1):290-292.
[9] Donaldson AJ, Thomson HE, Harper NJ, et al. Bone cement implantation syndrome[J]. Br J Anaesth, 2009, 102(1):12-22.
[10] Abou-Setta AM, Beaupre LA, Rashiq S,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pain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for hip fracture: a systematic review[J]. Ann Inten Med, 2011, 155(4):234-245.
[11] Andersen LO, Kehlet H. Analgesic efficacy of local infiltration analgesia in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a systematic review[J]. Br J Anaesth, 2014, 113(3):360-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