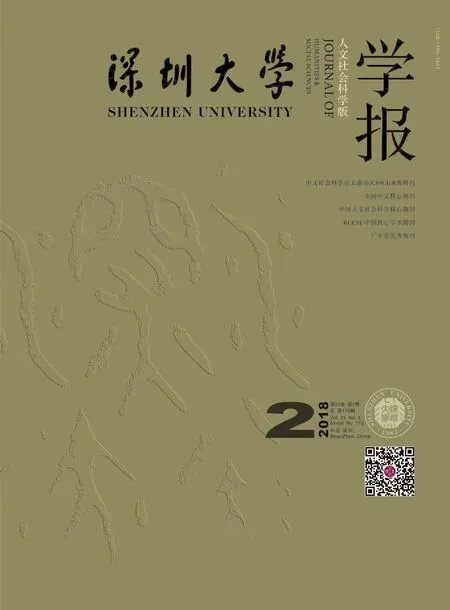元、清两朝藏传佛教政策管控及其效果
胡垚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在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引起各民族精神共鸣,促进民族融合上有其突出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1]。宗教可谓维持社会稳定的一大强有力的文化杠杆。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借助佛教力量为其政治服务的不在少数,其中,由于元、清两朝皆是由少数民族统一治理整个国家,所以对于民族团结与融合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两朝出于同样目的,都采取了“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策略,扶持藏传佛教以羁縻边疆。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各有侧重,且收到了不同的效果。
深入研究元、清两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差异及其效果,不但可以厘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整合两朝促进民族团结、治理边疆的成功经验,从而更有效地为消除民族隔阂、提高民族融入度与平衡民族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引导方案。
一、宗教领袖权力之“统”与“分”
宗教领袖往往对其下教民有着极大的感召力,中央政权对宗教领袖的权力制约对于宗教管控至关重要。历来,中央政权对宗教势力都是采取利用和控制的双重手段,既希望通过宗教信仰保持民众的稳定,为自身统治提供宗教上的合法解释,又要防止宗教势力过多地干涉朝政。元、清两朝皆赋予藏传佛教领袖极高的权力,但在具体处理上又存在着不同。
在元朝,藏传佛教领袖在教内教外皆享有极高的权力。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诏封上师八思巴为帝师,自此帝师制兴于元朝。“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2](卷202,P4517)终元之世,皇帝皆奉喇嘛为帝师,新帝即位之前必先于帝师处受戒九次才能正式君临天下。作为宗教领袖的帝师享有极高的权力,负责统领总制院事务。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是管辖全国佛教及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元史·释老传》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2](卷 202,P4520)可见,帝师是西藏地区政教方面的最高领袖,也是朝廷在西藏地方上的最高代理人,享有颁布法旨的权力。此外,元朝又设置江南释教总统所,管辖江南佛教,后并入宣政院。因此,帝师亦成为全国佛教的首脑,不但掌握宣政院官吏的荐举,有权干预司法案件的审理判决,还控制着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
自八思巴始,元朝历代皇帝都册封有帝师,终元一代,共有14位帝师,多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或其下门徒弟子。帝师的家族也权势盛隆,当中不少人获封国师、国公、司徒、司空等爵位,更先后有数人被封为白兰王,尚蒙古公主,成为皇亲国戚[3]。帝师权力独大,加上家族势力膨胀,而无相应的体制加以监管制衡,以致宣政院管辖范围之内不法行为屡有发生,给元朝的法政造成严重破坏。
在清朝,朝廷同样赋予藏传佛教领袖极高的权力,但开始注重通过分权来削弱、限制其权力的膨胀。顺治九年(1652),清廷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并授金册、金印,使其成为藏蒙两地喇嘛教的领袖。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册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4]。开始体现出清廷在宗教领域分权统治的思想。随后,宗教领域分权统治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展。康熙三十二年(1693),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管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康熙五十年 (1711)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 “大国师”,执掌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最终形成四大活佛分主教权的格局,即: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主内蒙古。这在稳定各地区信众维持正常宗教信仰活动的同时,也从地域上限制了宗教高层对国家整体政权的影响和干涉能力,并为保持这些地区宗教高层忠于清廷,以及自身内部权力交替衔接过程中的稳定,提供了制度层次上的保障。
此外,与元朝一味赋予宗教领袖至高权力的做法所不同,在赋权的同时,清廷也相应地进行了权力的制衡:朝廷掌控对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的封赠、废黜大权;各大寺院活佛的人事擢用上,规定需由达赖、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签章才具效力;蒙古王公与西藏高僧的私下往来也被控制,须由西宁大臣及驻藏大臣共出批文方准通行。清廷借此一系列政策以达到分权管控的目的。“元明两代虽然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以行使国家主权,但一直通过西藏地方势力来管理藏务,朝廷并没有派员长期驻藏,更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直接管理西藏事务的中央派出机构。”[5]清朝驻藏大臣的设置,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漏。此外还规定“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人员不准参预政事”[6],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格鲁派宗教领袖干预俗政的权力,有效防止其家族操纵西藏地方政权。
尤其是“金瓶掣签”制度的设立,更是清廷行使宗教监管权的又一项创造性尝试。此前,地方上层贵族为争夺权势,使得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过程中“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授意,令其指谁”[7],致使蒙藏地区四大活佛的转世,几乎与世系封爵无异。为加强中央对蒙藏政教的控制,防止地方贵族势力过度膨胀,清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由驻藏大臣及各呼图克图在大昭寺当众于瓶内掣签,当签者在现场传阅确认为转世“灵童”后,需上报朝廷批准,再由皇帝派大员主持举行坐床典礼。这一举措既解决了以往活佛转世制度的弊端,“使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的任免大权,完全集中到清朝中央。”[8]也昭显着清朝对蒙藏地区的主权关系。
此外,乾隆七年(1742),为使宗教上层对朝廷“心生敬畏”,还建立了大活佛定期朝贡制度。规定达赖、班禅必须轮流隔年一次遣使朝贡,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等五年一次朝贡[9]。此制旨在时刻提醒其对中央政府的臣服关系。
二、特权礼遇之“放”与“严”
除赋予宗教领袖大权之外,元、清两朝藏传佛教僧侣还享有一定的特权以及礼遇。在元代,喇嘛僧享有各种宽放的司法、经济特权。宣政院曾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骂)之者,断其舌。 ”[2](卷 202,P4522)成宗以前,僧侣犯轻罪,由寺院主持僧独审即可;僧俗间发生田土等纠纷,由僧官会同地方官审处;即便僧侣犯重罪如奸淫、杀伤人等,地方官审理后仍须上报宣政院。藏传佛教徒实际上成了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的特殊阶层。
在宽放的政策庇护下,少数僧人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如帝师杨琏真伽利用职权之便,掠夺财物、掘盗陵墓、戕杀平民,为害不可胜言。抄没其家时,“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末露者不论也。 ”[2](卷 202,P4521)《元史》中亦多有西僧请旨“释重囚”之记载。帝师等藏传佛教高僧往往以佛事功德为由,奏请皇帝释放重囚,当中不乏暗箱操作以开脱罪责之举,严重破坏司法公正。对此等扰乱政纪之事,大臣们虽屡次进言,亦间或为皇帝所采纳,但收效甚微,西僧释囚之事始终未能禁绝。
元朝还对寺庙僧侣的财产所有权予以保护,禁止侵犯,并赏赐给大喇嘛数量庞大的金银财宝,以致史书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之评。忽必烈曾言:“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10]下诏免除僧侣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此后诸帝对待佛教,大都依循世祖的范例。成宗大德五年(1031),“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 ”[2](卷 20,P434)这种营建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的风气,几乎一直贯穿元代。
清朝亦给予藏传佛教僧侣特权礼遇,尤其对格鲁教派给予了大力扶持。除封赠名号外,还授予其与蒙古各部王公相同的品级特权,使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清廷对藏传佛教还不仅限于政治待遇,在经济上也给予了许多特权和优待,喇嘛们不仅可以不向朝廷纳税、不应差役,甚至一些享有特权的高僧还可向百姓征收赋税以及派差等。自七世达赖喇嘛起,转世灵童之父均被授以 “辅国公”爵位,其整个家族亦能获赐大量的田产奴仆;每次达赖、班禅进京朝觐,皇帝必亲迎,并赏赐各种御用之物;经济上,由达赖、班禅全权支配西藏地方征收的赋税。此外,除政府按定例每年的财政资助外,其它的额外赏赐更是不可计数。
清朝虽也给予藏传佛教僧侣特权礼遇,但却严防元朝那般僧侣干预司法之事,取消了不少元朝时期过度庇护藏传佛教僧侣的政治特权。乾隆指出:“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11]“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12](卷1393)足见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僧侣的特权礼遇有所规范限制,一切以“法”为据,严律相待。
三、管理制度之“泛”与“细”
元朝时,针对藏传佛教及西藏相关事务从中央到地方基层都设置了层级管理机构。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于中央设置释教总统所,至元元年(1264),又设总制院,负责管辖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政教事务,后更名为宣政院。《元史·百官志》曰:“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2](卷87,P2193)宣政院的设置,主要为管理以吐蕃为主的西部各民族地区。元代朱德闰曾言:“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唯事佛惟谨,且依其教焉。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13]对设置宣政院的现实意义、目的和职司都作了清楚的阐述。西部各民族地区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皆归宣政院处理。
元朝于地方上亦设立层层僧务机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都纲司,机构臃肿,管理混乱。尤其为辅助宣政院行事,元朝又建立了地方基层统治机构——宣慰司。“宣慰司……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2](卷91,P2308)宣政院辖下的朶甘思、朶思麻和乌思藏三个宣慰司,从地域上看相当于一个行省(有藏文史籍也称其为行省)。其中,乌思藏宣慰司不同于普通的宣慰司,而是直属中央宣政院,体现出元朝对西藏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重视。
虽然元朝设置了层层管理机构,但对于机构的权限却规定得过于宽泛,将行政、司法、宗教混为一体,为藏传佛教的规范化管理带来重重困难。相比之下,清朝的藏传佛教治理则逐渐步入“依法治教”的轨道,先后制定《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理藩院则例·喇嘛事例》等多项法令法规以对藏传佛教进行精细而周全的管控:
1.设置佛教管理机构。康熙三十六年(1697),设立管理清代宫廷藏传佛教事物的机构 “中正殿念经处”。乾隆时,立雍和宫为喇嘛教寺庙,成为京城藏传佛教的中心,并在中央设立管制喇嘛事务的机构——理藩院。
2.对藏传佛教传教的规范。(1)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清廷认为“国师名爵甚大,非有功绩,不得滥授”[14],故对国师禅师的封赠相当严谨,且多集中在青海地区。这是清廷着意扶持青海宗教人物派往蒙古,以削弱达赖、班禅在蒙古的影响,并防止蒙古王公把持教权。(2)规范喇嘛等级。据《大清会典》卷八十所载:“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转世者曰胡毕尔汗,其秩之贵者曰国师,曰禅师,次曰扎萨克大喇嘛,又次曰大喇嘛,副喇嘛,闲散喇嘛。”[15]不同等级的活佛,在薪俸、服饰、用具、车轿、仆从等方面都有不同待遇。(3)控制喇嘛寺庙的规模和住寺人数,尤其对于曾参与叛乱的寺庙,中央事后必严加控制其规模、人数。如乾隆时,廓尔喀入侵后藏,其怂恿者沙玛尔巴法王虽在战争末期病死,“但仍被处以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等严厉惩罚”[16]。(4)规范喇嘛的服饰饮食制度。清代对喇嘛的服饰作了详细规定。如康熙时,喇嘛人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班第许服大红色,伍巴什、伍巴三察则不许服金黄色、黄红色,且其余色服亦不得擅自使用。在饮食上,自南朝梁武帝禁断肉食,素食便成为汉传佛教的饮食制度。但藏传佛教无此戒规。康熙四十八年(1709),谕称:“尔等若能不食(生灵),并传内外寺庙众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万生灵。如此乃合喇嘛之道……”[17]自此始,形成了藏传佛教新的饮食制度,即平日不禁荤腥,而每逢佛教主要活动日,必须持斋素食。
3.对藏传佛教的禁约。《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所载《理藩院·禁令·喇嘛禁令》及卷五〇一《礼部·方伎·喇嘛禁例》,皆详细记载了清廷针对藏传佛教实施的多种禁约。白文固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如禁止随意私行出家建寺,严禁喇嘛久居京师或游方他地等[18]。这些举措大都为限制蒙古王公势力而设,主要为了防范他们在寺院中安插党羽,以及奸细混迹云游僧中刺探军情。
4.赏罚分明。清政府数次敕封在历次反叛、骚乱中,对祖国统一有过贡献的高僧。如康熙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领喀尔喀部内附,赐封“大喇嘛”;乾隆时,济咙呼图克图因助清军反击廓尔喀侵藏,袭封“慧通禅师”法号等等。反之,对参与叛乱的寺庙及僧人,事后亦必严惩。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廷将与事喇嘛或斩首或监禁[19]。清朝一向对藏传佛教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对此,乾隆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设如元季之供养喇嘛,一意崇奉,漫无区别,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截手之事,令喇嘛等无所忌惮,尚复成何政体!”[12]这一系列细致而周全的明文规定,以佛事活动制度化的方式,从各个层面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与管控。
四、宗教态度之“信”与“用”
元、清二朝在藏传佛教政策上之种种不同,究其根源,皆源于其皇室关于宗教信仰的根本态度之不同。藏传佛教可视为元朝的国教,自世祖忽必烈始,元朝历代帝王皆信仰虔诚,多数皇室成员亦接受过灌顶的洗礼。到了清朝,虽然同样扶持藏传佛教,但更倾向于利用而非信奉。“总体来看,清廷对各类宗教基本采取一种政治功利化的态度,有利有用则推举,无利无用则抑制。所以在清代,统治者始终没有为后来的某一宗教所控制,各教派的兴衰基本被限制在皇权之下。”[20]正是在这种功利化的宗教态度下,清朝虽扶持藏传佛教以治化藏蒙,但同时亦从思想上极力防范其影响。清代最盛行的藏传佛教流派为格鲁派(黄教),该教派赢得了蒙藏地区广大僧俗民众的拥护和崇奉。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中明确指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12]朝廷此番见解已说明了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态度,是提防和谨慎的,正如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在其《啸亭杂录》中所评:“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21]实质上,就是因俗利导,利用藏传佛教传统的力量和社会政治影响,来实现驾驭蒙古,安抚藏区,消除分裂,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
五、结 语
概言之,元、清两朝都一致采取扶持藏传佛教以羁縻边疆的策略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相较而言,在宗教领袖权力上,元朝帝师享有极高的权力,一统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宜,导致萨迦派宗教领袖权力坐大;而清朝让四大喇嘛分权统治,并对其权力作出限制,有效防止其势力膨胀。在特权礼遇上,两朝皆给予僧侣种种特权礼遇,但元朝对僧人过度庇护,诸多特权凌驾于国家司法之上,极度妨碍司法的正常运行。这种情况则在清朝得到遏制,清朝将藏传佛教僧侣特权严格限定在法度之内,凡事以法为据。在管理制度上,虽然元朝由中央到地方皆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但在具体的规范细则上却稍嫌薄弱;而清政府对藏传佛教及僧人的管理则更为细致,且目的明确,恩威并施,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与管控。在宗教信仰上,元朝皇室既利用藏传佛教,但因过度信奉和庇护而导致对宗教势力约束力不足;而清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态度十分谨慎,对其影响和教化作用认识清醒。
于这一“统”一“分”、一“放”一“严”、一“泛”一“细”、一“信”一“用”之间,元、清两朝对藏传佛教政策管控之高下立判。无论是在指导意识、监控力度还是细节实施上,清朝都吸取了元朝的经验和教训,将管控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就其效果而言,元朝由于对佛教的过度庇护,国家财富大量流入番僧手中,且一些寺院公然侵夺田户,导致民怨纷起。后期更由喇嘛引起后宫丑闻迭出,被不少史学家视为其亡国原因之一。清朝通过对藏传佛教的制度化扶持和治理,不仅赢得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拥戴,也赢得民心。无论在开国建业之初,还是在国家统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地喇嘛、蒙古王公均能“倾心中央”,反对分裂,共同护卫家国,并在客观上,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以古鉴今,藏传佛教在促进民族团结、融合,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元、清两朝藏传佛教政策管控之对比,可得者颇多:其一,可予以宗教领袖在教内的相应权力,但独权需慎,宜分权而治,尤其在中国多民族多信仰的国情下,任何时期教权都不应凌驾于政权之上;其二,法治社会讲究人人平等,不应该存在宗教特权,但这与出于对民族习惯的尊重,让民族地区的宗教人士享有特殊照顾不可混为一谈,后者对于维护宗教和社会的协调与稳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其三,从中央到地方设置层级管理机构对宗教予以管控是必要的,使宗教活动制度化,对不同级别宗教人士的生活待遇需规范明确,严格执行;其四,赏罚分明,维护民族和谐团结者,应大力表彰,反之则坚决论处;其五,寺庙的规模和住寺人数应该加以管控,这需要在地方寺院经济与社会生产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既使得宗教场所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又不至于社会生产领域因青壮劳动力的缺失而影响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1.
[2]宋濂,王祎.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J].西藏研究,1983,(4).
[4]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5]马连龙.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M].西宁:青海民出版社,2008.146.
[6]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G].张双智.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G].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317.
[7]张其勤,吴丰培.番僧源流考[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38.
[8]陈庆英,陈立键.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89.
[9]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146-152.
[10]佛祖统记[M].大正新修大藏经[Z].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435.
[11]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A].张双智.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G].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450-452.
[12]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13]朱德润.存复斋文集[M].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
[14]大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5]钦定大清会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6]周蔼联.西藏纪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1.
[17]妙舟.蒙藏佛教史[M].民国排印本.
[18]白文固.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整饬[J].中国藏学,2005,(3).
[19]张其勤,吴丰培.清代藏事辑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80.
[20]祁美琴.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151.
[21]昭琏.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