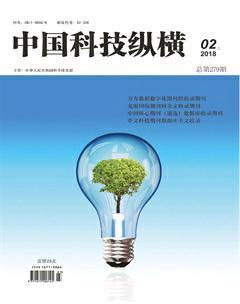哺乳动物的嗅觉通讯
黄大明+张雪妍+王瑜琪+陈实+John+F.Eisenberg+Devra+G.Kleiman
摘 要:嗅觉通讯作为化学通讯的一种,是由假定发送者生成化学信号,并将其传给相应假定接收者的过程。在哺乳动物中,假定发送者可将粪便、尿液和腺体分泌物的气味作为化学信号。它们将这些物质以不同的方式传播:沉积在某处或借助空气扩散。气味中包含了众多信息,如:物种和种族身份、性别和生殖状态、年龄、情绪等,实际接收到的信息则取决于接收者本身的状态。化学物质产生的嗅觉刺激可分为两类:释放者或起始物,前者将立刻引起反应,后者的作用时间稍有延迟。同一物质可同时承担两个角色。假定接收者具备能够识别、整合并从行为上或生理上回应这些信号的受体。部分哺乳动物还有特化的器官——犁鼻器来担负这一功能。动物有多种进行气味标记的行为,但嗅觉通讯的本质并非特殊行为,而是分泌物的释放和沉积。将气味物质行为的动机与气味功能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气味标记是交换信息的方式。它指导个体的行为,整合社会和繁殖。
关键词:化学通讯;嗅觉;嗅觉通讯;哺乳动物;信息素;种间信息素;标记行为;社会行为;繁殖行为
中图分类号:Q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8)03-0217-09
1 引言
目前,化学通信已成为许多综述研究的主题(Wilson[138];Johnston, Moulton & Turk[59];Wilson[137])。本文研究哺乳动物的嗅觉通讯。进行嗅觉通讯的过程中,假定发送者生成一种化学信号,并将其传送给相应的假定接收者(一般以空气作为媒介)。此接收者需具备能识别、整合并从行为上或生理上回应这种信号的受体。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故而信号分子的产生提升了发送者个体或种群受益于信息传输的可能性;整个信息交流过程被选择压力所支配。
用于触发同种生物反应的化学信号一般称作信息素(Wilson[137])——用于异种生物间交流的化学信号则称作种间信息素(Brown[16])。如此定义嗅觉通讯后,本综述将不对食物因素、栖息地因素等进行探讨,它们确实与化学感觉相关,然而属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信号交流,而非生物与生物间的交流。
嗅觉通讯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接受者能专一性地评估某些社会环境参数。但也具有一定劣势——由于化学通讯的信号传播一般不具备固有的方向性,为了确定信息来源的方向,假定接受者必须利用信号分子的浓度梯度。化学信号分子的“作用空间”一直是Wilson[137]和Wilson & Bossert[139]所讨论的主题。
即使发出者已经离开,信号分子的化学痕迹也能保留一段时间,这是化学信号相比视觉和听觉信号最大的优势。间断地进行化学物质沉积(deposition)通常被视为标记行为,本文将专门论述。
研究标记行为和嗅觉通讯的文献,大多没有将沉积气味物质行为的动机与气味的功能联系起来,这将带来一些问题,在讨论领域标记等概念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过去很多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气味标记的一些特殊行为上,忽略了分泌物的释放和沉积才是嗅觉通讯的主要特征。
2 化学信号感知
哺乳动物对化学物质的感知通常由三类不同的受体介导(Pfaffmann[100])。尽管具有较高的阈值,鼻腔粘膜的神经末梢还是能响应各种化学物质,其反应特性与嗅觉神经本身是非常相似的。Beidle已对鼻腔中起源于三叉神经的非特异性神经末梢进行过讨论[9]。味蕾中的哺乳动物味觉受体,仅能响应五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只能在溶解状态下与受体进行直接接触。味觉受体通常与第七、九、十脑神经相连(见Beidler[8])。
嗅觉只涉及某些专一受体,它们可能存在的位置有两处,(a)位于鼻腔后部的嗅粘膜,或嗅上皮的专一受体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属于第一脑神经,并终止于嗅球中。(b)多种哺乳动物中,由分散嗅上皮构成的犁鼻器内。嗅上皮的结构和功能已由Moulton & Beidler[89]、Moulton[87,88]分三篇做过论述。通常,我们认为嗅觉是一种特定的化学感受——引起刺激的分子通过空气传播,并被吸入鼻腔内,与初级嗅觉受体的细胞膜相互作用。具体的作用方式尚不明。
嗅神经受体被化学物质激活的方式仍有待讨论(见Amoore[3],Wright[141],Lettvin & Gesteland[71])。尽管激活机制的相关信息尚且缺乏,化学信息如何在嗅球中进行整合的概念模式也不精确,但事实:化学物质能够被哺乳动物感知,并确实影响到它们的行为。
2.1 犁鼻器
犁鼻器又称茄考生氏器,是一种涉及化学感受的,鲜为人知的解剖结构(Kerkhof[61])。有鳞目的犁鼻器由一些包裹在软骨囊中的嗅上皮构成,它们与鼻腔隔离,并在口腔内有开口。Burghardt从化学刺激角度研究了蛇和蜥蜴犁鼻器的功能,然而,哺乳动物犁鼻器的功能尚存争议。在哺乳动物中,犁鼻器是位于鼻中隔两侧,鼻腔底部的一种隔离密封结构。食虫目、啮齿目、有袋目、偶蹄目和奇蹄目的犁鼻器高度发达。然而在高等灵长类(猩猩科和人科)、一些翼手目和许多水生哺乳动物(鲸目)中,这个器官则可能退化甚至完全消失(Weber[132])。
犁鼻器盲袋(blind pouch)内侧的表皮细胞较厚,结构上与嗅觉器官的感觉上皮相似,然而侧壁以立方上皮细胞为主。在生长着嗅上皮的软骨袋的前端,通常有腔道通往鼻腭管(nasopalatine duct)的上部、中部和下部。在一些类群(如马属)中,鼻腭管完全不与鼻腔相连。在这种情况下,犁鼻器独立于鼻腔实现通讯(Sisson & Grossman[117])。许多物种中,犁鼻器与鼻腭管、鼻腔和口腔之间的解剖关系尚不明确。一部分哺乳动物的犁鼻器可直接與鼻腔沟通,或间接与鼻腔、口腔之一通过鼻腭管实现沟通。
通过一种特殊的神经:犁鼻神经终神经nervus termin-alis),犁鼻器中的嗅上皮与大脑嗅球相连。在某些哺乳动物中,嗅球有一个副叶与这根神经相连。终神经的通路旁经常并行生长着散布嗅上皮的浆液腺。Winans & Scalia[140]最近的研究表明,老鼠(Rattus norvégiens)犁鼻器的神经信号输入进到嗅球副叶中,并由此传至杏仁核。由于杏仁核将投射到下丘脑,作者认为犁鼻器有影响性行为和摄食行为的潜质。endprint
犁鼻器的腔体中几乎总是充满了液体。有一种生长着大量血管的壶腹状结构,它可以暂时充血,以增加器官内压,从而将腔体中的液体挤出。壶腹状结构消肿后,液体则会流回。这些结构通常被称作泵体(pumping bodies)[如 Schwellkrper(Weber[132])]。因此,尽管是封闭的,犁鼻器仍旧可以排出内部液体,并吸纳口腔与鼻腔中的液体。溶解状态的化学物质正可能存在于这些液体中。
不同于Adrian[1]用家兔(Oryctolagus)进行的早期研究得出的结果,Tucker[127]认为犁鼻上皮和嗅上皮同样敏感。Müller[91]证明,小鼠(Mus)犁鼻器的感觉上皮能对化学溶液做出反应。因此,小鼠与兔犁鼻器的生理活性已毋庸置疑。然而,犁鼻器在哺乳动物中发挥的功能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更多的研究佐证。
近来,犁鼻器在哺乳动物中发挥的功能已成为研究的主题。Poduschka & Firbas[101]描述了刺猬犁鼻器与口腔、鼻腔间通路的解剖关系。Verberne[131]则讨论了犁鼻器功能与猫科动物裂唇嗅行为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关系。
通常,裂唇嗅被描述为奇蹄目、偶蹄目及一些食肉目动物的特定表情。这些动物感知到多种嗅觉刺激,尤其是雌性动物的尿液(Schneider[110])后,便会产生这种行为。在有蹄类动物中,裂唇嗅表现为抬起或卷起上唇,将上门齿(奇蹄目和胼足亚目)或软骨板(鹿科和牛科)暴露出来。后来,Schneider在猫中也发现了类似由侧唇运动(lateral lip movement)引起的唇回缩现象。Schneider關注这种面部表情的产生原由。然而,感知到特定气味时,动物表现出了比预想更加多样的行为模式。Poduschka & Firbas[101]已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大体而言,这种现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a)动物嗅到某种气味物质;(b)有可能舔舐之;(c)抬起头,或是收缩唇部肌群或是抬起上唇(当其唇部可动时)。当动物具有象鼻状鼻部时(如沟齿鼩),其鼻子可能会向身体背侧卷曲抬起。然而,与这些动作同样重要的关联现象还包括松弛下颚、伸出或移动舌头、舔唇部、分泌唾液和改变呼吸速率。通常,呼吸会暂时停止,这之后,动物会短促地呼出几口气来。在呼气阶段,动物的鼻孔会从部分闭合变为完全扩张。
Knappe[66]认为,裂唇嗅现象与犁鼻器被刺激或激活有关。Poduschka & Firbas[101]证实,对于刺猬属的动物而言,抬起鼻子,张开嘴并分泌唾液的确能够刺激犁鼻器,因为舌尖推开了鼻腭道(Nasopalatine Canal)在口腔内背侧的开口。由此,潜在的嗅觉物质成为溶液状态,通过鼻腭道进入犁鼻器中。动物向自己身上涂抹嗅觉物质的行为(Selbtsbespucken,又称self-anointing),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衍生自裂唇嗅与犁鼻器刺激的行为(Poduschka & Firbas[101]),如刺猬将多余的唾液涂到刚毛上。
犁鼻器与口腔或鼻腔相连,且能行使正常功能的哺乳动物,其犁鼻器的激活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激活通常伴随着舌的运动,唾液的分泌和呼吸的变化。唇卷曲运动(lip-curling expression)是具有可动上唇的动物所特有的,它或是扩张了通往犁鼻器的通道[在phyllastomatid bats中(Mann[81])],或是帮助动物关闭鼻孔,这样空气便能滞留在鼻腔内。
尽管Dagg和Taubdeny否认长颈鹿的唇卷曲运动在犁鼻器刺激中的机械性辅助作用,但他们确实注意到偶蹄类动物在裂唇嗅反应中的重要特征:呼吸的变化和下一次呼气前空气在鼻腔中的滞留。然而Dagg和Taubdeny未能确切证明偶蹄目动物的裂唇嗅行为与犁鼻器受到刺激这件事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通过否定Knappe's[66]的原始假设来说明这点的。
尽管Knappe可能确实在物理模型的细节上有错误之处,但他的一般假设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还需要更多解剖、生理和行为学实验来证实。Whitten在1963年的一次未发表演讲中提出,犁鼻器可能与性信息素的感知有密切关系(参考Bronson[11])。
2.2 化学信号的来源
正因哺乳动物有着可以感知多种信号输入的接收器——嗅上皮,哺乳动物的假定发送方才能产生如此多种的化学信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描述各种具体代谢产物在化学通讯中的作用。
哺乳动物的尿液与粪便可发挥化学信号的作用。Altmann[2]认为动物在排便和排尿过程中的姿势和运动模式,以及行为模式中所包含的信息,包括扩散动作。此外,她还总结了每个物种排便和排尿位置相关的信息,以及多种环境下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不幸的是,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尿液和排泄物里包含的信息以及其隐含的社会关系还缺乏相应的实验证据。
腺体分泌物也参与了嗅觉通讯,Mykytowycz[97]指出了腺体在通讯中的作用。当动物会面时,其眼部的腺体可能会产生分泌物(Quay[102])[如,Dinomys,Microgale,Setifer (Collins & Eisenberg[33],Eisenberg & Gould[44])]。当动物用嘴唇摩擦物体时,口腔内腺体(Quay[103])可能与标记行为(marking behavior)有关。在很多动物中,附性腺也参与嗅觉通讯,这方面关于猪的研究很多(Sink[116],Signoret[115])。Schaffer[108]研究各种皮肤腺的分布与形态;Ortmann[98]研究哺乳动物肛门区相关腺体。
表1比较了两种无关的哺乳动物:黑尾鹿(the black-tailed deer),或称骡鹿(Odocoileus hemionus)(Müller-Schwarze[93])以及蜜袋鼯(the marsupial sugar glider, Petaurus breviceps)(Schultze-Westrum[112])。鹿的六个特定腺体区域涉及关于性别、年龄、身份和情绪信息的传达。分泌物由腺体产生,随后扩散到发送者身体的另一部分,或是沉积于环境中的某个特定位置,比如树枝上。endprint
腺体分泌物能够从发送者的身体上扩散到空气中,并传给其接收者。除了六个腺体区域之外,分泌物,如尿液和排泄物也涉及化学信息的传播。尿液、排泄物和腺体在有袋类动物的袋鼯属(the marsupial Petaurus)中也有相似的作用(Schultze-Westrum[113]),人们确定五种腺体,其中两种分别仅在雄性和雌性中发挥作用。
在一些情况中,这些物质的确切作用尚未被阐明。并且,哺乳动物分泌物仅有两例分离成功的活性物质(Müller-Schwarze[92];Brownlee,Silverstein,Müller-Schwarze & Singer[17];Michael,Keverne & Bonsall[85])。在第一例中,γ-內酯被证实为骡鹿(Odocoileus hemionus)睑板腺分泌物的活性成分之一。在第二例中,短链脂肪酸被认为是猕猴阴道分泌物的活性成分之一(Macaca mulatto)。
Sink[116]提出了雄激素衍生物(如雄甾烯醇,一种具有麝香气味的物质)可作为猪的性信息素(Sus scrofa),他列出了生物由血液中的游离类固醇合成具有气味的雄甾烯醇的几种可能途径。表2列出了马岛猬科四种动物两性婚配前,接触-促进行为(contact-promoting behavior)中涉及到的腺体分泌物。这里,从五个身体区域产生的腺体分泌物在婚配行为的协调和增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腺体分泌物在此交流过程中并不会沉积到环境中。
表2的B部分列出了四个相同物种来自部分相同腺体区域的可沉积分泌物,如唾液、尿液和排泄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们能够提供分泌者的身份和性别信息,当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相遇时,二者并不需要发生密切的接触行为。这将我们思绪引向标记(marking)。
2.3 化学信号分子的释放与沉积
化学物质的沉积通常具有五种情况(但并不绝对):沉积在环境中的某种特殊对象上;沉积在某种特定的物质上(与含有该物质的对象种类无关);沉积在某一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身上;从发送者身上的一部分沉积到另一部分(自标记,self-marking),以及从身体表面释放气味到周围的空气中。
在对象标记中,动物会用身体的一些腺体区域摩擦某一特定位置,或将尿液、排泄物沉积在环境中某些离散的位置上。对象标记行为通常非常复杂,为了将气味物质沉积到距地面合理的高度上,以加强气味在那个点源的“活性空间”,动物可能会做出非常奇怪的姿势(Wemmer[133])。图1画出了灵猫科食肉动物标记姿势的可能进化轨迹。
Tschanz,Meyer-Holzapfel & Bachmann[126]提供了一个关于哺乳动物标记现象更好的图解,并讨论了欧洲棕熊(Ursus arctos)的摩擦行为。雄性棕熊抬起后腿,用背部或是颈部摩擦某些特定位点,如树干。有时也会在抓挖树皮时采取正面姿势,用胸摩擦物体。雄性棕熊摩擦行为的频率在秋天达到一年中的最低点,繁殖期前的五月则达到最高峰。不同的雄性个体偏好不同的标记位点,有些位置可能仅被一头棕熊使用,有些则受到众多个体的青睐。雌性棕熊与雄性有着不同的位点,但它们也会使用雄性的公共位点。每头动物个体在它的栖息空间中都有一套固定的标记图示,它们按照成型的模式来选择标定点。年轻的棕熊会避开那些已被陌生雄性标记的位点。雄性可以区分标记者的性别。
除了摩擦,熊也会通过有气味的尿液和排泄物实现交流。排泄物的气味不是很重要,但雄性可以区分雌性尿液和雄性尿液的差别。相似的标记行为模式也存在于其它哺乳动物中(Kleiman[62])。棕熊的相关研究比较完整。标记行为的功能意义在后叙。
值得一提的是,哺乳动物的某些行为虽与标记行为有关,但并不涉及来自自身的气味沉积。它们可能会通过扰乱或释放气味来标记环境中的某个区域。摩擦土地尽管可能涉及到足腺(pedal gland)气味物质的沉积,但也会通过新鲜土壤本身的气味来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力(如猫科动物在气味标记后的抓擦行为scratching behavior)。折断树枝;用獠牙、角或爪在树皮上刻痕也可能会引起接收者的注意,此时发挥作用的是流出的树汁,而非标记者的獠牙、角或爪留下的任何气味痕迹(Eisenberg & Lockhart[45])。
某些种类的动物在气味标记过程中会采用非常显眼的姿势。有时,被标记地点也会具有显著性。这暗示了某种化学痕迹可能同时基于视觉和嗅觉两方面。前者在一些社会性动物中尤为重要(如狼抬腿动作);后者在相对独居生活的哺乳动物可能更为重要。视觉刺激和嗅觉刺激在动物对气味标记点的感知中的相对重要性仍有待研究。
每个箭头都指向一种现存物种采用的特异性姿势。黑色箭头是由蹲坐姿势派生出的几种姿势间的逻辑进化关系。白色箭头是普通四足姿势的两种可能蹲坐姿势来源(Wemmer[133])。
2.3.1 社会伙伴标记
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的标记行为在哺乳动物中广泛存在。具体表现为在爬过对方身体时,用会阴区接触对方;或是在对方身体上排尿。家鼠就有这样的行为(Steiniger[120])。然而也存在特化的标记行为。比如,在袋鼯鼠动物中(Schultze-Westrum[112]),雄性可能会用额腺(frontal gland)摩擦雌性的身体或是腹板腺(sternal gland)。
2.3.2 自我标记及其相关现象
一些哺乳动物对气味做出反应时,会把气味物质涂到自己身上的各个部分。Wemmer[133]详细描述了灵猫的滑颈反射(necksliding response)。将尿液或分泌物从身体的某一部分抹到另一部分也是一种自我标记形式,如骡鹿。它会将后腿前伸,并将睑板腺分泌物抹到上面(Müller-Schwarze[93])。endprint
刺猬的自我涂抹(Selbtsbespucken)反应是自我标记的另一种形式(Erinaceus)。这种行为模式涉及到对气味物质的接触和舔舐。刺猬分泌大量唾液,其中部分被用来浸渍被舔舐物质,由此气味便混杂在内。此后,舌的运动将这种具有气味的唾液选择性地涂在身体的一些部位上。Echinops telfairi有一种类似的自我涂抹行为,它们将唾液涂抹在前爪上,以此将唾液涂到身体的其他部位(Eisenberg & Gould[44])。
2.3.3 特定物质标记和毛皮标记
沙浴是修整毛皮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模式广泛存在,尤见于沙漠哺乳动物(Eisenberg[43])。典型的沙浴包括挖入沙土中,进行一系列物种特异性的摩擦运动,摩擦部位一般是身体两侧及腹部。在沙浴过程中,动物通过各种弥散腺体和局部腺体留下气味物质。有时,进行沙浴的动物可能会在沙浴地点排尿,并用尿液浸润自己的毛皮。沙浴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同时包含了毛皮修整行为和标记行为。单就标记行为这一点而言,沙浴涵盖了特定物质标记和自我标记两种行为的元素。此外,由于许多个体会公用一个沙浴地点,沙浴也可能导致腺体分泌物的交换(Eisenberg[43])。
2.3.4 气味的释放
将过多注意力放在化学物质沉积相关的某种特殊行为模式,或是化学物质释放(如可见气味标记、尿液或排泄物)的结果是,我们可能忽视了哺乳动物没有可见视觉信号的气味释放行为。事实上,许多物种在受到惊吓时的确会释放特殊气味(如骡鹿跖骨的气味(Müller-Schwarze[93])。此类气味释放经常被忽略,需要更多相关研究。
2.3.5 嗅觉信号的功能
在讨论嗅觉刺激的功能及其对接收者的影响时,以信号中潜藏的信息量和被确切接收到的信息为标准分情况讨论。可见响应(visible response)也许只针对接收到信号中的一部分。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某种给定的化学刺激可能包含远多于预想的信息,或者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被响应。对某种化学物质给出的响应取决于接收生物的状态,如它的年龄、性别、繁殖状态和情绪。比如,女性对环十五内酯气味的感知能力取决于她的月经周期,排卵期的时候最敏感。男性则通常缺乏这种感知能力(LeMagnen[70])。
3 化学信号传输的信息
3.1 物种与种族身份
Godfrey[53]的早期研究证明,岸(bank voles,Clethri-onomys)可以区分它们和亚种之间气味的差异,且每一个亚种种群的雄性都更喜爱它们近亲雌性的味道。如此,气味线索便成为生殖隔离机制的一种。而后,Moore[86]研究白足鼠属(Peromyscus)的两个种(P.maniculatus and P.poli-onotus),發现:和同属其他物种分布区重叠的P.manicul-atus更喜欢同种个体的气味,而非P.polionotus的气味;而与同属其他物种存在地理隔离的P.polionotus就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另一项关于小鼠(Mus musculus)的研究(Bowers & Alexander[10])指出,小鼠仅靠气味信息就能区分同种个体和白足鼠属其他啮齿类动物。最近,Dagg & Windsor[35]证明沙鼠(Merlanes unguiculatus)可以区分同种个体和其他四种小型啮齿类动物的气味。
鼠类这种区分同种与不同种个体的能力也可以由妊娠阻断(pregancy block)和布鲁斯效应(Bruce effect)证明。Parkes & Bruce[99]和Dominic[37]证明,当受精的雌鼠暴露在另一物种雄性的气味中时,它将终止怀孕。这项研究表明,来自陌生雄鼠的视觉、听觉、触觉刺激都不是必要的,它尿液的气息或是生活环境的切屑就能产生作用。尽管布鲁斯效应在其它鼠类 [田鼠属Microtus(Clulow & Clarke[32]),白足鼠属Peromyscus(Bronson & Eleftheriou[13],Terman[123])]中有效果,但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仅靠嗅觉刺激就能产生该影响。然而,田鼠和白足鼠,能像小鼠(Mus)和岸(Clethrionomys)一样,靠气味区分同种和非同种种族甚至族群(strain)。
研究证实,社会性哺乳动物的种群(group)或群落(community)确实具有特殊气味。普通狨(CalUthrix acchus)(Epple[47])和蜜袋鼯(Petaurus breviceps)(Schultze-Westrum[112])都能靠气味区分种群成员和外来成员。年轻的蜜袋鼯在遇到一个额部、胸部和会阴部腺体涂有陌生分泌物的熟悉动物个体时,会摆出防御姿态,因此,这三个区域共同产生了群落特异性的气味。
物种特异性气味和群落气味可能有几个来源。第一,气味腺体分泌物的活性成分,或者尿液和排泄物,可能因遗传控制的代谢差异而在物种、种系和种群间表现出不同。这种不同不仅限于分泌物和排泄物成分的不同,还包括活性物质在其中的比例。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物种、种系和种群产生不同的气味。第二,差异可能来自环境因子。在具有些微差异的栖息地中生活的种群,可能会有不同的饮食组成。由此排出的废物(如尿液和粪便)便会产生差异。
最后,化学物质产生过程所涉及基因的个体差异,能够增加社会性物种的群落气味。通过聚在一起睡觉或休息,个体间频繁进行身体接触,如此,群体中不同个体的味道传递和混合,并制造出一种均匀的气味。此外,一些特殊的行为模式能向同物种传递化学分泌物和尿液。在兔子、穴兔和小袋鼯鼠中,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用腺体分泌物标记种群成员(Lyne, Molyneux, Mykytowycz & Parakkal[75],Mykytowycz[96],SchultzeWestrum[113])。在兔形目和caviomorph rodents(Kleiman[64])中,当两只动物会面时,雄性经常在同物种个体,尤其是雌性个体的身上排尿。当一个个体标记其它所有个体时,种群也可能产生相同的气味。endprint
3.2 性别识别与生殖状态识别
Bowers & Alexander[10]进行辨别测试(discrimination test),结果显示,老鼠可以通过气味辨别同种个体的性别。此外,Dagg & Windsor[35]发现沙鼠也具有同样的能力。褐麂羚(Cephalophus maxwelli)、骡鹿(Odocoileus hemionus)、环颈西貒(Dicotyles tajacu)和棕熊(Ursus arctos)对不同性别个体分泌物做出的反应也不同(Rails[105],MüllerSchwarze[93],Sowls[118],and Tschanz,Meyer-Holzapfel, & Bachmann[126])。另一些研究重点关注了雌雄动物对不同生殖状态个体气味的反应差异。最早的研究由LeMagnen[69]和Beach & Gilmore[6]进行,他们分别证明雄鼠和公狗可以区分发情期和非发情状态(unreceptive)的雌性,并对前者表现出偏好。
近期对猕猴的研究[Macaca mulatta(Michael & Keverne[84];Michael,Keverne & Bonsall[85]),Macaca radiata (Rahaman & Parthasarathy[104])]指出,嗅觉信号,而非听觉或视觉信号在雄性对发情和未发情雌性的区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Michael & Keverne[84]研究发现,在切除卵巢的雌性恒河猴阴道涂上雌性激素处理后的正常雌性恒河猴的阴道分泌物后,雄性恒河猴和它们的婚配行为会增加。此外,他们还证实,嗅觉缺失的雄猴,婚配行为会减少(Michael & Keverne[84])。Rahaman & Parthasarathy[104]观察到,戴上头套,阻绝视觉、听觉和触觉的雄性在接触到发情期不同阶段雌性的气味后,自慰行为和性唤起的次数会增加。
人们还研究经验和激素因素对同型和异型性气味(sex odor)区分和偏好发育的影响。Carr的早期研究证明(Carr & Caul[23])未切除卵巢和切除卵巢的雌性都可以区分阉割和未阉割的雄性。反之亦成立。因此,生殖腺的有无并不影响动物对异性生殖状态的判断。
Carr与其同事的后期研究(Carr,Loeb & Dissinger [25];Carr, Loeb & Wylie[26];Wylie[142];Carr,Wylie & Loeb[28];Stern[121])使用偏好测试(preference tests),而非辨别测试。这项研究中,受试动物的性别、经验、激素状况和年龄以及测试气味是变量。Schultz & Tapp[111]在最近一篇关于啮齿动物气味偏好研究的综述中,发现使用一个受试动物和两种带有气味的动物可以产生80种无重复的实验组合。其中少于一半的可能组合已被测试过。在34种可能的组合中,13种被检出了偏好,然而两位研究者对同样的组合得出了不同的实验结果。尽管有差异,它们都表明,雄性的偏好性比雌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且性经验和激素水平确实对偏好有影响。因此,多种哺乳动物被证实可以仅靠气味区分性别和生殖状态。同型和异型性别都有对于气味的偏好,这些偏好取决于接收者的年龄和生殖状态。
对性别的区分可能基于几个因素。在某些哺乳动物中,雄性比雌性具有更发达的气味腺体[兔(Mykytowycz[96]);环尾狐猴Lemur catta(Evans & Goy[48]);仓鼠,Mesocricetus auratus(Lipkow[74])]。因此,区分标准可能基于某种特定分泌物的有无或者它的浓度高低。生殖状态的区分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机制,因为腺体的活性是季节相关的(Mykytowycz[97])。在这两种情况中,气味的产生将受到激素的调控,并且可能基于雌性和雄性分泌物化学成分相关基因的差异。
但是对于生殖状态的区分也可能依赖于这些影响生殖系统的类固醇激素。代谢废物,尤其是尿液的气味会产生差异。几种雄性激素的代谢产物有麝香的味道(Sink[116])。分泌类固醇的浓度和成分差异可能有以下两个来源:(a)类固醇代谢的变化。代谢产物的排泄会根据所在生殖周期的阶段不同而产生变化;(b)生殖周期中实际产生的固醇种类变化(如黄体酮和雌性激素水平在发情周期中的变化)。
另一种可被用来检验繁殖状态的气味源来自子宫和阴道分泌物。最近,Michael,Keverne & Bonsall[85]分离和鉴定了雌性恒河猴阴道分泌物中对雄性产生吸引的活性物质。
3.3 个体区分
Bowers & Alexander[10]对大鼠的研究首次证实了哺乳动物可以只通过嗅觉区分个体。Carr,Krames & Costanzo[24]研究性满足和未性满足的雄性大鼠的嗅觉偏好,间接证明了雄鼠可以区分两个发情期雌性当中曾与其婚配的个体。Dagg & Windsor[35]的近期研究表明,即便尿液已被稀释了1000倍,沙鼠仍可以区分性别相同的个体之间的尿液气味。
3.4 年龄区分
证据表明,哺乳动物能够区分青春期前和性成熟个体的气味,因为许多气味腺体的功能和气味标记相关行为都是激素决定的。Mykytowycz[97]發现兔的颏腺(chin gland)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发育。成年公狗和公猫的排尿行为(举起腿并向后排尿)模式在性成熟后会发生变化。相对年龄的区分标准是不同性成熟度动物的气味取决于激素的多重效应,这可以作为区分相对年龄的标准。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哺乳动物可以以生殖状态和个体特征之外的标准区分成年个体的绝对年龄。
3.5 情绪区分
哺乳动物可以仅靠气味区分同种生物的情绪与社会地位。老鼠和兔都可以识别同种动物的危机气味(Angst Geruch)。这种能力并不基于个体识别(Valenta & Rigby[128],Müller-Veiten[94],Sprott[119])。Müller-Veitenv[94]发现,在小鼠中,尿液产生的气味能够保持7-8小时(它能够引起回避反应),但这种作用在24小时后就会消失。Müller-Schwarze[93]认为骡鹿跖骨的气味是一种警告暗示,因为当骡鹿暴露在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如遇到一只狗)时,它们便会释放这种气味。此外,当闻到另一只鹿的跖骨气味时,骡鹿会减少舔舐监护人(caretaker)头部的频率。endprint
小鼠被非生存条件(如电击)惊吓时,会产生气味。但也有数据证明,当“惊吓状态”来自与竞争性的个体的遭遇时,小鼠也会产生能被同种个体识别的气味(Carr,Martorano & Krames[27])。
在偏好测试中,生活在稳定优势等级的大鼠(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的警报反应alarm reaction不会产生)会花更多时间嗅未知顺从雄性的气味,而非占统治地位的雄性(Krames, Carr & Bergman[67])。因此,大鼠可以区分顺从个体和统治者的气味,即使产生气味的个体最近没有参与争斗。
哺乳动物在压力状况下释放气体的情况已有诸多记载。典型的,也是最特殊的反应是臭鼬(Mephitis mephitis)在倒立状态下,肛门腺分泌的气味。其他哺乳动物也会在压力情况下由气味腺体产生强烈的气味,如骡鹿(Müller-Schwarze[93])。此外,在引发危机感的情况下,动物还会条件反射产生尿液和排泄物,但在一些物种中,该反射受到强烈的自律控制。毛丝鼠(Chinchilla laniger)和豚鼠(Cavia porcellus)在被惊扰时会向引起该反应的人类喷射尿液。这种受惊时特异性的气味释放不仅仅发挥了警告作用,还可能是一种防御行为(例如臭鼬)。
4 气味的生理和行为效应
一般嗅觉刺激分成两类。一些物质能担任释放者(releaser)的使命,是因为它们可以立刻引起特异性反应。然而,在哺乳动物中,这样的气味非常罕见。第二类物质通常被称作起始物(primer),因为它的起效存在延迟,或者没有对应的可见行为反应。大多数关于起始物的研究都涉及生殖过程(如布鲁斯、魏顿氏效应、Whitten效应和Lee-Boot效应)。然而,个体行为也可以被起始物影响,因为所有体现了生物体物种、种族、性别、和情绪的气味,或多或少都为个体间的遭遇打好了基础,它们可以让接收者做出某些特异性反应。比如,Müller-Schwarze[93]指出,在遇到角上涂有雌性小鹿睑板腺分泌腺的雄鹿时,一只七个月大的雌性骡鹿会立刻跑向一只雌性小鹿。气味中包含的年龄和性别信息让这只雌鹿跑向最符合所接收到的气味的个体。
在起始物的分类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大类物质,它们只是简单地唤起个体,使它为环境变化作出准备。比如,陌生气味通常会使圈养动物的活动水平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气味的新颖性。尽管这些物质不涉及通讯,它的作用方式可能与同种动物间的气味交流具有类似的机制,因为非特异性的唤起可能来源于对同种生物某种嗅觉刺激的感知,它们都对接收者具有新颖性。
同理,同一物质可能同时具有启动(priming)和释放(releasing)效应,能引起某种特异行为模式释放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接收者的生殖状态、情绪或一般唤起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它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的行为效应。因为一些嗅觉刺激可能具有多种效应,我们将在下文中按照功能分类进行探讨。
4.1 繁殖
4.1.1 繁殖功能
Bruce[18]的早期研究表明气味对生殖过程有显著影响;研究证实,陌生雄性能让近期受精的雌鼠通过阻断着床中止怀孕。后来,人们发现,仅靠气味就可以发挥这种效应(Parkes & Bruce[99],Dominic[37])。若雄鼠在青春期前被阉割过(Bruce[19]),或者雌鼠的嗅觉功能缺失(Bruce and Parrott[21]),怀孕阻断将不会发生。
这些嗅觉刺激物最终影响着下丘脑;抑制垂体催乳素的释放,促进FSH与LH的释放,从而诱导正常发情周期的循环(Bronson[11])。近期研究表明,最近受精的雌性小鼠,在接触到陌生雄性后,脑垂体会释放LH(Chapman,Desjardins & Whitten[30])。外源催乳素(Bruce & Parkes[20],Dominic[40])、垂体异位移植(Dominic[39])、外源黄体酮(Dominic[38])在婚配后起到防止妊娠中止的作用。
肾上腺也与此密切相关,可能是一个影响下丘脑的途径。妊娠终止經常发生的环境条件(例如种群密度过高)通常也是影响到肾上腺大小、功能的条件(Christian[31])。妊娠阻断现象也存在于北美鹿鼠deermouse,Peromyscus maniculatus(Bronson & Eleftheriou[13])和安纳托利亚田鼠Microtus agrestis(Clulow & Clarke[32])中,但还没在其他哺乳动物中得到实证。
嗅觉刺激的第二种启动效应是Lee-Boot和Whitten效应(Whitten[134],Whitten & Bronson[135])。关在同一笼中的雌性小鼠(Mus)和鹿鼠(Peromyscus)表现出不规律的发情周期,并经常表现出假孕。然而雄性、雄性尿液和成年雄性的气味 (Whitten, Bronson & Greenstein[136],Bronson & Dezeli[12], Bronson & Marsden[14])可以让同种雌性迅速发情,并同步它们的周期。在其他几个物种中,雄性的出现也是诱导发情的必要因素——如the green acouchi, Myoprocta pratti (Kleiman, personal observation);野生豚鼠the wild guinea pig,Galea musteloides (Rood & Weir[106]);绵羊和山羊(see Whitten & Bronson[135])等——但是发情的诱导是否仅靠嗅觉刺激完成尚不明确。最近证实了雄性尿液气味或雄性个体本身的第三种生殖效应(Vandenbergh[19,130])。当和成年雄性一起圈养、或者暴露在它们的气味中时,雌鼠会更早地开始青春期。Termalll[122]证实了,当鹿鼠被成对饲养时,会出现性成熟提前和繁殖增强现象。当它们被养在高密度种群的环境中,繁殖则被抑制。养在一对异性鹿鼠的环境切屑或者干净木屑上的鹿鼠不会提前性成熟。因此,在高密度种群中抑制怀孕的单一或众多信息素,在鹿鼠被成对饲养时,可以增强繁殖。性早熟的发生也见于雌猪(Brooks & Cole[15]),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效应仅靠气味调节。endprint
在鼠类中具有抑制怀孕、诱导发情和促进性成熟提前的生殖启动激素,可能是一種所有成年雄性尿液中共有的成分。它在雌性身上所起的作用可能取决于雌性接收到嗅觉刺激时自身所处的生殖状态,以及雌性的早期嗅觉经历。
4.1.2 性行为
人们早就意识到,雌性发情期的气味是向雄性表明其情况的首要刺激(Hafez[54])。在狗(Beach and Gilmore[6])与鼠(LeMagnen[69])中,雄性往往会花更多时间去嗅发情期的雌性,这不仅表明它们具有识别其气味的能力,更表明它们对发情期雌性气味的偏好。此外,婚配前的一个基本互动模式是嗅闻彼此的腺体区域,特别是肛门-生殖器(会阴)区域。
要成为性行为的释放者,一种气味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能被感知与偏好;第二,其缺失必定导致性行为频率的下降甚至缺失。这种嗅觉刺激对于婚配的重要性仅见于叙利亚仓鼠Mesocricetus auratus (Murphy & Schneider[95])、恒河猴Macaca mulatta (Michael & Keverne[84,85])。在狗(Hart & Haugen[56])、大鼠Rattus norvegicus(Heimer & Larsson[58],Larsson[68])、公羊ram(Lindsay[72],Lindsay & Fletcher[73])中,气味缺失不能诱发行为缺失。在某些物种中嗅觉丧失并不能完全消除雄性的婚配行为,只能导致行为频率的下降(如大鼠和公羊)。
嗅觉刺激对婚配行为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详细验证。因为雄性在爬跨和触摸过程中的触觉输入对诱导雌性动物脊椎前弯,摆出婚配姿势(Lordosis behavior)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对发情期雌猪(Hafez & Signoret[55],Signoret[115])的研究显示,雄猪的气味在建立“婚配姿势”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当人类轻抚它们的后背而不提供其它任何来自雄猪的刺激时,仅有48%的发情雌猪摆出婚配姿势。当引入雄猪的气味后,这个比例上升到81%。泰森腺对雄猪的气味有重要贡献(Dutt, Simpson,Christian & Barnhart[42])。
4.1.3 母性行为
与性行为相同,Beach & Jaynes[7]证实母性行为也受多重感受的控制。来自年幼个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线索诱导和维持着适当的母性反应。近期研究大都支持这一假设[绵羊(Lindsay & Fletcher[73]),山羊(Klopfer[65])。但近期对鼠类 (Gandelman,Zarrow,Denenberg & Myers[51])两个研究却于此相悖。关于小鼠Mus(Gandelman,Zarrow, Denenberg & Myers[51])和大鼠Rattus(Fleming[50])的研究表明,嗅觉刺激的丧失可能使母性反应完全消失,导致幼鼠被嗜食或被忽视。
4.2 社会行为
4.2.1 逃跑与服从
前文已经提到,当小鼠(Mus)暴露在因非社会状况受惊的同种个体所释放的气味中时,会做出回避反应(Müller-Veiten[94])。闻到跖骨气味的骡鹿,其活动会被抑制(Müller-Schwarze[93])。对于社会交往中释放的气味,只有辨别测试和偏好测试能够有效评价其效应。Carr,Martorano, & Krames[27]将小鼠暴露在采自三个类别测试对象的成对气味中:(a)社会交往中遇到压力的同种动物(如,在争斗中被打败);(b)无压力同种动物(争斗中胜利的、或是被隔离养育的动物);(c)在非社会情形下遇到压力的同种动物。假设在这些实验中,对一种气味的偏好同时也表明了对另一种气味的回避。以这种假设为前提,我们发现除一例外,无论受试小鼠是统治者还是下位者,所有闻到被打败或受惊的同种个体气味的小鼠,都更偏好后者。在唯一一次受试小鼠选择了前者的实验中,该鼠曾被释放前者气味的小鼠打败过。这个结果暗示了被打败或是受惊小鼠的气味也能产生回避效应(avoidance,即对另一种气味的偏好)。因此危机气味(AngstGeruch)也会产生于被打败的动物,并引起同种动物的回避。值得一提的是,Carr实验室中用大鼠(Ratius)所做的类似实验(Krames,Carr & Bergman[67])与小鼠实验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因为大鼠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嗅闻被击败的陌生雄性,而非统治地位的雄鼠。尽管大鼠可以区别被打败的同类和非社会条件下受惊的同类,没有证据显示大鼠会产生危机气味(它在小鼠中会引起回避反应)(Valenta & Rigby[128])。当然,鉴于判断标准是动物嗅闻两种味道的时间长短,要用实验来区分动物对其中一种、两种或者它们之间任意组合的吸引、回避或无视现象是非常困难的。然而,Carr的实验结果具有一定价值。
4.2.2 攻击与支配
哺乳动物在仅有气味而没有同种个体在场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案例鲜有记载。仅仅闻到另一只成年雄性肛门腺的气味,Brush-tailed possums(Trichosurus vulpécula)便会摆出威吓姿态(Thomson & Pears[125])。仅暴露在陌生成年雄性的气味中,袋鼯对隔壁笼子的雄性个体的攻击性就会增强(Schultze-Westrum[112])。在其他物种中,攻击行为的变化仅见于成对或成群动物的遭遇。最常用的实验动物是小鼠。
早期研究(Mackintosh & Grant[76])指出,当拿走一对相互熟悉的雄鼠(Mus)中的一只,并在它的会阴部涂上另一陌生雄鼠的分泌物时,它们之间格斗行为的频率会增加。相反的,当两只陌生雄性相遇时,如果其中一只事先被涂上了另一只小鼠所熟悉的同种个体的分泌物,格斗行为将减少;如果只是被湿棉花擦拭过,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Dixon & Mackintosh[36]证实,如果在其中一只小鼠身上涂上雌性的尿液,两只雄鼠间的攻击性行为会减少。Archer[4]发现,成组的小鼠暴露于陌生雄性的气味中时,攻击性行为会增加。Mugford & Nowell[90]发现在被阉割雄性小鼠身上分别涂上攻击性小鼠、顺从小鼠、和被阉割小鼠的尿液,并与陌生雄性小鼠放在一起时,它们的被攻击频率顺次减少。Ropartz[107]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切除了小鼠的嗅球,由此彻底消除了攻击性行为。此外,将一对小鼠放在某种强烈香气中时,其攻击性行为减少。endprint
总之,成年雄性小鼠会产生一种物质,在和其它个体首次相遇时,会增加争斗倾向。它可能存在于尿液中。尚不明确这种信息素是否和产生生殖效应的信息素相同,因为活性物质还没有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似乎并不必分离出独立物质来,只需证实这种气味能引起性别差异反应即可。
以上主要讨论陌生同种个体气味产生的效果。此外,应该注意个体气味(personal odor)对攻击性和统领性影响。对于大部分哺乳动物而言,最常接触到的气味来自其自身和一些熟悉的同种个体:体表散发出的分泌物气味,和领域内的日常活动会遇到的气味标记(以腺体分泌物、粪便形式存在)。这些气味可以使个体感到安全(Ewer[49]),当它们横穿自己的领地时,这些气味会增强它们的信心。这种由个体气味引起的信心增强,解释了为什么动物在自己的领地上通常胜多败少。
4.2.3 气味标记(scent marking)
对于强烈气味的感知、气味的产生和沉积,在几乎所有嗅觉为主要感受系统的哺乳动物中都密切相关。任何陌生气味都可以刺激气味标记行为,因此,探索新环境时常伴随有气味标记行为增加。
个体气味、来自熟悉或陌生同种个体的气味可能诱发气味标记行为的释放。响应个体气味的标记行为的规律发生,并且遵循一种很少变化的确定频率。比如,间蜂猴Nycticebus coucang (Seitz[114])进行尿液标记的频率与日常活动模式直接相关,在活动强烈时期,标记行为的频率也更高。这些标记帮助个体在环境中定向。对许多雄性和雌性个体而言,陌生或熟悉同种生物的气味会增加气味标记行为的频率。成年雄性尤其会对其它成年雄性的气味做出反应(见Rails[105])。
4.2.4 唤起
前文描述了嗅觉刺激的直接和长时效应相关的行为,是一般唤起效应(general arousal effect),这种效应可能由某几种气味引起。在通讯中,一些物种特异性气,味可能仅仅起到了唤起接收者的作用。当然,那些包含了物种、性别和情绪等信息的气味也可以产生唤起效应。唤起水平的增加可能表现为进行气味标记、增加攻击性、进行梳理行为等等。不同的是,很少有人区分,是所有频率增加的行为模式都由气味引起,还是仅仅他们所研究的行为是这样。
4.2.5 气味偏好的发展
物种识别,以及种、亚种层面上的气味偏好被称为嗅觉印记(olfactory imprinting)(Carter & Marr[29])。Mainardi[77,78],Mainardi,Marsan & Pasquali[79,80],Keimedy & Brown[60]指出:與双亲共同饲养的年轻雌性小鼠最终倾向于与不同种系的雄鼠婚配,它拒绝和它共同生活的雄性的味道。然而,未和父亲共同生活时,雌鼠会与同一种系的雄鼠婚配。通过气味物质对断奶前的年轻雌性进行人为调整,使其气味与同窝出生幼仔(littermates)相同,在性成熟后,该雌性会对带有同样气味的小鼠表现出偏好。这种现象未见于雄性。从Mainardi的工作开始,类似的效应已见于大鼠Rattus (Marr & Gardner[82], Marr & Lilliston[83])与豚鼠(Carter & Marr[29])。在这些研究中,受试动物被饲养在正常或人工的气味环境中,研究者检验它们对气味的偏好。根据初次暴露在人工气味中的年龄、暴露持续的时间、实验距最后一次暴露的时长,以及所使用气味,人们对大鼠和豚鼠的部分实验进行检验。发现,初次暴露的年龄(大鼠和豚鼠)和暴露时长(豚鼠)对之后的偏好有影响。越早、持续时间越长的暴露,产生的影响就越大。然而,在豚鼠中,饲养期间的人工气味没有引起永久性的偏好改变。不管早期经历如何,所有的个体最终都更喜爱正常个体的气味。有趣的是,豚鼠天然具有对两种人工气味的偏好,即,比起苯乙酮,它们更喜欢苯甲酸乙酯(Carter & Marr[29])。
气味偏好的发展通常始于母亲与后代间的联系。对于临产的雌性来说,最初,新生儿气味和她自身产液味道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新生儿的吸引力(Klopfer[65])。后来,频繁毛发梳理能使母亲的唾液沾到幼仔身上,加上养育期间的接触,这二者可能保持母子之间的气味相似性。在很多物种中,哺乳期的雌性,其某些腺体区域的分泌活动会增强[如,大棕蝠serotine bat,Eptesicus serotinus的口鼻腺(the muzzle gland)(Kleiman[63]),小袋鼯鼠Petaurus的囊腺(pouch glands) (Schultze-Westrum[113])]。幼仔对母亲气味的偏好(性选择可能从这里产生)毫无疑问是因为母亲(和同窝出生幼仔)的气味最初与温暖、食物和安全相关。之后,偏好性是因为母亲是最熟悉的存在。
4.3 总结
对动物园和非洲自然环境进行广泛观测后,Hediger[57]提出假设:在特定位置沉积排泄产物或腺体分泌物与领域性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标记行为与领地防御(territorial defense)相关。很多哺乳动物个体都会避开同类气味标记过的区域。另外,文献中很少提到同种个体会避开其邻居的标记点,特别是那些领地大面积重叠的物种。标记点是特定群落中个体可以沉积气味的地方(Eisenberg & Lockhart[45]),动物会按一定频率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同种个体的气味。标记行为不一定是领主的特权,也不一定发生在领地范围内。由Schenkel[109]提出并由Goddard[52]证实,间隔生活的物种——比如黑犀Diceros bicornis——没有对熟悉邻居表现出防卫的倾向。过路动物标记促进了领地意识,但一般情况,不会表现出领地防御行为。此外,雌性哺乳动物在发情期前和发情期中表现出的广泛标记行为显然与领地无关,受惊动物释放的气味也如此。
气味的沉积与释放有许多功能。它让生活范围重叠但独自觅食与行动的动物们实现化学信息的交流。它提供关于年龄、性别和生殖状态的信息。接收者对气味标记的反应部分取决于它所处的位置、情绪和标记的性质特征。Ewer[49]在她关于气味标记的研究中,区分了个体对自身气味标记和外来标记的感知。但她没有考虑不同外来气味(熟悉或不熟悉的同种个体、性别、年龄等来源差异)、接受者的物理位置或心理安全感对相应的影响。一个在它人社会空间中移动的潜在接收者,在感知到原住民的气味标记前,就已经表现出信心降低和提高的逃跑准备度。SchulzeWestrum[113]对袋鼯鼠的研究清晰地证实,不仅是所接收到标记的类型,接收者的情绪也很大程度决定反应倾向。因此,文献中鲜有个体接收到同种个体气味后,所产生回避行为的明确展示。一个明确的反应模式需要将多重变量分离开来。endprint
因此,气味标记不是领地防御手段,而是交换信息的方式。它指导个体的行为,整合社会和繁殖行为。
5 气味沉积和释放的动机基础
动机研究可能涉及到那些影响行为模式形式或频率的外部或内部刺激。激素调节对气味标记行为的影响(例如 Thiessen & Yahr[124])以及感觉和神经控制对标记的影响 (Baran & Glickmatr[5])都属于这个类别。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控制环境,并确定外部环境如何影响行为的发生。标记通常是对有着外来气味新环境的响应。尽管这类研究与行为的起因有关,但不管是涉及生理机制或者刺激控制,都很少用到动机和情绪的概念。
相反的是,许多研究倾向于将情绪和动机归咎于进行标记的动物。经典行为学手段被应用于分析标记行为的动机。Rails[105]在这方面作了很多贡献。她认为气味标记的初级动机来自攻击倾向。标记行为在无法容忍同类的统治者中表现最为强烈,此时它们倾向于攻击。气味标记与攻击暂时相关,并出现于倾向发生攻击的环境中。不幸的是,她主要考虑的那些标记行为高于正常水平,故而绕开了正常水平下标记行为的动机[“...它们可能完全不同”](Rails[105])。間蜂猴(the slow loris)进行尿液标记的周期性随着活动周期的不同而变化,动机并非攻击倾向。雄性金豺(Canis aureus)和雄性金钱豹(Panthera pardus)在日常巡逻中的尿液标记也不具攻击倾向(Eisenberg & Lockhart[45])。尽管这些观察案例中都包含了尿液标记行为,但腺体分泌物的沉积也在其中。
Rall研究的另一局限性是,她过分关注腺体分泌物在特定对象或同种个体上的沉积,而忽视了自我标记与不定向气味释放。此外,她还忽视了尿液和排泄物在气味通讯中的应用。释放气味至空气中这一行为,经常与令动物恐惧的环境和逃跑行为有关。此外,Kleiman(62,64)认为,进化上,一些哺乳动物由恐惧引起的自主排尿行为可能演化出了它们如今特定的尿液标记模式。一种最初因恐惧产生的行为,在特化后,其动机转变为了攻击,这是不太可能的。
以往研究着重于雄性的标记行为,而忽略了雌性。在雌性哺乳动物中,气味腺体活性、相关标记模式、以及气味标记,会随着生殖周期的变化而变化。此外,还存在标记行为率上升的现象,这与攻击倾向并不直接相关。
用特化的皮肤腺体进行标记通常是一种两性异型现象(sexually dimorphic phenomenon)。许多物种中,雄性个体具有功能的皮肤腺,在雌性中往往没有功能甚至退化消失。(如,穴兔Oryctolagus(Mykytowycz[96]),金仓鼠Mesocricetus (Lipkow[74]),亚洲象(Eisenberg,McKay & Iainudeen[46])。这些动物中,雄性的腺体通常对雄性激素敏感,阉割将导致腺体萎缩以及标记行为的减少或消失 (Thiessen & Yahr[124])。
因此,一些物种的雄性进行标记行为,必要条件是身体未受损、且血液中有高水平的雄性激素。显然,这些雄性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中表现出显著的攻击性行为。动物被激怒时,确实会表现出一些标记行为,但它的目的并非标记,而是表达自身的攻击性。
对每个个体进行综合考虑(它们的年龄、性别、情绪和生殖状态),得以探寻气味标记行为的动机。最适气味场(optimum odor field)是指能够给动物带来安全感的适宜气味水平。这个气味场由来自动物自身、环境和同种生物的嗅觉刺激构成。各种嗅觉刺激的比例和它们的总强度(即,气味饱和度水平)将影响动物。对气味场造成干扰的因素有:(a)动物生理状况的改变,此时它对最适气味场的敏感度和认知将发生变化;(b)外来气味的引入;(c)已有沉积气味的耗散,这时,动物会通过释放或沉积气味来试图恢复之前的平衡。根据性质,气味场的变化可能唤起个体,使之表现出其它行为模式。
对许多雌性哺乳动物而言,发情期前,它们都很少进行气味标记行为。而发情期时,尿液标记行为的频率会大幅上升。这种行为变化并不来自攻击性、领域或性倾向,而来自动物自身气味的变化。它们可能无法忍受高水平的同种气味。为了获得最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同种个体气味与自身气味的新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是雌性动物的自身激素水平影响了它的最适气味场。
社会等级不同可能会使生理状况不同,因此,个体的社会地位也可能影响最适气味场。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对同种外来雄性气味的忍耐度很差,甚至已知同种雄性也不行。因此,外来气味的引入可能会导致高的标记水平基础。亚优势地位或下级雄性对非己气味的忍受度就很高。但当气味域发生变化时,它们也会增加气味释放率。
产生自各种哺乳动物的众多气味物质都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气味标记行为。一些物质与特异的反应相关,这些反应可能不会导致气味标记行为水平的变化。比如,危机气味会影响老鼠的气味场,但产生的反应是回避。某些情况下,反应也可能是气味标记行为的完全抑制。
此外,和气味场无关的因素也可能导致动物释放或沉积气味。比如,香囊被触摸(如灵猫)(Wemmer[133])。被电击或受到惊吓后的自主排尿也是一例。
尽管我们提出一些标记行为的动机基础,但我们并未打算将各种释放气味的情况一概而论。气味的释放和沉积没有单一动机。单一刺激也不能解释所有行为。
参考文献
[1]Adrian, E. D.1955. Synchronized activity in the vomeronasal nerves with a note on the function of the organ of Jacobson. Pfluigers Arch. Gesamte Physiol. Menschen260:188-92.endprint
[2]Altmann, D.1969. Harnen und Koten bei Sugetiere. Wittenberg Lutherstadt: Ziemsen Verlag. 104 pp.
[3]Amoore, J. E.1966. Psychophysics of odor. Cold Spring Harbor Symp. Quant. Biol.30:623-37.
[4]Archer, J.1968. The effect of strange male odor o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male mice. J. Mammal.49:572-75.
[5]Baran, D., Glickman, S., 1970. Territorial marking in the Mongolian gerbil: a study of sensory control and function. J. Comp. Physiol. Psychol.71:237-45.
[6]Beach, F. A., Gilmore, R. W. 1949. Responses of male dogs to urine from females in heat. J. Mammal.30:391-92.
[7]Beach, F. A., Jaynes, J.1956. Studies on maternal retrieving in rats. Ill. Sensory cues involved in the lactating female's response to her young. Behaviour10:104-25.
[8]Beidler, L. M.1954. A theory of taste stimulation. J. Gen. Physiol.38:133-39.
[9]Beidler, L. M.1966. Comparisons of gustatory receptors, olfactory receptors, and free nerve endings. Cold Spring Harbor Symp. Quant. Biol.30:191-200.
[10]Bowers, J. M., Alexander, B. K. 1967. Mice: individual recognition by olfactory cues. Science 158:1208-10.
[11]Bronson, F. H.1968. Pheromonal influences on mammalian re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Sexual Behavior, ed. M. Diamond, 341-61. Indiana Univ. Press.
[12]Bronson, F. H., Dezell, H. E. 1968. Studies on the estrus-inducing (pheromonal) action of male deermouse urine. Gen. Comp. Endocrinol.10:339-43.
[13]Bronson, F. H., Eleftheriou, B. E. 1963. Influence of strange males on implantation in the deermouse. Gen. Comp. Endocrinol. 3:515-18.
[14]Bronson, F. H., Marsden, H. M. 1964. Male-induced synchrony of estrus in deermice. Gen. Comp. Endocrinol.4:634-37.
[15]Brooks, P. H., Cole, D. J. A. 1970.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ce of a boar on the attainment of puberty in gilts. J. Reprod. Fert. 23:435-40.
[16]Brown, W. L.1968. An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function of' the metapleural glands in ants. Am. Natur.102:188-91.
[文獻17-143由于版面有限省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