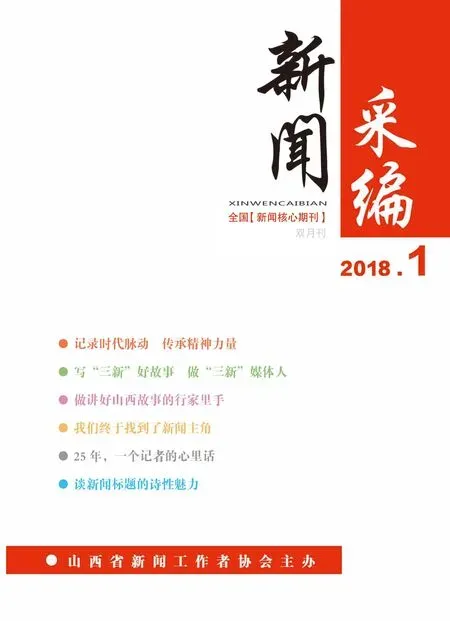我们终于找到了新闻主角
——《别了,白家庄矿》背后的故事
◇ 张临山
2017年11月8日上午,第18个中国记者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正在举行,我代表山西日报和我们团队上台领奖,捧回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也是山西日报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意义非常。
获一等奖的作品是我和冷雪采写,丁伟跃编辑的通讯《别了,白家庄矿》。这篇作品从策划选题,到采访写稿,及至最终出炉,前前后后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两次失败教训深刻,屡败屡战连续三年冲刺
每一个新闻人的心中,都有着中国新闻奖情结,这是中国新闻界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是对一个新闻人最好的肯定和嘉奖。十多年来,没有获得中国新闻奖就是我的一个心结。
还记得2005年7月,我从山西日报夜班编辑转岗到工交部做记者时,就连续买了近3届的《中国新闻奖作品选》,认真研读,咂摸味道,模仿写作,细细体会结构语言、故事人物,知道了最好的新闻作品“长得是什么样子”。
2006年我读了张严平的人物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佩服之极,模仿写作了我的第一篇人物通讯《一个人的信使之路》。
几年之后,我读到了石家庄日报记者赵俊芳、郝斌生的通讯《栾城草农敢闹海》,非常震撼,经济报道竟然可以这样写。这篇经典之作,写出了挂着露珠的“事”和活蹦乱跳的“人”。前辈范敬宜都对这篇作品进行了评析。
此后,我就多有留意,和我的良师益友赵峻青、齐作权多次探讨,如何能写出一篇中国新闻奖的新闻作品。从2001年到2017年,我拿了11个山西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但独独缺一个中国新闻奖。
2015年,入行14年后,开始有了转机。当年,我的评论《改到位让市场做主》代表山西参评中国新闻奖,通过文字审核一关,但最终没有评上奖。2016年,我的深度分析性报道《一吨煤的价值》再次参评中国新闻奖,且被报社给予厚望,却被查出4处差错,复议未果,直接倒在了文字审核关。这次打击极大,因为文字表述不严谨,大意失荆州,连续两年败走麦城。
屡战屡败,屡败再屡战。2017年,我和同事冷雪合写了通讯《别了,白家庄矿》,第三次参评中国新闻奖。我的想法是,连续三年冲刺能拿上奖就可以安慰了,若能争取个二等奖就很知足了。最终,万万没想到竟是个一等奖,大出意料之外,可以说是幸运之极。在此,非常感谢中国记协和评委老师的认可与厚爱。
一次中国记协座谈会,大开眼界迸发诸多新闻灵感
2017年能够拿奖,还得从一次会议说起。那是我此前新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我幸运的起点。
2016年11月底,中国记协组织在北京召开中国新闻奖和长江韬奋奖“两奖座谈会”。
因为有2015年和2016年的连续失败教训,山西记协和山西日报推荐我参加会议。临走前,山西日报总编辑丁伟跃还让我统筹采写了3篇年终深度报道。临走时,他对我说:“好好去北京学学,看看人家是怎么拿到奖的,看看你是怎么丢掉奖的。”
这次北京之行,让我醍醐灌顶,有拨云见日之感。唐湘岳、许志峰、王国庆等前辈老师的亲身讲解,让我感觉到,新闻界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大有人在。会上,专家和获奖作者的解读,让我零距离学到了“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怎样采出来的,写出来的。”
我一边培训学习,一边思考如何打造一篇关于“宏大主题”的“小切口”的精品稿件。
2016年,我国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年重点是推进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年关闭25座煤矿,退出煤炭产能2325万吨,居全国第一。山西煤炭去产能在全国力度最大、贡献最多,直接扭转了全国的煤炭供求关系。于是,我在北京就确定了写作的中国大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山西小主题:煤炭“去产能”。
回到报社,我向丁伟跃总编辑汇报了此行的收获以及写稿的初步想法,得到丁总的支持和指导,并与丁总商议形成了初步思路。
最终确定了“煤炭去产能”和“人的故事”这两个关键词。想讲一个“与众不同”的、大事件之中的“人”的新闻故事,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
三上矿山深挖典型人物,五易其稿精雕细刻文章
煤炭去产能,得先选定煤矿。前期做年终特稿时,工交部主任崔新龙带领我们已经去了阳泉、长治、晋城、太原等地的多座煤矿,心里已经基本有了目标。经过一番仔细梳理,最终,始建于1934年具有82年历史的白家庄煤矿入选。第一次上矿采访时,直觉告诉我,在这里一定能挖掘出很多感人故事。
选定煤矿,再进一步选新闻主角。讲好大主题下的故事,核心在人。寻找最合适的采访对象,决定着这篇宏大主题稿件的成败。
我第二次上矿山,通过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宣传部采访了几对矿工,有姐弟的,有夫妻的,还有兄弟的,但总感觉故事的典型性都欠点儿火候,味道不足。他们的故事我后来用到了几篇消息和特稿的写作中。
第三次,我就联合我的同部门记者冷雪,一起上山采访。我们去了矿上的机关,要来了工人的花名册,挨个看,寻找符合要求的。在几千人的花名册中,祁彬茂父子引起我们的注意。祁家三代都在白家庄矿上班,煤矿关闭,尚在岗位的父子二人有着不同的安置方式,他们的经历几乎是整个煤矿大部分工人的经历,极具代表性。
只有一对父子,显然有些单薄。就在矿上的办公室,我们拿起电话,对着花名册挨个打了过去,只要能打通电话的,都会详细询问对方的家庭、工作状况,安置情况,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沟通后,终于找到了第二对理想的采访对象——张保艾父子。
“我们终于找到了新闻主角”,我心中大喜。
一直以来,工业经济领域的报道是新闻报道方面的难点,难在核硬、面广、数据多、专业性强以及叙事角度有限、共鸣群体范围小等方面的难题。而在采写《别了,白家庄矿》这篇通讯时,从采访到写作,我们俯下身子,将共鸣点放在了人的身上。
我们总共采访了16位矿工,故事很多,细节丰富。稿件框架搭好后,写作一气呵成。
第一稿成文后,丁总给文章调整了结构,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几稿,丁总、冷雪和我一起研究、打磨,稿件前后一共修改了5次,每一次都有侧重点:梳理脉络,精选细节,细抠文字,核对标点符号……5易其稿后,丁总给文章起了现在简洁明快的名字《别了,白家庄矿》,将我们原先的文章题目做成了副题。

作者和冷雪(左)与矿工
发稿当晚,我跟着上夜班,逐字逐句,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进行了几次审定修改。稿件上版后,我又请资深校对叶建平老师帮助检查,排除差错。稿件最终尘埃落定,下班时已是凌晨3时。
我2001年进入山西日报,16年磨一剑,未轻言放弃,才有幸捧得一等奖,心情异常激动也充满感恩。报社前辈给了我很多指点,业界同仁给了我不少鼓励,行家大家们带给我诸多灵感借鉴。这个一等奖是大家共同帮助的结果。
想起1997年我在大学写的一篇文章《走向澄明之境》,其中有尼采的一句话:“你站在哪里,就在哪里挖掘,下面就是清泉。”
2017年记者节前,前省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宪写了一篇文章《新闻工作者首要的是社会责任感》,广为流传,我觉得新闻人的担当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还记得去年11月王部长荣调山东前夕,我随丁伟跃总编辑与他辞别,请他留言。王部长给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就是这句话——“新闻工作者首要的是社会责任感”。
我们已经进入伟大的黄金时代。于我们而言,好记者的使命,就是要书写记录新时代的好作品,讲好带有中国味道、山西特色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