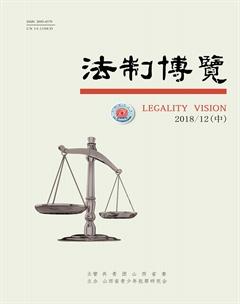论系统层化空间中的藏族习惯法
摘要:藏族习惯法是长期居住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法理自足的行为规范。然而,在中国法治建构推进的过程,藏族习惯法逐渐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出现了冲突。本文以法治中国和国家治理为基石,将法律看成一个整体系统,并将该系统层化为: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我们在不同的层化空间中理性的分析国家制定法和藏族习惯法,并为两者良性互动沟通提供方法。
关键词:系统层化空间;藏族习惯法;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35-0018-04
作者简介:刘娟(1984-),女,汉族,甘肃陇西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理论法学教学与研究。
Investigation of Tibetan customary Law in the Stratified Space of Law System
LIU Juan
School of law,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730070
Abstract:Tibetan customary law is the code of conduct of Tibetan people,which possesses distinctive features,rich connotations,and legal self-sufficiency in legal principle.This law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of Tibetan people,who long lived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Howev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w construction,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law and the Tibetan customary law appears slowly.In this paper,we consider the Chinese law as a system,and divide the whole system into two parts-the national space and the non-national space.we analysis the national law in the national space,and the Tibetan customary law in the non-national space.Consequently,a way for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laws are provided.
Key words:Stratified space;Tibetan customary law;Positive interaction
在以人為中心建立的系统中,多元共存是基本态势。一个社会、国家乃至全球都是由处在不同层次空间的主体主导并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由此而形成内部协调统一的体系。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想独霸控制权的行动,均是以失败告终。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孕育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中华民族气质,形成了礼、义、刑、德各要素相互融合的封建法制,天理、国法、人情高度统一的中华法系由此诞生。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族群之一,长期居住在雪域高原之巅,有着宗教信仰的传统,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法理自足、利益平衡的习惯行为规范,学者将之称为“藏族习惯法”。
一、系统层化空间论
法律是调整主体与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不管愿不愿意,一部法律出台后将纳入不同的系统层化空间适用。法律的主体决定了法律所处的层化空间。如在全球系统中,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和非政府间国家组织跟民族国家一样,分享着世界的治理权。又如在一国系统,国家、政府、政治党派、社会团体、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一起,通过自治与他治两种方式维系着整个体系的运行。哪怕是在一国系统之内,因各主体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同而决定了其参与度的高低。如法律中假定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能够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为一定的行为,如果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范的规定,则应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即承担法律责任。然现实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会受到社会环境、情绪、认知能力和水平的影响和限制,很难达到绝对的理性。波士斯皮尔认为,一切社会的法律体系都存在法律层次,因为社会是由整齐的等级的次群体组成,每个次群体都有其自己的法律体系,它由该次群体的权威所作的法律制裁的原则之总称构成。所以,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一套相应于其群体体系的等级,法律层次是同一类型的次群体的法律体系的总和,所有的人一般都同时属于许多次群体,因而也必须服从于不同的法律体系的要求。①法律体现的是主体的意志,也暗含着意志背后的利益,故而系统中各法律主体高举权利的旗帜,实质上是通过权利的争夺而获取最终的利益,使本主体的意志最大化。应然状态中,主体意志及利益是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各方地位的固定,这种地位的固定是相对的,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但均在可承受之范围之内,否则将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为各主体赖以生存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而最终取决于人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主导之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创造了经济领域的奇迹。法律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步。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并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了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和民生法治观为主的人本法律观,最终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然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信仰各异、地理和自然环境不同,加之我国“让一部分地区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均导致了东中西部发展极度不平衡,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制定法,就与社会实践,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有了罅隙。正是基于此,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释放东部过剩产能,发展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是多民族融合和聚居之地,基于对历史和民族的尊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规定。
正是有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在研究嵌入国家法中的民间法时,有必要提出系统层化空间的概念。在一国法律运行系统中划分为国家空间和弱国家空间两种。国家空间是国家对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取得成绩进行确认而形成的国家制定法运行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国家利益与各法律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各法律主体同样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创造者和利益获得者。弱国家空间是处于“国家空间”这一层化空间辐射之下,受国家影响较弱而自生自发的形成社会自治规范运行的空间。在弱国家空间,法律主体参与性不强,比如民众和社会团体,参与到法律关系与法律事务中的机会很少,法律意志尚未自主,权利意识不强,更多的依靠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行为模式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看,在同一法律系统中,运行在国家空间的国家制定法的层次要高于运行在弱国家空间的习惯法,但在纠纷的解决上,作为在弱国家空间的“活法”,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比国家制定法更大。
西藏自治区及藏族聚居的自治州、自治县所在区域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国家空间。改革开放以來,尽管国家自上而下的送法进藏,在藏区推行国家制定法,可是收效甚微。空气稀薄、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高寒地理特征决定了该区域较明显的封闭性,另加上藏音藏字这种独立的语言文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藏传佛教逻辑自足的教义影响,让信教的民众有精神上的依托和行为上的自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制定法的有限性,甚至于,快速构建的国家制定法与自生自发缓慢推进的藏民族的习惯法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有理念上的冲突,也有行为规则上的冲突。总之,在弱国家空间,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占有份额较少一些,纠纷的解决主要靠宗教人士或乡贤等权威人士主持之下的私力救济,而并不完全表现为公力救济。
二、辩证看待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每个民族即使是人数很少的民族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和社会控制系统。现代社会中都实际存在着两种运行机制,一种是现代型的法理机制,一种是传统型的习惯机制。前者由国家或法律确认和维持,是一种带有“公”的性质的主导机制;后者是由乡土村落或民间来维持,是一种带有“私”的性质的补救型、自治型的机制。而习惯机制更多的是靠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长期形成的习惯来维持。②藏族习惯法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处理本民族内部政治、经济、宗教、民事、刑事纠纷时所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适用范围包括今西藏、四川西部、甘肃、青海及云南迪庆等藏族族群之中。藏族习惯法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而形成的社会各主体利益相互平衡和制约的结果。是体现社会利益并由社会力量保障实施的,调整人们之间一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藏族习惯法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内容的宗教性、体系的完整性、功能的社会性和适用的地域性。具体表现为:
首先,从内容上看,体现了宗教性的特征。(1)藏族习惯法的主体或承载者是藏族人民,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宗教不仅指引着人们的思想,而且深刻的影响着藏族人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藏族先民面对高耸入云的雪山、广袤无垠的草原、寒冷缺氧的生存空间和瞬息万变的天气变化,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于是就开始了造神运动。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雷有雷神、每个村寨、各个部落,也都有各自的神灵。万物有灵为基础的苯教是公元8世纪之前藏族聚居区域唯一的宗教,而世间万物都依附着灵魂的观念深入到藏族人民灵魂深处,根深蒂固;(2)藏族习惯规则深刻的反映和暗含着藏传佛教的教义要求。佛教在与苯教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吸收了苯教的精髓,首先,佛教以“六道轮回”、“灵魂转世”和“放生”等形式来表现万物有灵;其次,“不杀生”是佛教中最主要的戒律之一;再次,“灵魂转世”观念是藏传佛教对万物有灵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杀人案件中并不坚持“杀人者死”的观念而形成了“杀人者赎”的习惯法观念。要求人们弃恶从善,杀人本身就是不好的事情,再把杀人者处死,就更不好了,是一种罪孽。③这是藏族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用“活着”的方式彰显着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渴望,对和平及和谐的向往的一种表现;(3)藏族习惯法则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更多的体现为以宗教为核心的宗教义务。比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训令:“从藏历正月初至七月底,寺庙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以外的动物,违者皆给不同惩罚。总之,凡是在水陆栖居的大小一切动物,禁止捕杀。……为了本人(达赖)的长寿和全体佛教众生的安乐,在上述期间,对是所有大小动物的生命,不得有丝毫伤害。”④可见,习惯规范是宗教义务的延伸和扩展。
其次,从功能上看,体现出社会性的特征。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其是比国家更早的一个法律概念。在“弱国家空间”的藏族族群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更显常态化,而与国家及国家机构的交往不是那么频繁,这就使得在社会经验的层面上形成人们所信守的宗教观念和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的藏族习惯法。它是一种“行动中的法”,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活法。内容包含政治、经济、宗教、刑事、民事等涉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诸多方面,是社会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为藏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谐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再次,从适用上看,体现了地域性特征。藏族习惯法适用于居住在今西藏、四川西部、甘青及等地的藏族族群当中,涉及人口约541万,根据方言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均属于高寒区域,自然条件恶劣,偏远而交通又不便。这种居住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藏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流的有限性,更甚者在藏族族群内部也是“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由此可见,藏族习惯法的适用有明确的地域限制。
国家制定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意志,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的总称。⑤其特征呈现出多面性和多层次性,国家主导性、国家意志性、利益性、阶级性、社会性、规范性、普适性、可诉性、义务性、权威性、程序性等不能同一囊括。但国家主导之下以国家意志体现出来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分配和确认格局,却是极其明了的,勾勒了“国家空间”中以国家机构为载体的权力运作和整体社会利益的走向“图式”。国家制定法产生其重要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将与其他社会主体制定的社会规范明确的区分开来,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水波纹”似的“国家空间”。在“国家空间”内,由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机构保障法的运作与实施,持续而有力国家强制力,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主体。也就是说,国家制定法有效的保障了民族国家独立与统一。国家制定法中的法律主体由公民、组织和国家构成,均体现为权利的承担者或义务的履行者,作为一种“理性人”而存在,拥有国家制定法中分配的利益或负担。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藏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属于同一系统内部的不同层次空间的行为规范。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在不同层次空间实现着各自的职能,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优势,可以相互勾连、吸收、借鉴。“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套引导和制约人们活动的规范,即规范系统,并以此来规定人们在地位与角色、权利与义务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⑩因而,打破偏见,辩证看待藏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在两者之间建立互动机制,是必要的。“社会控制是人们依社会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施加影响,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及和谐发展的手段和过程。”○11与藏族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宗教信仰丝丝相连、与民族习惯习俗相符合的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丰富和弥补了国家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应继续在藏区适用,实现藏区各方利益主体的平衡;另国家作为一方利益主体,应当在各方利益结构中寻求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鉴别藏族习惯法中合理成分,将其吸收到国家法。比如“赔命价”中对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权益的保护可以为《刑事诉讼法》中建构刑事公诉“四方构造”提供本土化资源,也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实践依据。因为应当明确:无论是藏族习惯法,还是国家制定法,在终极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幸福安康。
三、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建立法治中国的伟大构想,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任务,并用治理的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分别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的塑造。由此可见,系统层化空间在顶层设计中确实存在并表现的极为突出,这为藏族习惯法功能的发挥留有了很大的余地,让其在藏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其价值,也为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良性互动提供可能性。
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有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因为治理本身就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而不仅仅是国家一方主体。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穿透性是有限的,有时候根本影响不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习惯法的生命力顽强,它铭刻在人民的心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弱国家空间,它的运作空间和存在价值要比国家法大得多。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实现良性互动,需要制度创新,即在相互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和合作。正如苏力先生所说:“当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少数民族习惯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妥协与合作。”⑥作为国家法,首先应尊重藏族习惯法,历史的辩证的看待并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赋予运行有效的习惯法规范法律效力或是发掘藏族习惯法中的本土资源将其作为法源纳入立法,而不是单纯的对抗和打压。“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重要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人们经过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制度就会被规避、失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⑦因此,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互动和沟通就成了处理国家法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的合理途径。
(一)立法思维的多元化。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包括法在内的行为规范的多样性,国家立法思维应坚持多法源化,尤其是从本土资源中提炼规则和原则等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引进和移植外国制定法。中国的法学经过了两次断裂,第一次是“翻译法学”阻断了中国古代律学的传统延续,而第二次则是革命的“斗争法学”阻断了“翻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⑧直到十九大,才提出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未来构建一套“运用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的法学知识体系成为必然。因此,发现和挖掘行之有效的习惯法规则,吸收进法律是最恰当的选择。比如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苗例》中主张的对于杀人类的犯罪,不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的方式解决,而是“认为杀人本就是不好的事情,再把杀人者处死,就更不好了,是一種罪孽”这种朴素观念指导之下的“杀人者赎”,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体现了对人权,尤其是生命权的尊重。这与国际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废除死刑”的理念是一致的。又如刑事诉讼法中的“四方构造”。
(二)地方治理方式的多元。多样性和差别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实际面貌,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区域。“地方性知识式的放任式沟通与权威意识形态式的强控式沟通以及党派化政策式的劝教化沟通都有存在着明显的形成某一传统的霸权可能。”⑨在一个小的社会系统中,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力量的此消彼长是缓慢渐进的,只要能实现各方平衡,就是很稳定的社会结构。国家纯粹为了法治的统一性而忽视社会现实,就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我国民族众多且生活区域、方式、信仰和经济、文化发展不一,想让国家包办一切是不现实的。那么,藏族中“措哇”及其自治体系,鄂温克族中的尼莫尔及其他们的“毛哄达”,苗族辖区范围内的山官、头人、长老及“董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场域、特定的文化范畴内仍起着治理的作用。国家应该认可并赋予他们国家的权力,附势而治,逐步实现治理模式的多元化。
(三)法律实施方法的创新。藏族习惯法属私力救济的范畴,由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构成,而国家法律的实施,是公力救济,着重体现在诉讼和审判。但是藏族所在区域的地理特征和诉讼特点决定了国家公力救济的滞后性和无力感,因而,在国家法律实施方法上进行创新,及时、快捷、有效的解决纠纷,将藏族习惯法引入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制度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私力救济的结果,是可行的。
藏族习惯法“嵌入”国家制定法的历史进程是需要缓慢推进的,不能以一方的稳定为代价。国家制定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鉴别、引导、吸收藏族习惯法,另一方面藏区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藏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利益上的一致,从而更好地保障藏区地区的稳定有序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注释]
①杨平.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M].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12:228-229.
②田成有.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补与对接[J].现代法学,1996(2).
③苏永生.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J].法学研究,2007.6.
④中科院民研所《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文献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56).
⑤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7.
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1.
⑦同上.
⑧舒国滢.中国法学之问题——中国法律知识谱系的梳理[J].清华法学,2018(2).
⑨谢晖.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J].学习与探索,2000(1).
⑩金泽.宗教禁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9.
○11同上.
[参考文献]
[1]虎有泽.论民族工作法治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5.
[2]王勇.嵌入在国家法之中的民间法[N].甘肃法制报,2016-9-18.
[3]李向玉.民族习惯法转型期的法治现代化——以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一起“鼓藏民约”司法个案为例[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1-13.
[4]牛绿花.谈谈藏族“赔命价”习惯法[N].西北师大报,第848期.
[5]苏永生.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J].法学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