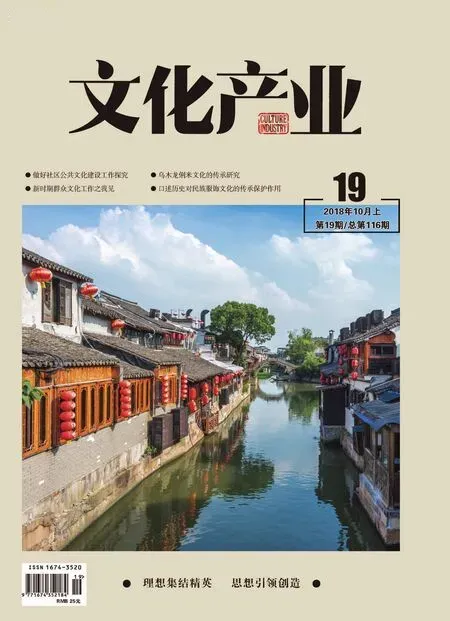浅谈《呐喊》角色之“相术”
◎肖雪媛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鲁迅在《呐喊》中写到的每一个角色,无论篇幅的多少、刻画的详略,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角色的存在不再只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而是成为了当时“混沌又躲避清醒”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衬托,即人物角色本身及其表现成了时代的背景,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神态外貌都暗自透露着世态炎凉、世风日下。鲁迅的高超之技便在此处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基本上不用大段的笔墨来对《呐喊》中的大小角色进行完整细致的描摹,而是采取白描手法随意又精准地勾勒出人物之形,以形读心,将面相之术融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中,当这样的艺术手法应用到《呐喊》中的人物甚至一掠而过的画面小人物时,其戳人心扉、启人深思的力量尤为强大。
一、中国相术
《说文解字》:“相,省视也。”本义即为仔细察视,而后延伸出人的相貌、面相之意。从它的意义发展中便可发现“相”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观察主体通过对观察客体外观的考察以分析及认识其内在实质。而“相”在中国古代也被发展为“相术”,这门神秘的术法其实就是一种原始意识活动,是把外部感官感觉内化为心理认识活动的神秘体验,并将这种体验上升至自然祸福和人生命运的探讨和预测。如此没有科学理性思辨的自我意识行为难免会被现代人归为迷信的范畴,但我们却不能否定“相术”中显现出的自身“正确合理”的“面相符号”,它用有限的外相分析来表达无限无形的天命概念,以相对的形式表达绝对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看相”对于分析人物的心性命理是有一定揭示作用的。
古之“相人”,乃根据人的容貌、气色这类“外相特征符号”来预知人的吉凶祸福,即使战国时期荀子曾言“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君子不道也”[1],相人之术也依旧深受世人追捧。而后“相人”从一般性的看相算命进入到写作领域,演化为对人的外貌描写,即作者通过观察形貌言行以求“知人”。但这类有着看相性质的外貌描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某些形貌与其心性、命运之间的特定关系,形成了某些明显的共性,才能够使读者看到其外貌描写便对这个人有了与作者相通的判断,比如《左传》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豺声”,宣公四年楚国子文说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国语·晋语八》中叔向之母说杨食我“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此时“豺声”这一人物的声音性状就成为人们公认的“恶人”之标志。
二、《呐喊》中的“相术”
鲁迅在《呐喊》里对人物的描写,也常采用“看相式”的白描手法。对于此技巧,他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己。”又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2]不过多着笔,因此一笔就得点睛,毕竟观察主体也大致只记得观察客体的最突出特点吧。
在《故乡》中,鲁迅为曾经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看相——“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3]这段简略的形象描写中真正算的上是看相内容的只有“凸颧骨、薄嘴唇”,在面相学中,颧骨高耸的女人性格过阳,善于专断独行、权谋霸道,而嘴唇薄扁的女性则是很有个性、聪明有主张,但是心眼小、过于算计,由于天生的薄嘴唇方便说话,因此这类女人非常伶牙俐齿,但是缺少一些人情味儿。鲁迅在描写杨二嫂的外貌时,只狠狠抓住这两个面相特征,总共也就六个字,但这两个面相符号背后却隐藏了太多对杨二嫂的个性分析,而鲁迅并未像相术大师一样为读者一一指明,仅是通过最真实、客观理性的面相观察提供了杨二嫂简单却精准的面相特征,至于得出怎样的面相分析结果则由读者自行判断。不过刚才已经提到在中国相术里,面相符号所对应的人物个性特征都是社会共识的结果,所以杨二嫂“凸颧骨”与“薄嘴唇”只需有印证材料即可,好在鲁迅在文中好几处地方都为读者提供了佐证依据:第一,杨二嫂一出场便用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泼辣尖锐之气顿时暴露无遗,在与迅哥儿的寒暄唠叨中也是尖酸刻薄、毫不留情,好说些逼人墙角又令人无从反驳的话。第二,杨二嫂一板一眼的“要木器”,毫不做作的“偷手套”,恶人先告状“在灰堆里埋碗碟给别人栽赃”,毫不迟疑地飞快“拿狗气杀”,这类可耻的“偷鸡摸狗”之事被杨二嫂一做倒成了有理有据的正义之举了,隐隐中其自私霸道、爱占小便宜的本质属性被揭露得十分深刻,这些举证都印证出鲁迅所相的“凸颧骨”与“薄嘴唇”的准确性,使杨二嫂小市民形象的庸俗嘴脸和恶劣习气一览无遗。但鲁迅在文中也提到一个问题,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杨二嫂并非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么在鲁迅离开故乡的这几十年,杨二嫂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看到了她两种鲜明的面相对比,感受到了她截然不同的性格变化,不过从一位年轻美丽的豆腐西施变为如今势利虚假、尖嘴利舌的中年大妈与其谋生的环境也应是密切相关的,我猜想这段鲁迅空缺的时间于杨二嫂而言大致也是人生的难多于生命的喜罢。
在《呐喊》中前后有着明显面相变化的角色除了杨二嫂,那就当属鲁迅儿时的玩伴闰土了。先来看孩童时期的少年闰土的面相——“紫色的圆脸”。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紫色和赤色一样都是五行中“火”的代表颜色,代表着好运、健康、富贵,所以才有成语“大红大紫”“紫气东来”。而“圆脸”自然暗含着圆润、有福气的意思。所以从面相上来看,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说明当时的他积极有活力、健康、饱满。但如此有福气之面相也未能逃脱苦难岁月的摧残,终究还是变成了苍老、毫无神韵的相容——“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面色呈灰黄色则属气重有滞,气重有滞的人大多形容愁楚,似愁似苦,举止无力,言语声微,凡滞由营养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因素所致。这样看来,闰土真正的面相变化主要在脸的颜色上,与之相应的他的性格也有了更变,从健康积极、天真烂漫的英俊少年变成了迟钝、麻木、无言的中年,而促使这一变化的缘由也应和杨二嫂一样,即消极地在生活中被扭曲、被毁灭、被改变,其个性棱角被苦难的生活渐渐消磨成圆角,没了愿景也没了希望,只可恭敬地喊出“老爷”了。由于小说容量有限,故事中角色的前后时间差又太大,很难在有限的作品空间中展示人物的精神、命运的历程,而鲁迅却采用了“看相式”的人物描写来刻画出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在前后对照中完成,以简练的语言塑造出有特点的人物形象。
三、结语
“有心无相相由心生,有相无心相由心灭”,实际上一个人的本心才是其性格命运改变的溯源之所。相术即心术,心性虽难以穷尽,相容却可侧面揭露。鲁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便是采用简要精炼的“看相式”描写,讲出人物故事背后无尽的岁月经历,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寓真实性于概括之中,置主观评价与客观描写之中,短短几言而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