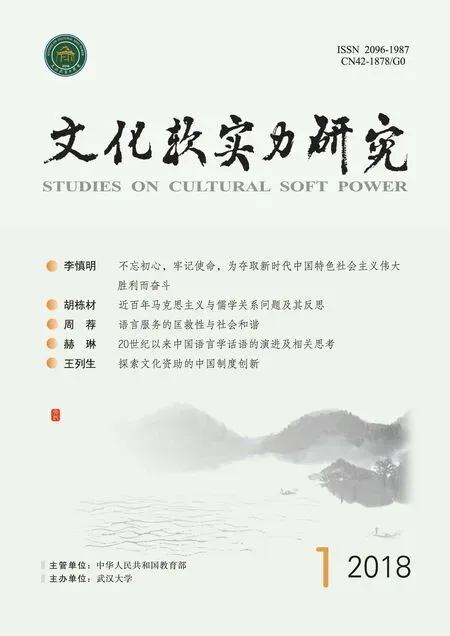探索文化资助的中国制度创新
——评《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
王列生
无论在艺术史长河中,还是在公共文化政策领域中,“文化资助”只是一个很小的知识节点。但通过这一节点,可以连通公共文化政策、艺术史研究领域诸多重要的知识范畴,如文化公共性问题、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价值转换、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等。黄玉蓉博士的新著《被资助的文化:中外文化资助体系及制度设计》力求通过对上述与“文化资助”有密切关联的理论命题的探讨,创造性地将知识界的最新理论建树和中国文化建设领域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导入公共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力求探索文化资助的中国制度创新,是对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的拓展和推进。该研究力求把“文化资助”及其重要构成范畴“艺术资助”以及相关命题的已然事态、或然事态抑或必然事态澄明出究竟来。以此为基础,再基于不同的问题境况、利益立场和逻辑思路,找出有效的现场解困方案与可选择的理想标杆。
一
既然黄玉蓉博士自觉而且前置性地引用爱德华·泰勒有关文化概念作为意义本体的人类学定位,即所谓“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那么在笔者看来,她就已经拥有了正确而且清晰的逻辑起点,并以此为知识驱动杠杆,促使其进入关联性事态现场以及不同国家以此为资助对象的种种关联性政策处置义项编序。
对象的清晰问题之所以在此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对象的本体性分存与现象态混杂总是纠缠不清,那些已然自明者又因其自明而常常作具体言说前置限定的省略,就仿佛日常不经意间省略陈述方式所呈现的诸如“文化资助”“艺术资助”,或者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研究者们灌输的所谓“文化消费”“艺术消费”。不清晰者的纠缠不清与清晰者的自明性省略,自觉不自觉地合力生成所议知识场域的任意表达,并在言说伦理合法性对知识准入合法性的无条件置换后,导致许多大词叙事文本或者个案描述文本,在迷失逻辑起点的同时,也让进入对象讨论的相当数量涉身者,不得不于五里雾中被抛至“命题真值率丢失”的言说狂欢甚或符号骚乱。正因为如此,忧心忡忡的文化政策研究专家们才会认为“如何使文化政策研究得以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Jim McGuigan:Cultural Policy Studies,in Justin Lewis and Toby Miller(eds):Critical Cultural Policy Studies: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3,Oxford,p.23.是头等麻烦的场域困境。
头等麻烦之处在于“意义”和“意义物化承载”的本体大相径庭与现象杂然一体,在于从“意义物”求取“意义”既有复杂的转换过程,又有一系列可转换的条件。“文化”或者“艺术”,哪怕是广场大妈在最原始的价值层面,意欲捕获的一点点精神寄托或审美净化,那都是“意义本体”,是个体存身或在世确证其人性此在价值的意义本体,更何况那些委身于文化创建与艺术创造的精神使者,居然会是“视自身为祈祷者。他们声称要呈现审美理念,探究存在的秘密与灵魂的深奥”*Sandro Bocola:The Art of Modernism :Art,Culture,and Society from Goya to the Present Day,Prestel Verlag,1999,London,p.97.。就中国知识史而言,凡所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又或者“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皆莫不是立论于意义本体和精神本体。
但任何一种意义本体和精神本体,都在其本体生成过程中经由显形和现世的出场通道,而且这一通道远非俗常泛论的所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所谓“物化承载”,既包括意义和精神创造者的存身境遇,也包括意义和精神展现的机遇和条件;既包括传统范畴的物化符号介质,也包括当代高科技背景下的技术支撑形态;既包括传播渠道的影响面,也包括资金保障的助推力,总之涉及外在前置条件的方方面面。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文化资助”或者“艺术资助”,其资助的驱动所及与影响有效性预期就在于此,而保障性、激活性、助推性的种种制度安排,以及与这些安排相适应的既丰富又具针对性的诸多政策工具与平台工具,则是不同预期得以落地并赋予其行政刚性的技术方案。当然,在资助预期与意义生成或者精神创造之间,并不具有线性可测值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其中存在弹性可举证的间接因果关系的要素影响因子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广泛案例事实,而这就是资助预期及其制度安排、工具匹配成为各国例行做法之所在。
从黄博士的知识研究报告来看,尽管在知识逻辑梳理过程中还每有紊乱与缝隙,但她显然已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前置逻辑关系予以清晰性先行给定对于其后续学术作业的重要性,并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者某些自明性悬置某些关联性讨论中,由隐而显逐步延展其问题域与命题解决方案。笔者很肯定她的这一思考问题的逻辑思路,亦如略嫌她在路上不时有自乱阵脚之不足。
二
如果我们把此议的纠缠在一种自明性拟设中暂时予以悬置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跟进的照面事态直接就是:(1)谁来资助;(2)资助给谁以及资助给哪些应该资助的对象;(3)以何种方式或何种比例额度进行资助;(4)所有这一切的法律授权或者法治化执行保障。
谁来资助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或者不同资助模式之间差异甚大。有的模式主要由中央政府对相关文化事业支出给予预算拨付,例如法国个案中的“跨财政年度拨款法预计在5年内(1978—1982年)编列1407000法郎的预算,以保护历史遗迹为考量,优先修复重整国立博物馆。就工程计划来看,卢浮宫整建计划占此编列预算的30%,凡尔赛宫则占21.9%,其他经费则作用在枫丹白露宫、康比埃纽市、波城(Pau)、艾辜昂(Ecouen)、圣哲尔曼和玛拉梅庄(Malmaison)的建筑工程和改善博物馆设备”*杰郝德·莫立耶:《法国文化政策:从法国大革命至今的文化艺术机制》,陈丽如译,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01页。。有的模式则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预算框架下,按照事权支出原则确立受资助文化承载条件的依法授权资助主体,诸如联邦制国家治理架构的美国,其中央政府预算资助与地方政府预算资助就呈现出十分清晰的资助主体间性,所以也就既有联邦层级所谓“尽管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乃是联邦艺术资助的旗舰,但联邦政府的文化项目处于碎化状态,分置在一系列不同的行政专门机构,由不同的议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监管”*Margret Jane Wyszomirski and Kevin V. Mulcahy:The Organization of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in :Kevin V. Mulcahy and Margret Jane Wyszomirski(eds):America’s Commitment to Culture:Government and the Arts,Westview Press,Inc.,1995,Oxford,p.124.,也有地方政府层级市政当局的诸如“迈阿密的戴德县及其负责工程项目的公共事务议员,会承担提供建筑设计费用85%的责任,以及35%的运行预算支出……并支付其后所有的债务”*Joanna Woronkowicz,D.CarrollJoynes,and Norman M. Bradburn:Building Better Arts Facilities:Lessons from a U.S. National Study,Routledge,2015,New York,p.71.。还有模式甚至具有超越主权国家预算的跨国资助功能,譬如欧盟框架下乐透彩票的文化支出总量份额比例和国家间按预算财年按动态分摊方案进行资助的特有机制,以及更具跨主权预算体制性文化资助的所谓“文化政策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in Cultural Policy),使欧盟框架资金的资助能力成为“存在于欧盟的跨国以及政府整合功能的体制化了的欧洲化资助制度”*Patricia Dewey:Power in European Union Cultural Policy,in J.P.Singh(ed):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and Power,Palgrave Macmillan,2010,London,p.123.。这种非穷尽性个案举证本身就已表明,文化资助主体的制度安排模式因国情不同而各自有所选择,后发制度建构国家甚至会在自身价值目标支配下,从这些异质性制度安排模式进行功能链接最大化的随机选择,由此形成梯次配置的协同创新制度建构。
与此不同的是,任何一种谁来资助的文化资助主体存在模式,都会存在资助给谁以及资助给哪些政策匹配工具和平台运行工具的问题。这意味着杂乱纷呈的事态表象后面,其问题隐存的必然性乃是一致的。其事远不止于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专家所学理参悟到的所谓“如同文化语域中如此多的术语一样,‘体制调节’具有各种不同的语境性的意旨”*Jim Mcguigan: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4,Berkshine,p.17.,而更在于到目前为止这些学者何以不能参悟透彻诸如“所获得通过的国家剧院的职责,是要按照民主治理的原则来进行,同样的东西要满足对艺术进行资助的其他形式。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议会内,多年无休止争论的很表象的议题,就在于花政府资源以支持艺术和文化是否无条件的。尤其在于,涌现出来的那些农民政党与那些工人阶级政党,在艺术领域的责任承诺针锋相对”*Jorn Langsted:Strategies in Cultural Policy,in Jorn Langsted(ed):Strategies:Studies in Modern Cultural Policy,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00,Aarhus,p.12.。至于在美国,参悟中的此类针尖麦芒,则更体现为究竟是资助极度个体性精神自恋的“精英少数”还是追求日常参与最大化的“大众多数”,典型的针尖麦芒当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曾经历过的彷徨,也就是“任何正在从事的公共政策其固有的内在问题在于,谁才是资助的应该接受者以及将要采取何种资助形式”*Kevin V.Mulcahy:The Nea and the Reauthorization Process and Arts Policy Issues,in Kevin V.Mulcahy and Margaret Jane Wyszomirski(eds):America’s Commitment to Culture:Government and the Arts,Westview Press,Inc.,1995,Oxford,p.176.。之所以此类问题在不同时空位置都成其为问题,根源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资助主体而言,由于人与文化基本关系的价值分层,决定了处在不同价值诉求层级的资助主体,必然会根据当时诉求主旨重心来选择其资助倾向,并由此导致异质性选择倾向之间的意愿紧张甚至行为资助冲突,陈述为学术话语就会有所谓“臂长原理在西欧国家中,乃是最一般的公共政策法则,适用于极为广泛的体制化公共事务。该原理基于‘审察与平衡’的一般体制,并被认为在弹性民主中规避不合理的权力集中与利益冲突很有必要”*Harry Hillman-Chartrand and Claire McCaughey: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the Art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Milton C.Cummings JR. and Mark Davidson Schuster(eds):Who’s to Pay for the Arts: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for Models of Support,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Arts,1989,New York,p.71.。另一方面就资助对象而言,受助方存在于不同地缘文化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所进行的不同文化活动内容,必然导致所有这一切都会处于“治理分类”的预设资助方案,继而其所需要获得的额度、拨款周期、绩效激励标准与运行基本保障水平等,往往就会在分类治理过程中给予更加缜密的政策方案配置才能确保资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使在同一个剧院进行不同演出机构的不同艺术种类轮演,也很难按划一的资助标准来给予政策处置。而同轮演出过程中有商业演出介入其中时,无论演出方的机构属性如何,都无法在法定范围内使该机构成为此次演出活动的资助对象。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仅好莱坞电影工厂不能成为文化资助对象,而且即使像长期从事公益文化活动的博物馆,当它插入式进行大型时尚品展示与视觉消费推动行为,其平台机构、参与主体以及具体文化活动等,就都会排除在资助对象之外,哪怕它是“改变旧模式的新经济形态,并被纳入文化工艺产品的文化创意”*Dave O’Brien:Cultural Policy:Management,Value and Modern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Routledge,2014,OX,p.51.,也应该由非资助性的另外一些文化政策制度安排来给予支撑抑或激励。笔者在这里只不过粗线条地给予事态描述,而在黄玉蓉博士的知识性研究文本里会有更加复杂的问题脉络梳理。当然,至少就笔者有限的涉猎范围而言,此议所引起的事态后果与处置方式,世界各国政府已然面对和将要面对的,其复杂性、纠缠性和经验多样性,较之黄玉蓉博士所关注的还要多得多。
此外,所谓现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个中要义之一,就是使所有的制度设计、工具匹配以及功能运行都处在法治的框架之内。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制度形态以及功能运行给予资助,对政策工具与平台工具的功能运行给予资助,对意义物化承载的所有形而下条件给予资助,以期在活动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升华至意义本体,以期在类的特殊活动中更有效地在不同时空位置支撑和建构类主体性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以期通过积极的文化活动在更广泛的场域效应中凝聚社区共同体、社会交往共同体、民族传承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所有的“给予”和“以期”对各国政府和各层级政府而言,无论选择的制度性文化治理框架以及匹配的政策工具与平台工具究竟有多少同质性和异质性,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没有转化为刚性的法治化责任限定,就都难以确保其必然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各国的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专家们愈来愈趋于某种认知一致性,那就是所有多样性文化治理的行政方案,尤其是本书所具体讨论的“文化资助”或其中的“艺术资助”,其模式、过程、手段、权责、绩效和监管等,都必须获得合法化同时也强制化的法律授权形式。黄玉蓉博士的研究文本中涉及一些,有些则还没有涉及,但这不要紧,关键是一旦有了这一意识惯性,就会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过程中,将文化治理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资助活动及其关联性的方方面面,都能放在法治化的现代社会价值之维上来予以谋划和应对,而这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助推着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也就包括文化资助有效性与积极性的实际提升。对此,财政专家声称由此才“使预算更加阳光透明并确保支出平衡”*Katherrine Willoughby:Reaching and Maintaining Structural Balance:Leaders in the States,in Sally Wallace(ed):State and Local Fiscal Policy:Thinking Outside the Box?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0,Massachusetts,p.182.,而过去我们却常常忽略文化预算与文化资助的具体方法,只是空洞地埋怨投入不足或资助不力。
三
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就是说,在讨论文化资助问题时,我们要统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按照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规律和外在条件要求,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五位一体”战略下文化治理过程中的文化资助,从制度设计到工具匹配,从运行有效到保障有力,都必须面临新问题、迎接新形势、设计新方案、满足新要求,如此等等。与此相一致的价值诉求就是,必须立足中国问题境况、立足中国利益立场、立足中国治理方案、立足中国探索经验。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黄玉蓉博士的知识研究文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以此为其研究行为的逻辑起点,由此而在国外知识参照与经验吸附中致力于中国文化资助制度的建构,尽管这种努力还较多地停留在笼统而且粗线条的宏观构思阶段,尚未进入精准资助政策方案并清晰呈现出关联问题与无缝隙功能链接间的逻辑关系和义项编序。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客观地承认,无论理论成果层面还是实践操作效应层面,至少在文化资助这个问题上,我们较之先行现代文化治理国家还有一段时差和某种技术落差。清醒意识和客观承认本身,实际上就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现场体现与当代体现方式,是一种正在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时代以历史加速度大踏步走来的坦然姿态。所以,黄玉蓉博士的知识研究文本,用了不少的篇幅对域外状况进行知识地图式的分类叙事,既十分必要也很有背景知识积累成果,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姿态,为中国文化资助制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完善,捕获了必不可失的知识资源与实证参照。读了黄玉蓉博士的知识研究文本后,我想到了如下两个引申性的所议的中国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垂直社会结构中,文化权利与文化资源基本上被封建贵族与文化特权者所把持。早在20世纪初,毛泽东同志就有过总体性判断,认为文化的不民主是导致封建社会更加灾难深重的内在根源。从延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草根社会与人民大众的文化解放上,只可惜那时资源、条件和可推进范围都很有限。1949年后,文盲率持续不断地降低,从1952年起就在全国设立乡镇文化站这一制度安排本身不难看出,对人民大众的文化资助,一直是我们想要努力去办但始终没有办好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进入新时代以后,这一想办却未完全办好的事情就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尽快办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努力实现文化制度重心下沉,文化资源向社区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倾斜,文化政策工具与平台工具的日常运行要和社会的文化最大公约数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实现文化建设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并有效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文化生活领域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所有这一切,具体落实到黄玉蓉博士此时所重点讨论的中国文化资助问题,其实就是要在全面社会进步背景下,如何解决基于中国事态现场的“资助结构”问题。显然,资助结构的力学指向——人民大众和最大公约数诉求是无须讨论的,至此已获得学理与法理的自明。因而此议所纠缠的问题实质上在于,不是由此就放弃对精英少数及其所从事文化活动的更高条件要求与更专业的政策工具配置和平台工具配置,而是我们在文化资助制度设计上必须有至少两大基本预设规避功能:其一是规避少数精英因资助而更加远离“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自我中心主义地凌驾于人民之上后完成其“摇钱树”和“摇头丸”的利益最大化身份塑造,就像我们资助其离开生活后又不得不资助其尽可能地“深入生活”“贴近生活”;其二是在特殊资助过程中成为失去文化创造活力的利益固化精英集团,并且在“圈子文化”狂欢中垂直性地将负能量文化影响进行加速度态势的社会抛洒,就像那些不健康的“极端追星效应”或“极值平尺主义”所带来的良性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秩序解构。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近5年来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获得“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的突出经济转型成就,国家文化投入同步性地保持了高投入的递进态势,不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飞速发展,而且各类文化活动的运行经费基本上做到了保障有力。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资助力度已经不是编序靠前的遭遇性文化建设问题。但问题是,文化支出并未完全像其他支出口径一样,尽可能做到减少项目审批支出方式而代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经常性安排。其结果就是文化资助的层级行政审批持有与分发式配置,文化活动机构、文化活动平台和基层文化活动大众由此也就无法使自己的应有资助诉求与层级文化行政项目的“审批”与“分发”之间产生积极资助助推后果的“对位效应”。总体而言,中国文化资助虽然有所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式资助”阶段,离“精准性资助”还有比较大的文化体制功能落差,所以资助效率相对较低,而这显然与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严重不相适应。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与前面的“资助结构”问题凸显一样,在这里则是“资助方式”的问题聚焦。黄玉蓉博士的知识研究文本中,不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也努力设计更精细的技术方案来化解其中的隐存矛盾。但其乏力之处在于,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不解决,任何精细的资助技术方案,其效力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功能失灵。原因就在于,各层级文化行政权力拥有者,之所以不愿意在中央“放管服”的改革大潮下放弃“审批文化”“分发资源”“配置资助”等权力,就在于还有程度不同的“权力感”和“权力寻租”小九九在作怪,所以要想完全解决问题,必须有待“新时代”的雷霆万钧之力,真正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体制改革的革命性进展。
笔者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迅速推进下,公平有效的文化资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