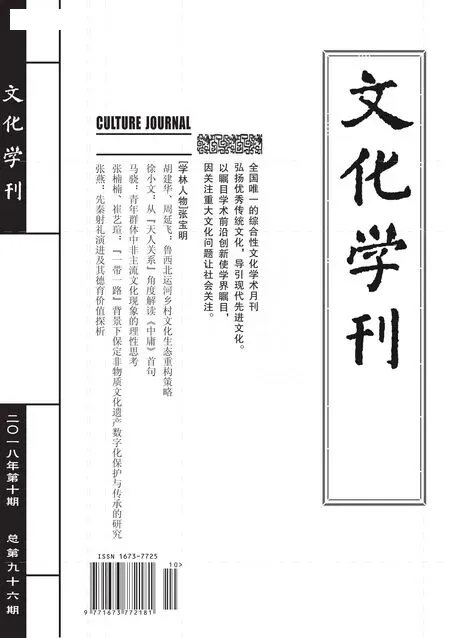人文:只有底线,没有上线
——由民国八年“厚载门学案”想到的
张宝明
一、从当下到历史:惊人的相似?
今年10月,因一系列学案倒逼在案头,便不得不将惯于长夜的写作搁置一边。学校相关部门也跟着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应对这些棘手的“学”与“校”之关系:本着教育部第41号令的人文情怀,一个关于艺术学院替考女生是否“开除”的边界问题可谓一波三折。然而,由此引来的诸多思考总是让我割舍不下:巧合的是,时值本人正在着手一项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课题研究,于是当下与历史的勾连让我更多地想到了民国八年的北京大学那场学案。那一年3月,北大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一是解除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职位,另一个是开除了法科政治门学生张厚载。两者地点、时间一样,唯独一个是在“3月26日”夜间悄悄进行,另一个则是在“3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以“本校布告”的形式公之于众。尽管涉及的当事人在时间、地点上没有什么差异,处理的方式也是一个基调,但在目的上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要息事宁人,另一个则是要杀一儆百。
这里,我们暂且撇开前者,说说一个感同身受的“厚载门事件”(离本人寓所不远处有一条路叫厚载门街,为了便于表述便取巧引用过来)吧:“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本校布告(一)》,《北京大学日刊》第346号,1919年3月31日,第一版)这则发布在《北京大学日刊》第346号头版左下角的“本校布告”对张厚载本人而言算是摊上大事了。想当年,事件发生后就不断发酵、围观。看今朝,对这一“厚载门”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譬如,有人以“北大开除张厚载真与胡适无关吗”吸人眼球,有人以“胡适把持下的北大无视民主迫害无辜?”先声夺人,也有人以“五四领袖们为自由做了什么?”引人围观,还有人以“自由主义的污点”为张氏张目,更有人甚至将蔡元培捆绑在一起作为审判的对象,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质问怀疑。
针对这些网上的声音,邵建曾以《87年前那场师生恩怨——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为题为胡适“辩诬”。他的“矛”针对的是“真名网”上吴洪森前后两文的观点:前文说,“读了《京剧丛谈百年录》,我才知道,五四时期,有位北大学生名叫张厚载的,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除了。这时离张厚载毕业只差两个月。”后文曰:“胡适也有污点。胡适乱骂中国京剧,说是腐朽文化的代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胡适他们居然将张厚载开除,这时离张厚载毕业还有一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大校园立块碑,记载这件事情。警戒后来者以此为耻。”“胡适与开除学生有关?”邵建直奔主题。他根据《京剧丛谈百年录》的一段关于张厚载的注释以及周作人晚年的一段回忆断定:“根据以上两条,我们知道,张的被开除,与他在《新青年》发表反对文章无关,更与胡适无关。吴文所谓‘胡适他们’,至少是对胡适不负责任。我这里不妨是为胡适‘辩诬’。如果我们读过胡适和钱玄同有关张厚载的通信,如果我们再对胡适的生平哪怕有个大概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邵建:《87年前那场师生恩怨——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新京报》2006年5月8日)
这就是“厚载门事件”旧事重提的原委。
不言而喻,邵建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人文的严肃性,出发点是真诚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用“胡适的生平”与“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挡箭牌或说杀手锏,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不但没有能给胡适“辩诬”,反而有污化胡适的嫌疑。以下便是笔者对这一笔墨官司提供的一点证词。
二、从公案到私案:谁来负责?
翻阅张氏履历表一目了然:张厚载,字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号采人,原籍江苏青浦(现属上海)。1895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张仁寿为京官。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之前,曾在五城中学(堂)与林纾有师生关系。1917年起,张豂子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与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北大教授就京剧存废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期间,兼任多家小报“记者”,以小道消息、独家秘闻为兼职写手,多涉北大内幕。1919年3月毕业前两个月遭北大勒令退学。北大肄业后,在天津做过一段戏评自由撰稿人。1928年入职交通银行天津分行,1936年调交行上海总部。1949年因病退休。
本来,“厚载门事件”只是一桩对违规学生处理的公案,但是由于“历史”的——诸如小道消息、私家报道以及公开争论等——原因,“公仇”很容易演变成“私恨”。还是让我们从张厚载病退之后说起。那时,上海有一张小报叫《亦报》,周作人等名家在上面连载过不少忆旧文章,张厚载以“票友”的身份也在那里谈艺说戏,由此我们可知道当事人的一些愤愤不平的心态。张厚载被开除的时间离其拨苏正冠之日不到三个月,因此这一事件本身对这位北大高材生来说的确是一件遗恨终身的事情。1951年3月15日《亦报》上署名“苍生”的作者曾这样追忆说:“北大学生张厚载根据这一点,写信指出胡老师的错误。胡老师却强辩……,后来刘半农、钱玄同等又纷纷起而答辩,……很缺少接受批评的雅量。这个特征,表现在《新青年》右派诸人的身上最为强烈。打开《新青年》通信栏的文字来看,关于各种问题向他们提意见的人很多,却从来不见有他们认错的表示。第一个是钱玄同,往往用很不恭敬的句法把对方臭骂一通。”对照当事人晚年的记忆,事情的“来龙”并不复杂:“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这个话本来不错,毛病却出在他自己在‘俗剧’下又加注一句:‘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之京调高腔皆是也。’高腔即弋阳腔,它的命运和昆曲一样,早被所谓‘俗剧’给打跑了,从来没有高腔起而代替昆曲的事。”正是根据“这一点”,有了胡适及其同仁的回应:“‘我所说的高腔,是指四川的高腔,不是指弋阳腔的高腔’。后来刘半农、钱玄同等又纷起而答辩,硬说‘京剧完全废唱而归于说白’,是可能的。这些都证明他们对于京戏的认识其实都很有限,而要强不知以为知,……”(余苍:《<新青年>谈屑》,《亦报》1951年3月15日。参见张豂子:《歌舞春秋》,广益书局1951年版,第133页)从“强辩”到“硬说”再到“有限”,这些一面之词情绪满满。至于其中的原委曲折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
这样一个争论在《新青年》那里本来也不算什么,对提倡“真理愈辩愈明”的同仁来说,更不会因此你死我活起来。余苍曾这样转述当事人的“来信”中对“厚载门事件”之原委的追忆:“其时替北京报纸写剧评,最初还得到蔡孑民校长的称许,蔡先生找他去讲话,告诉他:大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校外活动。不过劝他要旷观域外,对欧美戏剧的源流和发展,也应作一研究。后来豂子为了投书《新青年》,指摘胡适谈剧的错误(属于常识的),同时他又在京报中,公开反对钱玄同的打击京剧论,(钱先生是主张无条件的毁灭京剧的,尤其反对京剧中的许多丑恶形象,至斥脸谱为粪谱)因之颇为胡钱几位老师所不喜,这已经种了他后日被开革的根。林畏庐的《妖梦》公案,不过是爆发的借题而已。”这段“立此存照”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佐证:一是张厚载的剧评角色是校外兼职,或说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践。这也是蔡校长对其“称许”的原因。二是蔡校长提醒他不要局限于传统戏剧,而要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对中西戏剧进行比较研究。三是胡适、钱玄同等老师有“常识”性的“错误”,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以当事人的旧戏素养来看,不但有发言权,而且对北大教授们“过激”、极端化的做派之“指摘”也可以说不无道理。但是,那第四点则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将戏剧改良的争论与自己被“开革”绑架在一起,叙述成“根”由、因“果”关系,而且把林纾“公案”说成是“爆发的借题”。这就不符合历史现场的原发情形了。当事人的说法很明显搅了混水。
这样的搅混水,显然是为了避重就轻——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于是,下文的对“仅差两个多月即毕业”之“心有未甘”的写照,就有着耿耿于怀的叫屈成分:“找蔡校长,校长推之评议会,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即又推之校长。本班全体同学替他请愿,不行,甚至于教育总长傅沅叔替他写信,也不行。他因为校中挂牌开革,理由是‘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特请他所担任通讯的《新申报》出为辩白,列举所作的通讯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足以构成‘破坏校誉’之罪,结果仍然不能免除处分。蔡校长给了他一纸成绩证明书,叫他去天津北洋大学转学,仍可在本学期毕业,他却心灰意懒,即此辍学了。”(余苍:《节录张豂子来信》,《亦报》1951年4月15日。参见张豂子:《歌舞春秋》,广益书局1951年版,第138-139页)细读张豂子的“来信”,有两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情绪上的心灰意冷;二是上蹿下跳的“找人”折腾。不难想象,一个即将修成正果的本科学士,却在离毕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被“临门一脚”踢出校门,自然不免悲从中来、寒蝉凄切;也可以理解,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大大小小的“求爷告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上至教育部长这样的头号人物,下至同班同学的“众势”都不了了之。张厚载如同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在蔡校长和胡主任之间滚来滚去。最后,将自己兼职的舆论媒体《新申报》拿来救援也无济于事,那蔡校长的“一纸证明”变成了学生的满把辛酸泪,这彻底佐证了他的崩溃和失败。
对于这个记载,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当事人记忆的“裂缝”:北大当年“开革”的理由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而非夫子自道的“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与戏剧改良争论的一字不差相比,张豂子在“开革”原由问题上每每要么言不尽意、要么语焉不详,比葫芦也画不成瓢。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蔡校长给他一个“证明”,而作为“评议会负责人”的胡适却拒绝帮助。进一步说来,以当时的教授治校的大学章程来看,胡适是理所当然的掌握处理学生生杀予夺大权的“主任”。胡主任这时的寸步不让、毫不退却,与学理讨论时“低首下心”的“周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钱玄同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绕了一大圈,基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定论:针对开除张厚载这一处理决定,胡适应该负主要责任,即使他一度推给校长,也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罢了。
三、文人与人文:谁之正义?
有了担当责任的主体,我们就可以贴船下篙,到历史现场勘察一下“人证”和“物证”了。
说起张厚载的人生经历,不能不提到他与五四时期一个著名人物林纾的师生关系。这还要从他们共同与《新青年》同仁结下“梁子”开始说起:那是1918年上半年的事情。四卷三号的《新青年》之“双簧”,钱、刘哼哈二将一捧、一棒,不由分说将以林纾为代表的“学究”狠狠打下了三百“杀威棒”,接踵而来的四卷六号便是对其门生张厚载的共同“围剿”。于是,问题不断发酵、矛盾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了1919年那个多事之“春”新旧之间的激战:张厚载将当红恩师布局在“前锋”位置,自己则躲在后面作“后卫”。一前一后、一明一暗。林老师这把明晃晃的刀剑冲锋在前线,张同学这支暗箭躲在幕后专射新文化阵营里“冷不防”的要命部位。
先说经学生引荐的《新申报》。林老师在上面安营扎寨是从1919年2月4日开始算起。那“营帐”上打上了“蠡叟丛谈”四个大字,这就是林氏晚年自称的由来。一年多来,林老师一忍再忍,他已经被这批新文化的追随者给奚落、嘲弄得无地自容、斯文扫地。于是,2月17、18两天便有了短篇小说《荆生》的问世。就在老师抛出“伟丈夫”荆生的关口,学生在《神州日报》“半谷通信”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发布滋事生非的小道消息。这师徒二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配合可真够默契的,整整一周之后的2月26日,“半谷”即“豂”(子)的一半就成了“半仙”:“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这一“风说”透露的远不止这些“风声”,还包括诸如陶履恭、胡适、刘半农也“拟令一律辞职”的“风言”,以及有关当局对于“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的“失察”等等。最后这一来自“北京特约通信”的品牌代言人以非常自信的口气爆料:“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颇闻陈独秀将卸文科学长之说最为可靠。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讨论大学改组问题,欲请某科某门改为某系,如是即可以不用学长。此种讨论亦必与陈学长辞职之说大有关系,可断言也。”(《学海要闻》(半谷通信),《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所谓“东海”即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傅沅叔即傅增湘。记者把风言风语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说,关键在于一会儿是“果系属实”的疯传,一会儿是“可断言也”的定论;一会儿是北大出版物“十余种之多”的事实,一会儿是“某科”“某门”“某系”的某某之含糊其辞;一会儿是刘师培“组织《国故》杂志提倡绝学”,与《新青年》《新潮》的“绝异其趣”的情形再现,一会儿是“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的猜测推断。就这样,忽忽悠悠、颤颤巍巍的不确定性将北京朝内野外搅合得满城风雨。一时间,“半谷通信”中的陈谷子、烂芝麻看似家长里短,但这种暗枪冷箭式的“乱撂”很容易打乱新文化大本营的阵脚。
新文化派处于四面楚歌的重重围剿之中。其中张厚载这个来“萧墙”之内的后院“火种”点燃的还不止这一把火。继2月26日《神州日报》的神乎其神的煽风点火之后,他变本加厉地在“学海要闻”中再添“祸种”。3月3日的“半谷通信”以更加有料的口气来满足读者刨根问底的心理诉求:继“前次通信报告”之分解如下——“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闻已往天津,态度亦颇消极。大约文科学长一席在势必将易人。而陈独秀之即将卸职,已无疑义,不过时间迟早之问题。且并闻蔡校长之意,拟暑假后将文理两科合并,而法科则仍旧独立。彼时各科学长,自必有一番更动也。至胡适、陶履恭、刘半农三教授,则蔡校长以去就力争,教育部已均准其留任矣。”小道一旦改辙为大道,那“不确切”就有可能演变成“无疑义”的新闻报道。“小道”因川流不息的人来人往也容易拓展为大道,这与鲁迅所说的“地上本没有路”的道理没有什么两样。“学海要闻”可谓步步为营,有着一步一步逐渐坐实的韬略。可不,3月9日的小道消息大摇大摆地这就来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先声夺人。这几个用特大号字体印刷的打头文字显然是“标题党”精心炮制的。标题的“不由分说”来自于内容的一手资料和现场直播:“记者往访该校校长蔡孑民先生,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课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云云。”这可是面对面采访得来的“真金白银”,信不信由你!
应该说,张厚载这段报道在“时间”的催逼下予以了证实。只是这属于不便言说、发布的内部机密,你张厚载未经许可是不能随意散布、发表的。否则,那就是辜负了信任:在小的方面说,是侵犯了隐私权;往大的方面说,那就是泄露了“天机”。1919年4月1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一则《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的消息:“理科学长秦汾君因已被任为教育部司长,故辞去代理学长之职。适文科学长陈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校长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348号,1919年4月10日,第三版)不知事后蔡校长作何感想,面对自己的学生,尤其是他要“秀”出自己“记者”那一面时,作为“新闻发言人”,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或许是感觉到了这个春天的不寻常。1919年3月10日,胡适专门写信给《北京大学日刊》:“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愈传愈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28号,1919年3月10日,第四版)辟谣之时已经是谣言四起、越描越黑的格局了,《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如同两艘捆绑在一起的小船,飘摇在乌云滚滚、山雨欲来的风口浪尖上。
下雨偏逢屋漏,又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南北呼应。谣言、传言竟渐渐变成了“公言”。林纾在《新申报》上继《荆生》之后,又有更为露骨的新“骂”《妖梦》,在“蠡叟丛谈”中于3月19日起连续刊出。也许是巧合,就在此期间,林纾收到蔡元培的一封信,大致是说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请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炳麟、严复、林纾诸先生代为品题。对这一具有抬举意义的厚礼,林纾大为感动,一面催逼张厚载追回箭在弦上的《妖梦》,一面以友人身份开诚布公地致信蔡元培。在“往文”不可追的情形下,《致蔡鹤卿太史书》于1919年3月18日发表在北京《公言报》上。于是,才有了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捷足先登的《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林蔡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潮的激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林蔡握手之间,张厚载的被动可想而知。在撤稿无望、木已成舟之际,只好亲自吞下自己烹调的“苦肉计”了。他给蔡校长写信解释,但蔡校长表示:你的老师我可以理解,但作为学生的你却是一错再错。就在与答林琴南公开信同一天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蔡元培竟然一气之下单方面公开了张厚载的私人信函。从实说来,这次张豂子也算诚实,他在给蔡校长的信中不但承认“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的事实,还为自己未能追回的小说之“渎犯”请罪:“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恳请先生“大度包容”并回复。在他看来,这“实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在“学生张厚载拜启”之后,蔡老师不以“老师”对应,反而以“豂子兄鉴”开题,可谓意味深长。在蔡校长看来,你和林老师有“师生之谊”,那就应该“爱护”老师;你和北大有学缘关系,那就应该“爱护母校”;你和我既然是师生关系,那你就应该尽“爱护本师之心”。而你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一错再错:其一,对林老师这样一个有威望的人,你却将其“谩骂语”“轻薄语”以放任自流的形式流入社会;其二,既然你明知“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你却推波助澜,为谩骂、轻薄张目;其三,你一方面对林老师不负责任,也没有把“本师”放在眼里,他骂我蔡元培事小,问题是骂人者的失德、失颜比骂我更不划算。最后,当蔡校长以“往者不可追”深表遗憾时,也还是以“好自为之”勖告(《蔡校长复张豂子君书》,《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第六版)。
以“毁坏本校名誉”之名对张厚载“开革”,不是蔡校长单方面的意见,也不是胡主任一个人的主意。蔡校长“好好先生”的称谓不是说他是非不明、敌我不分,他的“兼容并包”建立在自由、民主之底线原则之上。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也并不是一味“容忍”、随便拿“自由”作代价。胡适一生反对“差不多先生”,他毕生守护着自由的防线、民主的基线,就此而言,胡适在原则性问题上不含糊、不苟且、不变通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正是对底线意识的呵护。他的“坚持”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留下了可资寻绎的最后线索。如果我们将此与1935年12月28日在他读完汤尔和日记后的“固守”相互印证,更见其坚守底线的“志气”:“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致汤尔和(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
胡适所说的“那一夜”就是在他看来改写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汤府晚间聚会。他将汤尔和的“力言”与张厚载的“流言”相提并论,充分显示出胡适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私德”和“公人”分属不同的范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不可混为一谈。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理清、澄清、厘清公私界限的思想史。否则,人类随时可能以种种“莫须有”的变相口实将自己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马克斯·韦伯曾将人类的事业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其实,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人文“底线”或者说是“志气”,那就是人文“志业”。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孔老先生已经给它命名了,那就是“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道”作为匹夫之志、作为为人的气节,于公于私,势不可挡。孔子在斯文扫地、走投无路之窘境中,每每不舍昼夜的“志(于)道”“守道”“布道”就是明证。
以上这些纷纭复杂的“公婆”之争,说到底都是文人之间的唇枪舌战。但是一旦将文人翻转成人文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文人可以是臭大街名词,可以是迂腐、酸细的冬烘先生的指代,而人文则不是大概、可能、也许的糊里糊涂、人皆可夫的“乡愿”代名词,更不是胡适所批评的“差不多先生”,固有的底线决定了始终如一的情怀和格局。
这也正是胡适意义之所在。如果要在北大校园立下纪念碑,座右纪念“厚载门事件”,那么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对象应该是胡适、蔡元培等一代思想先驱。对“厚载门事件”的受害者,倒应该镌刻下蔡校长那句话:“往者不可追”;而在胡适,为这一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第一大公案留下“立此存照”的界碑应该题下这样的界说:“人文:只有底线,没有上线。”因为从点点滴滴、细流涓涓的“小善”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里存在一个无限大的空间;而对人文的底线而言,爱恨就在一瞬间,稍稍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千夫指、万古恨。
(本文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