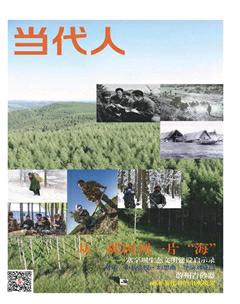古村画意
肖学文
水墨·暮归
拐过山嘴,一线水从头顶落下来,跌进脚下的山沟。起风了,那水不小心撞在突出的岩角上,溅起的水花,飞入石壁的绿苔间,倏然不见痕迹。由两条一丈长的青石架成的小石桥,安静地卧在溪上,时光,就像一个走惯了山路的老者,悠然地踱过石桥,一不小心,就走过了千年。路是极少有人踩过的,萧萧艾草,已你推我搡地挤到路上,只留一抹浅浅的白。在路的拐角处,三两面淡黑的屋顶,掩映在森森古木之间,若隐若现。
暮色就是从屋前那棵古老的白花玉兰树上泻下来的,有些风,那暮色便飘起来,细雨一般。只一滴,即在我的心上漫漫洇开,洇成一抹淡墨。
白花玉兰树早已过了花季,记得去年来时,一树的白,一树的香,把整个村子浸得迷糊而亢奋。而此时,一树的墨绿,将山坡上的泥房子都遮挡得高深莫测了。
一棵树的苍劲,不全在于它的高大粗壮,往往那树干上斑驳的苔皮,更能见岁月的风尘,而这树,似乎无关岁月,也无关风尘。三人合抱算不得最大的树,但缠绕在树干上的巨蟒般的常青藤,绝对是仅有的。那藤,比小蛮腰还粗,只轻轻一扭,便让人的心一紧,它恣意贴身而上,将每一根气根都扎进白花玉兰的皮肉里,就像一个尘世里的女子,将生命深入到了一个要托付终身的人身上。于是,她便毫无顾忌地伸枝展叶,将这树包裹在它的茎蔓间,也融入到它柔软的血脉里。这树,也便不再是一棵树,藤,也不再是一茎藤,而是一场持续了千年的生命或爱的合奏。
芭蕉在山间的屋前屋后,一点也没有古画里的孤高简远,萧散秀逸,它一蓬蓬地生长着,有的竟然高过了屋檐。这样的山间芭蕉,决然装点不了谁家的窗子,也成不了谁家的画屏,它只是放纵地生长在土地里的生命,就像那野性的村姑,或者是那庄户人家当得了家,撑得起门面的婆娘。
几株李,几株桃,不经意地立在晒场的石坳下,一点也不扭捏。那挨挨挤挤地栖在树丫上的果,压得枝头有些喘不过气来。从枝叶间露出的娃娃似的脸,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摸一下,掐一指,或者干脆纳入口中,品咂几回。
对面的山,虽隔了深壑,但那一壁竹影与松风,不是信手可以勾勒的,只有那些画家,屏住呼吸,尽情地泼洒,才能稍得气韵。远处,有晴岚渐起,将几笔嶙峋悄无声息地化去,化入暮霭轻染的空漾里。
归巢的鸟飞来,没入幢幢树影间,只闻啁啾,难见鸟影。而山涧里的瀑声,在鸟鸣中愈显遥远。偶尔一两声蛙鸣,更是让山色淡远得迷离而虚无了。
有鸡犬之声传来,炊烟独自从竹林那边升起。转过竹林,一间有些破败的明三暗五的老屋卧在林下,大门是敞开的,空落的堂屋里有些昏暗,正在火塘边做饭的青衣老娭驰见有人来,从堂屋出来,往外张望了一会,脸上有些兴奋,说:“后生家是不记得路了么?怎么转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
“老人家,我们是专程到这里来看山的呢!”
“唉,而今的后生伢也是怪得紧,村里的細伢崽都争着往山外出讨生计,你们城里伢崽却又跑到这山旮旯来看么子景。这破地方冷火秋烟,除了鬼和老不死的树精,就是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人,有么看头哟!”
“这山看不厌呢,去年春上到您家打住过一夜,您还记得啵?”
老娭驰眯起眼,说:“不记得。”
“今夜,想到您家打住一晚,行啵?”
老娭驰笑道:“屋里破旧了些,但还干净,你们只管住哟。”
白描·夜籁
清白的月,从山头爬上来,有些吃力。那如水的光,从树影间漏下来,簌簌索索,一地斑驳。
打坐于屋前晒场,一切声响,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天籁入耳,荡涤灵台脏腑。
蝉声夹着月光而来,渺远如梦。如梦般迷惘的,还有白果树上子规的怨怼,三言两语,就让人心生寒意。夜猫子守在树洞里,那叽叽咕咕的声音,如老巫念动的咒语,让天地之间的流光暗淡了不少。有山气从沟壑峰峦间弥散出来,山与山之间,便有了明显的距离,高低之间,反而模糊得错落无致了。
萤火虫飞过竹篱,不小心误入蛛网,它奋力振翅蹬腿,晃晃悠悠的丝网,在这个时辰也是一网的微露与月光,每一次挣扎,都有网丝嘣断如裂帕之声,每一次逃离的企图,都会引来黑蜘蛛嗜血的绞杀。而就在那篱笆下,草丛里,无数无名的小虫,正小心翼翼地窃窃私语,一切与山间有关的事物,都在它们的争吵中发酵,比如一场山雨何时来临,比如弱肉强食的搏杀。
丛林中,偶或有三两声麂子求偶的应答,随后便是孤狼的嗥叫,一切便在这一声凄厉中归于沉寂,连虫鸟的喧嚷也几近于无,除了山风过林,松涛低回。
老娭毑早已入梦,屋场里值夜的狗追着一只独行的兔跑过小路,不紧不慢的脚步惊得蛰伏于艾蒿间的鼠子吱吱乱窜,猫旋即踏着瓦片跳到檐下的桃树上,几个跳跃,便将那鼠子按到爪下。老娭驰突然咳嗽几声,骂道:“瘟猫,家事不管,野事瞎操心。”猫闻声,便怏怏松了前爪,跳到那搭着竹笕的山磡上,再一个轻跃,悄无声息地落在屋檐上,没入树影中。
泉水从那架在山砌上的竹笕里泻落石臼中,咚咚叮叮,清越如珠落玉盘,月光透过连珠的水滴,散出剔透清寒的微芒,而一入石臼,那一泓泠泠的水中,便映出一轮瑟瑟的月。泉水漫过石臼,白白的月光也漫过石臼,消失在芭蕉的影子里。芭蕉则轻扬了宽阔的叶,于微风中一晃一晃,千万个光影便翩然如轻快雀跃的舞步,恍若千万个精灵的月光舞鞋在凌乱地踢踏。有从竹笕中溅出的水珠偶尔蹦到芭蕉叶面,即刻裹着一身的晶莹从叶上滚落,再次跌入石臼,击起的回声,轻至若无,但又有如叩钟罄,鸣佩环,溯着光影入耳。
原来,月光是有声音的。
似有人声嘈杂,时远时近,循声而望,竹林那边的山坦上,月色如洗,若三两人影临风而立,眨眼间,又声影皆无。忽记起老娭驰的话,不禁浑身一颤。
山雨来时,是在枕上,恍然入梦间。
若有风吹窗,咯咯作响,瓦片落地,哗啦一下,啪地一声。白花玉兰树浑身的叶瑟瑟而鸣,白果树上千万把小扇齐齐地摆动,簌簌有声,接着便有千军万马踏响屋顶上的瓦面,千万粒珠子敲击窗前的蕉叶。endprint
有万兽奔腾入村,翻石倒树,哔剥乱响;有百溪流注入谷,夹枝带叶,哗啦有声。世间所有有形无形、有声无声的事物,都在顷刻间有了想要夺路而逃的迹象。
声响慢下来,轻下来,万籁皆渺然消隐于夜的黑,直至归寂。突然有敲门声急切而杂乱,门吱呀开了,有人声絮叨:“下屋麻爹只怕要享福了,没得人在可不行,快去守夜。”
门栓吧嗒扣上,村庄如沉入深潭,寂水冷清。
误为梦中故事。
青绿·晨曲
晨起,弥天大雾将村庄掩藏得像个谎言。
老娭驰安详地坐在门坎边,择着刚从园中摘来的菜蔬,好像夜间什么事也未曾发生。
山是见不到的,树也谜一样缥缈,站在晒场上,脚下若临深渊。只有芭蕉形单影只,宽阔的叶被撕成几绺,有些破落。晒场边上,粉红的桃和晶黄的李落了一地,桃枝李叶也落了一地,有一队蚂蚁起了个大早,抬起地上的蚯蚓,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水冲过的泥石路面,有些沟纹,碎石与树叶交缠,湿漉漉,仿佛仍有昨夜激流痕迹;而窄窄的水泥路面,则干净得很,偶尔有细沙的渍迹,如小儿尿床留下的抽象画意。
晨风起,白花玉兰、银杏、大叶桐都披着乳白色婚纱,丝丝缕缕飘扬起来,轻盈曼妙。凝于叶上的湿气或雨滴,纷纷散落,仿佛又来一场急雨,偶或飘落脸上,清凉透肤。
近处的雾随风慢慢轻薄起来,一切远山近树从薄雾中现出清晰的轮廓。脚下的深谷中,静若凝脂的乳白雾层,次第铺排,线条婉约,在雾层之间,露出的绿,碧如翡翠。山顶的粉雾,从峰峦间流泻而下,如巨瀑跌崖,直入谷底,卷起雪白浪花,溅起片片飞絮。
頃刻间,山间雾气皆从千峦万壑中流走,山水一片青绿。昨天黄昏中一切低矮的物事,都高大挺拔起来,昨天夜里一切模糊的东西,都清晰亮堂起来,那遥不可及的山峰反而不再高耸入云,仿佛伸手即可触摸。
太阳是从东边两峰之间挤出来的,像是母体分娩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先是有血红的光茫渗出,紧接着露出半张红红的脸,当整个身子喷薄而出,丛林上瞬间闪出无数耀眼的光茫。
古树上有鸟歌唱,三声长两声短的句子,如宋词般婉转。也有清丽如唐诗的格调飘来,那是阳雀子在草丛间呼朋引伴。当一切暗语得到印证,便有鸟从密不透风的树叶间飞出,先是一只,又一只,再是一群,俊逸的姿态,斑斓的色彩,从透明的空气中飘过,没入另一棵树的绿里。
山坦上,草浪轻舒,有一红裙女子架起了马扎,支起了画架,正在专注于眼前的风景。远处是大片雄浑的山体,近些是绿浪滚滚的山坦,是黑压压小山包般的古木,古木与竹林掩映中的是露着灰黑色的屋顶,板着斑驳墙面的老屋,一幅多么和谐的初夏山居图!
见女子,才知昨夜月下所见,并非心中山鬼。
立于女子身后,看宣纸上展现的山水,不禁心动情乱。女子见有人观画,回眸一笑,再转身落墨,画面便有些摇晃起来。
“怎么一人跑到山间写生?”
“怎会是一人?还有几个画友呢!”
“这个时辰,他们躺在被窝里,怕是错过了最好的风景。”
女子沉吟一刻,轻声叹道:“昨夜大雨,老东家突然发病,村里没有年轻人,他们几个便冒雨将老人抬送到镇上的医院去了,到这个点儿还没回,山里手机信号不好,难通音信,也不知怎么样了。”
心不禁也是一怔,原来,昨夜风雨,并非梦境。
编辑:刘亚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