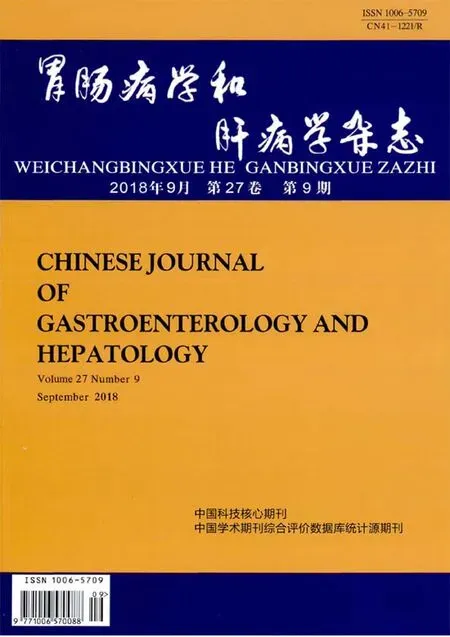从循证医学看《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制定和价值
于乐成, 陈成伟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全军肝病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2;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上海临床肝病研究中心
药物性肝损伤是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先后出台了近十部关于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的专家建议、共识或指南,其中早期的专家建议和共识论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推荐意见差异较大,导致各类药物性肝损伤相关临床研究的标准和依据不一,可比性较差,广大临床医师对此甚感困惑。在此背景下,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学组历时一年半组织编写并于2015年发布了我国首部系统规范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1]。新近王吉耀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评价体系》(AGREE-China)为我国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修订和完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原则、程序、方法和方向[2-3]。以AGREE-China标准来评估2015版《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显示这是一部基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证据系统分析、制定过程规范而严谨、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质量较高的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不仅反映了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的最新进展,纠正了长期以来药物性肝损伤诊断证据链和逻辑不完善、诊断标准不统一、停药等治疗建议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严谨EBM证据体系,平衡了不同干预措施的利弊,能够为临床医师提供最佳指导意见和为患者提供最佳保健服务的16条推荐意见,也指出了当前药物性肝损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研究方向[1]。厘清这些不同的方面对于更好地应用、发展和完善药物性肝损伤指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近十余年来国内外药物性肝损伤诊治建议、共识和指南回顾
2007-2013年间,我国相关临床专业学术团体先后出台了《急性药物性肝损伤诊治建议(草案)》(2007)[4]、《血液病患者药物性肝损伤的预防和规范化治疗专家共识》(2012)[5]和《抗结核药物所致药物性肝损伤诊断与处理专家建议》(2013)[6],这些建议或共识曾被广泛引用,对引导相关临床专业药物性肝损伤的处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均有明显缺陷。随着药物性肝损伤研究的深入,对药物性肝损伤流行病学、致病药物、发病机制、病理特点、临床特征、诊断思维(诊断流程)、诊断标准及停药和治疗措施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期待新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制定。2014年美国胃肠病学会发布了全球第一部较为系统规范的关于特异质性药物性肝损伤(idiosyncratic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iDILI)诊断和管理的临床实践指南[7],该指南有若干新的资讯值得借鉴,这更增加了制定符合我国情况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迫切性。
2014年8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学组启动了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编写工作。药物性肝损伤指南的编写本着指导医师、服务患者的宗旨,秉持严肃、公正、独立的原则,严格规避利益冲突,力求任何推荐意见都有当时所能获得的最佳EBM证据的支持,从而确保药物性肝损伤指南的权威性、科学性、严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此,在启动会上,首先由贾继东教授向编写组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写作手册,确保整个编写过程严格遵循如下程序:构建关键问题→获得指南评估委员会的支持→证据检索和系统评价→应用“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系统”(GRADE)进行证据质量评价和制定推荐意见→撰写指南草案→指南草案进行外部评审→对指南草案进行再修改和编辑→上报指南评估委员会获得最终批准。指南撰写过程经历了数百次的各类交流,5次大讨论,个别议题还进行网上投票。编写组还专门邀请了王泰龄教授和胡锡祺教授分别对药物性肝损伤相关的肝组织病理学改变进行了专题讲座,以期全面客观地评估肝活检在药物性肝损伤诊断中的价值。最终于2015年10月形成了近1.5万字的药物性肝损伤指南[1]和10余万字的药物性肝损伤指南解读。为增强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指南还被译为英文版并发表于亚太肝病学会会刊《Hepatology International》[8]。
自2015版药物性肝损伤指南发布后,中医药学会于2016年迅速出台了《中草药相关肝损伤临床诊疗指南》[9];同年,肿瘤和血液病专业也对《血液病患者药物性肝损伤的预防和规范化治疗专家共识》进行了更新[10]。这两部指南/共识针对各自的专业用药特点提出了较为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药物性肝损伤防治方法,其对于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标准、策略和流程基本遵循了2015版药物性肝损伤指南的建议,这必然有助于临床各专业在相同的诊断标准和流程下开展药物性肝损伤临床数据收集和分析。据悉,《抗结核药物所致药物性肝损伤诊断与处理专家建议》也在更新准备中。关于中草药肝损伤,除了《中草药相关肝损伤临床诊疗指南》(2016版)以外[9],还有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协作组制定的《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版)[11]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中药药源性肝损伤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18版)[12]。这3部中草药肝损伤相关指南/共识/原则的问世,充分说明了中草药肝损伤越来越得到我国临床医师和药监部门的持续重视。因此,《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影响和价值显而易见。
2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主要贡献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1]的问世无疑是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终结了以往我国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研究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和结论欠科学、不同研究之间可比性差等混乱现象,对推动我国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科研的规范化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2015版《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
(1)对药物性肝损伤进行了严谨而明确的定义,指出导致肝损伤的药物不仅包括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和天然药(natural medicine,NM),广义上也包括保健品(health products,HP)和膳食补充剂(diet supplementary,DS)。
(2)指出了宿主对于药物的肝毒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可表现为“耐受”、“适应”和“易感”三种不同情况。
(3)从作用机制、病程、靶细胞等不同角度完整阐述了药物性肝损伤的各种临床分型。特别指出了根据靶细胞的不同,不仅可将药物性肝损伤分为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两者的混合型,也要高度重视含有吡咯双烷类成分的植物(如土三七)等所致肝窦阻塞综合征(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HSOS)/肝小静脉闭塞征(hepatic veno-occlusive disease,HVOD)等肝血管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
(4)在疑似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药物性肝损伤时,推荐以1993版RUCAM量表[13]作为对药物和肝损伤之间因果关系进行评估的工具。
(5)纠正了以往专家建议/共识中有关R值计算的错误方法。R值是判断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药物性肝损伤的重要生化参数,以往建议R值采用以下算法:R=ALT实测值/ALP实测值。后来发现这样直接计算不合理,约于2004年后国际上修改为R=(ALT/ULN)/(ALP/ULN),其中ULN为ALT或ALP的正常上限值。但国内的专家建议/共识2015年以前仍在采用旧的R值计算方法,故需要予以更正。
(6)客观阐述了肝活检在药物性肝损伤诊断中的应用时机和地位。
(7)提出了完整而清晰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断流程。
(8)结合国际上对药物性肝损伤严重程度的划分标准,并充分考虑我国对肝衰竭的定义标准,对肝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划分。
(9)提出了药物性肝损伤的规范诊断格式,避免了药物性肝损伤相关肝病命名的随意性。
(10)关于药物性肝损伤治疗的基本原则,强调在可以停用肝损伤药物时应及时停药,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充分权衡停药后原发病进展的风险和继续用药时肝损伤加重的风险。对于抗炎保肝药物的应用,建议应当根据不同药物所致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特点和发病机制的差异合理选用,避免滥用。
3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反映当前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研究中的不足
从《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可以发现诸多问题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1)我国药物性肝损伤在普通群体中相对准确的发病率,目前尚无相关数据。
(2)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的各种危险因素,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和评估。
(3)不同药物所致肝损伤的机制有何异同?
(4)药物性肝损伤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十分缺乏。即使发现体内某种标志物与某种药物相关,但是否能就此认定该种药物与肝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5)同时或先后服用多种药物时,如何准确辨识引起肝损伤的药物?
(6)有基础慢性肝病的患者,如何辨别是基础肝病还是药物性肝损伤?
(7)ALT是反映肝损伤的敏感指标,但是非特异指标,且与肝损伤的严重程度并非总是呈正相关,甚至存在肝组织学有炎症坏死但血清ALT水平不升高或仅轻微升高的情况。因此,推荐诊断肝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的ALT界值为>3 ULN可能不尽合理,需要建立相关的补充信息以便更准确地诊断药物性肝损伤。
(8)推荐诊断胆汁淤积型药物性肝损伤的ALP界值为>2 ULN。而传统上对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生化诊断标准为ALP>1.5 ULN[14]。是否应当将两者进行统一?究竟采用哪一种界值更为合理?这需要结合肝组织病理学进一步探讨。
(9)肝损伤的临床生化分型和肝组织病理学分型一致性如何?
(10)目前尚无理想的基于药物理化特性和宿主体质相结合的药物肝毒性预测模型。
(11)药物临床试验中关于肝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的停药标准虽然值得参考,但在真实临床中,发生药物性肝损伤后必须及时强制性停用肝损伤药物的合理标准是什么?对于胆汁淤积型药物性肝损伤,必须立即强制性停用肝损伤药物的标准又是如何?
(12)关于药物性肝损伤的治疗,由于高质量的EBM研究目前较少,因此关于抗炎、保肝、利胆、退黄、抗凝药物的选用和联用建议,有待更精准的阐述。
4 循证医学与药物性肝损伤诊治及其指南的未来
如上所述,《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发布大大推进了我国各临床专业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研究的规范化,开创了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研究的新局面,必将引导更多的临床问题设置精准、研究对象选择得当、诊断标准统一、观察指标科学、随访时间足够、研究设计合理、可比较性更强、循证质量更高的EBM研究产生,从而能够回答首版《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暂难以充分讨论、希望在未来得到精准回答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新近一些药物性肝损伤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部分回答有关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了新的思考。
简要而言,未来需要通过EBM加强论证和回答的药物性肝损伤相关问题主要包括:
(1)以新R值(nR值)全面取代R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待论证。nR是指选用ALT/ULN和AST/ULN两者中的高值与ALP/ULN相除所得的比值。据研究,采用nR可以对更多的患者进行相对合理的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生化分型,基于nR的海氏法则(Hy’s Law)能更好地识别药物性肝损伤危险因素和预测药物性肝损伤的病死率[15-16]。
(2)判断肝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的血清ALT界值,可能要区分不同情况而定。国际上自2011年以来提高为ALT>5 ULN,并在2015版RUCAM量表中得到运用[17-18]。ALT界值的提高,自然有助于排除对肝毒性具有自适应性的部分患者和ALT基线值本就偏高的患者,但单纯通过提高ALT界值来增加药物性肝损伤诊断的特异性,可能会遗漏许多重要的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和情况[19]。根据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I)、凝血功能变化、病程持续时间及临床症状的轻重设置阶梯ALT界值,可能是更为合理的思路。例如,在ALT>3 ULN但≤5 ULN时,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考虑及时应用RUCAM量表进行评估:(1)ALT不能出现自适应性降低时;(2)伴TBIL>2 ULN;(3)伴国际标准化比率(INR)<1.5%或凝血酶原活动度(PTA)<70%;(4)伴明显乏力、过敏和/或有消化道症状时。
(3)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GGT升高的倍数明显高于ALP升高的倍数且可排除饮酒等其他引起GGT升高的因素时,采用GGT来替代ALP计算R或nR值是否可行[1]?
(4)对RUCAM量表的评分要素和计分规则进行优化是十分必要的[19],特别是基于我国人群体质特点、饮酒等生活习性、药物使用习惯等对RUCAM进行本土化优化和完善。
(5)关于药物再刺激试验(DRT),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第一,DRT阳性是临床判断药物性肝损伤的金标准[20],但由于个体体质状况变化、免疫反应的复杂性,及药物剂量、疗程、批次及生产工艺等的影响,DRT阴性不能作为排除药物性肝损伤的标准[21]。第二,鉴于DRT阴性并不能作为排除药物性肝损伤的依据,因此在RUCAM量表中将DRT阴性作为减分因素不太合适。第三,关于DRT的实施方法和结果判断,1993版和2015版RUCAM及药物临床试验所采用的标准不一致,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三种方法进行判断可能会得出相左的结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通过EBM和相关基础研究加以深入论证和统一的重要问题,以免像当初R值的误用那样给临床和科研带来混乱。第四,DRT能否故意进行?如果能,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实施?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20-21]?
(6)肝活检组织病理学特点对于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特别是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鉴别诊断价值,有待更多的药物性肝损伤患者队列和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队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获取两者区别与联系的更多病理组织学信息。
(7)通过大样本药物性肝损伤队列研究,探讨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生化分型标准与病理组织学分型之间的差异,从而论证是否需要对药物性肝损伤临床生化分型的标准进行调整,寻找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8)关于药物性肝损伤严重程度的分级,现有指南对药物性肝损伤严重程度的分级主要适用于肝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1]。而对于胆汁淤积型药物性肝损伤和血管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如何进行严重程度分级,尚需临床深入研究。
(9)关于慢性药物性肝损伤的定义问题,目前国际上有不同的标准[22]。既往多推荐以发病后6个月内肝脏生化指标恢复正常作为区分急慢性药物性肝损伤的病程界值。但近年西班牙学者提出应当以1年作为区分标准[23]。对于我国药物性肝损伤患者而言,如何从病程上界定慢性药物性肝损伤?1年还是半年?是否需要按不同临床类型分别设定病程界值?这些问题均需要进一步的EBM论证和明确,避免对临床诊疗和研究带来新的混乱。
(10)中草药肝损伤是一个特殊的问题[24]。如何从成分复杂的中草药复方制剂中鉴定出关键的有毒成分?中草药属地和炮制过程对其肝毒性的有何影响?遵循传统医药“相恶”、“相反”、“十八反”、“十九畏”等配伍禁忌的复方制剂是否足够安全?这些都是未来需要通过基础和EBM研究加以探讨的重要问题[12]。
(11)如何通过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研究探索药物性肝损伤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如何通过理化模型、细胞模型及数字模型等精准预测药物肝毒性?
(12)预防性应用抗炎保肝药物的前提条件、适用人群及卫生经济学。不同抗炎保肝药物单用和联用对不同类型药物性肝损伤治疗效果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现实中不同类型药物性肝损伤的停药时机和标准。
5 总结和展望
总之,2015版《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是我国关于药物性肝损伤诊治、预防和管理的首部系统规范、遵守WHO临床指南写作规程、基于严谨EBM证据评估和分析的指南,是我国药物性肝损伤临床诊治和研究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发布近3年来,指南已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所认识和接受,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基于EBM磨合了以往的分歧,统一了当前的认识,大大促进了我国药物性肝损伤临床诊治和研究的规范化及可比性,同时也反映出有关药物性肝损伤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病理组织学、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选择及药物肝毒性的预测和预防,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更多设计合理的EBM研究加以探讨。《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评价体系》(AGREE-China)的最新发布[2-3],及药物性肝损伤相关EBM证据的不断积累,必将为今后《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的修订带来更好的指导、更多高质量的证据和更精准的推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