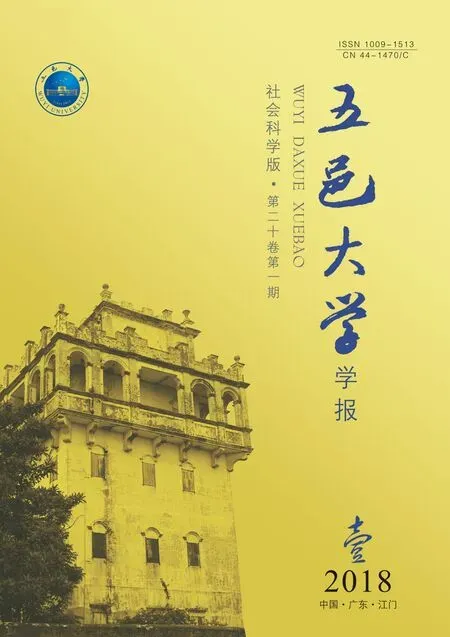开平侨乡社会兴起与传统县制的衰落
司徒炜民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近代广东江门五邑无论是华侨人数还是侨汇都在全国占有相当大比例,因此研究五邑侨乡对整个华侨华人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五邑侨乡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以张国雄、梅伟强、刘进等为代表的学者强化对近代五邑侨乡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1]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广东侨乡研究较少关注侨乡政府职能、民主观念和基层权力关系的变化,[2]换句话说,近代五邑侨乡的基层权力关系较少被关注。清季中央权力日衰,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县政权日益失去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并引发了民国时期“新县制”建设问题。五邑地区县权的衰弱与侨乡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笔者以开平为例,解析侨乡社会兴起与传统县制衰落之间的关系。
一、开平县的建立
据康熙《开平县志》记载,开平建县肇于明末,成于清初。建县前的开平地区地处广州、肇庆两府交界之处,分别由隶属肇庆府的恩平、新兴与隶属广州府的新会三县共同管辖。地处两府三县交界给开平的治理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应地方官员与士绅的请求,明廷作出了在开平建县的决定。开平建县之事其后虽因明季动乱而暂时搁置,但建县已是势在必行。“本朝顺治六年,家孝廉蒙自张巨璘偕诸文学陈请用成其事,遂割三邑之土田封域,通为里五十而设县于屯,即古所称仓步村也,建邑伊始。”[3]28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乱后,开平正式置县。
自秦行郡县制以来,建县就是历代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有效手段。在开平建县前,该地区内虽已有明政府设置的开平屯,但军屯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其对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有限。针对开平建县一事,成书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开平县志》记载:“开平以前其地或郡或县或县复为郡,沿革建置固不一矣。然终鞭长不及,萑符啸聚,阻险负隅,其势使然也。今建城立县,文武并置,城其险阻,抚其人民,居中以治,奸无生心,亦其势使然也。闻之设屯之日,有□设屯者目前之计,立县者有百年之计。今会宁高兴四邑与开平接邻,环绕于外,开若腹心,宰制于中,中而无忧,四境皆安,立县保民真百年之计也哉。”[3]110清初开平建县不仅使开平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形势迅速稳定下来,亦使得国家权力进一步深入其中。康熙年间,清廷即在开平施行保甲法。雍正年间,清廷又在开平行保甲制。嘉庆年间,清廷又将阳江协分驻开平各营兵弁改归新会营管辖并在水口设立镇康炮台以加强防御。在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下,清代中叶前开平及其周边地区再也没发生大规模的动乱。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开平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4]319加之朝廷厉行海禁,因此开平置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非经济目的,这也可从开平最早的县权所在地反映出来。清初开平县政府并没有设在潭江下游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沙,而是选址原明代军屯所在“苍城”地区(见图1)。从军事角度来看,县的治所设在位于地理中心且易守难攻的苍城对在历史上动乱频发的地区维持县政权至关重要。清嘉庆年间海盗张保仔集团曾沿潭江入侵并洗劫长沙,县城则因位置而幸免,可见县府选址苍城的必要性。
总之,清初新建的开平县还只是清王朝治下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其产生缘于国家权力加强其于该地的存在,而其落后面貌的改变则缘于近代侨乡社会的产生。侨乡社会的产生亦导致开平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逐步转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开平县政府遂由原来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苍城迁到了三埠①(见图2)
二、 近代开平侨乡社会的产生
关于开平侨乡社会的产生,成书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开平县志》记载: “按道咸之际红客交讧,水荒并作,邑民疲悴至斯而极。……是时海风初开,客乱难民纷走海外,阅时而归,耕作有资,于显己足。”[5]321最新出版的《开平县志》则记载:“开平县毗邻港澳,水陆两路四通八达。立县后一段时间,往外国谋生的人甚少。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后,门户开放,外国商品涌入,手工业受到冲击,劳动人民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被迫起来反抗斗争,有的逃往港澳谋生。而此时,西方侵略者利用拐骗、绑架等手段进行‘猪仔贸易’,掳掠劳动力出国奴役,使大批乡民出国成为可能。到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红巾军起义失败,土客械斗不止,一些参加支持红巾军起义的农民,为了逃避迫害、灾荒,纷纷逃往港澳、南洋、美洲等地,开平县华侨港澳同胞人数逐年增加。”[4]1399
大量华侨的出现是开平侨乡社会产生的先决条件,而开平华侨的大量产生则与19世纪中叶以降清王朝逐步衰落密切相关。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这就要求政府尽力降低人口流动性并把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以保证对小农的徭役赋税征派,《清史稿·职官志》中就记载知县的职责是“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6]。且清代统治者为维持统治,长时间厉行海禁,清代律法对沿海人民出海有着严格的限制,“回棹时照前查点,如有去多回少,先将船户等人严行治罪,再将留住之人家属严行追比”[7],清廷对地方官执行海禁不力更有着严厉的处罚。在19世纪中叶以前,清廷在地方严格执行其海禁政策,其时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几无可能,侨乡社会更无从谈起。而自19世纪中叶起,因西方国家的持续入侵,清廷日益失去对东南沿海的控制,已无法制止因内部生存压力与西方国家掠夺而导致的人口大量外流。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虽被迫与各国陆续签订允许华民出国的条约,但海禁并未废除,可见其时清廷对于限制人民出国,非欲不想,而是不能。如张国雄教授指出:“在 19 世纪60 年代之前,清政府对海外移民有严格的控制,海外移民与家乡的联系不是公开的,在 《大清律例》中未经批准的海外移民以及其与家乡的联系都是非法的,不少人因此被砍头处罚。这一政策的实际转变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 年的 《北京条约》和 1868 年的《蒲安臣条约》都制定了允许两国民众自由往来,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不得禁碍的条款。虽然此时大清对海外移民的禁令还没有废除,但是从此之后向海外移民和移民与家乡的联系开始公开化……”[8]因此,近代开平侨乡社会的产生无疑是清廷统治日衰而无力维持海禁的产物。
“这一时期,开平往海外谋生的人渐多,侨眷消费能力渐强,侨资兴办的商店日增,直接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县内的墟集已发展到35个,其中赤坎、长沙、水口已形成了与外地商业往来的小商埠,商品流通频繁。”[4]740“其影响生计固大,对于邑内维持治安推广教育裨益弥多。”[5]320随着海外华侨经济实力的增强,侨汇逐步成为推动开平社会运作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代侨乡社会因此形成。然而作为国家权力弱化的产物,其时侨乡亦有着诸多阴暗面,因县政权无法有效提供安全保障而导致的匪患频发即是一例,“及入民国后,土匪蜂起,劫杀焚掠,无所不至。”[5]281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侨乡社会中的新兴势力开始对传统的县权发起挑战。
三、 侨乡社会的商埠与商会
“粤语系地区侨乡社会的形成,表现在以商业为中心的圩镇的渐次出现与扩大。”[9]145商业繁荣是侨乡社会的显著特征,赤坎、长沙、水口等商埠的出现是开平侨乡社会兴起的重要标志,这些商埠催生了能与国家权力代表的县权相对抗的地方实力派。
以赤坎为例,“赤坎镇是县辖镇,……赤坎商家们为了联络客商、了解市场信息,商议设立商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成立开平县最早的第一个商会——赤坎商会。”[10]270“建国前,工商企业基本由商会管理,个体摊贩摆卖,市场兴建与管理、收费、违法处理等,则由地方和警察部门负责。商标、广告多是民主。进出口走私属海关缉查,没有健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10]238赤坎商会本是因商业需要而成立的民间组织,但却在镇内逐步掌握了一定的管理权,这就与过去“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6]的情形有所不同。
在商埠内,行政管理权力被分割为若干部分:工商业管理权被交给了作为民间组织的商会,缉私工作则交给了直属中央政府的海关部门,县的行政完整性由此受到破坏。笔者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两点原因:一是旧制度并无包含近代工商业管理的内容,二是中央权力衰退引发了权力真空。“后来,商会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商会会长,由国民党县党部委派一些乡绅名流或官商身份的人物担任,使商会逐步为政府所控制,名义上为商界组织,实际上成了政府管理商业的机构。”[11]随着国民党政府逐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如赤坎商会一类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受到国家权力的渗透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侨乡中的商会并不是简单的商人团体。宗族势力在广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以致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上有赖于宗族力量维护乡里的稳定”[12]。邓玉柱的研究就表明了司徒氏、关氏两宗族对赤坎的影响力,②因此赤坎商会不仅代表了赤坎商界的利益,还代表了地方宗族的利益,这也可从赤坎商会会长的变化上看出:
相比于民国时期开平县长频繁更换的情形,拥有地方宗族势力背景且长期任职的商会会长显然是“政坛常青树”,故其在与国民党县政府的斗争中并不占下风。烟赌盛行是民末开平一大社会问题,其时国民党政府就与以司徒声仰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围绕开平禁烟禁毒问题开展了激烈斗争。在1948年正是司徒声仰等商会领导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检举时任开平县长幸耀燊包庇烟赌。而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派员调查的结果却是“光裕中学校长关宗儒、赤坎商会会长司徒声仰参加演戏主会,庇纵烟赌,更查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习与司徒声仰两人对二区各乡演戏多有关系,此辈拥有地方实力以操纵行政为能事,实为演戏开赌之作俑者,其贪图私利捣乱禁政似应予以追究”并指责县长幸耀燊“畏惧地方封建势力,平日对于参议院师士绅及地方恶霸遇事辄以迁就为能事,演戏聚赌每次均有暗力撑持,故该县长常存不敢闻向之心而其分令制止亦谨属应付公事,无彻底执行之决心,惟该县长身负行政总责威信不加,权力不用,在责任上显属失职”[13]。幸耀燊案发生于1948年4月,而司徒声仰事后竟未受任何制裁并一直担任赤坎商会会长直至1949年,足见地方势力在开平侨乡社会中的地位与分量。
“本邑环境复杂,情势特殊,地方姓氏之成见素深,凡事多分畛域,故每有具笔亦必意见分歧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故对于地方建设与廉政推行亦难划获邑中士绅之能协调一致。”[14]伴随着侨乡社会的兴起,开平当地的宗族势力亦大为增强,故以赤坎商会为代表的宗族商业复合体遂成为一支左右地方政治的重要力量。
“台开社会以表面言目前甚觉繁荣安定,惟从实际观察实为一种畸形之发展,盖全境缺乏农业生产,亦无工厂实业与大规模之商业,除小部贫农外大部人民生活全仰给于侨汇,而大量侨资之汇进又无适当消纳,只浪费于衣食之消耗与奢侈之享受,刺激物价上涨,增重经济危机,亟宜由政府作有计划之运用吸导侨汇于工商实业之正当投资。……青年子弟多无正当职业,习尚浮华,逸乐群趋不务正业之途,演戏烟赌之炽此为一重要原因,……亟宜由政府作有计划之补救,使人有职业生活能返璞归真,并使一面减少消费一面增加生产机能。”[13]显然国民党政府对于侨乡烟赌遍地的根源在于其内在畸形的经济结构这一点心知肚明,亦明白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国民党政府对宗族势力的依赖使其对解决侨乡烟赌问题尚且力不从心,要进行触动地方势力利益的改革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其县权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四、结 论
中国传统的“县”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为实现对地方的控制与管理而设置的一种行政单元,开平县的产生正是国家权力加强其在该地区存在的表现。开平侨乡社会的产生则缘于国家权力在该地区的弱化。自19世纪中叶起清廷统治日衰,海禁名存实亡,由此引发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及因此而产生的侨乡社会表明:把“劝课农桑”作为基本目标的传统县制在开平已难以为继。且新生的侨乡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旧制度下的县政权并无对近代工商业进行管理的内容,故为管理封闭性农业社会而设计的旧制度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制度真空下因商业需要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商会遂逐步取得了侨乡社会中新兴商埠的管理权。商会与当地原有的宗族势力相结合从而衍生出能左右地方行政的地方实力派。
近代开平出现的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在同时期中国的各口岸城市均有类似现象,如上海就出现了中国政府、租界工部局与青帮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因此旧县制在开平的衰落不仅源于旧有的行政制度因其缺陷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转型,也源于地方势力对近代国家权力持续弱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填补。实现全国统一以完成国家重建任务是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的历史性任务。事实上针对清季以来地方势力坐大以致失控的情形,南京国民政府曾希望通过施行“新县制”以重新恢复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正如在开平禁政问题上的表现一样,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15],其所领导的县政府是无法在基层立足的。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县”才重新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并重新控制地方社会,开平的侨乡社会亦随之被重新塑造。
注释:
① “三埠”是近代五邑地区对伴随侨乡社会产生而兴起的隶属开平县的长沙与隶属台山县的荻海、新昌三个商埠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三埠”被合并为三埠镇。
② 参见暨南大学邓玉柱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侨乡宗族研究——以开平县赤坎镇司徒氏、关氏为中心(1912-1949年)》。
③ 据《开平县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二十三编第二章相关内容统计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