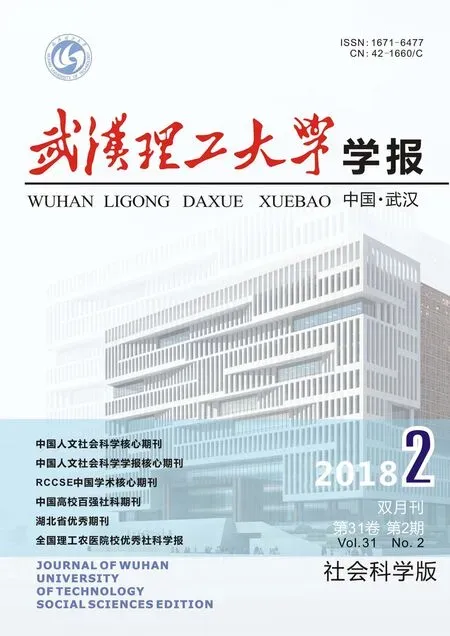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崇拜”的超越
樊美筠,王治河,高淮微
(1.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 克莱蒙 91711;2.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美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占据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地位”[1],常常成为各国争相追赶和仿效的对象。然而,西方学者、特别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反思表明,这一系统内部其实弊端丛生,其弊端已危及到整个人类乃至地球的生存和发展。流行于美国大学的“学科崇拜”即是其弊端之一。通过考察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科崇拜”的反思和批判,中国高等教育可以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走一条适应生态文明需要的跨越式健康发展之路。
一、“学科崇拜”的内涵及其表征
“学科崇拜”(disciplinolatry)是当代美国大学盛行的一种“偶像崇拜”[2]125。该概念由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小约翰·柯布在《为了共同的福祉》一书中首先提出,是指一切把学科视为神圣,坚执过度学科化,重学术轻思想,拼命捍卫学科权威的文化现象。
“学科崇拜”的重要表征是对学科化的顶礼膜拜。这种学科化导致大学被划分为不同的院系。而且,一个院系成员与外界的最重要联系,不是与该校其他院系成员,而是与其他大学相同学科研究者。这意味着大学教授的忠诚不是表现在对学校和学生上,而是表现为参与学科行会和提升学科地位上。“对许多人来说,推动学科发展的确是人生意义的源泉和生活的中心,值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科成了他们的上帝。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学科崇拜’。”[2]33-34在达利和柯布看来,学科崇拜业已成为今日美国大学里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宗教,以至于如果在大学内部对其提出挑战,就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行为[2]125。
学科崇拜在经济学那里显得尤为突出,保罗·萨缪尔森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发表就职演说时,就曾默认这一点。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学者是为了唯一值得拥有的回报——我们对自己的歌颂——而工作”[3]。作为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学科中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学科,经济学被看作是一门成熟学科,是大学规范的体现。所谓“成熟”和“规范”,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学过细的学科分类,过度的专门化和对数学化的热衷。
这种对学科自恋式的崇拜,对知识学科化的迷恋,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内下设不同的学科。通常包括42个学科,尽管每个学科都宣称自己的重要性,但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更重要,而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更是在这学科金字塔的顶端,被认为“比其他学科更重要[4]”。
在这42个学科中,每个学科有自己确定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每个学科都具有一个与其他学科有明确区别的研究主题,每一学科还要求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所开创和使用的方法致力于推进该领域的知识。这就必然要求在学科之间划出界限,导致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如果说博雅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那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则是以学科为中心。如果说博雅教育是以发展人的能力和改变文化与社会为目的,那么研究型大学则是以增进知识为目的。
也正是对学科分类的迷恋以及对学科的忠诚,使得招收以这个学科为专业的学生成为主要兴趣所在。这不仅表现在给该学科学生讲授过去的研究成果和增进该领域知识的方法,更表现在为一般学生群体讲授课程,更多地吸引主修这个专业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发展,而不是帮助局外人理解学科的研究主题。该学科教授的主要精力是思考如何将学生吸引到这个学科中来,并通过研究生和博士生项目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储备学科带头人。
二、“学科崇拜”的危害
毫无疑问,在人类认识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学科专业化是必要的。对于增进人类知识和推进知识精化和细化,学科专业化无疑居功厥伟。然而,坚执过度学科化,将学科分类“固化”乃至走向学科崇拜,则贻害无穷。正如著名学者德克萨斯大学特纳教授指出的,过去400年科学的进步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科学每一次大的发现和进展都破除了学科间的一些障碍;而另一方面,“我们学术界的学科设置则随着这些成就变得更加碎化和专门化”[5]。不仅如此,学科专业化、知识碎化也迫使专家成为他/她的研究领域之外的无知者,导致害人害己的双输结局。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学科崇拜”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
其一,封杀了综合性思维和原创性思维发展的空间。
由于学科越分越细,研究对象越来越窄,导致学科之间的壁垒愈来愈森严,“学科与学科之间耸立着高墙”[6],这无疑封杀了综合性思维和原创性思维发展的空间。正如美国著名后现代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分析指出的那样,在当代美国大学中,“每个专业和学科都被看作是自主的、自我规定的。”因此,该学科的实践者或者至少其中的名教授和有影响的人物,决定学科的范围和界限。那么,在这样大学中谁来负责整合各种学科和专业,以期对事物的性质和秩序有个整全的了解呢?答案是:没人。而且,在麦金太尔看来,即使这个回答也是颇具误导性的,因为“在当代美国大学,这样一个任务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将不同专业联系起来,整合不同知识的任务不再是当代美国大学的考量,它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an irrelevant concept)”[7]。现代大学不再致力于提供一种首尾一贯的对世界的看法。它们的任务被局限为“产生知识”[8]93。这意味着过分的学科专业化不仅“孵育和滋长了琐碎”[9]128,而且阻碍了人们对理论之间、不同学科研究对象之间联系的了解,从而封杀了综合性思维和跨学科研究发展的空间。结果,很难产生真正开拓性的有创建的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无法在物理学界存身,只好在瑞士的苏黎士专利局谋生了七年;研究历史哲学的科林伍德在牛津哲学界普遍不受待见[10]19。
学科崇拜的拥护者往往津津乐道大学是纯粹做研究的地方,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地方。他们为此庆贺思想被从大学中罢黜,将“从思想到知识的演变”视为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排除思想的大学则是极端危险的。用柯布博士的表述就是,“大学的确造就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学者。他们推动某个特定领域的进步。但是他们只是在一些想当然的发展道路上推进,实际上很多进步正在把世界推向灾难。”[11]
其二,抑制了批判思维能力的发展。
由于每一学科都将自己学科的大前提亦即学科假设视作无需作批判性分析的“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很少有人追问自己理论的前提预设,很少有人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历史进行考察,追问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很少有人质疑学科界限的设置是否合理?更鲜有人质问他们学科对社会的作用。大学不让学生去反思各个学科的基本假设,而只是让学生去接受它们。学者所要做的就是在前辈圈定好的研究领域内闷头耕耘,立身扬名。
这种教条主义态度无疑抑制了批判思维能力的发展,“贬低了批判的视角”[12]。事实上,在这种体制下,喜欢追问和兴趣广泛往往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是“不专业”的标志[10]149。自然,“对新情况作新研究”也是“不被鼓励的”[2]34。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缩小学生的兴趣范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项针对人们认识其他领域与经济学相关性所作的调查显示,物理学得分最低,而生态学或是任何其他生物科学甚至没有被列入名单中[13]。难怪有时经济学模型与生物物理现实存在冲突。那些对此提出根本质疑的该学科学者几乎没人待见。实际上,他们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发表研究成果时也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很可能失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即使去了也会发现自己不受欢迎。简言之,他们被放逐了。因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海德格为什么要发出“科学不思想”的感慨,柯布博士更愿意把其翻译成“学科不思想”[8]95。结果,由于批判能力的衰退、广泛兴趣的缺失、诗意目光的匮乏,学者个人的生活也被撕裂成两半:作为专家是个“标准的机器人”,作为私人则极易成为弱智或“白痴”[10]60。碎化的知识不仅极易把我们的人生切割成碎片,使我们变得弱智,而且极易使我们变得琐碎甚至猥琐,导致捡了“知识”,丢了“良知”[14]。
其三,放弃了大学的社会责任。
学科崇拜画地为牢,鼓励从单一学科视角看待现实,不仅妨碍了对人类真实境况的理解,扭曲了现实真实的图景,弱化了人类应对灾变的能力,而且致使大学最终放弃了本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按照特纳教授的分析,如果将现行的大学学术模式比喻成田野,被拥有自己一套语言和方法的学科瓜分成彼此无涉的一块块田地,而宇宙则是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的巨大的金字塔。这意味着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知识结构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宇宙的结构[5]。宇宙的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每时每刻都在生长的。这使得我们实际上“是在处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状态”。[15]而过度细化的学科分类导致的知识的碎化,使得人们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毫无觉察。由于在现实中人类存在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各学科则各自为政,将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结果势必如盲人摸象,失去对事物整体风貌的关照,进而导致对现实的扭曲理解,空耗思想资源。例如,虽然生态问题已经如此重要地摆在了人类面前,但在学科崇拜的影响下,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依然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的“专业研究”。在美国,不仅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继续连篇累牍地做自己的研究而丝毫不涉及生态危机问题,就是许多生物学杂志也丝毫不涉及生态危机问题。哲学领域也好不了多少,“大多数哲学家抛弃了对探究整体图景的兴趣”[8]95。传统的综合追求让位于描述和分析,这也就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流行的原因所在。除了极少数领域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主流哲学依然故我地只讨论它们所关心的问题。哲学家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所谓纯哲学方面,即认识论、逻辑和语言分析上。生态危机问题对于他们俨然不存在。这无异于主动放弃了大学的社会责任。难怪有学者宣称美国大学的灵魂已经“失落”[9]112。所谓高等学府成为“没有灵魂的机构”[16]。
学科崇拜的拥护者常常祭起“价值中立”的大旗来为大学的社会责任感淡漠辩护。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要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就要客观地对待所研究对象,摈弃任何主观的偏见。假如一所大学支持一种观点(如支持环保),不支持另外一种观点(如质疑环保)会损害一个大学的形象。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价值中立”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带有很大的自我欺骗的成分。它往往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甚至成为谋取特殊利益的帮凶。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理性对永恒普遍真理诉求的背后是对当下自身利益的诉求。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价值中立,所谓追求理解的纯粹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变化的逃避,“因为变化会暗中破坏”学术自由特权以及闲适地“玩”纯理论的特权[9]130。实际上,人类不可能价值中立地活着,为知识而知识在古代就不存在。正如著名伦理学家孔汉斯所分析的,“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每个学科(甚至包括语言系、艺术史、应用数学和逻辑)都有其社会意蕴、政治意蕴,都有其利益、预设和结果”[9]62。简言之,不存在纯粹的“知识”。
此外,大学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假如大学失去社会责任的航标,大学教授没有共同分享的价值观指导他们的研究,加之批判力衰弱和思想力退化,将极易被外界所操纵。德国大学被纳粹所操纵,美国大学被公司和军火商所操纵,就是很好的例子。更现实的问题是,要进行研究就需要课题费,学校无力支持昂贵的研究经费,而公司可以提供丰裕的资金支持,这就导致了谁给钱就给谁做研究的局面。也就是说,研究的目的是为公司利益而并非为全社会的福祉服务。当然,政府也资助一些研究。但除了其中一小部分经费走向医学研究,“绝大部分是走向了国防工业,这是支持美帝国的委婉说法”[8]96。按照印度著名科学家与环保运动领袖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的考察,“80%的科学研究致力于战争工业”,特别是致力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制造[17]232-256。这无疑也从另一个侧面宣布价值中立的破产。
至于“赢利大学”的出现则更是彻底扯下了价值中立的遮羞布。因为,“赢利大学”干脆放弃了一切关于推进知识的堂皇说辞。在那里,除非能证明一门人文课程可以增进学生的经济利益,否则将不会开设。这是一种纯粹市场导向的大学。教育完全变成了商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存在。而忽视人文学科,不注重价值观的培养,放弃社会责任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其素质成问题便注定成为一种必然。美国社会之所以充斥物质至上主义、精神空虚、信仰匮乏、道德颓败,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患‘道德疾病’最严重的国家”[18],显然与这种办学理念不无关系。正如特纳教授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最稀缺的是价值观”[5]。
三、“学科崇拜”的哲学基础分析
随着“学科崇拜”的负面后果日益呈现,人们逐渐意识到其危害所在,有学者甚至认为“学科崇拜”正在“毁灭我们的教育”[19]。虽然,著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先生肯定适当分科和专业化是必要的,但在他看来,“学科崇拜”所尊崇的过分专业化特别是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对立的坚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悲剧,对社会未来将造成严重伤害。对于当前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学科崇拜”无疑负有责任。
尽管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诟病,但“学科崇拜”在美国大学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日益大行其道。为什么“学科崇拜”如此顽强?自然,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学者队伍)捍卫自己利益的努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学科崇拜”背后的哲学思维依然强势,不能不说是另一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揭示和颠覆这种思维。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学科崇拜”背后的哲学支撑物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之有过一个经典的界定:“把自然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看作是活的东西,而看作是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0]60-61。恩格斯从辩证思维出发,充分肯定了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他强调“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0]61。大致来看,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是机械思维、碎化思维和科学还原主义。
所谓机械思维,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思维,它把宇宙以及世间万物都看作机器,只承认事物之间外在的机械联系,把关系与过程视为事物偶然的存在,否认事物之间存在任何内在的联系,否认关系与过程是事物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似乎“惟有分离才是真的”[21]8。按照斯普瑞特奈克的分析,这种机械思维影响了甚至“造就了整个现代西方思想的进程”[21]55。
所谓“碎化思维”是指在思维的时候总是以解剖的方式来分析事物,把事物切割成为零散的各个部分。当把分割出来的东西赋予其特殊的重要性时,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就走上以偏概全的道路,从而忽略了事物之间广泛存在的内在联系。正如著名后现代物理学家伯姆认为,弥漫于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碎化倾向强化碎片思维,因为“它给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是世界仅仅是分离的原子式建筑砖头的堆积,它使人们觉得‘碎化’是存在状况的‘真实表达’”[22]。
将这种碎化思维运用到教育中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密西根州立大学校长把同专业的人安排住在一起,认为这样有助于学习和研究,这样该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和化学专业的学生就很少接触,更不用说接触人文专业的学生了[23]。
所谓“科学还原主义”,按照《没有边界的科学》一书作者的界定,系指“牛顿式的古典信仰:任何复杂的动态系统可以通过研究它的部分而得到理解。一旦你知道了部分,你将至少在原则上知道整体。为了理解一个复杂的系统,应该将其次分解成部分,每一部分应该运用学科方法逐个进行研究”[24]。还原主义本体论的假设是:一个系统可以被还原成它的部分;所有系统都是由同样的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是原子般的离散的;所有的系统具有基本的机械过程。
这种还原主义的关系模式不仅为学科崇拜提供了科学基础,而且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用特纳教授的话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对还原主义有一种危险的嗜好”[5]。我们的总是试图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获得简单、确定、不变的知识,而视复杂的、变动的东西为“不真的东西”[5]。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逆天而动的。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表明,我们人类今天所面对的众多问题,其内在关联往往同时发生,每一问题都不可能单独得到解决。在这方面,由各门学科所分别培养的受机械思维和碎化思维熏陶的专家,面对这些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不仅无能,而且有时由于它的“专业知识”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用著名物理学家希娃的话来说,就是“遍布全球的多维度的生态危机可以看作是还原主义科学对自然实施暴力的结果”[17]232-256。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充斥着对所谓专家的怀疑之风,为什么《医生的两难抉择》一书的作者所提出的“所有专家都是对付大众的同谋”一语在当下如此流行的原因[25]。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学科崇拜的破产。
四、生态文明呼唤超越学科崇拜
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学科专业化有过辉煌的过去,导致了学科发展的繁荣,但发展到迷恋过度专业化的“学科崇拜”则走向事物的反面,致使人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今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人为的危机。正如柯布博士指出的,“人类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它正在快速冲向悬崖,如果继续下去不改变航向的话,几乎没有人能够活下来”[8]90。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现代大学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著名后现代教育家奥尔的话说就是,“生态的危机是彻头彻尾的教育危机”[26]。即使时至今日,现在的大学也几乎很少告诉学生关于危机的存在以及可能的可选择方案。这其中,学科的崇拜难辞其咎。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式微,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的崛起,“范畴时代已经寿终正寝”[6],学科崇拜走向穷途末路已是必然。
作为工业文明的超越者,生态文明呼唤教育转型,呼唤从教育理念到办学模式到学术范式根本性的变革,这自然也包括对学科崇拜的超越。这是避免生态灾难的发生必须做出的选择。而要超越学科崇拜,走出过度学科化的误区,就要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摈弃机械思维和碎化思维,拥抱综合思维和有机思维,大力发展跨学科研究。现实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整合性的有机思维。后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业已表明,“相互联系”是事物“真实的本质”[21]3。
要超越学科崇拜,就要把大学的重心从单纯的传播知识和逐利或“一头扎进市场”转成为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福祉服务。从“纯粹的职业培训所”回到担负起大学本应担当的“大”任务。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毫无疑问,职业培训无论如何都是极为重要的,但将教育等同职业培训则是错误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大学当然要利益个体,但同时也要有利于更大的社群和整个世界。这意味着将校园从“职业培训所”转变成“生态负责任的共同体”,把“回应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作是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27]。
大学当然要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是大学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9]114。但是,将各学科人为分开,画地为牢,闭门造车则是荒谬的。它既无法应对变化,也把人类引向灭绝的边缘。正如柯布在跟中国学者谈话时尖锐指出的,“很不幸,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真正革命性的观念才能保护我们避免无法预料的灾难,可是我们的大学在这个方面组织得很差,无法承担这个任务。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大学当作思想库了”[11]。
人类要规避灭绝的命运,就要破除学科间的壁垒,倡导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因为没有一种学科可以垄断所有知识,建设性后现代鼓励各学科携手共同解决全球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问题。这种后现代大学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大力发展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从而鼓励学生发展一种整合性的视野,以应对“整个世界面对的问题”[28]。
挑战大学的学科崇拜,并非反对大学本身,只是强调有其他办学理念存在。后现代教育绝非让人们放弃客观性和学术性,而是挑战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组织教学材料,接受不同假定,提出不同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后现代大学就是其中的可能性之一。
首先,大学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学生理解形势的严峻性并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因为今天生态危机如此严重,我们应该形成一个整体的图景;其次,所有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也应该围绕阻止生态灾难的发生来进行组织。
关于如何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应对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著名生态学家柏励开出的方子是用生态模式来组织大学。他指出,“大学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简单地设立一门生态课程就可以解决的”。因为,生态学既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个项目。它是所有课程和项目的基础,所有职业的基础,“生态就是一个功能性的宇宙”。他强调,大学必须做出决定,或者在衰败的新生代里继续培训养家糊口的专业人员,或者为正在呈现出来的生态纪而培育学生[29]。柯布博士在《怀特海式大学》中则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设想。按照他的设想,我们的大学可以就地球和它的居民的健康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该问题涉及资源消耗、能源、水资源、人口、全球秩序、一个有效的经济政策、道德价值、人类健康、政治和小区问题等系列问题,教授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那么按照种整合理念组织起来的怀特海式大学应该是怎样的呢?柯布博士的设想计划如下:
第一年,学生可以对生态——社会历史、文化——思想史作一个总的观察,了解我们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并且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作一个调查,以及计划和实施这一年工作需要的技术和想象力。虽然教授指导和信息交流很重要,但是学生参与也同样重要。学生们在这一计划中可以以个人和小组的方式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需要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了如指掌,而不至于被问题的难度吓倒或失去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了解学科研究领域的宽广,正如我们上面探讨的领域。从这些领域中,他们选择其中一个领域进行研究,他们对这个领域有充分准备,并且愿意献身这个领域的研究。
第二年,学生们将以六个人到十人的小组进行工作。他们由一位教授带领,教授的兴趣与学生们的兴趣相同。在教授指导下,他们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一起工作。首先,把问题弄清楚,了解资源,展开研究的初步规划。在通常情况下,每一个学生首先在小组里承担自己的任务,承担了解相关的问题或者收集信息的责任。小组的反应则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学习怎样变得更加有能力帮助别人,而他的帮助又是现实的。等到第二学期时,学生们对于更富于意义的任务有了充分准备,他们的任务还可以包括旅行。如果学生还不能阅读研究工作中需要的语言,或者对数学和统计学还不够了解,无法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那么他们必须掌握这些工具。学年结束时,小组在一起工作并写出一个报告,说明他们如何了解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哪些课程。如果他们认为需要以小组的形式继续工作一年,他们也可以做出决定,继续探索和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选择是,他们可以决定另选题目。小组成员在一起,对一个题目或者两个题目工作两三年,有可能写出对社会有真正价值的报告。这样,课程就可能对人类的需要,例如知识和远见的增长,做出直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参加这一工作的研究生在分析和解决社会面临的复杂的问题时,能够具有与其它人一起工作的能力[30]。
柯布的这些设想未必完善,但却为我们指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超越学科崇拜,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那就是重新调整学科研究方向和学科设置,以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组织课题研究,通过帮助解决重大急迫问题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从现代工业文明到后现代生态文明的跨越。
[参考文献]
[1] [韩]金容沃.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256.
[2] Herman E. Daly,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3] Paul Smauelson. Economist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52(1):18.
[4] 杰伊·迈克丹尼尔.超越四十二个学科:关于跨学科问题的思考[J].光明日报,2013-10-15(11).
[5] Frederic Turner. Design for New Academy: An End to Division by Department[J]. Harper Magazine, 1986(9):50-53.
[6] Russell Shorto. Breath of Thought[N]. the New York Times, 2009-01-23(6).
[7] Alastair MacIntyre. God, Philosophy, Universities: A Selectiv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M].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16.
[8] John B. Cobb, Jr. Spiritual Bankruptcy[M]. Abingdon, Maryland: Abingdon Press, 2010:93.
[9] David Ray Griffin. Theology and the University: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B Cobb Jr.[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10] Mary Midgley. Wisdom, Information, and Wonder: What is Knowledge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91:19.
[11] 柯 布,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3):5-10.
[12] Fred Curtis. Ivy-Covered Exploitation: Class,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M]∥J.K. Gibson-Graham. Representing Class: Essays in Postmodern Marxism. Durhu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95.
[13] Colander,D., A. Klamer.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Economic Perspective[J]. 1987 (1):95-111.
[14] 鲍鹏山.知识就是力量 良知更是方向[J].解放日报,2015-04-05(16).
[15] 菲利普·克莱顿.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J].陈伟功,译.江苏社会科学,2014(3):27-32.
[16] Sidney Hook. 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4:90.
[17] Vandana Shiva. Reductionist Science as Epistemological Violence[M]∥Ashis Nandy. Science, Hegemony and Violence: A Requiem for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232-256.
[18] 樊美筠,斯蒂芬·劳尔.美国最好的部分已经被现代性最坏的部分所折损[J].光明日报,2014-04-16(16).
[19] Charles Birch. Toward a Post-Modern World[D]. The State of Victoria: La Trobe University, 1987:6.
[20]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61.
[21] Charlene Spretnak.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M].London: Routledge, 1999.
[22] Davi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13.
[23] 成长春.未来的高等教育:过程思维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2007:270.
[24] Willy ∅streng. Science Without Boundaries: 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 Society and Politics[D]. Hangzhou: UPA, 2009:14.
[25] Bernard Shaw. The Doctor’s Dilemma[J].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001(2):227-245.
[26] David Orr. In Ecological Literacy: Educating Our Children for a Sustainable World[M]∥Michael K. Stone, Zenobia Barlow.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2005:10.
[27] Derek Bok.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88.
[28] 小约翰·柯布.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几点思考[N].世界文化论坛,2006-06-24(1).
[29] 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98-99.
[30] 小约翰·柯布.怀特海式大学[N].世界文化论坛,2003-0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