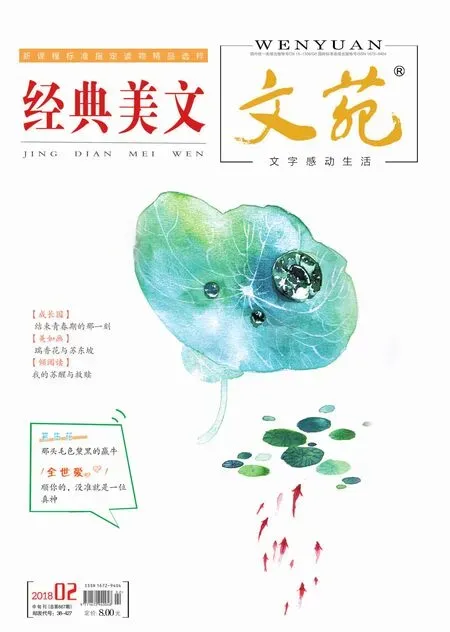冬去春来,好物不惧岁月长
文/潘云贵
潘云贵
温和如植物的90后学长,又如海底孤独的鲸,常在旧时光中与从前的自己碰面。对于未来,心存光亮,觉得时间会眷顾愚笨但努力的人。
在“过剩时代”,我们总能轻松找到每一种事物的替代品,但在某个物件上有过的情感却难以复制。有些事物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与之相关的时光也变得残损不堪,所以我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物件,像爱恋人一样爱它们。
我的布制钱包已经用了九年。深蓝色牛仔布褪成浅蓝,边角也不再整齐,有了抚不平的皱褶。好几次跟朋友去逛街吃饭,付钱时拿出它,好多人都投来嫌弃的目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换一个,这么旧了,我没直接回答,只陪着她笑:摸惯了,换个新的手就不认识了。
我喜欢用旧的字帖和羊毫脱落的毛笔。字帖是水写的那种,用笔蘸水即可在特定纸质的帖子上书写,水干字消失,内容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闲暇时我常从书柜里取出它,静下心写上几个字,特别是写到“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和“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两处时,内心尤为澄净,笔下的羊毫也写得慢,仿佛在细细咀嚼,轻轻回忆。
这本水写字帖被我写了无数遍,已是垂垂老矣。最近一次拿出它,才看清楚它现在的模样:红色线条已经模糊,水蘸上去后成墨的效果也不明显,纸张更是发黄。毛笔上的羊毫也不白了,黑的黑,掉的掉。竹制的笔杆表面早已不复油亮顺滑,有了大大小小的黑点,洗也洗不掉,仿佛人的心中无法去除的污迹。
时常触碰它们,彼此有了感情,日后若再用新的纸、新的笔都不顺手。我见它们老去,身体里竟翻起酸液,捣得内心不是滋味。
手里离不开的还有书。我的居室尽被书筑墙,它们把我围困,给我爱,我像缺爱的人竭力抱住这些沉默却忠诚的情人。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所以我期待去天堂做客的那天。中意的书看过一次是不够的,隔三差五翻翻,才能细细品到个中说不明道不破的味道。
经常去二手书店里淘书。看到有些书未被太多人翻阅就沦落至此,跟着其他旧书一起发出霉味,感觉自己是在面对一群过早衰老的人,多少有点替这些书遗憾。
我承认自己也喜欢新事物:海边的日出、刚出世的孩童、新开的饮品店、初绽的凌霄花,但这种喜欢往往只是眼睛的想法,我的手不干。我的手早已不如幼童那般光鲜饱满,时间有时变成刀,刻它,有时成为鬼,吸它。它的皮和血,都已伤痕累累。或许是新事物让它有压力,所以它选择跟它一样被时间刻了痕迹的事物。
时间真不是个好东西。曾在台北看过蔡明亮导演的电影《天桥不见了》。影片里陈湘琪扮演的角色在车站前不断地徘徊,像在等谁,又好像等不到谁。市声嘈杂,天气闷热,她神情抑郁,心情焦躁,想站在对面高楼上把这一切看得清楚些。这时一女人拉着行李箱横穿马路要到对面去,她便跟着过去,警察吹起口哨,拦住她们。在与警察的争执中,她辩称自己原想走天桥的,可天桥因城市建设被拆了。天桥不见了,记忆像被挖掉一截。事物模样的改变或消失,影响着原本依靠它、习惯它的人群。
人与人相识,讲缘,人与物,同样如此。画满青春符号的笔记本、以孤独为食的多肉植物、桌角层层堆叠的CD……每件日常物品,都住着我们的灵魂,在相当寂寞而艰难的时光里,它们支撑我们前行,让我们走到现在。它们在时间里浸泡,而时间又把它们酿制成了绝妙的酒醋。真希望这酒醋能珍藏得再久一点,等到坛边青苔长出,覆盖所有光阴,我会将它取出,尝一口,提醒舌苔,别忘记过往的味道。
李宗盛说:“多年以后审视摩挲旧物对我来说,往往意味着自己与人生某些部分的和解与释然。”
旧物的意义是它随时为我们铺设一条可回去的路,看见那扇叫作昨天的门仍旧敞开,欢迎着面对世事已经学会放下的我们。
风来雨去,因为它们,所有的旧时光才如此温暖,让人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