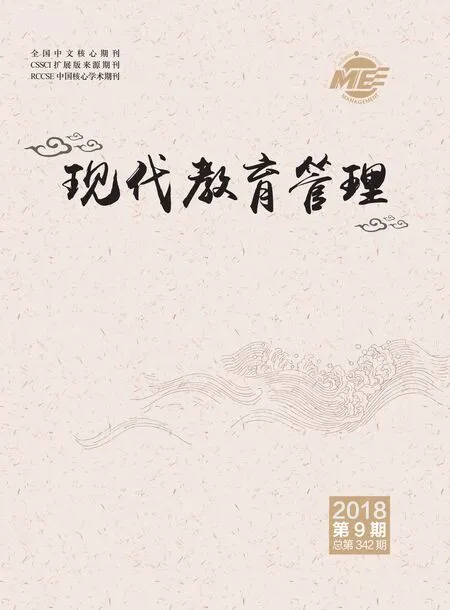“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研究*
欧小军
(惠州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2017年7月1日,即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在中央统一统筹部署下,粤、港、澳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这一协议标志着国家把粤港澳大湾区①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建设工作全面启动。纵观全球,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世界上每一个一流大湾区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拥有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心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因此,在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第四大一流湾区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以“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为引领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建设。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意义
国际一流湾区高水平大学以知识和创新为联结的集群发展是20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一般说来,越是经济发达的大湾区越是高水平大学集聚的地方,高水平大学集聚的地方也是创新型产业集聚的地方。在高水平大学集群效应下,通过知识的流动而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既能够凸显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也能形成支撑知识经济增长的高等教育网络,促进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高校的技术、知识和研究产出不仅适合于地区,也适用于全国乃至全球,物理上的接近性在高校与产业的关系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1]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地缘相近,不同城市间的大学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创新知识和技术的分享、扩散与交换更容易进行,彼此容易建成互补、互赖、互动、互争的竞合关系,其大学集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水平大学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建设之基
纵观世界三大一流湾区可以发现:作为国际一流湾区之首的纽约湾区是因为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0多所高水平大学组成的大学集群才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与科技重镇;旧金山湾区因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20多所高水平大学的集聚使其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集中地区;东京湾区也不例外,由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著名大学形成的高水平大学集群效应造就了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最大国际金融中心与交通中心和商贸中心。粤港澳三地应参照世界一流湾区大学集群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高水平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世界一流湾区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其重中之重是要缩小与世界一流湾区的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差距,因此亟需统筹构建以在粤、在港、在澳的高水平大学②为引领的集群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发挥深圳特区的区域优势引入全球最优势的大学资源,通过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突破大湾区城市之间发展关联度不强的空间割裂问题,不断催生并强化其巨大的集聚外溢效应,强化湾区创新型经济的聚合功能。从这个意义讲,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根基,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石。
(二)高水平大学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创新中心的支撑之点
科技创新是国际一流湾区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世界一流湾区的研究发现,国际一流湾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世界一流大湾区不仅是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同时也是世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国际一流湾区旧金山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创新之都的魔力就是实现了人才、技术、资本与创新四大要素的强力集聚,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形成的高水平大学集群所具有的智力资源在该区域的密集投放且真正融入产业界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和重要支撑。东京湾区仅仅东京一个城市就集中了全日本2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30%以上的教员,同时聚集了全日本30%以上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50%的顶级技术公司[2]。《协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统筹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要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必须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把培育创新企业和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作为重点,形成创新优势,最后通过高水平大学集群这种抱团创新的有效模式从根本上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转型升级,建成具有引领世界科技水平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因此,打造世界一流湾区必须有一流大学为引领的高水平大学集群,高水平大学集群所具备的超强基础研究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创新中心的有力支撑。
(三)高水平大学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动力之源
高水平大学既是湾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站。在这一点上,作为世界最为著名的电子工业中心,旧金山大湾区的“硅谷”经验值得借鉴。以斯坦福大学为引领的高水平大学集群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脱节问题,打通了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关键中间环节”,促进了科技与产业“联姻”,使高水平大学成为产学研的真正结合地,同时也促使“硅谷”具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产学研创新系统。《协议》指出:要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显然,没有高水平大学集群焕发出来的创新力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般说来,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关系通常分为三种主要形式:跨国公司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高校与小型高科技公司的关系;在区域背景下的公司,通常是中小公司与当地高校发展出来的关系。[3]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聚集着较为发达与门类较为齐全的产业系统,为了使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向高端化,只有通过高水平大学集群充分发挥高端引领作用,打通国内外产业创新资源进出循环的通道,才能催生出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与协同效应。“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高校集群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无疑最为频繁、程度也最为强烈,它主要通过智力资源的流动来实现。”[4]从这一点上讲,高水平大学集群与湾区产业集群形成的互动关系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三地协同合作、抱团创新与集群发展,有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潜质和实力,粤港澳“三位一体”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模式已具雏形。2015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正式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批准在粤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7所高校作为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将在粤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列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港的有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世界100强之内的一流大学;澳门拥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高水平大学。可见,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有着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诚然,港澳回归祖国以来,粤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频繁,愈加紧密,互动性较强,但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三地的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协同创新、合作交流互动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无论是在合作交流的次数还是在协同创新的成效方面都不如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效,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差距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基础较薄弱:数量较少、水平不高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世界顶尖级大学的数量偏少,在全球100强的大学中,其综合实力排名相对靠后。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短板最为明显的还是高等教育方面,美国加州的高等教育基本可以与东海岸等量齐观,而粤港澳还不如京津冀、长三角[5]。建设世界级的城市和大湾区需要一大批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纽约湾区有50多所高水平大学,其中有波士顿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一大批世界顶尖级大学在内组成的大学集群;旧金山湾区有20多所高水平大学,其中有南湾的斯坦福大学、东湾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旧金山艺术大学以及加州北部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世界顶尖大学或美国国内一流大学组成的大学集群。东京湾区也聚集了30所左右的高校,其中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都市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为国际顶尖级大学、亚洲或国内一流高水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在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方面,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大学集群发展的基础不够雄厚。
(二)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均衡、不充分
地理靠近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地理位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主要分布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4个核心城市,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等7个中心城市的高水平大学资源相对匮乏、差距较大,整体水平不高,很难支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技术、智力资源的巨大需求。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为粤港澳其他城市聚集创新要素与资源、构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设置了障碍,必将影响大湾区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综合集成,拉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链中的核心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从人口、面积等基础指标来看,是目前为止最大的湾区,但从科技、创新、金融等核心指标来看,具有大而不强的明显不足,科技创新网络还远不成熟,不仅缺乏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也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高水平大学与产业之间还没有真正发展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集群基地,要达到斯坦福大学与产业界深度融合的水平,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三)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内在驱动力不足:集而不群、合作面不广
作为大湾区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大学集群一般是指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的大学之间相互配合、分工合作而形成的一个“生态良好”的知识创新与分享的网络结构和系统。粤港澳高水平大学之间具备地理上的临近优势,但相互之间的知识创新协同效应还未真正产生,每一所大学结构性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没有通过大学集群的交流、整合、互换、共享等方式得到很好解决,高水平大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调节的“耦合”系统还没有形成,大学集群基本上还处在“集而不群”的状态。目前看来,粤港澳三地大学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与合作更多的体现在对优质生源的招生录取上,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创新协同发展的实质性相互影响很少,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还没有形成较好的协同共享机制。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的联系与合作更多还是局限在行政区域内,高校创新要素无法快速有效流动,导致创新协同发展能力不足、合作面不广、集群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以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产业创新活动很难得到前沿基础研究的支持[6]。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问题的成因
(一)高等教育行政壁垒尚未完全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是一项需要内外力量协同合作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政府(政府权力)、高校(学术权威)、社会(市场)“三角”力量相互博弈、相互协调而构成的动态的、充满张力的空间结构系统,其中政府作为关键一角,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本区域大学的发展水平和办学质量。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不仅需要大学具有本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也需要政府制度的外部推力,大学集群发展动力是建立在“内在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基础上形成的合力,尤其在大学集群发展的初期,政府行政权力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行政区划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较,其特殊性十分明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面临的最大的特殊性就是“一国两制”下的跨区域集群发展,香港和澳门分别拥有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权,港澳政府与广东省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差异等将会影响三地高水平大学集群的“深度”发展。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两制”的差异常常导致其教育行政模式以及政策手段很难有效对接,这为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形成推动集群发展合力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二)高等教育合作共享机制尚未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正式启动意味着由单一区域走向跨区域的全方位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但现实是,粤港澳作为三个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行政区划的区域主体,基于各方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共享的管理机制和政策创新机制尚未有效发挥引导高水平大学向集群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三地的大学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层面还没有完全从“民间”“非正式”合作上升到政府间的“制度化”“法制化”合作层面,合作的范围也没有实现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以及构建粤港澳创新网络体系等多方面的广泛合作。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许长青认为,尽管粤港澳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但高等教育方面的联系却没有加强,三地高校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相互影响,长期下去将浪费宝贵的区位优势。[7]目前,三地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体制性障碍,由于缺少利益共享机制和配套政策支持,大学集群的战略发展平台没有很好地搭建起来。
(三)高等教育政策法律尚未完全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高水平大学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创新主体,能否充分发挥其在参与跨行政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而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离不开法治的有效保障,三地合作发展的法律冲突仍然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11个城市的法治水平总体上呈现一种差序法治发展格局,大湾区不同法域之间的法治协调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的体制框架内,分别各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评价指标,虽然有港澳基本法、CEPA协定、区域合作等其他协议,但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深度协作的制度条件主要还停留在以政府协议为主的政策导向型机制上,缺乏立法先行的法治推行型合作方式。因教育法律政策而造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很难获得优质创新资源与要素配置的集聚优势,高水平大学之间长期处于“貌合神离”相互分割的状态,三地之间高水平大学的集群发展问题并没有因为港澳的回归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没有合作的法律基础,只是在区域行政协议里涉及到部分比较原则化、抽象化的与教育合作培训相关的条文,这种类似于“政治宣言”的框架性协议,如不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对程序、责任、义务等多方面予以明确,最终很难操作执行。
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在集群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资源互赖与空间集聚的互惠共生形成协同合作的集群发展新秩序,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在“一国两制”背景下,要创造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模式,真正发挥高水平大学对粤港澳大湾区创造世界科技创新之区的强劲引领和知识外溢作用,实现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带来的“抱团创新”,亟待从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一)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行政机构,促进高水平大学有序发展
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地高水平大学的集群发展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现实中三地行政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分治割裂与需要超越行政鸿沟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此,构建符合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大学集群需要有跨区域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与共同的政策行动框架,不断打破原有行政区划形成的藩篱,实现优质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宏观发展目标比较明确,发展的路线也比较清晰,但对广东9个城市具体的经济功能定位还不够清晰。粤港澳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要求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必须实行错位发展,围绕区域或地方核心产业形成产业链网络,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产生大学集群发展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融合效应。为了减少相互之间的高等教育内耗性竞争,急需建立一个由中央、广东、香港、澳门四方联合组成的教育行政机构,对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进行统筹规划,通过合并、新建、引进、升格等多种适当方式大力发展高水平大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跨越式发展。因此,借《协议》之力,在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之间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高等教育行政机构,是促进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关键。
(二)健全粤港澳高水平大学协同机制,促进高水平大学创新发展
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教育行政主体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衔接与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教育融合政策是化解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壁垒的重要手段。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建立政府间的协调体制可有效推进三地高等教育政策体系的衔接和融通,解决粤港澳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教育政策、财政支持、合作协调、互补互通等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三地高水平大学通过搭建跨区域合作交流平台,吸引湾区高水平大学在内的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积极参与,使高水平大学“创新集群”在粤港澳大湾区即将形成的“以知识经济驱动、资源全球配置”为特点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全方位实现政产学研用的一体化,大力提高科技创新的辐射力,构建粤港澳产教融合的科技创新特区。此外,粤港澳三地之间的产业集群发展为粤港澳大学联盟的建立催生了有效的组织机制,高校战略联盟能够促进三地大学从相对松散状态向边界模糊、资源共享、学科共融、科研集聚方向发展,有效推进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形成和谐共生的高等教育教育生态。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国际上大学联盟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理顺事关大学发展的内部组织关系,争取有利于大学集群发展的核心外部资源,统筹规划、密切协同,使之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又一重要的集聚地,构建具有世界高水准的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8]。目前,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发展基础和模式也不一样,国际化程度差异也较大,三地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需要科学规划并引导三地大学空间集聚和集群化发展,实现高水平大学之间和大湾区产业行业之间以及大学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制定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法律政策,促进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世界一流湾区的特殊性,如何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形成与世界一流湾区相匹配的高水平大学集群,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大学集群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制定与粤港澳大湾区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与国家(区域)政策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关键。未来在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同时,应出台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规划,并制定相配套的、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将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纳入正式的法律轨道。另外,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色彩,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性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倾向性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出台并实施相关支持政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朝着健康的方向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关键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加大粤港澳三地大学投入,增设粤港澳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基金,解决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的经费问题;其二,促进大学之间高级人才的正常流动,建立健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解决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高端人才缺乏问题;其三,实现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优质资源共享,促进资源无障碍配置和边界流通,解决高等教育资源跨区域协调与运作问题。
注释:
①粤港澳大湾区是由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等九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9+2”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②主要以在粤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在港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大学,在澳的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大学为主。
③世界上成熟的大学联盟有常青藤大学联盟(Ivy League)、北 美 大 学 联 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罗素大学联盟(The Russell Group)、澳洲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ofEuropeanResearch Universities)、东盟大学联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