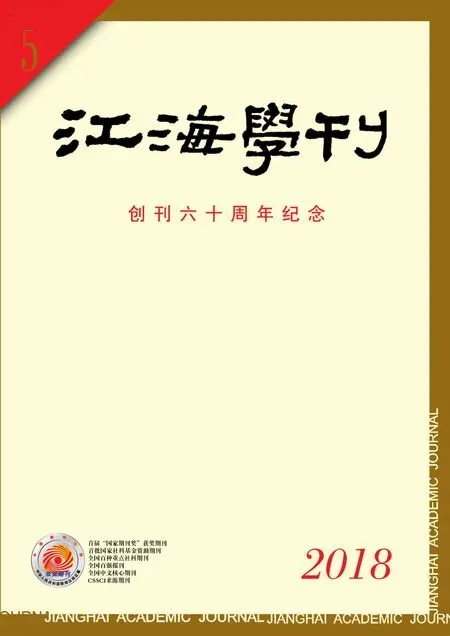论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英美警务社会学研究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警务行动必须在法治逻辑下展开,然而行动的严格合法性是否意味着对自由裁量权的排斥?合法行为和自由裁量之间是何关系?如何理解警察的自由裁量行动?围绕自由裁量的疑问一直是警察行为研究与实务讨论的重点。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应然性讨论,缺乏实证研究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本文从英美警务研究已有的丰富讨论出发,就“社会学如何研究自由裁量权”做出梳理: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视为社会事实,探讨自由裁量权设置的具体社会情境与实践结果,冀望为中国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
引言:社会学视角的特殊性
近年来,警察工作中的自由裁量问题——即是否能够依据具体情境做出判断、能否依据主观判断对当事人采取行动、行动的有效性如何界定,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所谓自由裁量,按照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的界定,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以恰当和公正的方式做出作为的权力”。事实上,现代国家法治原则确定以来,与国家权力相关的行动主体如何处理法律的普遍性规定和现实的具体情境的关系,就成为困扰法学和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作为症结之所在,关于自由裁量的讨论一直“被证明是一个十分丰富的讨论和争论的来源”(尚水利,2012)。一方面,作为街面秩序的实际维持者,警察所实施的自由裁量是行政裁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执法主体的警察,其自由裁量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司法裁量的性质。梳理国内学术界的文献,我们发现,针对这一问题的已有研究也是从司法自由裁量、行政自由裁量两个角度展开,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警察管理学等领域。
法学领域关注于“合法律性/自由裁量权”的两分范式。根据戴维斯的研究,自由裁量权在1960年代法律与社会运动兴起后才进入法学视野。此前,法理学研究者看重法官、立法者、法律原则与规则,而轻视行政过程、政策与警察权力中的自由裁量。行政法学研究者则更重视正式行为与司法审查。
我国法学界的研究则集中于法理学与行政法学,围绕着自由裁量权与正义、自由裁量的法律基准等问题。如王锡锌(2002)对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研究;周佑勇(2007)、朱新力(2007)、郑雅方(2013)等对裁量基准的技术操作、法理学定位、正当性依据进行了研究。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常止步于法学与法哲学的抽象层面,缺乏对自由裁量过程的具体观察。因此多呈现表层化的倾向,较少直接针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探讨。简而言之,目前仍未见到具体关注于警察自由裁量行为本身的问题意识。
警察管理学领域的情形则大不相同。自由裁量权在法学与政治学领域获得广泛承认后,“如何规制”的研究也出现在警察管理学领域。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较为单薄,大致只有功能分析与规制建议两类:自由裁量权有助于警察“主体性品格”的提升,但也为规范警察行为增加了困难,因此需要将之引向理性化。
自由裁量行为在现实情境中存在领域之广泛、可能形式之复杂,决定了单一技术手段进行控制的设想必然难以实现。因此除了大量专门从立法、司法、行政监督(如黄力,2006;李丹阳,2011;赵杰伟,2010;赵燕萍,2011等)以及职业素质、道德约束(如卢军,2009;董晓文,2016等)等各单一环节或方面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控制提出建议的研究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应使用复合手段对自由裁量行为进行控制。如王锡锌(2009)将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技术和主要路径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自由裁量控制的四个理论模式,即“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通过原则的指导控制模式”,“通过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以及“通过监督的审查控制模式”。通过多种模式综合运用,王锡梓认为自由裁量行为可以得到较好的引导,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
但警察管理学的规制设想仍只及于理论分析,且多用“权力必然会有被滥用的可能”“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等粗糙判断进行常识性推理,进而归结于“立法+司法+行政规制+职业道德管控+群众监督”的通用公式,呈现出无法深入的常识性重复。
总体而言,前述各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一部分研究者从执法过程的客观规律及警务活动的特殊属性以及更深一层的“徒法不能自行”“理性存在自身的限度”等方面论证了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并对其发生与运行机制等进行了具体分析(郭春青,2008;张小涛,2008,李涛,2007等),并有学者分析了警察自由裁量权在现代国家中的意义(张彩凤、辛素,2008),但绝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应然讨论,或是始于法学、行政学的讨论,而滑向警察行政管理层面的政策建议。因而对于警察在何种情形下拥有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如何影响具体的警务工作,相关研究付诸阙如。
相对地,国外尤其是英美的警察自由裁量权研究已较为完善深入,社会学与法学、政治学并驾齐驱,发展出以自由裁量权研究为中心的警务社会学体系,其贡献一方面在于实证和调查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应然研究获得了实证材料的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则在法学与政治学价值判断导向的分析之外另添视角,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视为既定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存在,并反思它们对于社会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意义、分析各主体应此而生的行为策略,从而提示政策制定时需留心意料之外的多重反应。
警察执法是专业行为,外界颇难评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得宜。这一方面自然诱发出滥用,另一方面也滋生出公众的怀疑。随着我国民众监督与维权意识的增强,对警察行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学术关注不容拖延。而国内虽有法律学者注意到自由裁量权的社会维度(薛文超,2016),但从议题设置、理论视角、实践机制多方面进行的社会学系统研究仍是空白。
自由裁量权:英美警务社会学的重点议题
19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对自由裁量权的讨论有其社会背景。首先是民权运动及随之而来警务压力,使得一些学者借鉴英国早期巡警经验,提出扩大基层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警民关系、提高警务效率。同时民众集中抗议警务中的歧视与贪腐,也促使研究者调查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社会情境及具体后果。
其次是美国的法律与社会运动。当时社科方法被大量引入法学领域(Gould & Barclay,2012),法学界也正经历法律形式主义向法律现实主义的迁移,后者不再将法律视作“内部连贯的现象”,强调法律过程因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会呈现一定的不确定性,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有必要与社会共同进化等思想(Weinrib, 1988)。
法律与社会运动首先强调了“书本中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别,这种差别在极端复杂的警务活动中格外明显。Davis(1970)发现,法律条文作为警察的行为指南,变化速度远比现实要慢——“有关于着装的规定,却没有如何调解矛盾的规则;有如何清理手枪的说明,却没有何时可以开枪的规定;有关于公共财产使用的规定,却没有规定要不要驱散人行道上的集会;有规定要管制流浪者,却没规定要怎样对他们展开审问。”法条空白之处,警察只能依据惯例等法外原则。有法可依之处往往也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警察同样必须在实践中做出种种即时性判断。法律与社会运动迫使人们正视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之获得“被讨论”的合法地位。
其次,这一运动引入“社会控制”话语,引发了对于警务模式的反思——执法者在行动中需考虑社会影响,而非仅仅伸张法律本身的逻辑。这也导致了警察形象的再定位:之前的专业化时代,警察应当理性、客观、公正、严格,“执行法律”是过程也是目的。如今警察更需服务居民、维护社会秩序,践行法律精神而非文本。目的不再是机械执行法律,而是最优的社会控制(Goldstein,1963)。警察基于具体情境,为了做出符合社会公益的决定,便需要适量的自由裁量权。
1960年代兴起的社区警务核心理念之一即是“给基层警察赋权”。基于早期警务社会学家们的观察,倡导者们认为这能使基层警察对社区民众需求的反应更为灵活迅速。但增大自由裁量权,则可能引起更多的公平问题。因此1960年至今,社会学家持续进行着实证研究,评估调整警察自由裁量权引发的具体社会影响。
总体而言,由于警务工作的天然特性,自由裁量权一直存在于实践中。但1960年代后成为英美警务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则源于社会学对警务研究和法学领域的介入。另一方面,强调权力下放的社区警务成为主流的警务模式,也是原因之一。
自由裁量的社会情境
不同于单纯从行政法角度进行的逻辑推理,社会学对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往往具有实证性基础,即使体现出价值取向,也是在充分的观察发现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从1940年代末Westley使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学术史上第一例针对警察活动的实地调查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开发警察日常工作的“真相”。
值得关注的第一个视角是警察工作界限的模糊性与日常生活的整全性,呈现于早期警务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中。1960年代,研究者注意到警察的日常规范与价值观念。Banton于1964年发表基于田野调查的《社区中的警察》(The Policeman in the Community),指出警察日常事务很少关乎犯罪,而多数是治安维持与琐碎服务。警察更多地表现为“治安维护者”“服务者”而非“执法者”。尽管专业执法者这一职业群体意识开始形成,但“巡警维持治安”仍是警察的最主要活动。这一活动的质量与态度,塑造着警察文化及其公众形象。早期研究者如Westley和Banton还原了自由裁量权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一边是专业化执法者的职业要求,一边是现实中无从摆脱的服务性工作,自由裁量权行为正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
第二个视角则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警察文化。1960年代后期,警察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形成(Loftus,2016)。Skolnick(1966)指出,警察的日常工作未必遵循法条与科层制规则,工作中的非正式惯例、规范、习惯对于警务研究有重要意义。自由裁量权行为研究即是其中的重要部分。1973年,警察角色研究的开创者Cain出版《社会和警察的角色》(Society and the Policemans Role),观察巡警日常的自由裁量权行为,描述了大量因前述间隙而造成的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现象。1978年Linda Hancock的研究则发现这类行为中由于偏见与对特定群体的标签化而导致的不公。这些研究都说明了非正式文化对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行使过程的影响。
第三种视角将执法作为一种技艺,探讨警察自由裁量行为的策略性。如Muir将警察视为街角政客,通过描述警察与居民的“勒索型互动”,展示了自由裁量权之存在使其成为更复杂的行为主体的事实。Campbell(1999)借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分析街头警察的裁量行为,将警察作为处于结构之中、受到结构限制的行动者,揭示了其自由裁量行为的选择策略。这些研究已经脱离了“应然性”的视角,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了自由裁量行为的真实内容。
警务社会学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社会情境和具体内容做出了回应。
社会学的另一研究重点是如何界定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作为Cain与Hancock等学者控制执法不公的思路的延续,从1990年代起,一批以如何控制自由裁量权为主题的研究涌现出来。Livinston(1997)从司法、管理和组织方面提出了控制警察自由裁量权膨胀的建议。Jones(2009)则在Clark(2005)民主警务范式的基础上对放权与监管的平衡进行了更深的考量。这些学者秉持着规范警察文化的态度为限制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诸多思路。
而在另一方面,警务社会学的一部分研究始终将基层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视为提高效率和增强警民连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1960年代的警务改革时期,这种推崇达到顶峰。专业化时代的警察机构是典型的科层官僚制度,民众与真正拥有集中权力的警察距离遥远。因而民众的需求无法顺畅上传,对警察的监管也极为困难。1970年代有学者认为必须赋予基层警察更大权力、缩减决策过程来解决此问题。基层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决定着法律的现实意义。在更好的双向沟通中,警务活动能够在警察与社区共同建立的价值观念下有效开展(Brown,1988)。
总的来说,尽管长久以来,无论是出于工作效率和有效性的考虑,还是警察对本身执法者形象的维护,都对自由裁量权的深入研究构成了一定的阻力(Goldstein,1963),但英美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关注,改变了对自由裁量权价值性讨论的状态,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带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为认识和改变现实打开了一扇门。从1970年代社会学家对“警察日常工作真相”的大规模探索开始,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关注就在Westley、Banton、Skolnick、Bittner(1972)等人的著作中屡屡出现;及至警察组织与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Manning(1977)、Cain、Muir等人的研究中,警察自由裁量权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社区警务研究的热潮中,警察自由裁量权应如何赋予,更成为警务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重点。
自由裁量的实践影响
自由裁量究竟在警务活动的具体情境中造成了怎样的实践影响?在此基础上,如果政策要求调整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应注意哪些问题?围绕这些核心关切,近年来英美警务社会学形成了三个主要议题:歧视性行为研究、基层警察工作压力研究、警察日常策略性行为对警民互动过程的影响研究。
(一)警务活动中的歧视Mastrofski(2005)指出警察的危机表现为自由裁量权难以控制。警察能够自由选择他要关注的犯罪或嫌疑人,在这一挑选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各种区别对待,即歧视。
第一,警务社会学研究发现大量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黑人等少数族群社区长期遭遇警力不足与过度执法的双重境况(Greene,2015)。在警察眼中黑人带有不友好的负面标签(Holdaway,1983)。1990年代研究者仍发现伦敦巡警拦下黑人询问的概率是当地黑人人口比例的2.5倍(Norris等,1992)。Patterson and Wildeman(2015)则证明美国成年黑人平均被监禁1.79年(成年白人0.33年),平均携带出狱者标记11.14年(成年白人2.31年)。
第二,年龄也成为影响警察自由裁量行为的重要变量。Riksheim和Sherman(1993)的研究发现,警察的行为在嫌疑人是青少年与成年人时有显著差异。警察更可能逮捕青少年嫌疑人(Visher,1987),也更可能对青少年嫌疑人使用暴力(Brown, Novak,et.al., 2009),而上述差异与警察的职位、工作态度无关。另有一部分研究发现,对于不涉及毒品、酒精或没有明显物证的犯罪,警察更可能宽大处理未成年嫌疑人(Stinson等,2007)也有学者综合考虑社区、种族、年龄因素,如(Mastrofski等,2005)研究发现对社区警务消极的警察更容易逮捕青年嫌疑人。Brown和Frank(2005)指出青年黑人被捕的可能性高于成年人9.2倍,青年白人则为2.7倍。
第三,警察的决策受嫌疑人的举止、阶层、社区背景的影响(Brown,Novak,et.al.,2009)。警察更容易逮捕怀有明确敌意的青少年(Myers,2004)。Wilson(1968)则通过八个美国社区中警察行为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社区特征的影响。
警务工作具有“主动性”怀疑的特征——需要对面临的事件、当事人预先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断,因此警察可能会因为固有的经验与偏好形成“自由裁量歧视”。年龄、种族等人口性因素与阶级、社区等社会性因素都能使警察行为的态度与结果发生偏差,这是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也是自由裁量权本身的体现。
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和社区警务办公室发起过“如何衡量警察行为”的大讨论,结果收录于《Measuring What Matters》(Greene,2012)一书中。其中社区调查部分明确展现了居民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关注与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期望。可见其中可能包含的歧视已成为民众关注、需要改革解决的问题。
(二)街角政客
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警察可以扮演制度想象不到的更多元的社会角色,成为复杂的行动主体。Muir的经典之作《警察:街角政客》(Police: Street Corner Politicians,1977)指出,警察必须以威胁对方的尊严、自由或人身的方式获得公众的服从,然而这种勒索关系非常微妙,面临悖论:面对最需要被控制的对象,警察却最缺乏勒索资源,如一无所有的底层、自暴自弃的犯罪者、缺乏理解威胁能力的吸毒者、酒鬼、精神错乱者。Muir认为“好警察”应针对性地丰富“武器库”。
基于行动策略的分析能够显示警察如何使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如何实质性地重塑警察的权力地位与形象。策略武器有多种。Muir发现好警察会主动了解辖区人群重视的事物。通常警察会利用刑事法律之外的合法资源,例如无法阻止酒鬼买酒的警察能够通过制造麻烦(要求辖区商店停止向酒鬼售酒)来获得控制力(Waddington,2015)。Holdaway(1983)也分析了警察的多种日常策略,如加快时间分配(比如巡逻中使用无线电)或减慢(单次出警时使用更多时间)或创造时间(例如拖延抓捕嫌疑人)等。为实现对公众的控制,警察能够使用国家机器的符号权力、限制与牵制手段、哄骗、言语控制和威胁、教育和惩罚等策略,最终则是使用暴力。
暴力永远是警察的终极武器。尽管过度使用暴力常受公众的质疑,但警察在使用暴力手段时仍偏向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行为。这种倾向能够以街头警察文化角度加以解释。首先,公共舆论、正式培训体系与非正式的经验传授都将警察工作描述为非常危险、可能致命。对危险的反复强调有助于为使用暴力提供合法性。实践中的警察会使用各种叙事与修辞来合理化自己使用暴力的行为。其次,警察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为危险而容易犯罪的“符号化的犯罪者”很容易激发警察的暴力行为。第三,警察的实践工作需要控制现场,因此在场面有失控趋势而在真正的危险发生之前,警察就会实施暴力。特别是警察预感到严重的危险而无法准确识别犯罪者时,更可能采取“宁错杀不放过”的策略控制场面并自保。最后,警察会使用暴力实现“街头正义”(street justice),例如在镜头下也忍不住暴打刚抓到的杀人犯(Marenin,2016)
Muir根据对暴力态度的差别区分了街头警察的四种理想类型:“非黑即白”的专业型(professional)警察以暴力为警务工作的工具;“强制型”(enforcer)警察乐于使用暴力(尤其是面对他们眼中的坏人);一类警察也区分他者群体,但尽力使用谈判而非暴力;无所事事的“制服架子”(uniform carrier)警察很少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也尽量不承担任务(Waddington,2015)。这四种行为模式在现实中可能混合出现,使警察成为复杂的行动主体。
Muir的最重要启发在于,自由裁量权使警察在街头与公众形成了勒索式的胁迫关系(extortionate)。这种关系对于秩序是必要的,也支持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同时也质疑了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警察不再是单纯的权力层级结构中受制于制度的行动主体,而是手段丰富的“街头政客”,这令自由裁量权的分析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三)警察工作压力
1990年代,社区警务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开来,这种强调警民互动的警务运动提倡给基层赋权。然而,自由裁量权的赋予一方面回应了自由裁量实际存在的状态,但也给日常警务工作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影响。
首先,警察职能的扩大。Dempsey和Forst(2010)发现,在社区警务模式下,美国警察每天至多有20%时间用于处理犯罪,其余则用于治安、社会服务与行政事务。警察成为民众眼中“解决问题”的组织,无论困难为何都可能向警察求助。因此警察工作的范围与难度都迅速增加。
其次,警察需要介入更深的社区生活。在社区警务模式下,警察除传统的巡逻与治安维持外,还需与社区结成伙伴关系(Clairmont,1991)。尽管当代西方社会原子化越来越深,社区自身动员日益困难,与社区搞好关系仍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基础。警察需要定期参与社区会议、组织居民顾问委员会、设立情报网站、做调查、开课程,这些都要求大量、长期的精力投入。
随着工作范围与深度的扩大,警察的工作压力必然增加。基层警察的职业倦怠已成为当代西方警务研究与实务中的重要论题。Vila(2002)等人的研究显示超加班工作、睡眠不足已成为基层警察的常态。也有研究发现过度疲劳的警察更容易发生摩托车事故(Senjo and Dhungana,2009)。
制度的设计与落地的实际效果往往存在偏差。自由裁量权在以往的管理学与行政法等视角中意味着高效率(与潜在的公平隐患)。而社会学实证研究揭示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意味着事务范围与复杂度的增长,同样影响效率。调节尺度为何?需进一步谨慎思考。
如何理解自由裁量?
我们从围绕自由裁量权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能够看到对于社会情境、具体内容、实践影响等诸多方面的探究努力。警务社会学用田野研究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为在警察各种活动与各环节中的存在,将其视为客观的社会现象,超越价值判断进行分析。对于策略选择与互动过程基于结构功能视角进行解读。而在全球的社区警务浪潮中,实证研究解释了基层警察自由裁量权这一变量对于警察、罪犯、社区等多重主体的实际意义,形成与现实的持续互动。
诸多学科都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了价值判断与政策建议,但社会学在此论题上的特殊性在于,政策建议之外,仍要求密切保持对政策实施后实际效果的持续观察。限制自由裁量权是否真的增进执法公正?赋权于基层警察是否真的提升效率、缓和警民关系?基于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见到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过程,而非单纯抑制或扩大即可妥善处理的单向因素。
当代中国社会,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增长,警察自由裁量行为牵引着媒体和公众等多方群体的关注。英美警务社会学的研究提示我们,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策制定,不能仅依靠法学、政治学等宏大理论,更需要社会学为其提供现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