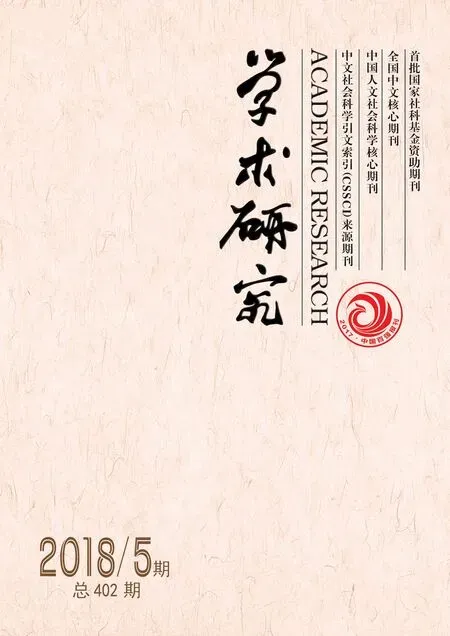论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
李博昊
《花间集》由后蜀勋臣赵廷隐之子、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纂,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前后。此时赵廷隐虽居高位,但在后蜀新主孟昶削减武将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文治政策的政治形势下,仍觉临渊履冰。面对众多勋绩卓著的武将或是夷族或是流放的惨烈情形,赵廷隐最终选择了由武向文的转型。《花间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编纂成书的。此书虽由赵崇祚主编,但编纂《花间集》却是家族行为。赵氏家族动用大量人力编纂此书,不仅于词作内容风格的遴选上用力甚多,在编纂形式上更是用心良苦,以期投合孟昶的文学喜好,逢迎后蜀的文治政策,昭示武将家族的转型,表达忠心为臣之意。此是赵家身居要位、全身远祸的一种方法。①《花间集》成书后,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而广泛流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家族政治危机的作用。兹详论之。
一、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选词取向
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言“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②[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成都文类》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蜀先主孟知祥初到四川之时,面对“蜀中群盗犹未息”的局面,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之苦,安集流散之民,“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66页。蜀中的经济渐渐得到恢复。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④[宋]王明清:《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2页。他没有披挂上阵、血染疆场的经历,身上少有武将的专横,却多了文人的儒雅。其兵不血刃,通过“擒王”这一简单有效的方式,铲除了军事强将李仁罕等人,扭转了武人跋扈恣睢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针对五代时期军事将领常拥兵自重的局势,孟昶着力摒弃“武功”,提倡“文治”。其力戒前蜀王衍荒淫骄佚之失,颇勤于政,孜孜求治。罢兵修睦,与民休息,蜀中渐趋安定富庶。至广政二年(939)、三年(940),“边陲无扰,百姓丰肥”。①[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049页。
孟昶抑武事而扬文教,其提倡儒学,主张以文教礼乐治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刻经修史。孟昶“绍汉庙学”,②[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篆刻石经。后蜀石经肇刻于广政初年。宋曾宏父《石刻铺叙》言“益郡石经,肇于孟蜀广政。悉选士大夫善书者模丹入石”。③[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后蜀宰相毋昭裔曾“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④[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9页。蜀石经有经有注,为历代石经所罕见。清人杨宝臣言“蜀石经悉遵太和本,为唐代传写之遗,开成仅刻经文,孟氏并镌各注,故可宝贵”。蜀石经刊刻时间长,规模宏大,体例严谨,经注结合,堪为教民之典范。经书可为教化,史书则可为借鉴。后蜀重修史,设有史官史馆,修史制度比较健全。中原的五代修史仅是后代纂集前代在位帝王的实录,无后代修纂前代纪传史之举。而十国中的后蜀,既纂集本朝皇帝实录,又修撰前朝纪传史,是五代十国时期完整继承唐代修史制度的政权。⑤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0页。后蜀李昊主持修纂四十卷《前蜀书》,又主持修《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后蜀后主实录》八十卷。且有《蜀祖经纬略》一百卷,《枢机集》二十卷,合编当时朝廷的制诰奏议。孟蜀注重修史,其意不仅在借鉴前代兴亡,更在加强政治认同,乃是“文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兴办学校。学校的广泛设立是教民的重要环节,是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径。此在治蜀历史上有成功先例,可为孟昶借鉴。宋人吕陶在《经史阁记》中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⑥[宋]吕陶:《经史阁落成记》,《成都文类》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石室乃是西汉时期蜀中所设立之学校。礼殿指东汉兴平元年(194)蜀郡太守高公于文翁石室之东建周公殿,并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九经即后蜀所刻石经。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教化的推行失去了基本的场所。孟昶于是“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⑦[宋]张俞:《华阳县学馆记》。宰相毋昭裔亦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⑧[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此皆为培养人才,施行教化,维护统治。欧阳炯之忘形交景焕曾言孟昶“承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⑨[宋]王明清:《挥麈录》,第291页。其“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⑩[宋]张唐英:《蜀梼杌》,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100页。又“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⑪[宋]王明清:《挥麈录》,第291页。
第三,镂印书籍。后蜀镌刻石经的同时亦刻印经书以推广教化。四川在唐末已有很多书坊,但其刻印的书籍多是阴阳杂记、字书小学等。始至后蜀,毋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自毋昭裔雕《九经》及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文学复盛。⑫[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页。后蜀镂印推广书籍之举,带有恢复文道、提倡教化之目的,亦是孟昶文治政策的重要表现。后蜀刻印经书,也镂印文学书籍。在后蜀立国之际,如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⑬[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文学之道受齐梁之风的影响,大有凋敝之态势。前蜀后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常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①[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王衍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一时间浮艳之作风靡,社会风俗习尚亦随文道而凋敝。孟昶有感于此,故试图通过刻印书籍的方式,大力推行教化,引导官民阅读,以建立新的文学和文化风尚。宰相毋昭裔在孟昶的支持下,“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②[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769页。孟蜀所刻印之三种书籍,是现知总集、类书最早的刻本,亦是李唐时期官方提倡阅读的文本。《白氏六帖》注重历史的经验,《文选》注重文体与文辞,《初学记》文质兼备,三者皆与唐太宗的教育要求相吻合,故作为国家重要的教化书籍广泛推行。孟昶刻印推广此类书籍,亦是重教兴文之展现。
孟昶提倡文治,喜好文学,其品位高雅,不喜浮薄之作,《蜀梼杌》记昶“尝谓李昊、徐光浦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③[宋]张唐英:《蜀梼杌》,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6093页。但正如《花间集序》所言,其时教坊所歌之辞多承“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拙俗鄙俚、荒嬉佻达,与后蜀宫廷高雅的文化品尚不相符合。孟昶常创作诗词于宫廷奏唱,自是需要一部高雅的乐歌集以丰富乐伎表演之曲目,赵崇祚家族深谙于此,《花间集》之编纂必定要符合孟昶的文学喜好与文治政策,方可达到取悦孟昶之目的,是以《花间集》遴选词作首求典雅。在词牌的选择上,赵崇祚所录多为“乐府相传”与“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言之“乐府相传”乃是由汉魏古调衍变而成的古朴雅致的词调,其中以《杨柳枝》《落梅花》《采桑子》为代表。《接贤宾》《赞成功》《满宫花》等未见于《教坊记》,亦未见于敦煌歌辞的词调,即欧阳炯所谓的“豪家自制”。这些自制之词,亦可“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同样展示出《花间集》逐雅的文学品尚。《花间集》迎合孟昶喜好而重视文字与声律。孟昶对字声颇为看重,宰相毋昭裔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孟昶次子元珏的老师陈鄂仿唐李瀚《蒙求》、高测《韵对》,为《四库韵对》四十卷。崇文馆校书郎句中正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故《花间集序》开篇即言字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合歌”与“谐律”,明确指出编纂者对于词体内部音律的重视。“剪裁”与“雕镂”,乃是对文字与声律的反复琢磨。此说明如琢如磨的作品在经过“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挑选后,方能进入《花间集》,成为唱词的标准。《花间集》择录词作之时于声调文情的配合上亦十分留意。赵崇祚着力寻求声辞配合最佳的作品,在选调上注重区别刚柔哀乐,同时留意语调的缓急、叶韵的疏密、句子的长短,以增加词作的韵致。《花间集》于众多题材中独钟情于闺情与花柳,集中更多的是如顾敻“为一时艳称”④[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813页。般的小词。此类作品风格旖旎婉媚,情致幽杳绵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典雅的情致,既适合宴会奏唱,又符合孟昶所好。
孟昶崇文,《花间集》选词遂以典雅为基本原则,但值得指出的是,此仅为《花间集》编纂规则之表层,此书的编纂实本着一定的政治原则,以更好地与孟昶的文治政策暗中契合。
二、《花间集》选录“十八”词人的政治喻意
与五代时期其他词集不同,《花间集》收录十八位作家。此举看似无心,实是经过慎重的考虑 。因为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五代时期,“十八”皆非普通数字,而是带有一定政治文化内涵、人物群体指代的符号,具有丰富的内蕴。
“十八”带有政治文化意蕴或始于汉代。《史记》载汉高祖“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⑤[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28页。《汉书》记“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⑥[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7页。此十八人曾辅佐刘邦开疆拓土、一统江山,功勋卓著,故裂土封侯。这个群体是汉初天下的中流砥柱,于君民心中有崇高地位。是以“十八”这一数字隐隐带有政治色彩,渐渐深入人心。至唐,“十八”的政治意蕴愈加浓厚。唐高祖李渊因秦王李世民功大,前代官位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又开天策府,并于天策府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旧唐书》记“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又“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931页。李世民文治武功,其仿汉高祖封十八列侯之举,确立十八学士,此种行为带有以政治力量引导文化发展之意味,亦含有成人伦、助教化的政治动机。其后唐代君王多有效太宗之举,以显示朝廷对于人才的渴求与尊重。《旧唐书》记武则天时“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915页。唐玄宗开元时下诏以张说、贺知章等人为十八学士,命董萼画《开元十八学士图》,记录十八位学士的姓名、表字、爵位等,并亲自撰写赞文,以示推崇及颂扬。唐十八学士之说影响很大,五代“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都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9208页。宋代对“十八学士”亦甚推崇,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亲洒宸翰,画秦府十八学士像,书学士姓名,并御笔题诗二首,以示其延揽人才之心。北宋钦宗、李公麟,南宋刘松年也都曾创作或临摹十八学士图。④王隽:《“十八学士图”的绘制、衍变及其文化内涵》,《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
唐十八学士之说的影响还渐至宗教、文学等领域。佛教十八罗汉的说法,就是在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唐高宗永徽五年,玄奘译成《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介绍了十六位大阿罗汉。随着佛经的广泛流传,十六罗汉的信仰及图像流播开来。⑤于向东:《五代、宋时期的十八罗汉图像与信仰》,《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但或受十八学士的影响,十八罗汉的说法亦产生。唐人李华《杭州余杭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言“天宝十三年春,忽洒饰道场,端理经论,惟铜瓶锡杖留置左右,具见五天大德、十八罗汉幡盖迎引,请与俱西”,⑥[清]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34页。已经有了十八罗汉的记载。苏轼有《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禅月乃五代时期的贯休和尚,《十国春秋》记贯休尝“绘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貌,不类人间。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⑦[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672页。十六罗汉并两位大士,即为苏轼所谓之十八罗汉。苏轼又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言“蜀金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张氏即前蜀画家张玄,其同贯休一般“攻画人物,尤善罗汉”,他所绘制之十八罗汉,所本或是贯休的应梦罗汉。五代时期,“十八罗汉”渐渐成习,其中即或有着十八学士的影响。
“十八”对文学领域亦有影响,一些诗文集在编纂时,选录作家数量皆十八位。这些诗文集或与宫廷宴饮相关,或带有教化的动机,《花间集》同样带有这样的编纂目的,其编纂体例的设计,颇有可能受此类诗集的启发。如唐代许敬宗编纂之《翰林学士集》录贞观年间唐太宗、许敬宗、上官仪、长孙无忌等十八人的宴饮唱和诗50首,分为十卷。而《花间集》选录十八位词家500首作品,亦分为十卷,与之极其类似,或有《翰林学士集》的潜在影响。唐代殷璠录武则天末期至李隆基开元时期丹阳郡包融、储光羲等十八位诗人的创作而成《丹阳集》,书前序言指出其时诗道大有凋敝之态势,当崇尚建安风骨,反对齐梁绮靡,力求永明规矩,在诗歌的选录上体现出盛唐诗声律风骨皆备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带有变革风俗、化成天下的意味。《花间集》与之有着诸多相似:地域性较为明显,有着教化的目的,强调声律格调,选录十八位作家,作家中亦皆有宦达与不显者。这其中,暗暗透露出《花间集》对于《丹阳集》的借鉴痕迹。 可见,《花间集》这部文人词集选录的词家数量确定为十八位,意在借助“十八”之内蕴与影响,提升《花间集》的政治文化地位,以迎合后蜀的文治政策,其中既有仿效唐代君王“彰礼贤之重”的意味,也包含以集中十八位词人引领文学风尚之动机。另外,为发挥《花间集》引领文学风尚的作用,赵崇祚为集中所录的十八位词家皆标注了姓名(字)与职官,《四库全书总目》谓“于作者不题名而题官,盖即《文选》书字之遗意”。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23页。《花间集》意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告集中词人词作的地位,入选的十八位作者,是后蜀推崇的词家十八学士,此亦呈显出《花间集》“标准本”的地位。
三、《花间集》不录帝王词的政治暗示
《花间集》所录十八位词家中并无帝王,这与相近时期的其他词集有着明显差异。《花间集》的姊妹书《尊前集》录有唐玄宗的《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唐昭宗的《巫山一段云》之“缥缈云间质”“蝶舞梨园雪”,后唐庄宗李存勗的《阳台梦·薄罗衫子金泥缝》《忆仙姿·曾宴桃源深洞》《一叶落·搴珠箔》《歌头·赏芳春》等众多帝王词。就词之内容及风格而言,《尊前集》所录帝王词与《花间集》中词作相仿,然《花间集》却未收帝王之作,此或是赵崇祚出于政治因素而有意为之。
第一,《花间集》不录李唐帝王词乃是出于对唐皇室的尊崇。后蜀尊唐,《容斋随笔》言“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②[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孟蜀避唐讳,还曾模仿唐朝而刻印经书、修纂史书,此皆是其仰慕唐朝的表征。唐玄宗与昭宗均有词作,但此时词体文学仍为“小道”,尽管赵崇祚有意提倡,词之文体地位仍不可与诗文比肩。贸然将李唐帝王之词收至歌集中以佐酒宴清欢,似有不尊之意。且玄宗与昭宗的命运常引人悲慨,他们惨淡的人生结局从某种角度而言亦与音乐相关,或出于对李唐统治者的推崇,《花间集》略去了见证这些历史片段的帝王之作。
第二,《花间集》不录五代君王词乃是出于后蜀对地方性政权的否定。后蜀高祖孟知祥本为后唐将领,在后唐气数将尽之时割据四川,建国称帝。对于后唐来讲,孟氏当属叛臣,孟蜀不愿提及于此,故处处以李唐为尊,强调正统。孟昶避李唐君王之讳,却不避后唐之讳。《容斋随笔》言“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勗’、‘嗣’、‘源’字乃不讳”,③[宋]洪迈:《容斋随笔》,第49页。此表明孟蜀对于后唐不认同的政治态度。后唐庄宗李存勗“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创制了很多词作,庄宗溺于享乐,为帝仅三年有余便死于乱军之中,其词纵风流可爱,亦是亡国之音。或鉴于此,赵崇祚未收庄宗词入《花间集》,且对于李存勗所用的词牌《阳台梦》《忆仙姿》《一叶落》《歌头》等,《花间集》亦不曾收录。后蜀对后唐的疏离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花间集》不录前后蜀帝王词。《花间集》未录王衍之词,除不认可前蜀政权外,乃是借鉴前蜀亡国的教训。前蜀后主王衍失国与后唐庄宗有相似之处,纵然王衍“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④[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531页。词作流播广泛,赵崇祚仍未将其选入《花间集》,以防官员沉迷、百姓相习。《花间集》亦不录后蜀孟昶之作。孟昶喜制小词,其词亦工稳高雅。但唐五代时词之文体地位实难与诗文并提,词或为酒宴樽前聊佐清欢之具,或是文人相竞的文字游戏,常被视为“小道”。此种情况下,录孟昶词作入《花间集》中以佐酒宴之欢似不甚得体,将之流播于天下更易形成君王耽于乐舞之舆论,于统治有大弊。《花间集》既为取悦孟昶,自不能行此举。
四、《花间集》在后蜀的声望地位
《花间集》所确立的编纂原则极大程度上迎合了孟昶的文学喜好,亦与后蜀的文治政策相吻合,故此书编成后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在后蜀宫廷之中有一定的声望,不仅成为了唱词中的标准本,甚至刊刻以行蜀中,成为编书之人仿效的对象。
《花间集》现存最早刻本为南宋晁谦之跋本,双照楼覆正德本吴昌绶叙言晁谦之“跋称‘建康旧有本’、‘是正复刊’,盖其守郡时也”。①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页。绍兴本《花间集》的跋语乃晁谦之为建康府守郡时(1145—1148)所作。其言“建康旧有本”,表明在作跋语之前,建康已有《花间集》流传。清人杨守敬曾言:“《花间集》十卷,末有绍兴十八年晁谦之跋,谓以建康旧本复刊。避宋讳并避嫌名,如‘镜’、‘树’等字。”又言:“近时有海源阁翻刻本,言以淳熙十一、十二等年册与纸印行,其每卷题目尚是北宋之式,是此又为晁氏所节删,而其本‘镜’、‘树’等字,却皆不避,岂杨氏重刊时,将其缺笔补之耶?杨氏以藏书名,不应鲁莽若此。岂虽为南宋所印,而实刊于北宋,故不避‘镜’、‘树’等字耶。”②[清]杨守敬著,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68页。杨守敬依据《花间集》的避讳情况,认为此书曾刻印于北宋。然根据后蜀的文化情状,可揣度《花间集》的刊刻时间或早于北宋。后蜀发达的刻书业,使《花间集》的刻印成为可能。
四川刻书名扬寰宇,有“蜀刻甲天下”之说。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时官卫尉少卿,乃文官中地位很高者,其或曾参与刻印各种书籍之事。后蜀林罕有《说文》学著作《林氏字源编小说》,林氏自序言明德二年(935)“与大理少卿赵崇祚讨论,成一家之书”,又言“古人穷困湮厄而述作兴,罕也卧疾数年,饱食终日,思有开悟,贻厥将来,非欲独藏私家,实冀遍之天下。乃手书刻石,期以不朽”。③[清]董诰:《全唐文》,第9291页。林罕一生落魄不羁,而《林氏字源编小说》撰成不久即可刻石蜀中,颁示学界,或与赵崇祚的参与推荐相关。④闵定庆:《花间集论稿》,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69页。将书籍“刻石”远难于“刻印”,赵崇祚既可推动书籍刻石,刻印自身主持编纂的《花间集》当非难事。《花间集》成书的广政三年(940)亦是长于刻印书籍的毋昭裔政治平顺即将升为宰相的时期,其刻书之业也在这个时候不断扩大。刻书业如此蓬勃的环境中,《花间集》受到皇室肯定后刊刻流播以成典范,颇为可能。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乐曲类》录有《唐花间集》。⑤[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明代顾梧芳《尊前集引》言“先是,唐有《花间集》,及宋人《草堂诗余》行,而《尊前集》鲜有闻者久之”。⑥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9页。二人皆言唐时即有《花间集》。五代这一历史时期常被划入“唐”的范畴,若此,《花间集》极有可能在五代时期刊刻。明人杨慎《词品·毛文锡》言《花间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⑦[明]杨慎:《词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页。昭觉寺乃蜀宫旧址,此或可为《花间集》曾刊刻于五代的佐证。
《花间集》成书后,蜀中还出现了模仿其体例的书籍。后蜀监察御史韦縠曾编纂歌诗集《才调集》。此书成于后蜀广政六年(943)以后,⑧刘浏:《〈才调集〉编选者韦縠生平考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晚于《花间集》成书的广政三年(940)。《才调集叙》言“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⑨[后蜀]韦縠:《才调集》,四部丛刊初编本。该书选人一百八十家,选词1000首,亦分十卷,每卷100首。类似《花间集》选人十八家,选词500首。但别于《花间集》的是,《才调集》乃为千、百、十之数而收诗,是先划定一个框架,确定编者总数、分卷数而收诗,可能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书籍的编纂工作。《才调集》选诗内容上亦力合风雅,以救时弊。其专收可供演唱的“歌诗”,编纂的方式体例亦有模拟《花间集》的痕迹,或是为仿《花间集》而编纂的另一部乐歌集。《花间集》被时人模拟表明其确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地位,而这正是编纂《花间集》的赵氏家族政治平稳的佐证。
中唐以来,战乱纷起。黄巢祸后,疮痍满目。书籍或毁于战火,或散落各地。《花间集》别于温庭筠《金荃集》、王衍《烟花集》而进入北宋,并广为流传,同样表明此书曾于后蜀宫廷民间流行。是以赵氏家族“广汇众宾”、“时延佳论”所编纂之《花间集》,或受到了孟昶的肯定,昭示着赵氏家族迎合孟昶之文治政策、由武向文转型的成功,亦在赵廷隐力保家族平安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