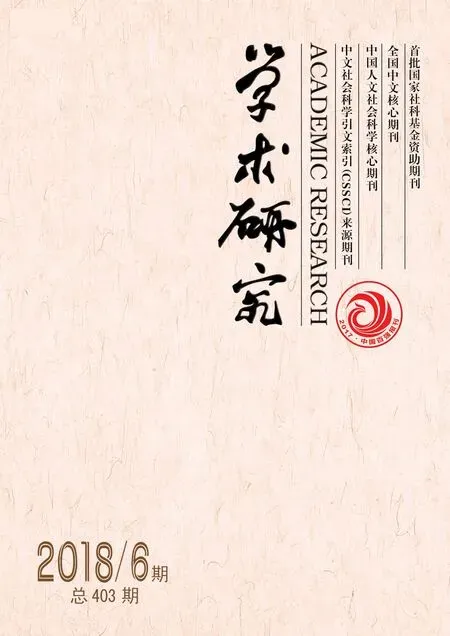贾谊与官儒时代的开启
关万维
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文学家和政治明星。贾谊聪敏早慧,年少弱冠即见过人才智,并因此得到举荐和重用,一年之内官至太中大夫;旋又因失意而抑郁甚至殒命,因此引来普遍同情和惋惜。贾谊在朝议中所表现出来的锋芒、机敏以及大抱负,给后人留下大才大智的印象;而传奇般的升迁与流星般的陨落,使其个人际遇有种宏图未展、大志未申的悲剧感。或许,正是这种悲剧感成就了古代政治思想史上贾谊的明星形象。对贾谊的看法,从他在世之日起就有很大分歧。《汉书·贾谊传》记同僚如此评价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虽然这些言论被《汉书》认为是对贾谊的诋毁,但却又被汉文帝采纳了,可见未必尽是空穴来风。而关于贾谊最主要的争议,则在于其政治思想属性:是儒家还是法家?抑或其他?研究贾谊政治思想的文章很多了,近来阅读贾谊的基本文献及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文章,发现尚有未竟之论,故而不揣浅陋赘述此文,惟望对贾谊的认识有所增益。
贾谊思想的复杂性是社会转型期思想家人格与政治结构发生冲突后可能出现的现象,其中既有历史性因素也有贾谊的个人因素。理解贾谊的矛盾,对理解汉以来思想史之人或事的复杂性有提纲挈领的意义。笔者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以《新书》为基础来考察贾谊思想版图,从这个版图来厘清贾谊思想格局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并以此为据判断贾谊政治价值观属性;二是根据《过秦论》与《新书》其他篇章之间的矛盾分析贾谊思想复杂性的外部原因;三是考察贾谊思想中残存的儒家属性及其局限,贾谊“官儒”身份的转变,既有社会背景的决定因素,也有他个人气质的因素。贾谊的转变,预示着儒学之官儒时代来临。
一、从《新书》看贾谊的思想结构
贾谊的基本史料主要有《新书》及有关逸文、赋、《史记》及《汉书》的贾谊传。其中《新书》是核心材料,最直接和全面地体现贾谊的思想、才情及政治主张。贾谊《新书》的真伪,自宋代以来出现了争议。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传世《新书》“其非《汉书》所有者辙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清季姚鼐《辨贾谊新书》云:“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今人侯外庐亦称:“他是少通诸子百家之书的,但他的书已佚失,现存《新书》乃后人杂凑之书,不足为据。”a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5页。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有关贾谊《新书》的章节,从《汉书·贾谊传》所引贾谊文字与《新书》的关系入手,给出更令人信服的考证,认为《贾谊传》采自《新书》而非今本《新书》据《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扩充而成,从而推论今本《新书》是可靠的。徐复观也就此为题的争议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新书》可信为贾谊之作。b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第112-116页。前贤的考论大致齐备,这里不复赘述,但附述笔者读《新书》所得的两个体会,作为基本采信《新书》的补充依据。其一,《新书》多篇屡见古字型及古字义,跟《汉书》情形类似,或可说明《新书》写作时间离《汉书》应该不远。其二,通览《新书》,文体浑然一格,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政治气质和人格性情,与《汉书·贾谊传》看见的贾谊优缺点大致吻合。
《新书》今存55篇,除去《过秦论》和《修政语》都是上下两篇,计有53个篇名。又,《汉书·贾谊传》中所载贾谊文有约600余字为《新书》未录者,与《大戴礼·礼察》篇部分文字略同,孙志祖《读书脞录》云:“本传中‘凡人之智’一段,与《大戴礼·礼察》略同,而《新书》无之,盖即第十卷《礼容语》上之文,而今本阙也。”孙志祖之论虽然只是推论,但既然《汉书》录之,必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也将之纳入基本史料,并沿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本附录,题为《礼察》。通览贾谊《新书》,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弱藩、等级、匈奴、铸币、礼制等,其中直接或间接论及弱藩、削藩的篇目最多,至少有13篇,在篇目数量上占55篇的1/4。以篇目为单位计,《新书》各篇论述的问题主要分六个类型。
其一,论弱藩。《宗首》认为目前的安宁,是因为大诸侯国国君尚幼,汉皇要及早利用天子之势行弱藩之力。《藩伤》与《藩强》二篇,都是直接表达了对于藩强的担忧。《大都》云: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大都疑国、大臣疑主,还是等级问题和强藩担忧。《益壤》主张扩大淮阳、梁两个直属皇帝的侯国,以牵制其他侯国——由此可见贾谊所计者是目前,并未考虑这两个得到加强的侯国对下任皇帝的威胁。《权重》所虑仍是恐诸侯势大则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五美》讲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则不知其所穷”:还是弱藩的事情。《制不定》论述地制不定的祸害。《审微》讲防微杜渐,明之者“除乱谋也远”,虽然没有直接讲弱藩,但实质还是担忧诸侯壮大。《壹通》建议罢黜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等关隘,以便人财流通,防诸侯作乱。《属远》讲淮阳、梁二国把边远的庐江作为属地,暗示庐江封侯,以避免淮阳和梁国二国借庐江来壮大自己的国力。《亲疏危乱》认为“疏必危,亲必乱”,担心诸侯王作乱。《淮难》反对给淮南王四个儿子封侯。以上13篇,不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对策,主旨均在于强化皇帝的势力,通过加大皇帝与诸侯之间的实力反差以寻求社会的稳定。贾谊认为,只有在皇帝对地方保持绝对优势,天下方可太平。
其二,论等级。《数宁》阐述贾谊对当今局势的焦虑:他认为奉六亲为至孝、治群生社稷得久飨为至仁、立法程为至明,但核心是“卑不疑尊,贱不踰贵,明若白黑”,强调等级的必要性。《等齐》认为强化等级可以规整社会。《服疑》主张:“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阶级》讲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尊不可及,同时君主也要敬重大臣、礼遇大臣以换取大臣的忠心。《俗激》所谓“移风易俗”即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孽产子》中一方面反奢侈之风,一方面反对富人享用天子皇家之服,既有安民的意思,也有强化等级的意思。以上6篇,主要分别通过观念、礼数、服装、风俗等因素突出皇帝“尊不可及”,强调皇帝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保持绝对优势方可社会稳定。
其三,论安民和经济。《忧民》劝行三年余一年粮之策,以备荒年。《时变》比较秦汉风俗,抨击商鞅之政对秦民风的破坏,认为对伦理礼仪的背弃是危险的。《瑰玮》一篇,贾谊认为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犯事,这是所谓“瑰政”。治疗这种瑰政的是玮术,实际上就是针对当时弃农从商风气的劝农论。《连语》通过列举史事阐述对百姓宽厚的重要性。《铜布》和《铸钱》均论私铸钱币的危害。《无蓄》认为灾荒是天下之常,应对灾荒从而稳定天下的是积蓄,对汉朝国库感到忧虑。
其四,论匈奴。贾谊并不满意汉初匈奴对汉廷咄咄逼人的局势,《解县》《威不信》和《势卑》三篇均认为这是一种颠倒了的关系。《匈奴》是贾谊系统论述匈奴对策的一篇,其主要对策就是所谓“三表五饵”,不述其详。
其五,论礼法。《辅佐》一篇,贾谊试图发凡起例,设计了他的理想朝廷,八种官职大多与汉官不同。这篇可能是贾谊改制的构想,也可能是任太傅期间给王太子灌输的制度构想。《礼》与《容经》二篇,前者讲礼序天地、通人情的重要性,后者规定各种场合的仪态。《立后义》主要讲立皇储的问题。《新书》之外的《礼察》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强调治理天下礼优于法,措辞精当,或是《过秦论》同期的著作。
其六,太傅课稿。以上五个类型文章均有比较明确的讨论对象,而其余各篇往往多是泛泛而谈,较多借春秋往事或圣王德行来阐述为政之道。徐复观认为《新书》主要分三个内容,第一是主动撰写的如《过秦论》,一部分是向文帝上书言事的,一部分是为梁王太傅时的教告问答之辞,这部分从第六卷开始。a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第116页。笔者比较认可这种分类方式,而其中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文暂且归类为“太傅课稿”那部分篇章,但笔者认为可能从第五卷开始即是这方面内容。如《傅职》与《保傅》讲对太子教育的重要性,《谕诚》和《退让》讲如何转败为功,《修政语》和《君道》述君王行圣德的重要性,《官人》提出君主的师友对合理行政的重要性,《劝学》和《道术》讲教化的意义等等,不一一概述。这类文章数量较多,或借古喻今,或谈对政治的看法,或阐述前代儒家的思想,似有先秦诸子风采,但又有一种“术”的意味,于人文主义、于思想史未见有新的突破,应该也是被后世学者以“不足观”为由而认为《新书》是伪造的那部分文字。
概览《新书》架构,贾谊思想版图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其主其次非常明白了:贾谊论弱藩、论等级、论礼法,虽然内容侧重不同,但都是主张加大皇权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是贾谊政治价值观的主要体现,不论从篇幅还是论述的充分程度,均占据着贾谊思想版图的主导性位置。这些篇章论述过程,贾谊几乎都充满激情和焦虑,可见这也是最令他关注的内容,最牵动他心灵的内容。贾谊不但将思考集中于此,也将情感倾注于此,贾谊思想的侧重点也就了然了。这些内容,在贾谊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如果姑且来量化这种比例,贾谊的思想结构应该是七分法三分儒,基本立场为法家立场,然后引儒以济法。
二、贾谊出仕前后的思想矛盾
从《新书》看,近1/4的篇目议论弱藩一事,6篇以上论等级制对社会稳定的必要性:突出皇权的绝对优势的重要性在贾谊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早期文章如《过秦论》中,贾谊对于封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过秦论》中贾谊认为秦二世有很多可使秦朝回避倾覆之灾的策略,其中首要的是“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秦国取得天下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继续推行郡县制,不效西周以藩屏周之策,“孤独而有之”,岂能不亡!“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过秦论》是为贾谊博得巨大声誉的作品,此时贾谊书生议政,尚有一定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贾谊强调“裂地分民”的重要性,但在身份改变、身居庙堂之后,裂地分民却成为最让贾谊坐立不安的因素。《新书》中关于诸侯的言论,均表示出分封诸侯的强烈担忧,如《权重》篇认为,当今“天下恬然者,遇诸侯俱少也”,刘氏诸侯反或不反者,取决于其强与不强,淮阴王最强,所以最先反;卢绾国最弱,则最后反,长沙因仅二万五千户,力不足以行逆,因此不反。这非人性有差异,而是取决于形势:如《藩强》篇所谓“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贾谊在周制和秦制这一矛盾中,并没有任何“制度创新”,只是提出“多封诸侯而少其力”,这可视为推恩策的前身。如《藩强》云:“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在贾谊看来,决定性因素是“势”,即侯国的实力,“势”决定一切。《权重》云:“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贾谊成为彻底的权势论者。
应该看到,文帝时代皇室与诸侯之间的确是缺少安全感和信任感,但造成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原因归结有三:其一,刘邦剿灭异姓王对诸侯与皇室之间的信任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其二,刘邦虽然效法西周分封建制,但缺少了必要的礼仪法度来构建起一种社会共识,给各个次级权力集团造就一种合法化的各自相安的法理环境;其三,在分封疆土时刘邦有较大的随意性,导致存在部分诸侯疆域过大而部分过小的情况。相比西周,周公制礼使得各种势力相安无事几百年,而刘邦未能给出这样一种法度。简单地说,刘邦的分封首先是粗放的,然后迫不及待地荡平异性王,进一步加剧皇朝天下社会秩序感和安全感的缺失。贾谊回避了这一历史动因,将诸侯王强则谋逆视为必然,因此不遗余力主张弱藩、削藩。《过秦论》中贾谊批评秦不信功臣,所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仕民”,然而身居庙堂时的贾谊不仅不相信功臣,甚至也不相信任何刘氏诸侯。
造成这种不信任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汉初的社会基础与西周初年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汉王朝面对的伦理和观念等社会基础条件与西周初年的情形完全不同,经过春秋的礼崩乐坏和战国的弱肉强食,古代贵族精神业已覆灭,功利主义思想盛行,权谋思想泛滥:这是价值观的迁改也是社会心理的变迁。其次,秦朝郡县制所产生的权力效应造就了新的历史基础,君主在新政治形态下得到更大的权力、更利于掌控天下的模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虽然汉初人们普遍把秦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孤独而有之”,但不论君主还是臣子大都不由自主地效仿秦制。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多封诸侯而少其力”可谓折中之策。贾谊此议是后来削藩政治的先声,目的非常明确:维护皇权、削弱皇权以外的社会力量。《藩强》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贾谊信奉的是实力,而不相信道德仁义。这与法家政治思想本质一致,只不过这是在汉初社会条件下的新表现。
在《新书》诸篇中,贾谊经常表现出一种迫切与焦虑。这一焦虑,容易让人误解是对社会的人道主义焦虑,其实不然,细察《新书》可知贾谊最焦虑的是皇权安危。《数宁》云:“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贾谊所谓“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埶,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冲决,国制抢攘,非甚可纪,胡可谓治?”侯外庐认为,“这不仅是汉初社会的矛盾,而且是封建制社会不能克服的矛盾。因此,贾谊理想中的政治治安及其阶级的正义心,被他所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讽刺了”,“封建贵族的超经济的剥削,和理想中的廉洁社会是不相容的,在汉代就以买爵卖子制为法令”等等。a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68页。
侯外庐对贾谊的言论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事实上贾谊文章中已经透露出他的焦虑所在:本末舛逆、首尾冲决。本末、首尾,也就是皇权与诸侯之间权势颠倒的关系,而非侯外庐所举的廉洁社会理想与超经济的剥削、买卖奴隶与农民暴动、社会奢靡等问题。而贾谊所焦虑的“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等问题,这是制度和礼仪的核心矛盾,是为了避免诸侯对皇权的挑战。简单地说,贾谊认为只有皇帝保持着对诸侯、对全社会的绝对优势,社会才可能是安全的。
徐复观认为,“盖削弱诸侯王以加强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儒法各家大体相同;但儒家有‘亲亲’的观念,不似贾晁两人主张的激烈。贾晁两人对此问题的态度,同出于法家精神,可无疑义。”a徐复观等:《两汉思想史》第2卷,第119页。徐复观认为贾、晁的削藩思想出自法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儒法均主张通过削弱诸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值得商榷。当然这是题外话,这里不做讨论。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贾谊憧憬着周代以藩屏周的封建制,而作为廷臣的贾谊则感受到来自诸侯的恐惧,千万百计削弱皇权以外的力量,这与商鞅政治基本原则相同。而削藩策则是周封建制与秦郡县制之间的一个折中,是秦朝“孤独而有之”导致迅速倾覆的教训和汉初已形成的皇权与诸侯对立的尴尬局面之间的权宜之选。
三、贾谊的儒家色彩与局限
贾谊较多地论述弱藩、等级对于社会安定的必要性,同时也谈论了道德仁义的重要性,而这部分内容主要分散在第五卷之后。从篇幅上来看,五卷之后的篇章差不多占《新书》一半;从内容来看,各种思想芜杂,其中较多谈历史、谈道德、谈处世、谈为君之道等等。这类文字较少为《汉书·贾谊传》载录,大概就是后世学者讥为“不足观”的一类,在《新书》中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前面所列举的第三部分论安民的相关篇章以及第六类内容的有关借古喻今的篇章,较多地讲到仁义礼法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是议论仁义道德,贾谊也不时流露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当然也有一些于儒家理义有所增进的思想,如佚文《礼察》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可以看成《论语·为政》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推演。《连语》篇云:“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予”,这是《新书》中为数不多的进步思想,虽然非贾谊的创见,但他既然秉承了先秦儒家这一进步思想,还是对他思想的儒家色彩有所裨益。再如《礼》篇云:“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报囚之日,人主不举乐”,这与《论语·颜渊》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一思想接近。总之,贾谊对经典儒家思想是有所秉承的,但像《礼察》那样比较中肯地表现出儒家政治思想的篇章并不多。《礼》又云:“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勿忍也”,对于“仁”给出更具体的含义,但也将“仁”的含义狭隘化。
后代学者对于贾谊的类儒家思想存在过度解读的情况,这是需要注意的。《新书·官人》论述其政治构想,如:“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斯役。”徐复观对这段文献的理解,就有过度解读之嫌:“统治权在皇帝一人手上,而行使统治权的意志,则出于师友,这实际是人君与师友的共同统治,甚至可以说人君是处于虚位,以持政治之统;而实际代人君来统治的,是品德才能在人君之上的师或友。”b徐复观等:《两汉思想史》第2卷,第133页。所谓“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霸”云云,表面上看是效法孟子的王霸之论,实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孟子所谓“王”,是指以圣德率领百姓兴旺者,意指合格的政治领袖,c关万维:《先秦儒法关系研究:殷周思想的对立性继承及流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211页。而贾谊这里将帝、王、霸并列,王已成为一个权力官阶。同样,贾谊重申“王者师”这个概念,看似与孟子当年呼应,但贾谊却有更明确的从政意图,有与王者共天下的企图。这也难怪他的同僚会给出“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判断。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中关于贾谊的儒学思想,大都有过度解读之嫌,这里仅举以上一例。
不管贾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强调仁德爱民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贾谊核心政治思想的,却是《新书·制不定》中表现出来的以仁为谋的思想。《制不定》云:“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全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由此可见贾谊的意图非常明确:仁义恩厚也好,权势法制也好,无非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在他看来,给百姓仁德目的是为了皇权稳固。这句话显然是贾谊思想的最短板,如果以木桶效应论,这才是其真实底线,贾谊所有关于道德仁义的思想动机都暴露了。为势而仁,为权而德,这是典型的权谋思想,是贾谊儒家思想色彩最大的局限。结合前面贾谊对于弱藩、等级等方面的强调,也就不难理解贾谊为何将仁德权谋化了。
显而易见,传统的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贾谊身上都出现了,这或是关于贾谊政治价值观取向的判断出现重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太史公自序》认为“贾生、晁错明申商”,而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则认为:“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司马迁和刘歆截然相反的看法,开启了这一分歧的先河,后世延续了这种分歧。而朱熹在对于贾谊政治价值观的定位问题上,给出更明确的判断:“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的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a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7页。而不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又均将《新书》列为儒家类。
从《过秦论》到《制不定》等文章,贾谊思想的转变非常明显。这不仅是贾谊个人的转变,也是思想史的时代性转变。商鞅的农战政治瓦解了传统的宗族社会、民间社会,传统多层次社会结构被简化,士人阶层失去生存空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单极社会,民众要体现其社会价值,就必须依附到郡县制体系的价值链条中,出类拔萃的贾谊走向朝廷是体现其社会价值的必要途径。以文名进而为官,贾谊的必然归宿与后来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同;一旦出仕为官,身份的改变难免影响其思想取向。这或许是《过秦论》与后来论弱藩诸篇之间矛盾的合理解释。但社会环境和身份的改变是否一定决定知识分子思想的高度呢?显然不能。贾谊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色彩,较之后来的董仲舒、仲长统等人都逊色很多,因此贾谊思想的局限既是时代的局限、身份的局限,同时也是他人格的局限,这种局限较多地来自贾谊天赋秉性的特质和人文情怀的欠缺。虽然先秦儒家诸子均有过出仕或者幕僚的经历,但是不论《论语》还是《孟子》甚至《荀子》,均有明显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可视为儒家的自由知识分子。从贾谊开始,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了整体性大转变。贾谊拥有了政治身份,失去人文主义立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人提出这样一种期望,但并不能真正实现。这一局面在皇帝郡县制时代实现了,而贾谊的转变成为一个很好的注脚。
四、综论:贾谊与官儒时代的开启
作为政治家,贾谊虽遭流贬,但此前无可谓不得志,《汉书·贾谊传》的评价恰如其分:“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被贬长沙或与其政治能力有很大关系而非全因同僚的排挤。贾谊一年连升三级,显然是个宠臣。少年得志的贾谊,在朝廷上锋芒毕露,有王者师的抱负,削藩策也为后来者所用。但是因为年少资浅,缺少阅历和历练,他提出的很多策略——最典型的如“五饵三表”之策——充满着天真的书生气,班固给予“其术固以疏矣”的评价,无可谓不精准。
贾谊试图通过削藩为皇权消解来自皇族内部的风险,通过服饰礼制的固化消解来自观念的风险,通过仁政施行消解来自民间的风险,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来保证皇室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但与典型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韩非等人的残忍、阴谋和敌视文明教化不同,贾谊有一颗脆弱之心、怜悯之心,主张教化、崇尚仁义。贾谊主张仁政,但他将仁政视为一种权谋,失去了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缺少孔孟所具有的道义至上的诉求。在贾谊身上也可看到他同代人最普遍的政治观念的徘徊:言称向往周制,行却效仿秦法;言必称仁政爱民,却不遗余力为皇权计。不论将贾谊视为儒家还是法家,均不能概括他的思想全貌,传统的儒家或法家,此时已发生了变化。不论从其身份看,还是从其思想结构看,贾谊都是郡县制朝廷兼采儒法思想的现实主义者,是权衡了当下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做出必要选择的政治家。简单地说,他的第一身份是“官”,因为贾谊兼采儒术,因此亦可称之为“儒”,但跟先秦时代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儒已经大不一样,亦官亦儒,即为“官儒”。而皇权政治模式下的“官”有着天然的法家性质,因此,在“官儒”二字中,“官”意味着必然承载着郡县体制的天然特质,具有“法”的必然属性,此为体;“儒”则意味着对经典儒家思想的选择性继承,此为用。
伴随着贾谊式“官儒”的形成,知识人也重新找到自身的定位,“官儒”完全取代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士人阶层。纵观儒者官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一,贾谊的时代,皇权政治基本稳固下来,早期藩国的存在,并未能改变郡县制的基本特质,天下一统成为基本模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重新定义,士人阶层失去独立生存的政治空间;其二,经过法家农战政治的打击,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为小农经济,社会层次简单化,传统的士人阶层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失去生存空间的士人,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在朝为“官”,在野为“道”。以儒家思想本身积极的社会态度而言,在大一统时代“在野为儒”也就失去儒的存在感。这种情况直到两宋之后,在市民社会阶层成熟之后,方才有所改变。
从思想结构看,贾谊虽然和荀子一样儒法杂糅,但是荀子有比较明确的民本立场,而贾谊的政治价值观则悄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当然取决于他与荀子身份上的差别。荀子虽然偶尔为官,但从身份与己任看,还属于自由知识分子;贾谊因《过秦论》闻名,跻身庙堂之后,不论身份还是己任,均属于“官”。因此,作为思想家,贾谊几乎未越前贤一步,且丧失了先秦士人阶层的理想主义情怀。贾谊阐述的先儒思想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贾谊重提“王者师”,却流露出与王者共天下的祈望;不论是弱藩还是礼制还是仁政,在贾谊那里并无存在根本冲突,都带着“谋”的色彩。贾谊思想的现状大致反映了汉初人文主义思想的停滞,从贾谊看先秦诸子到汉诸子的转型,是士人阶层的灭亡和官僚知识分子的产生,是古典思想家“子”时代的结束和亦臣亦子时代即官儒时代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