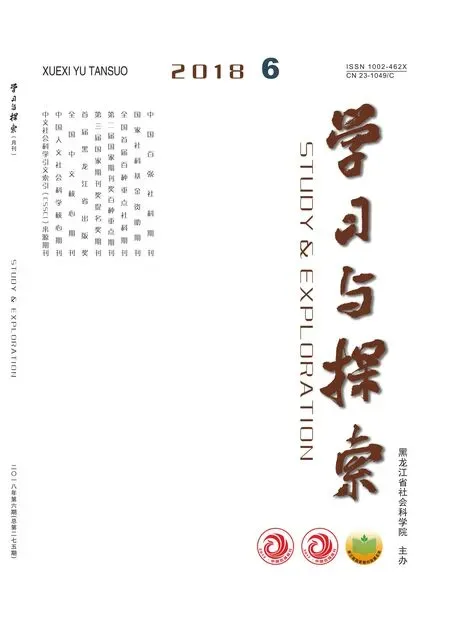淹没于瞬间里的非理性碎片
——对新媒体时代文化特征的反思
于 小 植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100083)
早在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就论述过媒体借助电子技术使人“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的问题,他说:“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1]20他认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1]34。
在纸媒时代,传播内容以文字为载体,体现为点对点的线性模式,囿于版面限制,其传播容量十分有限,时效性也远逊于新媒体。新媒体具有强大的复制、储存、编辑等数字化处理功能,可以将容量巨大的信息以光速传播,通过网络,新媒体如同一个庞大的多足动物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感知着由新媒体呈现的外部世界,人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审美取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媒体话语倾向的影响。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体现为传播方式的变革,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呈现了与以往文化不同的特征。
一、信息海量与行动乏力
与口头传播相比,纸媒传播不要求受众“在场”,这不仅扩大了传播范围,而且使有思想深度的内容以书籍等形式得以保存,在传播史上意义重大。对此,刘易斯⋅芒福德论述道:“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2]在纸媒时代,书籍、报纸、杂志的出版要经过审阅、排版、印刷等环节,在时效性和信息量上,远逊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发布,但是受众看到的信息一般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的,是经过审阅环节过滤之后的清明,积极、正面的信息居多,受众阅读后充满对社会的信任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彼此间的信任度也相对较高。
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传播方式的转变,电报传播信息比纸媒快捷,然而梭罗对此却充满了担忧:“我们急急忙忙要从缅因州修筑一条磁力电报线直达得克萨斯州;其实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需要拍发。……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打通隧道,让旧世界向新世界之间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黛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3]40电报给身处异地的个体间的联络提供了便捷,但是对于公共话语而言,电报能够发挥的正面积极作用有限,它甚至打散了公共话语,使其变得无序和无聊。
相比梭罗所处的时代,新媒体时代的技术更加彻底地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信息渠道的增多使人接收信息的机会呈几何状增长。然而,在这些信息中,有价值的新闻占比不高,更多的是低廉的、耸人听闻的娱乐信息。克林顿性丑闻、马加爵杀人、王宝强离婚,都曾引起大众对媒体奇观的追逐。一份新闻评估报告显示:1977—1997年的20年间,关于名人、趣味性故事和丑闻的特写从1977年的15.4%激增至1997年的43%,该报告认为新闻媒体在如何定义新闻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4]。新世纪以降,一方面,很少有媒体锐意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媒体执意走向娱乐领域,而不是启蒙;另一方面,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信息,全世界可以近乎同时通过电视、电脑或者手机观看奥运会,中国人可以与千里之外的美国人同时知晓美国总统的大选结果,然而信息对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信息不会使人放弃当日计划、更换近期目标,或者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因为这海量信息中能够对现实人生产生直接效力的信息很少。
实际上,人在海量信息面前更是无力和苍白的,信息或者事态不会因人的知晓与否有任何改变。“到处是海,却没有哪里可以供人游泳”也许可以形容新媒体时代的人在信息面前的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表面看来,新媒体笼罩下的地球如同一个村落,实际上,村民间除了共享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外,互不了解。纸媒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人所掌握的信息大部分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比”平衡,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新媒体时代,“信息—行动比”严重失衡,信息越多,人的无力感越强烈。每个人都知道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冲突不断,知道朝核试验,但是没有减小战争规模、去除战争风险的能力;每个人都知道大气污染、通货膨胀、老龄化、水资源短缺,但是拿不出解决办法;许多人听说过丝路书香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也只是旁观者,并不能从中采取任何行动。
新媒体作为产业,以拼接、复制作为技术手段,大规模、工业化地生产文化产品,创造媒体奇观,渴望轰动效应。人的眼球被媒体奇观吸引,头脑被海量信息填满,思想被束缚在“信息牢笼”之中,行动却空前无力,人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社会参与热情降低了,对现实世界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的态度。
二、意义消解与理性悬浮
以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为标志,人开始了建构自身价值理性的旅程。潘恩在《理性时代》中写道:“一切国家的宗教机构——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土耳其教的——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用以恐吓和奴役同类,用以确保权力和利益。”[5]摆脱教堂对人思想的束缚、探索真理、掌握知识、认知世界、建构理性都与纸媒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纸媒时代,文字发表以前要经过书写者的反复斟酌推敲,再经过编辑、出版商的审阅、把关,因此发表的内容一般逻辑严密、层次清晰、话题严肃、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文字具有“物含情物”的属性,对文字进行审美必须调动人的“统觉背景”,也就是说人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建构起相应的画面或者形象,才能完成“理解”。可以说,纸媒时代如果没有“理性”参与,人无法获得信息、理解信息,纸媒建构、完成并发展了人的现代理性。尼尔⋅波兹曼曾把纸媒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命名为“阐释年代”,他认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6]78
中国开启民智依靠的同样是纸媒大发展,清朝最后十年,为了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目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办报高潮,《通俗报》《女学报》《初学白话报》《演义白话报》《中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新白话报》《西藏白话报》等各种纸媒层出不穷。关于纸媒的功能,裘廷梁指出:“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古今中外,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7]陈子褒同样认为纸媒是开启民智、浚导文明的利器,他说:“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民智之开民智之通塞,每根由此。”[8]清末,纸媒在启蒙思想、宣传变法和推动白话文运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国民》《新潮》《湘江评论》等报刊作为启蒙大众的思想阵地,对于反封建、宣传民主革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把小说这一纸媒置于与家国同构的位置上。纸媒曾经承担的使命不仅是建构人的理性、启蒙人的思想,甚至是救亡民族国家。但在新媒体时代,重建人性深层意识的启蒙计划已经彻底衰败,衰败的原因并不在于“解构主义”的出现,因为有关“解构主义”的讨论仅限于理论界,衰败的原因在于人的“生命世界”被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完全殖民地化了。
纸媒时代,以文字为中心的表征是一种理性化的表征形式,与直观的图像相比,文字的“密度小”,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需要人用理性填补,主体的审美体验要通过自身对文字展开想象才能获得,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因为每个人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想象出的哈姆雷特是不同的,对哈姆雷特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但,一言以蔽之,对文字的理解必须要依赖智力和理性才能完成。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海量增长,鱼龙混杂,社会文化呈现了去中心、去层级的特征,缺乏理性深度和讨论价值。大众可以经常在电视等媒介上看到当下知名的政治家、公知,熟悉他们的样貌,提起他们,人们的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一张图像,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然而对于政治家或者公知的主张、观点往往所知甚少。大众对公知的了解从纸媒时代熟悉他们的主张变为新媒体时代熟悉他们的面孔,感性认识取代了理性认识,图像取代了文字,大众的理性参与度小,理性悬置。
新媒体时代,科技通过重构视觉经验的方式使人获得审美体验,形象代替文字,感性审美取代了理性审美。在新媒体时代里,观影、观剧取代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成了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文学作品时,人物形象是读者透过文字自己在头脑里建构起来的,而影视作品中,人物由导演指定的演员扮演,场景、道具、服装等一切细节由剧组包办,画面立体、音效逼真,新媒体的话语实践编织的网是严密的,呈现是完整的,受众只需调动感官系统欣赏,无须想象系统和理性系统的参与。
近二十年来,影视公司拍摄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雍正王朝》(1997)、《大贪官和珅》(1998)、《康熙王朝》(2001)、《天下粮仓》(2002)、《乾隆王朝》(2002)、《梦断紫禁城》(2002)、《神医喜来乐》(2002)、《百年沧桑》(2004)、《大清御史》(2004)、《大清洗冤录》(2005)、《少年嘉庆》(2005)、《康熙微服私访记》(2006)、《庚子风云》(2008)、《铁嘴铜牙纪晓岚》(2000-2009)、《七品芝麻官》(2011)、《武媚娘传奇》(2015),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取材于历史,然而目的却不是讲述历史、反思历史,而是戏说历史、消费历史。当下流行的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古装玄幻电视剧《花千骨》(2015)、《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更是以决绝的姿态为大众打造了一个毫无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虚拟世界。编剧任意想象,随意发挥,创造的主人公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可以活五千年,也可以死而复生。编剧想象力的无限放大导致受众理性想象空间的无限缩小,最后受众被迫彻底放弃自身理性,仅使用感官系统欣赏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
19世纪50年代,梭罗就对先进的技术有所警惕:“正如我们的学院,搞了一百种‘现代化的先进措施’;人们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实际并不总是有积极的进展。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追加股份,瞪大双眼盯着最后的收益。我们的发明宛如一些漂亮的玩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了许多正经的事情。”[3]40
新媒体技术打造的逼真画面、环绕立体的声音效果和各种“媒体奇观”,把形象直观地呈现在人面前,这种对影像的张扬和对文字的压抑客观上使人的理性、分析、想象、阐释变得无的放矢。人不再追求意义,追求的是视觉愉悦和快感体验。阿伦特认为这种娱乐满足的是人的生物性需要,她说:“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娱乐工业提供的物品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社会所消费,就像任何其他消费品一样。娱乐需要的产品服务于社会的生命过程,虽然它们可能不是像面包和肉那样的必需品。它们用来消磨时光,而被消磨的空洞时光不是闲暇时光——严格意义上说,闲暇时光是摆脱了生命过程必然性的要求和活动的时光,是余下的时光,它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是劳动和睡眠之后余下的时光。娱乐所要填补的空洞时光不过是受生物需要支配的劳动循环中的裂缝。”[10]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逐步过渡为消费社会,新媒体技术使大众文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洪流,对过去以知识分子为旗帜的启蒙主义构成巨大的挑战。知识分子身处于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象牙塔内,他们的研究、主张、口号日益成为其内部的自说自话。大众渐渐丧失了对纸媒的阅读兴趣,沉浸在新媒体呈现的物象的感官享乐中,不愿自拔。娱乐和快感体验主导的感性审美成为审美文化中的主导形态。新媒体使人进入了“只有外而无内;只有表(表面物象)而无里(内在本质);只有秀(show)而无隐(尤其是没有心理学上的隐情之隐);只有意符而无意指”的世界,使“现代主义里常表现的焦躁、孤绝、迷乱那种有关主观我(主体)的异化,现在则变为主观我的碎片化(或称主体之死亡)”[11]。
新媒体通过“浸透效果”影响乃至改变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消费是现代城市生产生活的动力和目标,名牌是商品这一符号系统中高档的代名词,新媒体通过广告促使人形成一种拥有的商品越多越贵,越幸福、越成功的观念。一方面,人对于名牌趋之若鹜,因为新媒体诱导人相信自己的身份、地位可以由使用的物品作为符号语言来描述和表征,自己的价值可以通过物的价值来体现和决定,因此人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跟随广告选择“名牌”,放弃对于商品价格、质量、性能等方面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广告商明确知悉重复和导向在人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因此不惜重金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重复播放商品广告,制造名牌效应。广告以美学为出发点,将漂亮的明星脸和欲售的产品放在一起拍成图片或制作成视频,可以吸引到大量的消费者购买。广告考虑的主要因素是画面感和如何吸睛,至于产品性能、价格等理性因素全然不在广告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一个成功的广告就是让消费者摒弃自我理性,完全按照广告的内容购买商品。
三、瞬间代替永恒
纸媒时代,作者慎重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书籍、报纸、杂志等固体形态中,以期产生永恒的价值。纸媒公开发行以前的审阅制度是信息内容正面积极的有效保证,因此,纸媒时代的人普遍感知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澄明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高。
新媒体时代,大量信息以新闻的形式呈现,碎片化趋势明显。这些海量新闻每天在有限的版面空间里争相占据“头条”位置,曾经炙手可热的话题是奥运会、拉登、刘翔、克林顿、文章、姚笛,几天后就被特朗普、马克龙、白百合取代,这些头条话题的目的不是促使人了解当下,而是促使人沉迷于当下,沉迷于永远处于流动过程中的当前。发展得快、变化得快,所以忘记得也快。人不仅忘记历史、遗弃历史,同时也逃离现在。德里达的著名说法是“archive fever”(档案热),新媒体的内在冲动就是把“当下”历史化、档案化了。用柯里的话来说:“此时尚在格林尼治平常时间下午6点20分,在夜幕尚未降临之前就已按某种标准将一些事件定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而将另一些事件排除在外。”[12]有限的空间迫使海量新闻匆匆被抛入历史。人对当下缺乏体验,有的似乎只是被封存和记录下来的“经验”。
马尔库塞曾经辨析过技术与艺术的二律背反:“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暗中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形式,而且也破坏了它的基础,这就是说,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使某些艺术‘风格’失去其合法性,而且还使艺术的要旨失去其合法性。”[13]技术的发展使高效成为现实,却使艺术品和文化产品失去了质感,陷入模式化的境态之中。
新媒体时代,多数家庭可以接收上百个电视频道,每个频道每天切换上万个图像,一个图像在电视上的平均呈现时间是3.5秒,人的眼睛应接不暇,人的头脑来不及思考新的图像就已经将旧图像取代。电视依靠图像传播,图像是片断的,传达的信息必然是支离破碎的,人很难将这些信息连贯起来构筑自己的历史视角,新媒体没有为人提供利于智力和理智发达的语境。“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罗伯特⋅麦克尼尔认为: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14]的确,与含义精妙、文字准确相比,电视新闻更强调画面感,视觉刺激代替了思想冲击。“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新闻媒体的作用便是把这新近的历史经验贬进过去之中,越快越好。于是,媒体的资讯功能可能是帮助我们遗忘,是我们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制。”[15]
电视上播出的讲座或科普节目同样不能深奥,任何理论、观点必须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述出来,因为一旦超出受众的理解范围,受众就会立即更换电视频道。高收视率是电视的本质需求,电视的关注点在于受众对节目的满意度,至于受众能否通过节目增长智慧不是电视制片人的主要关切。为了吸引受众长时间观看,电视在提供赏心悦目的图像、动听的音乐上煞费苦心,放松人的神经、慰藉人的情感,然而这一切只能概括为“娱乐”。波兹曼说“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6]98。新媒体文化是在消费社会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服务于消费社会,商品属性是新媒体时代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为了价值最大化,迎合大众口味、娱乐至上成为新媒体时代文化产品的显著特征。
新媒体时代信息量大,传播渠道多、速度快,既然把效率奉为圭臬,只能放弃对意义的追寻,人的思维呈现浅表化的特征。新媒体的广告不厌其烦地向大众讲述着流行和时尚,对流行和时尚的强调就是对消费的刺激和对物质欲望的蛊惑,促使人们将娱乐和享受作为价值追求。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奇观社会以广告为中心,遵循媒体文化被高度商业化的原则,通过休闲、消费、服务和娱乐的机制来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向奇观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实质上既是社会生活原有的、未被侵蚀的领域被迫接受商业化的过程,又是对休闲、欲望和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官僚主义式的控制逐渐扩展的过程。”[16]
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降低了人的批判意识,新媒体为大众呈现的文化产品是按“消费”定制的,内容和样态都由“消费”决定。文化产品是消费动机的体现,在“消费”这一最高宗旨的指挥下,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被消灭殆尽,呈现了“相同性”“重复性”“均质性”的特征。当下,人可以用手机点餐、订票、看影视剧、听音乐、拍照、网上购物、发快递、支付各种费用,日常生活的大量需求都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手机完成,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近乎相信这就是“幸福人生”,思考和追问是多余的,于是遵从代替了自觉。这样,工业由对自然的控制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人的控制。新媒体时代,文化被工业神权和商业至上主义砸碎,科技再将碎片化的文化片段粘贴和重组,当文化作为文化产品呈现时,主体“我”的存在感降低了,艺术的自主性消解殆尽。
结 语
1948年,乔治⋅奥威尔借小说《一九八四》讲述了对强权禁书、强权隐瞒真理以及剥夺人获得信息权利的担忧,断言强权统治下的人会在怨恨和恐惧中死去。时至今日,奥威尔担忧的事情似乎不会发生了,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不必禁书,人便丧失了阅读书籍的兴趣;人可以通过新媒体知悉各种信息,表面看来,人拥有知情权,遗憾的是,新媒体所呈现的大量信息是庸俗和重复的、充满了感官刺激、却缺乏理性力量,因此,新媒体时代,人的个性被淹没和遮蔽,人的主体性在文化工业生产链条上显得无足轻重。伴随人对新媒体依赖性的增强,新媒体成了文化生活的中心。
人的存在以获得“幸福”为目的,而真正的“幸福感”是要通过理性建构的。新媒体将理性拉下了神坛,文化呈现出无深度、浅表化、图像泛滥、拟像化的特征,完成了理性向感性的转向。新媒体时代,让人担忧的不仅是人的感性取代了理性、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更是人不知道什么是理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为什么不再思考。
当纸媒时代的文化被多媒体时代的娱乐悄悄取代,人对“精彩纷呈”的娱乐的裹挟习以为常,并逐渐适应了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披着高科技外衣的新媒体通过瞬间快乐的精神抚慰使人远离崇高、远离意义、远离历史、远离政治。人的结局是否是“娱乐至死”?社会是否将醉生梦死地消亡?波兹曼和赫胥黎的担忧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新媒体日益深入地介入了人的生活,在制造娱乐和传播娱乐中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新媒体文化是“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纸媒时代建构起的人的理性被新媒体瓦解殆尽,新媒体文化自身的理性处于未完成和待建构的状态。如果感官体验代替理性思考,娱乐信息淹没严肃话题,积极参与的主体变成被动接受的受众,那么对这种文化形态的反思和救赎就是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使命。我们有必要对海量的信息、感性的文化、瞬间的欢愉保持警惕。
[1]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3]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李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4] Peterson Iver,“Study Finds Less Traditional News as Outlets Seek More‘Relevant Content’”,The New York Times,Mar.16,1998.
[5]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田飞龙、徐维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7] 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
[8] 陈子褒:《论报章宜改用浅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9]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新小说》1902年第1期。
[10] H.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London:Penguin Books,1977,p.205.
[11] 《叶维廉文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12]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13]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14] 罗伯特⋅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983年冬季刊。
[1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乔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8-419页。
[16]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