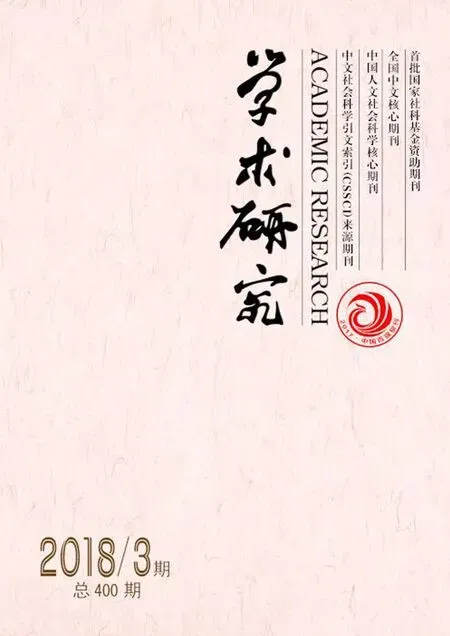马克思论“农村公社”的谱系逻辑与价值意蕴
吴阳松
“农村公社”又称农民公社、农业公社、村社、地域公社等,其本质上是指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进程中形成的,以地域性和生产资料二重性存在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世界各地普遍经历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公社”这一发展阶段的演进在东西方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在西方国家很快就被私有制取代而衍生出奴隶制与农奴制,而在东方社会却以一定的形式得以长期遗存和发展。“农村公社”问题贯穿马克思研究的全过程,全面梳理和明晰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演进谱系与认识逻辑,对我们更好地深化对农村公社问题的认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农村公社”在人类社会演进谱系中的方位认知
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探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如何说明人类社会第一阶段的生活样态和图景,科学揭开人类史前社会的“哑谜”,从而为唯物史观奠定坚实根基,这是马克思毕生的执著探索。而这一探索的重要载体,就是伴随着对“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认知而逐渐打开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但在创作该著作时期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认识仍处于朦胧状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沿用当时流行的指称共同祖先的共同体——“部落(Stamm)”一词,并与所有制联系起来,用“部落所有制”来代指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页。血缘亲属关系主导,社会结构限于父权制的扩大等,成为马克思对远古社会的认识。客观来说,这些认识带有浓郁的猜测和应然成分,其根本原因则是“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此时人们对史前史的认知主要依赖于有限的记忆和传说,马克思也无法跳出时代的窠臼。
19世纪50年代,农村公社问题逐渐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并成为他探索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窗口。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开始流亡英国。在英国,马克思读到了印度总督提交给英国国会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阻碍英国商品销售的原因是印度到处都存在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共和国”,即“村社”制度。“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1页。以村社制度为基础建构的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在东方社会,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和王权,是“国有”或“王有”,而实际上归属于生产者集聚的村社或公社,这些公社把土地分配给每一个农户使用,并定期对土地重新分配或调配,实质上是一种土地公有,这与土地私有的西方社会截然不同。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用“亚洲社会”、“亚洲式的社会”这一全新的概念来指代东方社会,意在区别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欧社会。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发现,激起了马克思浓厚的研究兴趣,并给予了他新的思考方向。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据黑格尔所发现的事物演进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公有制到私有制,再从私有制复归到公有制。但思辨的推理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如何从历史事实本身来印证人类社会的演进序列,这才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东方社会长期存在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发现,是否是人类演进的一个信号或依据,马克思给予了重点思考,并开始积极关注东方社会。
19世纪50年代后期,在深化《资本论》的研究进程中,马克思很快发现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并非只存在于“亚洲社会”,在欧洲历史上也曾经广泛存在过。“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页。农村公社并非一种地域性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普遍存在,这在事实面前得到了确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土地公有制和它的村社制度是考察史前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由此在《资本论》研究手稿中,马克思独立设置“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内容,对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公有制形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阐明。马克思根据公社的公有程度的不同,将农村公社分为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强调三者都是“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形式不一但本质相同,并具体分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东方社会长期存在的亚细亚所有制中,个人对公社从属性最强,与公社牢固地生长在一起,保存时间最为久远;在西方社会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中,个人对公社的从属性较弱,单个人已经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与公社的公有财产共存,是一种私有与公有兼具的公社形态,且不断受到私有制的蚕食而后被罗马奴隶制所取代;在日耳曼公社中,土地公有已经开始分裂并成为土地私有的一种补充形式,只限于“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公社作为形式而存在,“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地。”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2页。东西方存在的农村公社本质相同,命运各异。西方的古典古代城市公社和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很快就被私有制战胜而消灭了,“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它在各地都消失了”,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3页。而东方社会亚细亚式的农村公社一直保留到了近代,是农村公社的遗存和最新形式。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从空间上来说三者是并存的,而在公有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承序、衔接的关系,亚细亚式的农村公社较之于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农村公社而言,具有“先导地位”和“原型”意义。“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5页。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坚持把土地公有的亚细亚农村公社这一地域性概念赋予普遍性意义,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的起始阶段,从而有了这段名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重点关注了历史学家毛勒关于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制度史的相关著作,进一步深化了对农村公社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认识,提出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就是“欧洲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又一次强调“我说过,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的观点。
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前社会的研究进展,为马克思深入认识农村公社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养料,农村公社的谜题最终被廓清并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结合这一时期涌现的最新人类学新著,特别是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马克思明确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才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并由此与农村公社做了区分。“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氏族公社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共同体,而农村公社割断了这种联系。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586页。这样一来,农村公社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在人类社会演进谱系中的历史方位就得以清晰呈现:人类社会的起点和开端是原始氏族公社,这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并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家庭公社)两个阶段,这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而随后才被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所取代,从而“氏族公社(原生形态)—农村公社(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私有制社会(次生形态)”的演进图景就被完整地揭示出来。但是,农村公社这一东西方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古典古代的城市公社和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很快就被私有制战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奴隶制和农奴制;而亚细亚式的农村公社却得以在东方社会长期遗存和不断变异发展,直到19世纪仍广泛存在,是“古代类型的最新形式”。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以“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而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中,将原始社会分为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进而把农村公社定位产生于野蛮阶段的中级阶段,最终农村公社在人类社会演进谱系中的历史方位被清晰呈现,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演进图景遂得以完整揭示。
二、“农村公社”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知与未来走向
农村公社作为人类社会演进谱系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历史境遇。在西方社会很快被私有制所取代,而在东方社会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整套图样”,以“古代类型的最新形式”得以长期残存。如何看待这些长期残存的农村公社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论农村公社的又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探讨“农村公社”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走向,始终是站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宏阔视角下展开思考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民族史不断表现为世界史,在认识领域,“世界历史”观应运而生。较之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策源地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不是“世界精神”运动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过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由生产力发展及其交往程度所主导的前进过程,并必然表现为“落后从属于先进”的普遍式进步图景。“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关照下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普遍性认识。
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世界历史”演进的普遍史观被投射到亚细亚式的农村公社上时,东方社会的落后症结似乎被发现了。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农村公社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处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在其发展前途上持有当然的“否定”态度。“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2-683页。农村公社是东方专政制度的基础,使社会发展表现出一种强劲的停滞和难以逾越的制度刚性,从而使东方社会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而“根本没有历史”,因而马克思认为公社的瓦解是必然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从个人的感情来说”,看到农村公社的土崩瓦解,他为古老世界的崩溃而“难过”,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来看,“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具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3、686页。对农村公社的作用持有清晰的否定态度,明确了公社的未来是要建立起西方式的社会,从人类社会演进序列上肯定了农村公社瓦解的进步意义和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前,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史观视阈下对农村公社持有当然的否定态度,那么70年代后,伴随着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前途的论争,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农村公社发展的特殊新路径,本质上“有条件地肯定”了农村公社在未来社会演进谱系中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逐渐归于沉寂而东方革命蠢蠢欲动,显现出“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前途走向逐渐成为革命论争的焦点。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审视农村公社的作用与未来前途。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优越的地方”。特卡乔夫就公然宣称:“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96页。他认为俄国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俄国比西欧各国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与此相反,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农村公社是落后的代名词,俄国只能走同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以后,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以“历史必然性”为由,提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俄国革命的前途就是要“摧毁农村公社过渡到资本主义”。农村公社是必然“灭亡”还是革命的“优势”,成为俄国思想界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马克思极其重视这一新的时代论争,甚至自学了俄文,特别是通过对这一时期人类学、历史学最新成果的研究和思考,洞察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性。马克思发现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机械地套用到东方社会,比如不能用西欧的封建化进程来说明东方社会的解体,并严肃指出《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起源与进程的这一“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批驳了民粹派所主张的“落后优势论”,认为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自发生长出社会主义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不过是要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90页。如何回答农村公社的未来走向与时代作用,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它成为了晚年马克思重点审视的焦点议题。
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客观现实,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与民族特色和时代环境的交融中,探索性地回答了农村公社的未来可能。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各民族和国家已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使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够“嫁接”和“导入”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了民族性疆域而愈发表现出世界性特点,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必像在交往所处的隔绝状态时那样必须从头开始,在每一个地方都要独立进行。“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9页。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村公社正处于资本主义开创的有利的历史环境中,使农村公社完全有可能获得先进生产力的导入支持。如果俄国农村公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下成长,灭亡则是注定的。“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问题的关键是俄国农村公社被保留至今,处在“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页。这一有利的历史环境中,这就使得“农村公社”有可能“导入”和“嫁接”更为先进的生产力,而公社本身所具有的“公有制因素”这一特点,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有利条件,因而农村公社存在“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的可能性。
同时,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上高度肯定了农村公社的这一可能性。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只有在突破资本主义狭隘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得以形成,“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阅读相关人类学笔记时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印度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殖民化,在事实上也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9卷,第448页。西方殖民化无法推进东方社会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却不断暴露和显现,“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遭到了致命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9页。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这一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在现代历史环境下存在“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而这一可能性又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g《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本质上“有条件地肯定”了农村公社在未来社会演进谱系中的作用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三、马克思论“农村公社”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逝世后,俄国革命并没有如期发生,农村公社在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冲击下,不断遭到重创,最终并没有朝着马克思所期望的方向前进而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a《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8页。历史迈进20世纪,1906年俄国开始的斯托雷平改革给残存的公社予以最后一击并彻底摧毁了农村公社制度,继后的十月革命在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进程中,农村公社被集体农庄所取代,存续了数千年的俄国农村公社正式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但马克思论“农村公社”所散发的真理之光,具有极其独特的理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农村公社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演进的“钥匙”,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图景揭示具有“活化石”的作用。正如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分析“商品”开始一样,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是从“农村公社”开始的。马克思通过对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种公社形式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形态及其特点,分析了它与社会的次生形态即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之间的进化机制和演进次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来源得以完整说明,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演进的路径也得以清晰呈现。对农村公社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对我们认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活化石”的作用,而且对我们展望未来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即是农村公社的某种复归,“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马克思坚信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必然是古代社会在一种更高形式下的复活,是新型的更高形式的农村公社,这对我们展望、憧憬未来社会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二是通过对农村公社未来走向的理论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与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农村公社相比较,处于发展前端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东方从属于西方”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与普遍性,但“东方从属于西方”并非简单的线性向前,更不是“西方中心论”的注脚。马克思晚年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域与发展走向,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多维度考察,提出了一条农村公社未来发展的特殊性路径,明确了落后国家和地区跨越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本质上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普遍性的同时,成就了特色化和真正多样性发展的理论雏形,还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真相。这其中蕴藏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视角,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是农村公社在东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认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是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特质。“古代的公社,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农村公社阶段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以农村公社为载体的东方社会,在农业和手工业简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对商品经济具有本能的排斥,因而东方社会曾经是农业时代的楷模。而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演进,以农村公社为制度基础的东方社会的发展惰性就明晰地展现了出来。时至今日,农村公社的物质形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早已湮灭,但却以某种文化形式或多或少地得以存续。如农村公社中的宗族关系、种姓关系、地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等观念形态得以遗存,使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难以完全摆脱远古时代的阴影,从而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育。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在审视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运行差异的轨迹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直接,这是我们认识东方国家一个不可回避的显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