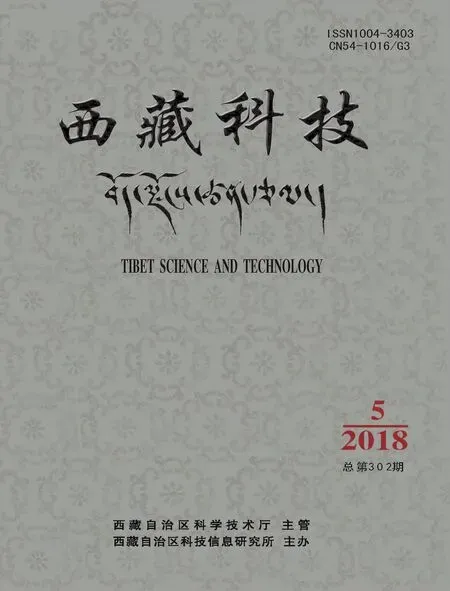浅谈西藏制陶技艺的历史与现状*
杨明芬次仁罗布班觉
(1.西藏自治区科技信息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8;2.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0)
西藏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的遗址或地点主要分布在昌都卡若和小恩达、拉萨曲贡、山南贡嘎昌果沟、琼结邦嘎、乃东的钦巴村、林芝红星、居木、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等地方。这其中昌都卡若是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年代较早,出土的陶片最多。卡若器类简单,器形以罐、碗、盆三类为常见,均为平底,不见圜底和圈足器。陶器均是夹砂陶,以夹细砂的陶质居多,其中一件单口双腹连体陶罐最具代表性。而拉萨曲贡遗址也出土了上万件陶片,代表着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1]。从挖掘的陶器来看,当时的曲贡先民已熟练掌握了慢轮修整技术,陶器的成型、焙烧、装饰等技艺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器形种类较多,以罐为主外,还有钵、碗、豆、盂、盘、杯等,都是圈足器和圜底器,平底器罕见,器耳比较发达。大部分陶器虽均为手工制作,但明显带有慢轮磨制的痕迹,其中以磨光黑陶最为精美。
卡若和曲贡陶器的装饰以各种线条构成的几何纹饰为主,体现了高原先民用线条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追求[2]。根据考古工作者对这两处遗址的年代测定,卡若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5300年之间,曲贡文化则是距今3500-3750年之间[3]。而阿里地区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和格布赛鲁墓地出土和采集的陶器属于前佛教时期,距今2000-2400年左右[4],绝大多数为泥质红陶,不见夹砂陶,但陶泥不纯,器型单一,以单耳圜底为主,不见圈足器,平底器少见,大型器较少[5-6]。札达县出土的陶器与卡若和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器型、器表装饰纹样、制作技术、以及制作方法上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陶器在西藏发展中的多样性。
到吐蕃时期,陶器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佛教的传播和弘扬,以及周边民族文化的吸收,使西藏各地的陶器在产量和品种上不断增多,陶器制造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在西藏发掘的吐蕃时期的墓葬内就发现不少陶器,如林芝地区出土泥质灰陶、褐陶、夹砂红陶,器种为小口细颈平底罐。乃东普努沟出土有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几乎全为素面,也有饰蓝纹,器种大都是圆底罐,或有耳和流。这些出土的陶器都是手制成型,作为随葬品可以证实陶器给当时吐蕃人的生活提供了众多便利,也深受吐蕃人的喜爱和器重,陶器制造业自然成了吐蕃手工业中较为兴盛的工艺之一[7]。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赞普赤都松为了得到饮茶的器具,曾派遣使者到唐朝求碗,唐皇帝没有直接给碗,而是派了一位制陶工匠。这位能工巧匠利用赞普从内库所取的陶土等原料,据说制造出连汉地都罕见的陶碗,其特点是“口宽,质薄,足短,光滑精细,有蓝色光泽”,在碗上绘有当地关于茶的来源传说和动物图案等,赞普还给碗起了名字。这则故事说明吐蕃在发挥本民族独特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唐人制陶技艺,积极完善和发展了本土的制陶技艺。随着佛教的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吐蕃王朝大兴土木,为建造寺院和宫殿烧制了许多砖瓦等建筑材料。值得一提的是现存于桑耶寺的砖有红、绿、黑三种颜色,其中绿砖施釉,形制有长方形、方形、梯形、子母口形等四种,釉薄而富光亮,瓦的内外饰有非常精致的图案和古藏文,施釉技术的出现将当时的制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显示出西藏制陶技术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吐蕃王朝灭亡以后,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各地的陶器品种不断增多,出现了许多图案及纹饰的内容与佛教密切相关的陶制宗教用具。据记载公元十一世纪修建夏鲁寺时,屋顶的汉式琉璃歇山顶和建筑用瓦原料均采自夏鲁寺附近的山上,釉药孔雀石和蓝铜矿则取自一个叫尼木彭岗的地方。当时瓦当的图案有花、狮、塔、宝石等5种。此外,还烧制了高13层陶塔和施釉陶塑狮像等,可见,制陶工艺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17至18世纪在墨竹工卡的塔巴制陶点也生产过各种工艺杰出的施釉陶器,成为全西藏制陶技术的典范。塔巴村曾出现过“杂堪钦莫”,是原西藏地方政府认定的制陶行业里的制陶大师,据说由“杂堪钦莫”施上等釉的陶器只有上等喇嘛及贵族才有权享用[8]。在1922年,塔巴制陶点就为修建罗布林卡金色颇章烧制了建筑用瓦。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解放前的旧西藏,塔巴村的陶匠们为西藏的地方政府、拉萨的大活佛、大贵族,以及各大寺院烧制过陶器,因而塔巴村在西藏享有类似于历史上官窑烧造场的地位。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西藏的陶器艺术未能出现质的变化,相反,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到,内地的瓷器、铁制、玻璃、塑制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的市场,冲击和制约了西藏陶器艺术的发展。根据上世纪90年代,西藏大学的其美多吉教授实地调查证实,当时西藏土陶器生产点有50余处,分布在拉萨的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尼木县;日喀则的江孜县、仁布县、日喀则市、昂仁县、拉孜县、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萨迦县、定结县、朗县;山南的曲松县、琼结县、桑日县、加查县、隆子县、错那县;昌都的察雅县、洛隆县、芒康县、八宿县、边坝县、贡觉县;以及阿里的普兰县[9-10]。制陶点主要分布在西藏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制陶人的生活主要以农耕为主,他们利用春耕前或秋收后的农闲时间烧制陶器来赚取副业的收入,而以制陶为生的职业制陶人非常稀少,陶器以露天烧制为主,包括平地露天窑、平台露天窑、竖穴窑、墙角窑等。虽然陶器生产点数量较多,各地制陶技艺层次不齐,部分烧制点的技术和工艺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水平[5,11]。
纵观西藏制陶业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的西藏陶器在其发展过程中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在工艺上与其他同期文化相比毫不逊色,之后的几个历史时期在陶器的装饰上不断地丰富,在制陶技术上不断地完善和提升。令人惋惜的是西藏陶器生产仍然是品种有限,工艺也处在手工状态,制陶业未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究其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吐蕃时期佛教的传入,也把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带到了藏区的社会,使得西藏手工业中的陶器和铁器等行业被列为社会最低阶层受到歧视,制陶技术只能在小范围中世代沿袭,仅仅停留在制陶人除了农业之外生计补贴的渠道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制陶村里年轻人愿意继承祖辈制陶技艺的越来越少,严重制约了西藏制陶业向技术型、专业化产业发展,远未形成独立的制陶手工业。其二是虽然上乘的陶瓦在部分寺庙和宫殿的修建中得到运用,但是陶器在制作上的粗糙和工艺上简陋使其未能成为上流社会和文人墨客所珍爱的工艺品,使得陶器制作仅仅停留在满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缺少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其三是藏陶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未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如公元7世纪出现的釉陶烧制工艺到了20世纪末濒临失传的窘境。最后,日新月异、价廉物美的现代化生活用品冲击着这一高成本低收益的手工陶器的生产和创新,使传统手工制陶业已失去其原有的优势。
基于藏陶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工艺退化、经济效益不高等瓶颈,政府加大了保护与发展这一传统手工技艺的力度,墨竹工卡县塔巴村烧陶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谢通门县“牛”村陶器制作技艺、扎囊县陶器制作技艺、曲松县陶器制作技艺和西藏红陶烧制技艺已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些民间力量也参与到藏陶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中,个别制陶村也尝试着通过既保留藏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又融入现代审美元素的新理念在开发贴近时代发展的新产品,以满足现代人的更高生活需求和时尚追求。相信西藏这一古老制陶工艺在新的时期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