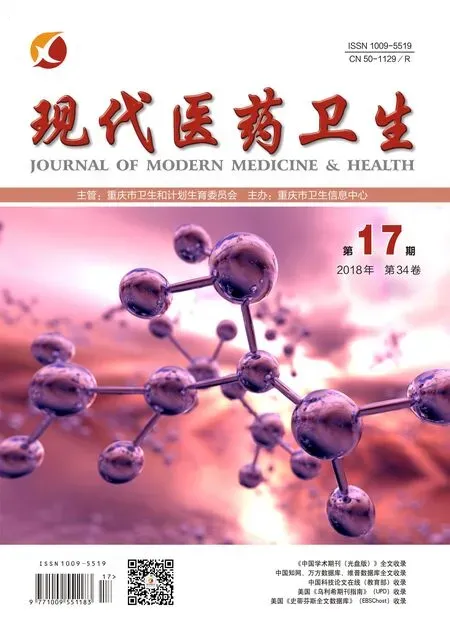异常肌反应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进展
张 杰 综述,谢宗义审校(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重庆400010)
面肌痉挛(HFS)是一侧面部表情肌发作性地不可控抽动,并且常以运动支中颞支、颧支支配的肌肉抽动起病,向下发展至颊支、下颌缘支的支配区域,严重者甚至有颈阔肌受累,抽动频率、持续时间可进行性加重[1-2]。HFS可以导致一系列的社交问题,发作性睑痉挛也会使阅读、驾驶、工作等受到干扰,发展到最后甚至可以引起患者的严重心理障碍。面神经的微血管减压术(MVD)现普遍开展,能明显降低绝大部分患者的肌肉抽动频率、程度、持续时间等,且可使部分患者的症状完全好转,总体来说极少出现并发症,有助于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状态[3]。异常肌反应(AMR)是一种仅对HFS患者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时可得到的肌电反应波形,可作为该疾病的诊断依据,且在MVD中有相当确切的指导作用。MVD术后的监测结果变化对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有一定的评估作用。本文就其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AMR定义及机制
AMR仅能在HFS患者中通过肌电监测发现。AMR会在面神经运动支的一个分支受刺激时产生,也能在运动支的其他分支支配的肌肉处得到记录[4]。AMR的确切机制仍然存在争议,目前有科学争论且广泛作为试验指导的假设有2种:外周假设指出,轴突间传递发生在血管神经压迫处,该处的面神经脱髓鞘改变导致顺向的轴突间传导冲动产生“侧方扩散”现象。而最新研究表明,AMR的起源为假突触传递发生于面神经的血管压迫部位而不是面神经核团;中心假设则认为在压迫处的血管产生有节律的搏动并影响该处面神经的轴突,长期产生逆向信号而导致面神经核团的高兴奋性[5]。2种学说能解释MVD中电生理监测中的部分AMR变化,以及临床结果中的延迟治愈等现象,但AMR的确切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2 AMR支持术前诊断
HFS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若有典型的一侧HFS表现,同时影像学检查(如MR增强)排除原发性病变,以及MR水成像明确有神经血管关系压迫,即可基本确诊。同时,HFS发作时,体格检查中可发现典型的“Babinski-2征”,即痉挛侧额肌、眼轮匝肌同时收缩,同侧眉毛明显上抬,同时眼睛闭合,这一体征特异度极高,但敏感度欠佳。另外,由于AMR是HFS患者的特征性肌电波形,可用于鉴别面部其他的异常功能性运动障碍。如果肌电图监测中可见自发的同步高频波形,则进一步支持HFS的诊断[6]。
由于部分患者在术前不能监测到AMR,目前其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HFS发生机制相关,故其有时难以作为证据,但结合上述因素,确诊HFS并不困难。
3 AMR术中监测的意义
面神经在脑内各段均有可能受血管压迫,其中以出脑干区(REZ)最常见,其他包括面神经在脑桥表面走形的部分、脑池段及内听道段等,各处的神经受压均可能导致HFS。因此,明确血管压迫的位置并对其进行充分神经血管隔离是提高MVD治疗效果的最重要步骤,术中AMR监测的效益归功于一定条件下对责任血管的寻找及对神经血管完全隔离与否的确认。
在MVD术中,当可疑血管与该处面神经隔离完全后,若AMR在肌电图上的波幅明显减小或无法再监测到,则此血管可以明确为责任血管,可避免识别错误或遗漏。同时,AMR在肌电图上的上述改变即表明神经血管隔离充分[7]。良好的AMR应用可以有效地指导手术进程,对于责任血管在REZ的患者,分离责任血管并垫上Teflon棉后,若AMR消失,则可以结束手术;若关颅后AMR再次出现,应再次开颅减压,因为绒球、小脑等的解剖复位可能导致新的责任血管再次压迫面神经;若血管压迫位置不在REZ,应认真探查面神经其他各段是否有可疑的压迫血管,并进行充分的神经血管隔离,之后若AMR仍存在,且余下振幅仍大于50%者,则需行神经梳理术[8]。若行完全的神经血管隔离后,且在肌电图上仍能监测到AMR,则行神经梳理术可以极其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临床表现。虽然短期内患者可能较容易发生面神经麻痹,但绝大部分患者长期随访时均能自行好转[9]。另外,有极少数患者的责任血管为静脉,由于临床数量较少,难以形成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故其更多AMR特点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
由于术中AMR监测可以帮助判断责任血管,避免不必要的解剖、牵拉等,减少神经血管损伤,因此并发症产生较少,但监测本身对MVD的临床结局并无太大影响[10]。同样,即使不行术中AMR监测,患者术后的临床治愈率在1周和1年以上随访的结果分别为83.33%、94.2%,与行AMR监测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尽管术中AMR监测并不能直接影响手术结果,但其临床应用价值仍然被广大学者认可,其作为一个特异性指标,在MVD中起客观的指导作用。但由于AMR在术中的可变性,导致其无法使每例患者受益,随着对HFS和AMR机制的进一步研究,AMR可能有更实际的效用。
4 AMR指导二次手术
HFS的MVD效果明显,有患者在手术结束后痉挛即可消失,但也有患者在术后数周、数月甚至1年后症状才逐渐缓解,其在临床上称为延迟缓解。对于这类患者,是否行二次手术及手术时机是神经外科医生关注的重点。其中,术后AMR监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有学者认为,延迟缓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减压不完全,包括责任血管的遗漏(尤其是被大血管遮挡的小血管)、Teflon棉滑落、填塞不当等。因此,对于术后痉挛没有立即缓解的患者,可在术后第1天行AMR监测,若AMR存在,则短期内再次手术减压可明显改善预后;若AMR消失,则可随访观察[12]。另外,由于Teflon棉不能被吸收,时间久后会黏附于面神经,致使分离困难,从而增加手术风险和并发症发生率,甚至可能切断面神经,因此建议二次手术越早进行越好。为确保减压充分,术中需仔细解剖面神经各个分区,尤其是面神经延伸至内听道处的探查;完全分离面神经营养血管,若术中血管痉挛则暂时停止手术,待缓解后再次操作[13]。
也有学者认为,二次手术不宜过早进行。对降低神经兴奋性一类抗惊厥药敏感的患者而言,面神经核过度兴奋可能是其主要致病机制,这类患者在术后需要数月来使面神经核恢复到正常兴奋阈值,继而出现延迟缓解。因此,如果患者术前对抗惊厥药物敏感,且术后症状持续,二次手术至少需延迟3个月以上[14]。
HFS的MVD术后症状缓解不满意,绝大多数是由于减压不充分引起。为解决其根本原因,有必要行二次手术,尤其是术后AMR仍然存在的患者。有研究指出,行二次甚至多次手术的患者,其中大多数患者能有持续的痉挛缓解,即使相对容易发生并发症,患者总体而言能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且其与年龄、再次手术时间、痉挛复发时间等无关。手术最好由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操作[15],手术时机目前仍存在争议,但无论早期还是晚期手术,临床预后均能得到明显改善。
5 AMR对预后的评估
已经明确AMR在HFS MVD中的必要性,其对临床预后的评估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仍然存在着争议,争议内容包括AMR在MVD中的早期消失对临床预后的影响,以及术后AMR消失是否预示较好的临床预后等。因此,明确AMR变化与临床预后的关系可进一步评估患者的临床结局,为再次手术的必要性提供更精确的指导。
5.1 术中AMR早期消失与预后的评估 术中AMR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MVD的效率。但遗憾的是,若AMR在神经血管减压前(包括硬脑膜打开前后及随后的脑脊液释放等)消失,且直到手术结束时仍未再监测到,则表示此类患者将不能受益于AMR对责任血管的判断和是否减压成功的确认。减压前后的AMR消失与临床预后的关系逐渐被学者所重视。
由于AMR在减压前消失且不再出现,术中监测对手术将无任何指导作用,因此,随后的责任血管寻找、减压充分与否等只能依靠术者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术中AMR早期消失可能是由于面神经压迫程度较轻,因此,此类患者术后HFS更有可能即刻缓解。同时,由于压迫简单而减少了某些不必要的操作,故发生的并发症较少[16]。然而,另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指出,在术后1周、3个月AMR在减压前后消失与临床结果无明显关联,而术后2年及以上AMR在减压后消失组的痉挛缓解情况较好[17]。
术中AMR早期消失的原因尚无定论,其与临床预后的关系在不同研究间也大相径庭。但是早期AMR消失对手术操作者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其没有客观指标的指导,一切仅能凭借经验,为避免手术失败,需要进行更仔细和更完整的解剖及减压。因此,外科医生的经验和术中认真仔细的操作也对手术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AMR早期消失,仍需继续监测AMR,以免AMR在余下的手术过程中再次出现,避免责任血管遗漏,指导充分减压。
5.2 术后AMR消失对预后的评估 HFS患者行MVD后,大多数患者即不能监测到AMR,也有患者出现AMR的波幅减小甚至较术前无改变。
经过充分减压后,17%的患者会残留AMR。这些患者在术前并没有典型的临床或电生理特点,且术后AMR消失与否与并发症没有明显关联[18]。有学者针对随访时间、术后效果等条件进行严格的纳入和排除原始资料,最后汇总1 301例样本进行meta分析,对于减压术后随访3个月及以上、AMR全部消失的患者其HFS缓解率是部分或没有消失患者的2.48倍[19]。因为AMR与血管压迫的相关性,术后AMR即消失表明REZ区的责任血管搏动产生的直接刺激消除,因此在短期内随访中有着较好的临床结局。由于神经血管压迫部位的长期病理生理改变,使得该处面神经产生微损伤,因此,即使充分减压后AMR可能仍然存在,但随着数月对微损伤的完整修复及面神经核高兴奋性的逐渐稳定,HFS症状逐渐好转。因此,术后AMR消失与否和长期预后并没有明显关联[18,20]。
术中AMR监测对临床预后的评估作用有限,MVD术后AMR消失的患者中有89%的患者能够被治愈,即使AMR术后仍然存在,也仅有24%的患者HFS无好转[19]。在充分减压后,即使AMR存在也不一定预示临床预后不好。
6 监测方式的发展
有时AMR在减压开始直到结束均不能监测到,或者即使在减压之后典型波形持续存在,又有术中波形不稳定或被手术操作影响等,均使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为增加AMR的监测率、稳定性等,提供更有意义的手术指导和预后评估,学者提出了新的联合监测方法。
“最佳监测”:刺激患侧面神经颧支,在同侧的其他所有运动支分支处接受记录,这样即使一支波形消失或不稳定,其他分支处可能监测到相应波形,可提高AMR阳性检测率和对减压结果预言的准确度,减少延迟治愈的发生[21]。“双重监测”:同时刺激颧支、下颌缘支,且同时在相应分支支配的肌肉处接受并记录肌电图,双重监测的AMR检出率较高,相比传统监测更加敏感。就结局来看,双重监测的患者无论术后AMR消失或存在都有着较好的临床效果[22]。联合ZLR监测:ZLR仅在术中刺激责任血管的时候出现,并且减压成功后即消失,其客观指导作用更直接、更精准,相比单一的AMR监测,联合ZLR监测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在以椎动脉为主要压迫血管的“串联型”患者中,术中ZLR监测对责任血管的寻找更是起决定性作用[23]。鉴于AMR可能在减压前即消失,此时对判断责任血管和减压成功与否的帮助非常有限,联合ZLR监测能提供更有价值的术中指导,尤其是可能存在多根责任血管的时候[24]。
在改进监测方式的同时,某些影响监测结果的因素也应该避免,但某些因素的改进和具体化能让监测更加有效。传统刺激强度范围大多为1~30 mA,由于范围较小,可能忽略AMR某些模式的改变,为达到AMR的引出阈值,推荐刺激强度范围增加到1~100 mA,这样可以提供更精确的临床评估作用[25]。另外,即使气管插管后继续行部分神经肌肉阻滞麻醉,其对AMR的监测成功与否并没有影响,并且在LSR监控过程中,如果保持麻醉后肌肉松弛监测的T1/Tc比例为50%,还能减少肌电图上自发波幅的产生,提高监测精确性[26]。
7 小 结
综上所述,AMR对于HFS的MVD指导意义巨大,但AMR变化对临床预后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争议,有待研究更加全面和有效的监测方式。在进一步明确HFS和AMR机制后,AMR监测指导下的MVD才能进一步改善HFS患者的临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