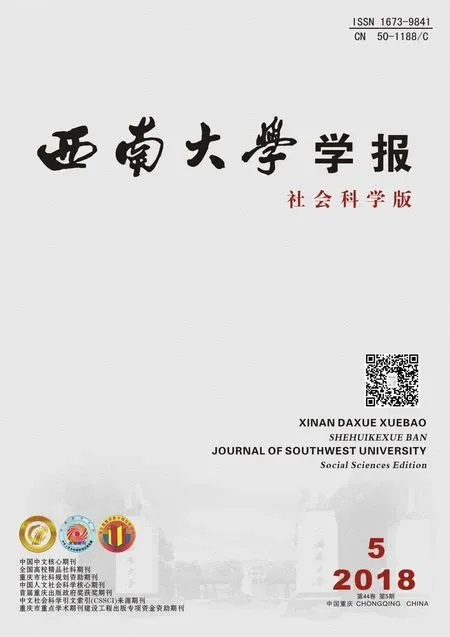国家起源水利说的再检讨
苏 家 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水利说意在强调水利工程的建设及管理工作对于促进古代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从一类更大的范围内来讲,实际上可以算作是文化生态学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探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水利说的演进
在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及人类学诞生之前,18至19世纪的许多社会及经济学家就已经在他们关于东方社会的研究中,开始探索水利建设活动对于古代亚洲社会的影响以及这类影响是如何最终导致东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1]2。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参与了这类讨论,譬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曾多次提到,波斯和印度等诸东方社会的“专制政府”身上所肩负着的对于维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而言至关重要的水利责任。而且像“监督用水”这样的责任,虽然毫无疑问地涉及全体社区成员的利益,但从一开始起就不得不委托给某些个人来执行,而这些社会成员在长期执行此类公共职能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并因维护这类特殊利益的需要而与原来出身于其中的社会日渐分离,于是这些人就构成了社会上最早的统治阶级或者叫做统治阶级的雏形[2]154,186-187。
这类论述中所涉及的社会内部的分化与兴修水利工程等生态环境改造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继续引起学者们尤其是进化论主义者的关注。战后,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在自己复兴文化进化论的努力中,为与博亚斯(Boas)学派所强调的文化传播论相抗衡,模仿摩尔根的格式,也提出了一套人类社会的演进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就有关于灌溉工程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具备重要意义的论述。斯图尔德认为,对于这些地区来讲,灌溉用水的意义,要大于农业生产中金属工具的采用与犁耕的发明[3]17。后来,经斯图尔德之手,还编辑出版了专门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灌溉文明发展情况的论文集。与此同时,包括在聚落考古学研究中较为著名的秘鲁维鲁河谷调查项目(Viru Valley Project),以及受此启发而在中美地区开展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与德哈康谷地(Tehuacan Valley)调查活动等田野实践,也都与当时学术界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有关[4]5。
稍后,德裔美籍学者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又译“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多年以来针对“治水社会”也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毁誉参半[5]195-198[6]187。30多年之后,中文译本面世,又引起了国内学者之间的热烈讨论,这其中批评否定者居多[7]。不过无论对于这部作品的具体态度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东方专制主义》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威特福格尔个人的代表作,而且在水利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是书中,威特福格尔认为,因为兴起于干旱或半干旱的自然环境之中,所以对于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新、旧世界诸早期文明而言,保障农业用水的供给就成为一个社会能否存续下去的关键,也成为撬动社会进一步复杂化的根本因素。而在这样的一些地区,水资源的存在形式也是比较特殊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以及黄河等流经这些区域的大河,一方面以自身丰沛的水量为灌溉农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正是因为水量巨大,且存在着周期性发生洪灾的威胁,因此要想变害为利,驯服这些大河使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就必须动用集体的力量,通过在人群内部开展合作来兴建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而要完成这样的工程建设活动,没有一个可以对于众多劳动者发号施令的统一的指挥中枢,那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个居于全社会之上的指挥中枢因水利事业的兴建而成立,并在此后的时期内负责对于这个复杂的灌溉体系进行维护。因为在这样的地区,脱离了灌溉系统的支持,农业生产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而农业的丰稔则是当时条件下维持社会复杂化深入发展的前提,所以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讲,农业生产活动是显化于社会中其他各部门内的一切权力及财富形式的最终源泉。因此谁负责管理灌溉系统,谁便获得了控制这一系统的机会,也就是获得了控制农业生产的机会,而对于这一要害部门的控制,最终会演变为对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其他各个门类的全方位控制。这种使得政府体制以外的个人及团体显得无足轻重的全方位的控制,用威特福格尔的术语来讲,就叫做东方专制主义。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威特福格尔那里,所谓“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亚细亚社会”或“东方社会”等其实都只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而已,它们的指涉对象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或从生产模式或从地理分布区域等方面对于该对象所显现出的某一类特点作了强调[1]13,19-20。
二、水利说的内在逻辑
所以对于解释早期复杂社会的演进来讲,水利说的着眼点在于,在人类为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必须与之打交道的诸种先于社会本身而独立存在的因素当中,恰巧存在着这样一种因素,它同时具备下述两个特征:首先,它可以被人类控制,即便只是依靠简单的木质或石质工具,这种控制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很久也已经实现了;再者,这种控制只有在开展大规模协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单凭个人、家户或是若干邻里之间的临时性的协助,根本无法对其实施类似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为实施控制,就必须在人群之中开展合作,而为开展合作,又必须首先建立起某种形式的集体组织,而一定形式的组织,无论是这里谈到的治水组织还是再分配体系中的生产或分配组织,总是意味着某种领导权的存在[8]136。这种领导权的存在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组织”是一类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形成的功能群体,并且为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其内部业已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分工关系以及制度化了的权力与支配关系,而且对于历史时代的早期来讲,这种支配关系还往往带有全人格的特征,即强调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9]193-195。
在与农业时代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因素当中,只有水并且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内,以大河或大湖等为载体的稳定的大规模的水源才同时具备上述两种特征,即既可被改造又不可为个人所改造。而气候、地形或土壤等其他同样可以对于农事活动造成影响的诸多因素,要么是难于以人力对其进行改造,譬如气候或地形等,一直到工业时代,这些宏观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人类对之往往无能为力,要么是虽可进行改造或干预,但这类活动所涉及的技术过于简单且劳动强度相对较小,因此仅仅依靠个人或家户的经验与力量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协作,譬如对土壤进行施肥等[1]3-6。同样可以借助小范围内的个人劳动即可实现的还包括浇灌园圃,因此虽然一样涉及对于水资源的利用,但与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不同的是,因为不需要协作,自然它也就不能引致社会与政治领域内产生深刻的变化[1]9。
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威特福格尔对于社会复杂化动力的解释,的确有着失之于简单粗糙的嫌疑[10]67,但部分学者对此所作的批评,似乎由于将这一简单化的体系做了进一步的简化而引致后来者对于问题的理解趋向模式化或片面化。
这其中最容易为人所忽略同时也是经常遭到误会的一点就在于,认为威特福格尔主张,在灌溉活动与东方专制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直线的机械的对应关系[6]193,196。但实际上,东方专制主义虽然被认为曾存在于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但它的产生仍然是需要一系列特定条件的,这其中除了水源本身的因素之外,还要求当地社会的发展水平“在以耗取自然资源为生的经济水平之上”,同时又要低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此外还要“远离雨水农业的强大中心”,只有在类似诸般因素皆具备的情况下,“对水源不足的环境有特殊反应的人类才会朝着特殊的治水生活秩序前进”。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水利事业与专制主义政治形态的产生之间,所存在着的是一类可能而非必然的关系,所以威特福格尔才着意区分出了“治水农业”与“浇灌农业”两种都是建立在灌溉活动基础之上的但却可以引起完全不同政治后果的农业生产类型[1]2-3。
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区别,正好可以在地理上同处于东方世界的古代中国和日本为例。虽然日本社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来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且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粮食生产也是建立在灌溉工程的基础之上的,但最终,在国家形态上,它却并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奉行着东方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帝国[6]189-192。相反地,包括威特福格尔在内,许多有志于比较研究的学者们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古代日本的国家形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与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世纪的西欧而不是它的那些东亚近邻更为相像[11]704-706,而温带欧洲在威特福格尔的划分体系内,则是雨水农业而非灌溉农业盛行的地方[1]10,13,22,36。可见,即便在这个常被笼统地视为是简单且机械的体系内,作为上层建筑基础的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也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双方发展出同一类政治结构。同样地,在分别奉行雨水农业与灌溉农业的社会之间,受到其他若干因素的影响,它们也有可能表现出相似的历史轨迹。
所以虽然与其他诸种自然因素相比,水被威特福格尔看作是一类蕴藏着特殊政治意义的资源,但实际上水也罢,灌溉工程的存在与否也罢,都不构成威特福格尔解释体系内最为核心的那个环节。真正占据着这个位置的,是大规模的分工与合作的必要性。正是这种必要性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了政治领域内进一步的复杂化过程的发生,也就是为这种必要性服务的更多更精密的服从于统一指挥的政治结构的生成,而水只是触发这种必要性的媒介而已,并且不是所有对于水资源的利用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照此思路,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存在着其他某种可利用而不可为个人所利用的生计资源的话,那么完全可以预见,它很可能也会像古代社会中那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样,引致类似的政治结构的建立。实际上,我们将会发现,分工与合作这样一对关系以及为提升其效率而施加于这一对关系之上的组织化的管理策略,是频繁重现于许多关于社会复杂化运动机制的分析中的一类核心议题,而且研究活动中的这种趋势至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首次出版的年代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确了。
三、考古学及人类学中的案例
正如恩格斯在其作品中所勾画的人类历史早期所发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一样,斯图尔德与威特福格尔等人在战后初期所提出的这套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管理为基本动力的解释体系,必然也面对着如何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而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理论假说总是要接受来自于田野材料的检验与审视,并在与各类反例的冲突中获得发展与完善。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兴起,向来被视作是水利说的经典案例,然而近来的考古活动已经证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普遍兴建,不是像预想的那样发生于国家机构建立之前,恰恰相反,这类建设活动是在国家出现之后很久才发生的。这样的话,仅就发生时间的先后来讲,也不宜于将之看作是导致国家形成的原因。再者,就必要性来讲,尽管傍依大河的灌溉活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对于两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类工程在建设与维护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由国家政权出面来做统一的规划,却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该地区一些当代农业社区生产状况的调查,似乎并不支持早先理论研究者们的预想。在这里,小规模合作兴建的不受社区以外势力干预的灌溉工程,就已经可以满足当地农事活动的实际需要了,并没有必要为此建构出某种跨社区的集权式的管理机制。换言之,归于国家政权所掌握的那种集中化的管理因为仅具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也就不能再被简单地看作是水利需求的当然结果了[12]222。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古代的埃及。在这个以往被看作是典型的由治水工程而引发专制主义国家建立的案例中,人们发现,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维护也是在地方层面上完成的。尼罗河的水量足够丰沛,沿河各社区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调节本地的用水额度,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受其他社区的影响,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开展那种跨社区的合作。而且似乎自史前时期以来,关于用水问题即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且简单的规则,而这套对于维持农业生产来讲至关重要的规则,其实很少受到国家政权本身的兴衰存灭的影响。那么反过来讲,自国家起源时期以来,包括用水问题在内,统治着埃及农村基层生活的这套生计模式既然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历尽政治风波而岿然不为所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坚持让它独自来为包括国家形成在内的各类政治事件的发生负直接的责任了。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首先,尽管在埃及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民事及刑事法典多次被修订以适应社会生活中各类新出现的情况,但这里面却很少有关于灌溉用水的全国性法令;再者,就从现在已知的古代埃及官制体系来看,在当时的政权架构内,也并没有这样一个负责对于国家水利事业进行集中管理的部门。因此,尽管法老的权威不容置疑,而且古埃及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很早就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与国家管理手段的集权化,但这些政治成就的取得是否就像水利说所主张的那样,是线性地得自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特别是起源于这类建设活动对于超越于社区层面之上的集中化的管理体制的需求,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则是很值得怀疑的[13]109-111。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一类极为平常的现象,宏观的理论体系与局部的具体材料之间发生若干龃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摩尔根与恩格斯,到怀特(Leslie A. White)与斯图尔德,再到他们二人的学生塞维斯(Elman R. Service)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至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赖特(Henry T. Wright)与厄尔(Timothy K. Earle)等人,对于他们中的每一位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所提出的类似体系或者解释模式,几无例外地,后来的研究者们总能在浩如烟海且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取自世界各地的实证材料里面,找到一些为现有的体系所不能予以完满解释的案例。但这些貌似反常的案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于原有的体系做一简单粗暴的完全否定。相反地,牴牾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提示我们,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原有模式做出一些必要的改进。与全盘否定不同的是,这意味着要在革新的过程中有所保留,而要保留的,正是原有体系内合理的成分,至少也是理论构建者当初希望能够以此方式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特定的研究思路或方向[14]9-10。
就像这里提到的水利说一样,斯图尔德与威特福格尔等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提出的理论,即便在当时的学术界看来,也仍然是将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过度简单化了,但在普遍否定的声浪中,直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也仍然还是有关注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者们在反复探讨水利工程建设与社会复杂化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15]65。因为很显然,下面这样一条基本的逻辑前提很难被推翻,这一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现在已有以及未来将要出现的一切社会制度,总是受着生产发展情况的制约[16]3。这些制度中当然包括国家机器在历史上的出现,而对于农业时代来讲,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无疑就是种植业,因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批出现的以及在这个时代中曾经取得过最为辉煌的发展成就的文明社会,毫无例外地全部都是定居的农耕社会。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上埃及以及秘鲁沿海等这样一些原生型文明形成的地方,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生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若说水利工程的兴建与当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没有关系,首先从逻辑合理性上来讲就是不可想象的。
再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虽然大型水利工程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普遍出现可能是在国家社会之中而非之前,但正如国家本身要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样,水利工程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理所当然地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因此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乎国家起源阶段的考古记录中的缺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当时就不存在这样一类的设施。只是在那个阶段,正如国家本身一样,它们的规模可能还比较有限从而不易进入发掘者的视野。此时的水利工程本身是简易的,修建与维护它们所需的劳动投入与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管理机制同样是比较简单的,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这一阶段上,作为一类新近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国家机器自身的结构同样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运行机制,而且规模一样很小。所以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类相互影响的共同演化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无端地设想在最早的城市国家出现之前,苏美尔地区就存在着规模可观的水利工程,并把这类大工程当作是催生出那类小政体的原因,这是不合理的。同样不合理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着归于当地社区自行管理的小规模水利工程,并见识到了这种工程对于生计经济的重要意义,便认为在这个领域内不存在着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好,在古代中国也好,乃至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古代国家社会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当政治实体本身实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成为了可能而且在国家政权的统一规划与管理之下,它们所能发挥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与自身的规模一样,也是那些村落级别的同类设施所不能比拟的[12]222-223。
再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在追溯人类起源的史诗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对于水的利用。而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宗教信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于既往历史经验的曲折反映。在这些史诗中,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因为神想把自己从修造并维护沟渠这类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于是人被创造了出来,他们用镐和锹建筑圣殿,开挖沟渠,垒砌河堤,生产出食物以赡养妻儿老小,并供奉诸神。而为了惩戒,甚至是毁灭人类,神所能用到的,也仍然是灌渠中的水。先是持续的干旱,河渠干涸,土地因普遍盐碱化而大面积减产,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的流行。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击垮人类,于是神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通过持续的暴风雨而使河渠泛滥。在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传说中,明确提到了建造并维护水渠是神的决定:“他(指神)虽然没有终止一年一度的洪水,但与此同时,也开挖了沟渠,引来了清水,并畅通了各条小运河以及水渠……”
从苏美尔人开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世俗统治者一向被看作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以执行神的意志的名义来统治国家,所以神所关注的,即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自然也就成为国家日常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这在当时颁布的法令中有着明确的体现。以第一部成文法,即乌尔纳姆(Ur-Nammu)法典为例,其中就规定了损坏水利设施的赔偿额度。其文曰:“若一人淹灌了他人已种植的土地,则应按照每伊库(iku)土地三古尔(gur)的量偿以大麦。”其中,“伊库”是当时的土地面积单位,折合3 600平方米,而“古尔”是容积单位,一古尔等于0.3立方米。而在三个半世纪以后,在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涉及到水利设施的律条就更加繁密。所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国家政权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关注以及对于灌溉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的期盼。
除了灌溉之外,人工水网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是沟通各个城市国家之间的便捷通道。苏美尔是一个虽然地势低平,但却资源匮乏的地区。金属、木材以及各种石材,譬如红玉髓、绿松石以及天青石等都需要从附近山区、伊朗高原甚至更远处进口。而人工开挖的运河和沟渠,就成为这些舶来品在进入苏美尔地区之后,于各个城市之间进行再次分配的通道,也就是贸易路线[24]120。在属于拉格什(Lagash)第七代统治者古地亚(Gudea)的一枚圆筒形印章上,就曾提到,他曾驾驶货船经由新开挖的水道前往另一座城市尼娜(Nina)。而这条由幼发拉底河供水的运河所连接起的,还不只是拉格什与尼娜,吉尔苏(Girsu)和扎巴拉姆(Zabalam)等也都是这一水系所辐射的重要城市。至于船的形象,就像与水密切结合的创造之神恩奇(Enki)的形象一样,遍见于这一时期的印章、浮雕以及模型等各类造型艺术之中[25]32-34。
即便是在像古代埃及这样的地方,虽然统一国家的出现可能并不能直接溯源至管理水利事业的需要,但作为组成国家的各个诺姆(Nome),它们的经济基础却是建立在灌溉农业之上的。所以尽管诺姆之间的战争被看作是对于理解埃及国家的统一来讲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但它们一样要以各地方上用以保障农业丰稔的水利工程的存在为其前提。因此,上述两者之间只能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不能说是完全无关。况且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在埃及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说就没有出现过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大型的水利建设活动,譬如第十二王朝以及托勒密时期对于法尤姆(Faiyum)绿洲的改造活动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显例[13]41,111。在被视为中王国黄金时代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执政时期,他继续开挖旨在沟通法尤姆洼地与尼罗河的运河,最终建成了一条16公里长,1.5公里宽的水道,古埃及人称之为Mer-Wer,意为“大运河”。同时还修建了与之配套的水坝,用以调节尼罗河向洼地的供水量。等到这一系列水利工程在其继任者阿蒙涅姆赫特四世(Amenemhat IV)时期完成的时候,运河顶端的加龙湖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每年可接纳130亿立方米洪水的大型水库,同时,运河沿岸及法尤姆洼地也因水而兴,成为古埃及历史上著名的粮仓[23]。
更多的案例来源于人类学的研究。因为考古学虽然可以借助于地层叠压关系向我们展示一个较长时段内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动趋势,但因为早期的水利工程往往规模有限,因此并不容易留下清晰的证据。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可以适当弥补这一缺憾。
厄尔曾经对于夏威夷人从酋邦到国家的发展历程开展过深入的研究。就他的观察来讲,威特福格尔等人早年间提出的理论体系的确有着再予完善的必要。因为在当时,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生计问题被看作是推动水利工程兴建的主要动力,而在这类兴建的过程中则衍生出了对于协调及管理工作的更高的要求。这种客观需求使得专职的管理人员的存在成为必要,同时,水利设施的兴修有利于对抗不期而至的水旱灾害从而可以使农业部门的产出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丰裕的水平上,这就使得那些脱离了直接劳动的管理人员有了长期存在下去的可能,而“长期存在”的结果则导致了权力结构的固化。厄尔并不反对灌溉设施在夏威夷复杂社会演进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只是强调,对于原有的理论模式来讲,我们只是注意到了经济需求,譬如人口压力所引起的生计问题,对于政治结构演进的意义,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政治集团借助于对特定经济设施,譬如灌溉系统等的有意识地操纵或利用,以期达到稳固甚至是深化政治结构分化的目的。
厄尔认为,在与欧洲人初步接触的时期,夏威夷本地的灌溉设施就其规模或结构来讲,并不像早期殖民者所描述的那样宏大复杂。即以考艾岛(Kaua’i)为例,哈莱利(Halelea)地区的44个灌溉系统的平均面积仅有2公顷左右,在这其中,仅有唯一的一处其面积超过5公顷,与此相对,则有多达16处的面积皆不足1公顷。而在单一的一个灌溉系统内,平均劳动人手也不过5人左右,除了一个个案之外,其他所有灌溉系统的范围也都没有超越所在社区的领地。因此有理由推想,传统的夏威夷的灌溉系统应该是小规模的,同时也是以所在社区为服务对象的。再从内部结构来讲,夏威夷的灌溉系统也并不复杂。作为火山岛,夏威夷群岛的地势普遍是中间高而四周低,因此河流都是从中央山地沿着各条山谷流向大海,这每一条山谷即为一个社区所盘踞,而灌溉系统也就依地势高下而修建在河流两岸堆积有冲积土的谷地中。一般来讲,人们会用河卵石在山溪中筑坝,这样坝体后侧的水面就会被抬高,然后从这里引出一条干渠,再由干渠分枝出更多的二级渠道深入田间,但无论是干渠还是二级渠道,都不会很长,或者直接任由溪水从地势更高的地块溢入下方的田地,直到最后又流回下游的山溪,因为那里地势更低。在这样的水田中,人们种植芋头,这是当地人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而在围拢水田的高埂上,则栽培香蕉、甘蔗和甘薯等。因此,无论就规模或结构来讲,修造并维护夏威夷这样的灌溉系统,只需要若干农户之间的合作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政治势力的参与。但实际上,夏威夷的酋长们不仅非常关心田间水利,而且往往要派遣下属的管理人员(Konohiki)亲预其事。从水渠的布局、开挖,梯田的营造,日常维护,洪灾之后的重建直到整地备耕等,这些管理人员都要亲自组织并监督其实施。之所以如此,按照厄尔的理解,是因为相对于旱地,水田的产量更高而且稳定,可提供50%至70%的剩余产品。对于自然经济体系下的一般农户来讲,这些剩余产品的意义不大,因为按照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AgeEconomics)中所讲的,承担直接劳动的农民只需要留足全家口粮并下一年的种子就够了,并没有动力去促使他们投入更多劳动以期获得更丰厚的产出。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政治集团来讲,剩余产品的多寡以及是否可经常性地获得这样的剩余产品,就变得十分有意义。夏威夷的最高酋长通过次级酋长,后者则通过地产经理人来从农民那里逐级征缴这些借助于水利设施的兴建而获得的剩余产品,之后将其用于举办宴飨以犒劳劳役承担者,赡养包括次级酋长、地产经理人、武士以及附庸工匠等在内的依附于最高酋长的各类专业人员。所以对于夏威夷来讲,虽然水利设施既不是维持家户生存所必需的,其规模及复杂程度也不会对于管理体系的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它们所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却构成了夏威夷早期复杂社会中政治经济体制内的关键一环。酋长们热衷于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渴望自其中攫取更多的剩余物,以便为自己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提供物质支持,而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复杂程度及效率自然也获得了提升[22]75-82。
四、对于未来研究的启示
就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以及近代夏威夷等处的案例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时是否存在着上述关系,而在于我们该怎样去理解水利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等经济行为与政治体系的演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的经验来看,这种关系肯定不是单因的或是单向性的,同时因为社会复杂化本身是一个在结构上分层级而在时序上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我们也不能奢望仅仅依靠考察最基础的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方面,譬如用水情况等,就可以凭此洞悉上层结构内部所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动的直接原因。换言之,治水活动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它可以对于上层结构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所能允许出现的具体结果可能是多样化的,并且是假手于其他中间因素或环节才间接性地波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活动的;最后,这种影响还是双向互动的,即政治行为也有能力对于包括水利事业在内的经济活动产生作用。
类似于这样,对于多因环境下,政治与经济行为之间所表现出的双向互动关系开展研究,并不始于20世纪的系统论者。实际上在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就曾颇为专注地探讨过这类问题,即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该怎样去理解唯物主义一贯主张的经济基础所具备的那类决定性作用[17]731-734。后来类似的论点,在斯图尔德与威特福格尔之后,又出现在普莱斯(Barbara J. Price)与库斯(James S. Kus)等人关于欧洲人到来之前,中美及秘鲁沿海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对于当地复杂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分析中。在这些分析中,正如库斯谈到的那样,我们既要追究是哪些生态及社会或文化的因素促进了复杂灌溉系统的出现,也要研究这些系统在投入使用之后,对于人们的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4]3-60[18]45-56。
这种影响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基本的经济生活领域内,像在古代也门这样的地方,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帮助统治者将不毛之地变为丰产的绿洲,在这些布列于沙漠边缘的绿洲上不仅聚集着大批的耕作者,而且也逐渐成为往来商路上的重要驿站以及为周边游牧民所向往的朝圣地。所有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被看作是神对于统治者的护佑,它赋予了后者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因此尽管与大型灌溉工程并存的,还有旱地农业、梯田以及归本地社区管理的小型灌渠等,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它们都足可以提供赡养大批人口所需的粮食,但像马里卜大坝(Ma’rib Dam)一类的大型水利工程也仍然有着进行重复建设的必要性。因为这除了能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当地最早的国家形成的时期以来,这样宏伟的工程便成为了政权威信与统治者能力的象征[19]64-67。
正是因为灌溉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活动有着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之外的重要意义,所以在有的情况下,社会精英阶层会出于自身政治利害关系的考虑而对之进行主动的干预,以引导其沿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因为处在这一关系中被决定的一方就被动地接受当下的经济现实。一般认为,复杂的政治结构的生成首先有赖于经济上剩余产品的经常性存在,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农业劳动者组织,在投资行为上经常表现出浓厚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力干预的话,劳动所得能够保证家庭成员衣食无忧也就可以了,农民们并不会主动地去追求产出的持续增长,在商品经济不甚发展的相对闭塞的地区,这种停滞的趋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要打破这种固步自封的局面,就需要有一种追求增长的动力,然而这种动力,既不可能来自于惜力如金的直接生产者本身,也不是出于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真正需要农业生产超出个人、家户或本地社区的实际消费能力而迈向一个更高水平的,是在社会上新出现的贵族阶层,或者更具体地讲,是由其设计出的以各种形式的税收为聚敛渠道的政治集团对于财富的追求。为了满足这种外来的强加的追求所造成的负担,社区中的每一个家户都必须增加劳动投入,动员更多家庭成员更长时间地参与田间劳动,同时兴建并利用包括灌溉工程在内的各种农业集约化生产手段以获得产量上的增长[20]314-315。
就像随着酋邦与国家一类的复杂社会在的的喀喀(Lake Titicaca)湖畔的胡利·波马塔(Juli-Pomata)地区兴起,大量的劳动人手向台田(Raised Field)区麇集,从而显著改变了当地原有的聚落分布格局。据估计,在高峰时期,该地区69%的人口都依靠台田系统的生产过活,而这种形势几乎与复杂社会兴起之前的情况正相反。在当时,有59%的人口生活在台田区以外,践行着一种低投入同时也是低风险的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从聚落实际上也就是人口的地区分布形势来看,这种生计模式在蒂瓦纳科(Tiwanaku)国家崩溃之后,又重新在农事活动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可见,台田生产规模的起伏与当地复杂社会的兴衰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在复杂社会兴起以前,还是崩溃以后,台田这种兼具排水与抗旱之利,又便于利用田间水道开展多种经营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技术[21]9,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其实也都并不陌生。但他们之所以此前没有采用,此后又予以放弃,这意味着这种技术所能带来的产量的增长对于他们维持自身的生存来讲,并不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没有外力的驱迫,仅从自身经济需求的角度来考虑,保守的农业劳动者是不会主动增加投入,采用这项技术的。由此可见,台田区人口所占比例的这种起伏变化趋势,应该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结果,它显示了贵族集团对于劳动力的支配以及对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干预和规划[20]326,329。
当然,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业产出与贵族的勒索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否则就有可能因为税赋过重而激起生产者的反抗,从而使得已有的复杂化成就付诸东流。所以这里面既体现着政治规划对于经济基础所发生的作用,同时也显示出了既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政治行为的活动范围与强度所造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限制。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地发生作用去创造一切,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行为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之中以及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归根到底是具备决定意义的[17]732。
对于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水利说来讲,至少对于某些早期文明而言,这一模式所关注的与水利工程有关的建设及管理活动就是这些具备决定意义的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虽然多数情况下,一提起水利说,人们总是首先想到威特福格尔,但我们应该知道,他既不是这一理论传统的创始者,当然也不会是它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