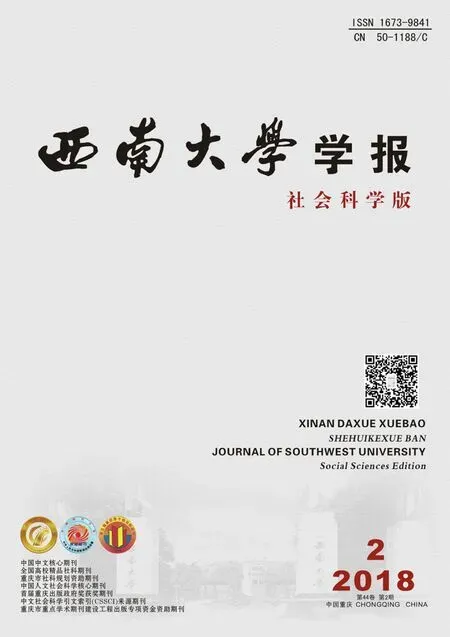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1800-1914年)
杜 林 泽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伊朗恺伽王朝历史的重要内容,就是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在面对西方冲击之时所经历的显著“变迁”。学界对此现象予以极大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却多有争论,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即是:1800-1925年间的伊朗经济到底是“停滞”还是显示出“现代化的开端”。学界对其中农业经济这一重要内容的评判同样是褒贬抑扬、莫衷一是,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结论。诺施瓦尼、盖得·吉尔巴、吉蒂·纳什特等学者强调其中的进步趋势,提出“农业的商品化”“制度的现代化”“人均收入的增长”等观点;查尔斯·伊萨维、朱利安·巴尼尔和尼基·凯蒂等学者强调“相对的经济停滞和极为缓慢的发展”,尤其是相比同时期的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约翰·弗兰则利用依附论的框架来阐释恺伽王朝时期伊朗经济社会的变迁,认为其本质上是“有限的发展”,既有进步要素也有消极影响。*相关内容请参阅:Nowshirvani, V.F., The Beginnings of Commercialized Agriculture in Iran, in Udovitch, A.L., editor,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1981, pp.547-591; Gilbar, G.G., Persian Agriculture in the Late Qajar Period, 1860-1906: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2, No.3, 1978, pp.312-365; Nashat, G., From Bazaar to Market: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Iran, Iranian Studies, Vol. 14, No.1/2, 1981, pp.53-85; Issawi, C.,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 1800-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13-19; Keddie, N.R., Roots of Revolutio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1; Bharier, J.,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ran, 1900-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9-20; Foran, J.,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 (1800-1925), Iranian Studies, Vol.22, No.2/3, 1989, pp.5-56.关于农业生产力这一微观层面的探讨,亦同样存在不同观点。如吉尔巴认为1865-1906年见证了“农业部门的快速增长……人均农业产出按实际价值计算持续增长”;弗兰认为尽管恺伽伊朗的农业总产值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人均农业产值是否增长仍存有疑问;艾哈迈德·赛伊夫则认为伊朗19世纪末的农业生产力比19世纪初更低,因为“在类似的浪费式耕作方法之下,利用同样原始的耕作工具,以及土壤肥力的下降和更无规律的灌溉供给,只能意味着更低的生产力和更加脆弱的农业”*相关内容请参阅:Gilbar, G.G., Persian Agriculture in the Late Qajar Period, 1860-1906: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2, No.3, 1978, pp.312-365;Foran, J.,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18; Seyf, A., Technical Changes in Iranian Agriculture, 1800-190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20, No4, 1984, pp.142-154.。
显然,导致学界观点迥然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预设方法或衡量指标上的差异。凯蒂等学者将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同期相邻国家或地区作横向比较的视角或许并不适宜,因为这容易造成过于强调“不足”而相对忽视“成就”的偏颇见解,导致对恺伽伊朗农业经济变迁的误读。从历史维度上纵向考察恺伽伊朗农业生产所经历的变化,无疑有助于“纠偏”,但这也需要在农业经济体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诸多层面综合考察,如诺施瓦尼等学者仅仅关注农业经济体制之类的单一层面也容易导致其观点失妥。众所周知,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因素众多,且往往呈现出并非一致的变化趋势。因此,在分析恺伽伊朗农业生产力变化趋势之时,如果考察对象片面化且存在差异性,那么观点出现分歧,甚至不符合史实也就不足为奇。依附论的分析框架也难以解决关于恺伽伊朗农业经济变迁的争论。尽管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与其宏观经济社会类似,呈现出发展与停滞并存的现象,但其主要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社会结构的“依附性”。本文试图结合恺伽伊朗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即西方冲击下伊朗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梳理分析农业经济领域诸多重要层面中的突出现象及具体缘由,阐述恺伽伊朗农业发展的历史特征。
一、西方的冲击与对外贸易的变化
伊朗与西方世界的交往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及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黑暗”长期阻碍了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商业联系,至13世纪伊朗开始逐渐恢复与亚平宁半岛沿海商业城市的贸易往来。直到18世纪期间,伊朗长期保持与欧洲世界的交往,双方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多有合作,其关系体现出平等互利的特征,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并不带有军事侵略或经济掠夺的色彩。*关于此间伊朗与欧洲国家交往的详细内容可参阅:Lockhart, L., European Contacts with Persia, in Jackson, P., edit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73-411.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与欧洲国家的进出口产品中均包括原材料和手工业产品,而伊朗在双方贸易中亦拥有自主权,甚至常有盈利,银的大量流入是为其主要体现。此外,这一时期的伊朗正处于传统社会的顶峰,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比较稳定,因此在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当进入19世纪后,原本伊朗与欧洲国家平等互利的基础即双方之间的实力平衡逐渐被打破,进而形成欧洲国家对伊朗的多方位冲击。伊朗亦随之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开始“由非欧洲的经济核心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外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115,其逻辑结果则是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出现相应的变化。恺伽时期,伊朗经济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不断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解体,西方势力的冲击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2]48。
19世纪初俄国和英国的战争威胁迫使伊朗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形成西方冲击伊朗的最初形式。一方面,伊朗失去大量领土并支付赔款,完整主权遭到侵蚀;而另一方面,俄英两国则以此为契机在伊朗逐渐获得诸多经营特许权和开发特许权,对其形成进一步的冲击。1863-1914年间,英俄两国强迫伊朗转让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烟草专卖、金融机构营运,以及运河和港口航运等一系列特许权。其结果是,到20世纪下半叶之时,西方在伊朗的投资从几乎空白增长到1 200万英镑,伊朗亦逐渐成为欧洲重要的资本市场和贸易市场[3]56。其中,英国于1860-1913年间在伊朗的投资总额就达1 000万英镑[1]110。
与欧洲诸国的对外贸易是“伊朗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形式”[4]46,亦是英俄等西方势力冲击的重要形式之一,对恺伽伊朗经济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在1828年对俄贸易协议,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相似贸易协议中,伊朗失去关税自主权,所有进出口的关税率不足5%[5]73。这一关税率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英、俄等西方国家与伊朗签订新的贸易协议,此前的统一关税率改为不同贸易产品执行差异关税,而棉花、大米、茶叶、糖、煤油等诸多重要贸易产品的关税进一步降低。英俄等西方国家通过关税特权的获取迫使伊朗门户大开,其逻辑结果就是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发生显著变化。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时期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2]45。
伊朗对外贸易在18世纪中一度因政治动荡而衰减。伴随着恺伽王朝的建立和政治趋于稳定,伊朗经由波斯湾和黑海的对外贸易在19世纪前30年中得以恢复。此后,伊朗对外贸易进一步迅速发展。1800年左右,伊朗对外贸易额大约为250万英镑[6]16。到1860年,伊朗进出口贸易总额约500万英镑,到19世纪80年代增至750万英镑,1901年超过900万英镑,1912/13年度为1 825万英镑,1913/14年度则达到2 000万英镑[7]595。如果剔除物价因素而考察贸易产品的实际总价值,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伊朗对外贸易实际总值增长了3倍,在1860-1914年期间则增长了4倍[4]47。换言之,从19世纪初至1914年,伊朗对外贸易总值实际增长高达12倍。
推动伊朗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首要因素无疑是伊朗与欧洲国家经济交往的扩大。随着与欧洲国家贸易的迅速增长,伊朗主要贸易伙伴亦随之明显转变。实际上,欧洲国家早在17世纪初就成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而生丝则是当时伊朗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17世纪20年代,伊朗生丝年产量大约为1 000吨,其中约三分之二出口到欧洲[1]35。直到18世纪20年代,伊朗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一直处于稳定状态。然而,自1722年阿富汗人的入侵开始,伊朗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急剧衰落。到18世纪后半叶,伊朗对外贸易重心逐渐由欧洲转向其周边区域。1800年,伊朗的主要贸易对象是阿富汗和中亚,占伊朗对外贸易总额的33.75%,随后是奥斯曼帝国和印度,分别占26%和19.5%,俄国仅占伊朗对外贸易总额的15%,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仅占3%;到1914年,欧洲贸易伙伴在伊朗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从不足19%增长到约94%(含英属印度殖民地)[1]113-114。
恺伽王朝时期,英、俄两国与伊朗的贸易此消彼长,共同构成伊朗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国。英国已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在伊朗迅速扩张,并逐渐成为伊朗最大的对外贸易国。到19世纪50、60年代,对英进口与出口贸易额在伊朗进口与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超过50%[7]597。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伊朗与英国的贸易一直维持稳定增长,其贸易总额从1875年的170万英镑增长到1895年的300万英镑,到1914年则进一步增长到450万英镑[8]11-12。然而,在贸易总额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英国与伊朗贸易额的占比却逐渐下滑。1903年英国在伊朗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下降到33%,到1914年则仅为20%[1]110。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国与伊朗贸易更为迅速的增长,进而逐渐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19世纪后半叶伊朗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国家。1875年,伊朗与俄国的贸易总额约100万英镑,到1914年则增长了11倍,达到1 200万英镑,对俄贸易在伊朗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则分别增长至72%和56%[1]111-112。
伊朗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同时,其对外贸易结构亦发生明显改变,逐渐趋向于一种典型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即由传统手工业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原材料输出国和西方工业品倾销地。1844年之际,伊朗尚有超过70%的出口货物由传统手工业制品组成,到1910年,除地毯以外的传统手工业制品出口微乎其微。地毯几乎成为伊朗唯一的手工业出口商品,在1911-1913年间约占出口贸易总额的12%。[4]48-49相比之下,农作物产品则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制品,成为恺伽伊朗最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类型。从1830年到1900年,原棉、生丝、小麦、大米、烟草、兽皮和地毯等商品的出口额从200万英镑增长至380万英镑。[3]511911-1913年间,生丝、羊毛和棉花占伊朗出口贸易总额的26%,大米、干果和鸦片则占32%。与此同时,大量西方现代工业产品涌入伊朗,在19世纪伊朗进口商品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9世纪50年代,西方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器皿等现代工业产品占伊朗进口商品总量的76%,到1911-1913年间仍占73%。而在相同历史时点中,伊朗传统手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仅为32%和13%,其中地毯就独占12%[1]115。
自19世纪中叶以后,伊朗进口贸易额迅速增长,相比之下出口贸易额则增速缓慢,进而导致贸易逆差逐渐形成并日趋扩大。伊朗在与西方国家的传统贸易中常有盈余,至1857年时,伊朗进口额约299.29万英镑,出口额约300万英镑,尚有约7 143英镑的少量顺差;到1901-1905年间,伊朗年均进口额约587.3万英镑,超出其年均371.3万英镑出口额约二分之一,年均贸易逆差约196万英镑;1911-1913年间,伊朗年均进口、出口贸易额分别增长至约1 072.7万英镑和789万英镑,年均贸易逆差亦扩大到约283.7万英镑[8]17,table 3。伊朗贸易逆差形成并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其带有殖民地特征的对外贸易结构。一方面,新的贸易结构下,伊朗主要进口与出口商品的性质迥然不同,出口农产品、原材料与进口工业产品具有天然的差价,在19世纪末伊朗进口工业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其出口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下,伊朗出口农产品价格明显受制于外部市场。19世纪下半叶后,诸多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持续降低。例如小麦价格从1871年的1.5美元/蒲式耳下降到1894年的0.23美元/蒲式耳[12]128,鸦片价格从1867-1869年间的18先令/磅跌至1901-1903年间的8先令/磅,生丝价格亦从1864年的1英镑/公斤跌至1894年的0.25英镑/公斤[1]115。伊朗货币(银)的贬值则导致伊朗出口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更为低廉。因此,伊朗诸多农产品在出口总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其出口额并未明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长期贸易赤字的直接后果,就是伊朗货币的大量流出。据波斯帝国银行主管拉比诺所言,伊朗在19世纪后25年中出现“持续性的货币缺乏”,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前10年中也没有改变[9]273。
对外贸易的增长,尤其是与英、俄等西方国家贸易的扩大显示出恺伽伊朗不断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历史进程。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则体现出恺伽伊朗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即所谓的“外围国家”。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传统社会达到顶峰,其突出现象在于自主的国际地位和封闭的倾向[10]391。然而,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英、俄等国的入侵,恺伽王朝统治时期的伊朗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并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毫无疑问,经济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深层背景。然而在恺伽王朝时期,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导致伊朗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特许权的出让则导致伊朗资源的大量流失,而贸易逆差的扩大亦导致伊朗贸易的增长未能实现财富的增长。显然,在恺伽时期伊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之初,西方的冲击成为促进伊朗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不仅仅是恺伽伊朗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内容,亦是推动其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因素。乡村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正是此间伊朗经济社会变革中的突出现象。
二、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
在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历史进程中,伊朗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于农产品出口的增长、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地产的私有化趋势三个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伊朗在恺伽王朝之前已有生丝等农产品出口境外。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后,诸多农产品出口急剧增长,并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制品而成为伊朗最为重要的出口货物,无疑表明其农业生产中交换或销售的目的性更为强烈,进而体现恺伽伊朗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显著发展。*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主要是指耕种生产者以交换或销售为目的而有意识地利用生产要素开展生产活动,偶然的剩余产品销售并不意味着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发展需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前提,即市场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出现增长。那么,这就意味着市场要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逐渐增强,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配置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种植结构亦随市场需求的变动而转换,进而体现出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趋势。
恺伽期间,伊朗种植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穆哈丹·法提米赫曾指出:“伊朗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特征就是鸦片、棉花、烟草、生丝等作物生产和出口的增长”[11]51。以鸦片为例,1800年左右鸦片已经在诸多省份种植,但是其种植量较小,绝大多数产品也仅用于本地消费。然而,当世界市场中形成对鸦片的强烈需求之时,鸦片的价格和利润随之增长。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植鸦片可获收益超过种植小麦可获收益3倍之多[12]128,这种高额利润促使鸦片种植急剧增长。自19世纪中期鸦片在伊朗南部广泛种植,并由英国大量销往远东市场。19世纪60年代,鸦片种植在伊斯法罕、亚兹德、法尔斯、克尔曼、呼罗珊、胡齐斯坦和克尔曼沙等地区开始持续增长,到70年代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作物之一。布什尔地区的一个英国领事曾于1873年称:“几年之前,鸦片的利益开始吸引波斯人的关注,在亚兹德、伊斯法罕和其他地区,几乎所有适宜的土地都放弃种植谷物或其他农作物而改为种植鸦片”[13]71。部分地区种植鸦片的热情甚至导致行政部门不得不采取强制规定来限制其产量,例如伊斯法罕长官齐尔·斯利坦(Zell al-Slitan)下令规定:每种植4英亩鸦片就必须种植1英亩小麦[6]27。与鸦片类似,棉花的种植也快速增长并大量出口到俄国。受美国内战的影响,国际市场棉花供应出现短缺,刺激了包括伊朗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棉花生产和出口。与此同时,伊朗的重要贸易对象——俄国则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出现大量的棉花需求。于是,在伊朗北部地区,俄国棉花商人向伊朗农民提供优质棉花种子,鼓励他们种植棉花[12]129。在此形势下,棉花种植在以阿塞拜疆、呼罗珊和伊斯法罕为典型代表的伊朗诸多区域迅速增长。“到一战前夕,伊朗(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0万公顷,约2.5万吨价值150万英镑的棉花出口至俄国。”[7]600
吉兰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可谓是恺伽伊朗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吉兰原本是一个以生丝生产为主要农业活动的省份,而到19世纪后半叶,该地区除生产生丝之外,亦种植烟草、小麦和大米,且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烟草种植始于1876年,到1877年大约收获43吨烟草,而到1891年,烟草产量达到450吨,增长超过10倍[6]27。吉兰省的民众本不吃面食,该地区所产小麦均出口至俄国。那么对该地区而言,小麦无疑等同于经济作物。大米虽是吉兰的传统种植作物,但却从未满足当地需求,因此长期从马赞德兰进口。然而到1870年,吉兰已经成为伊朗的大米之乡和大米主要出口地。其出口额由19世纪70年代的2.5万英镑增长到90年代的20万英镑,到1904-1908年间则平均高达50万英镑,占吉兰地区总出口额的近50%[7]599。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发展和市场化趋势,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恺伽伊朗乡村地产形态亦发生相应的改变。王室领地、国有土地的衰落与民间私人地产的不断扩大构成恺伽后期地产运动的重要特征[2]52。恺伽王朝在建立之初基本延续了萨法维王朝的土地制度,乡村地产形态主要包括王室领地、国有土地、宗教地产和民间私有地产四种类型。王室领地是国王及其家族的私有地产,被称为哈里塞(khaliseh);国有土地的税收用于国库,而并非属于国王的个人账目,其主要形式乃是“提尤尔”(tiyul),包括赐封军事贵族的土地,以及用于支付行省长官和部落首领等群体之俸禄的地产;宗教地产瓦克夫(vaqf)则是根据伊斯兰教义而用于宗教慈善或个人利益的永久性捐赠土地;除此之外,亦有少量的民间私有地产存在。19世纪上半叶,伊朗乡村地产形态相对稳定,王室领地和国有土地构成最为重要的两种土地类型。恺伽王朝延续萨法维时期的传统继续向政府官员、贵族亲信、军事首领赏赐封邑,提尤尔仍然是国有土地的重要形式。王室领地则是占比最大的一种地产类型,有学者估计,1861年时“三分之一,或是根据某些人所称的二分之一的耕地为哈里塞,或‘皇室地产’”[14]189。长期以来,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和衰落,伊朗王室领地和国有土地的规模呈现此消彼长的运动态势。尽管伊朗王朝历史中的一个长期现象就是国有土地、王室领地和宗教地产的私有化倾向,尤其是在萨法维王朝末期中央权力极度衰落之际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十分模糊,但在19世纪中叶之前,伊朗私有地产的规模仍然很小。然而,自19世纪中叶后,王室领地和国有土地转变为私有地产的趋势则日益显著。
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发展,促使农业生产的收益明显增长,土地作为财富和地位之象征的属性极为突出。“在整个恺伽王朝时期,土地所有者阶层(包括部落首领)是王国中最有权力的群体。”[15]140大量商人、官员和部落贵族投资购买土地而成为新兴地主阶层;诸多原有地主亦通过商人获取贷款来购置更多的土地。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作物出口的增长,城市商人购置土地的现象日趋显著。自纳绥尔丁统治时期以来,大量商人就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国有土地购为私有。[11]44与此同时,由于恺伽王朝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政府对游牧地区和封邑土地的控制力不断弱化,进而导致土地税收大量流失、国库空虚;而恺伽王室却需要大量货币来购买西方奢侈品、加强军备,以及偿还西方国家的贷款。由于财政困难,出售国有土地和王室领地遂成为恺伽政府获取收入的重要手段。自1850年以后,特别是1880年以后,土地所有权不断从皇室和提尤尔持有者手中转移到商人、欧莱玛和官员手中[1]120。1887年,纳绥尔丁国王亲自颁布命令,将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以外的所有国有土地出售给民间私人[12]45。另一方面,中央权力的弱化同时也导致封邑领有人对提尤尔的支配权增大,残余的提尤尔在实际上亦与私人地产差别甚小,可以世袭享有并出售转让,进而促使他们将传统的有条件的封赐土地转变为毫无限制的私人财产。
在土地私有化发展的趋势下,私有地产亦逐渐获得法律的保护。伊朗宪政革命期间,《卡轮报》(Qanun)即提出应当立法保护私有土地,防止私有土地被政府没收[12]45。1907年第一届议会颁布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中正式废除提尤尔,大量提尤尔转变为其领有者的私人地产。宪法还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1907年10月7日的补充基本法第15条即指出:“有产者的土地无法被剥夺,除非受沙里亚法的制裁,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在确定并支付一个公正的价钱之后方能实施”;第16条进一步指出:“禁止作为惩罚性措施扣押任何人的地产和财产,除非符合法律秩序。”[15]178伊朗涉及土地的法律制度开始逐渐形成,尤其是民法中的相关部分对土地所有权予以明确规定,体现出极力支持私人土地所有权的特征[15]194-209,402-404。
如果以整体农业生产为考察对象,那么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诚如吉尔巴所言,“毫无疑问,经济作物种植增长最为重要的经济影响就是农业总产品的增长”[16]80。尽管由于缺乏具体数据而难以准确量化此间农业总体产量的发展程度,但是出口数据无疑表明了诸多作物产量明显增长的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诸如原棉、鸦片、大米、水果和干果等经济作物产量的显著提高。
农作物产品整体出口规模的扩大,显然是来自于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这也意味着恺伽伊朗农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些增长的剩余产品又来自于何处?促进恺伽伊朗农业剩余产品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农业劳动力的增长、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地产的私有化发展。威廉·弗洛即指出:“1800-1900年间,伊朗人口增长了两倍,与此同时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进而促进农业整体产量成倍增长。”[6]26如果以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一长时段为考察对象,那么此间伊朗人口无疑呈增长趋势,*尽管学界关于19世纪80年代前伊朗人口变化的问题仍有一定分歧,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人口明显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也得到学界的公认。相关代表性成果可参见:Seyf, A.,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Iran, 1800-190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5, No.3, 2009, pp.447-460; Gilbar, G.G.,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Late Qajar Persia, 1870-1906,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11/2, 1976, pp.125-156.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农业劳动力的增长。其一,由于手工业遭受西方工业品的巨大冲击和农业商品化所带来的利益驱动,大量手工业劳动力转移至农业生产,其中既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向乡村农业的转移,也包括先前主要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传统乡村妇女更多地走上耕地;其二,大量部落游牧人口在定居化的过程中,因经济作物的利益驱动而转变为农业劳动者。从1800到1900年间,伊朗部落游牧人口占比从50%下降到25%,乡村定居人口占比则由40%增长到55%[13]69。除此之外,在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中,耕种作物的多样化发展无疑促进了多种作物之间的轮作,进而有助于减少农业劳动力的闲置时间,以及休耕地面积和休耕时间。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吉兰等里海沿岸降水相对充足的地区,民众砍伐灌木、森林以扩大耕地面积;在呼罗珊和阿斯塔拉巴德,部落人口逐渐从事定居农业生产,进而促进原本荒废的土地被重新用于耕种;在克尔曼沙、胡齐斯坦、锡斯坦等地区,政治环境的安全化也促使荒地被再度垦殖。除农业劳动力和耕地的增长之外,大量地产的私有化无疑有助于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室领地原本因管理不当和生产低下而臭名昭著,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往往给人以过于仁慈的印象。伊朗学者古拉姆·侯赛因曾描述恺伽时期的这一问题。一方面,王室土地所在乡村的管理者有意增加投入以提高生产,但却无能为力;而另一方面,恺伽政府本有增加王室土地投入的能力,但却无心作为。在新兴地主及其代理人更为有效的管理下,私有土地的生产效率逐渐提升。正如赛伊夫所言:“这一重要发展(国有土地和王室领地转变为私有地产)促进了整体生产,以及可耕地被更为有效地使用。”[17]457显然,上述原因均或多或少受到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之下,自然经济条件下典型的粮食作物生产渐趋衰落,而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则日益扩大,农业经济逐渐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进而不断排斥伊朗传统农业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到1900-1910年,我们不能再将伊朗农业视为自足农业。此时,它已融入国民经济之中,商品化关系也广泛发展。”[18]579土地的私有化发展源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亦体现出土地的商品化趋势。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是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的实质体现,构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作为农业经济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无疑有助于提升土地所有权的安全性,对农业生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所谓农业现代化,其核心内容正是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模式向现代商品化和市场化农业经济模式的转变。恺伽伊朗农业经济所经历的商品化发展和市场化趋势无疑标志着伊朗农业现代化的起点和开端。
然而,商品化关系的发展对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商品化关系主要是以世界市场而非国内市场为导向,世界市场中农作物的需求波动和价格起伏对伊朗农业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伊朗农业经济亦随之逐渐形成对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依附性”。伴随着19世纪后半叶商品化耕作的发展,伊朗农业日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7]473。
三、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与分成租佃关系的延续
尽管恺伽时期伊朗农业生产力整体呈发展趋势,但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生产技术却停滞不前。在阿巴斯·瓦里看来,伊朗“农业生产技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变化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生产仍与2500年前奴隶采用的方式十分相似”[19]214。大致而言,恺伽伊朗农业技术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农业工具原始、灌溉系统发展停滞和肥料欠缺三个方面。
赛伊夫即认为,伊朗的农业工具极为原始落后,在整个1800-1906年间均是如此[17]142。恺伽伊朗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工具被当时英国领事麦克莱恩形容为“原始的东方类型”[20]814。主要农具包括犁(khish)、铲(bil)、耙(piteh)、镰刀(das)、扬场耙(absi)、脱粒机(chuneh)、麻袋(khorreh)、驮篮(javal)、手磨等。*威廉·弗洛尔对恺伽时期的农业工具进行了详细介绍,参见Floor, W., Agriculture in Qajar Iran, Washington DC: Mage Publishers, 2003, pp.204-224.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的土地上,农民所使用的农具无疑具有一定差异。然而,无论农民们拥有或使用什么设备,所有“工具都是原始的,自易卜拉欣以来没有任何发展”[6]207。因此,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曾建议向伊朗运送简单有效的农业工具,例如坚硬而廉价的改良型单头犁、马力脱粒机或收割机[21]29。但诸多证据显示,恺伽时期伊朗几乎没有农业机械的引进。有报告称在1862年“呼罗珊地区的棉花种植方式、采摘方式和清洁方式都极为恶劣……”[22]870而到1897年,同样是在呼罗珊地区,另一份报告则称“还没有引入使用现代欧洲制造产品中的改良农业工具”[23]505。直到20世纪初,小麦、大米、大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方式仍然和几个世纪前一样使用原始的工具[17]148-149。
原始粗陋的生产工具极大的限制了恺伽伊朗的农业生产。正如部分欧洲观察家所言,“波斯的犁耕往往只是意味着抓挠一下土地”[24]327,“根据欧洲人的观念,(德黑兰地区)土壤准备的方式极不充分,犁地非常浅薄,土壤甚至没有翻面”[25]668。正是由于生产工具的简陋,恺伽伊朗农业生产对畜力和人力的需求极大。有学者估计,伊朗种植一公顷的大麦和小麦通常需要农民工作780小时,其中190小时与牲畜一起劳动;种植一公顷棉花则需要2 300小时的农民劳动和80小时的牲畜劳动[26]40。畜力主要用于土壤翻耕,通常是由耕牛拖拉木制耕犁而进行,部分地区亦采用铁制耕犁。收割、脱粒和扬场则多是手工劳作。农作物的收割主要是用镰刀,收割完的作物则通过牲畜或农民肩挑运往脱粒场所。收成的脱粒主要采用驮畜牵拉木质碾轮和人工脱粒交替进行的方式,但由于牲畜有限,手工脱粒则是更为普遍的方式。
除此之外,恺伽伊朗在灌溉系统发展和肥料使用方面亦停滞不前,甚至在部分地区有恶化的情况。由于绝大多数地区降水缺乏,人工灌溉对伊朗农业生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传统的地下水渠-卡纳特(qanat)长期以来便是伊朗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灌溉方式。然而,恺伽时期部分旅伊欧洲观察家发现,伊朗“自早期人类时代以来”,并没有系统性的尝试来发展这一原始的灌溉方式[27]5。在弗兰看来,恺伽期间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灌溉系统出现恶化[1]119。一方面,因公共权力的忽视,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并未开展,且传统的卡纳特灌溉系统亦荒于维护;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化之后,在私人领域中虽然偶尔会有少数地主有投资灌溉的能力和意愿,但其尝试也多以失败告终。肥料的缺乏也是限制伊朗农业生产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罗林森在1836年写道,在库尔德斯坦的左哈卜(Zohab)地区,农民“从未使用肥料来增肥土壤”[28]27。肥料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牲畜数量的有限,而且其粪便也多被用作燃料使用。伊朗中部的诸多地区有利用鸽子粪便作为肥料的传统,但是部分地区搜集鸽子粪便的塔楼在恺伽时期也因缺乏修缮而荒废。正是灌溉的不足和肥料的缺乏,进一步限制了土地的轮作,伊朗大量土地处于休耕状态。
限制恺伽伊朗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相关农业投入的匮乏。在农业经济商品化的驱动下,农业投入确有增长。然而,由于恺伽王朝大量国有土地和王室领地的存在,土地市场供给丰富,农业商品化进程所推动的农业投资首先体现为购置田地,进而导致土地兼并和地产集中的现象,私有大地产随之出现。投资用于改良作物品种的案例偶有发生,例如部分地区的地主或农户偶尔会使用从印度进口的谷物品种,但其主要原因乃是当地品种的产量极为低下而促使他们被迫使用国外品种;1865-1866年的大规模蚕病之后,部分地区开始从日本、希腊、法国和土耳其等国进口蚕蛋,但生丝的生产过程却一如既往。棉花或许是一个特例,文献记载早在1851年阿塞拜疆的乌鲁米耶地区和大不里士等地区就出现了种植美洲棉花的现象,在80年代之时俄国人为摆脱对美国棉花的依赖,免费将查尔斯顿棉花种子(Charleston cotton-seed)分配给当地地主[29]148。然而,除这些引进优良品种的少数案例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投入极为缺乏。
导致恺伽伊朗农业生产投入水平低下的原因较为复杂,大致而言,除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还包括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客观经济环境的限制。随着大量西方工业品的倾销,诸多传统手工业极度衰落,这一部门对伊朗农业不再能发挥积极贡献;再加上现代工业发展的落后,伊朗自身缺乏向农业部门提供改良生产工具或机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能力。其二则在于主观动机的缺失。显然,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后者,因为诸多不利的客观限制可以通过进口改良生产工具而得以解决。导致主观动机缺失的因素众多,例如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的增长,一方面对促进农业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削弱了因劳动力和耕地不足而改良生产技术的动力。然而,此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疑在于恺伽伊朗自身的传统农业经济体制。
恺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并未根本改变伊朗土地制度的封建特征。国王、王室成员、军事贵族、部落首领和行政官员等群体支配着伊朗绝大部分土地,他们通常并不居住在乡村地区,成为在外土地所有者。农民并不享有土地,绝大多数地产均按照实物分成的方式租予农民。自萨珊王朝以来,实物分成制在伊朗乡村土地租佃关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伊朗土地所有者榨取农业剩余产品的主要形式[19]193。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将分成制视为封建剥削的形式,它是“一个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从另一个阶级——无地佃农阶级——摄取剩余的非市场化形式(非资本主义形式)”[30]175。在分成制度之下,佃农的剩余价值被直接摄取,非生产性的土地所有者不通过价格手段,而直接从生产性的佃农那里获取农作物产品分成,这种超经济强制体现出明显的封建剥削特征。
分成佃农没有农业土地,地主赋予部分农民在其土地上进行耕作的权力,进而获取一定比例的收成,体现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交换的契约。这种生产要素交换构成伊朗传统农业生产的起点和基础,其表现形式则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分成协议。然而,伊朗传统分成协议通常是口头形式,书面协议很少,进而导致绝大多数佃农的土地耕作权利并无保障,即使是在生产过程之中亦有失去的可能。
恺伽伊朗农作物的收成通常按照五项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即土地、劳动力、种子、水源和牲畜,因此通常被称为“五项实物分成制”。就理论而言,作物收成平均分为五份,每种生产要素各占其一。由于地方传统、作物类型、土壤条件、耕作和灌溉方式等因素在不同地区普遍存在差异,实物分成的具体比例亦有所区别。大致而言,农民在生产中提供劳动、部分耕畜,偶尔也提供种子;地主则提供土地、水和种子,偶尔提供所需的资金[19]196。但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完全根据生产要素比例而进行的实物分成几乎不存在。地主通常在分配收成之前便扣留一部分以作为来年生产的种子。此外,由于地主对土地的绝对权力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他们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农作物收成,进而获取高额的分成,某些时候甚至高达五分之四*蓝布顿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恺伽伊朗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土地类型的实物分成比例,参见Lambton, A.K.S.,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Persia-A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306-329.。
这种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实物分成租佃关系正是导致伊朗传统农业投入缺乏,进而导致生产技术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外地主通过享有土地等生产要素已获得高额收入,在农业经济商品化背景下,土地所带来的高收益导致他们最初的农业投资更多的集中于购置和兼并土地,但却难以刺激他们增加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投入。在外地主通常任命代理人来管理土地,或是将乡村租给他人,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获取更多的作物分成和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而不是发展生产技术。大量的地产和高额的实物分成保障了在外地主的丰厚收入,他们通常拥有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但在实际情况中却更多地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消费以满足奢侈生活,抑或城市地区诸如商业贸易之类收益更为丰厚的经济部门,而不是用于改良土地、生产工具或引进新品种。另一方面,佃农并不拥有土地,他们的租佃权亦不安全,因此无心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他们的剩余劳动被在外地主无情榨取,收入极少,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再加上游牧部落的不定期掠夺,他们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因此也无力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这种情况正如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特征的描述那样,“许多年来,它们在技术状况方面没有经历过任何重大的变动”,因为“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31]32,26。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构成实物分成租佃协议的基础,被称为“纳萨克”(nasaq),意为耕作土地的权力。农民在享有纳萨克的同时,亦享有水源的使用权。享有耕作权并租佃土地的农民则被称为“纳萨克达尔”(nasaqdar)。按照伊朗乡村的传统制度,单个纳萨克达尔往往并不拥有某片具体土地的耕作权力,土地耕作权通常是由诸多纳萨克达尔共同拥有,实行被称为“穆萨”(musha)的土地耕作权集体所有制。与此同时,佃农耕作的土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纳萨克达尔集体内部实行土地轮换耕种。这种集体特征和轮换耕种的规定,无疑也限制了分成佃农对土地投入和生产工具投入的积极性。此外,农民是否享有纳萨克主要取决于当地的传统、习俗,以及土地所有者的意志。在理论上纳萨克不可世袭,但实际生活中纳萨克达尔的后代通常获许继承这一土地耕作权,其继承权往往是由纳萨克达尔的长子获得。由于收入来源的相对匮乏,纳萨克也很少转让。有学者指出,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土地耕作权与个人的农业生产技能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因此不具备现代经济活动的筛选机能,这也是导致伊朗传统农业生产力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27]35。
随着商品化关系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作物广泛种植的部分地区出现货币地租,开始逐渐否定传统的实物分成制。然而,货币地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分成租佃制度,因为收成比例可以很轻易地估算出其货币价值。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地区亦出现缴纳固定地租的趋势。尽管如此,恺伽王朝时期,实物分成租佃关系仍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到1914年,以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生产的农民仍占伊朗人口的50-55%[1]136。绝大多数乡村农业生产仍然采用传统的五项分成制,伊朗农业与现代生产关系的距离依旧遥远。
四、结 语
恺伽王朝时期,西方势力的冲击无疑是导致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的首要因素。对外贸易作为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伊朗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影响尤为显著。恺伽伊朗对外贸易的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时期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尽管农业经济的变化因时因地而异,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但就伊朗整体而言,其变化趋势无疑突出表现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
农产品出口的增长、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土地的私有化趋势构成恺伽伊朗农业商品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大量农产品的出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则是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的实质体现。与此同时,农作物结构的改变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此消彼长亦显示出市场因素开始对农业生产形成重要影响,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即商品关系与市场关系随之形成。伊朗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其农业现代化进程自此揭开序幕。商品关系的发展既是恺伽伊朗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其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农产品出口的不断扩大无疑表明农业生产剩余产品的增长,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即农业劳动力与耕地的增长,以及土地的私有化发展,均与农业商品化发展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毫无疑问,生产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构成历史发展的深层背景。然而,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明显来自外部因素的诱导,进而导致恺伽伊朗的农业生产在不断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亦逐渐形成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无疑对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体现出恺伽伊朗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恺伽期间伊朗农业生产技术仍停滞不前,其主要原因则是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实物分成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实物分成租佃关系与纳萨克集体所有制的长期广泛存在源于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却又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限于传统的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伊朗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关投资极少,在外地主对增加投入以提升农业技术是有力无心,而佃农对此则是无心无力。
综上所述,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之下和不断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过程中,伊朗农业经济所经历的,一方面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农作物产品剩余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逐渐增强,农业生产技术亦受限于传统框架而停滞不前。恺伽时期,伊朗传统农业制度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其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显然,恺伽王朝时期伊朗农业经济的发展仍束缚于传统框架之内,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可谓是传统框架内的“有限发展”。
[1] FORAN J.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2] 杜林泽.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D].天津:南开大学,2012.
[3] ABRAHAMIAN E.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4] KARSHENAS M, Oil, 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ISSAWI C.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 1800-1914[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6] FLOOR W. Agriculture in Qajar Iran[M]. Washington DC: Mage Publishers, 2003.
[7] AVERY P. edit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M].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FORAN J.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 (1800-1925)[M]. Iranian Studies, 1989, 22(2/3:5-56.
[9] RABINO J. Economist’s Notes on Persia[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01,64(2):265-291.
[10]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11] MOGHADAM F M. From Land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Iran 1962-1979[M]. London: I.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12] KEDDIE N R. Ira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M]. London: Frank Cass, 1980.
[13] MALEK H M.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Iran[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1,27(1):67-78.
[14] GILBAR G G. Persian Economic in the Mid-19th Century[J]. Die Welt des Islams, New Series, 1979, 19(1/4):177-211.
[15] LAMBTON A K S.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Persia-A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6] GILBAR G G. The Opening up of Qajar Iran: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M].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 49(1):76-89.
[17] SEYF A.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Iran, 1800-1906[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9,45(3):447-460.
[18] NOWSHIRVANI V F. The Beginnings of Commercialized Agriculture in Iran. in A.L. Udovitch, editor,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C].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1981:547-591.
[19] VALI A. Pre-Capitalist Iran: A Theoretical History[M]. London: I.B. Tauris, 1993.
[20] MACLEAM H W.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of British Trade in Persia[R].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26, XCV.
[21] BAKSH B M. Report for the Year 1896-7 on the Trade and Agriculture of Khorasan[J].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he Trade and Finance, 1897, MMVIII.
[22] EASTWICK, Report on the Trade of Khorasa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he Trade and Finance[M]. 1863, LXX.
[23] YATE C E. Khorasa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he Trade and Finance[M]. 1898, XCVII.
[24] PREECE J R. Reports of Journey Made to Yazd, Kerman, and Shiraz and on the Trade and of the Consular District of Isfahan[R].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 1894, LXXXVII.
[25] GREENE C. On the Propose Establishment of a Sugar Industry in Persia[R].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 1895, CII.
[26] AMID M J. Agriculture, Poverty and Reform in Iran[M]. London: Routledge, 1990.
[27] GLEADOWE-NEWCOMEN A H. Report on the British-Indian Commercial Mission to South East Persia During 1904-05, Foreign Office, No. 8778.
[28] RAWLINSON H. Notes on a March from Zohan, at the Foot of the Zagros, along the Mountains to Kurdistan, and from thence through the Province of Luristan to Kermanshah in the year 1836[J].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9,9:26-116.
[29] SEYF A. Technical Changes in Iranian Agriculture, 1800-1906[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84,20(4):142-154.
[30] 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1] 西奥多·M·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