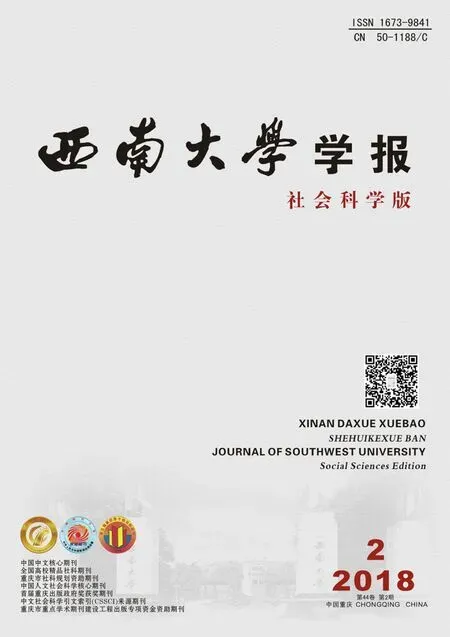从刘宋拟乐府书写范式的转型看士庶乐府之分流
——兼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之社会动力
郭 晨 光
(北京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中华文明传播中心,北京市 100875)
继西晋陆机之后,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如鲍照“代乐府”,又如谢灵运、谢惠连同题《鞠歌行》《顺东西门行》、沈约《悲哉行》等,均以古题表达旧意。此种创作程式,清牟愿相评为“谢康乐吐翕山川,妙绝千古,独其乐府不满人。康乐乐府专拟大陆,大陆固不满人也”[1],抑或“缺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能体现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2],古今学者们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学界目前对刘宋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考察,仅有少数学者如王志清[3]、文晓华[4]等研究了刘宋时期乐府创作的总体情况,主要着眼于文人乐府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个体情志等方面,但仍不脱传统乐府研究之窠臼。其实,刘宋士族有意识截取陆机乐府、汉晋乐府、汉大赋、古诗以及晋宋山水、行旅诗等以往文学经典的文本片段植入乐府写作,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行文结构,从文本重构上获得新的生命。本文从此点入手,希望能将这种特殊的拟作范式及其转型之社会动力的研究引向精细与深入。
一、“回顾过去”的文学时期
刘宋之前的东晋时代,文人大量创作的诗类基本是玄言诗,前代文人热衷的乐府诗和拟古诗被弃之不用。此期有关文人拟诗的作品,有梅陶《怨诗行》、张俊《薤露行》《东门行》、孙绰《情人碧玉歌》二首、王献之《桃叶歌三首》、桃叶《团扇郎》、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袁弘《拟古诗》、谢尚《大道曲》、赵整《琴歌》三首、杨方《合欢诗》五首、王嘉《歌》二首、符朗《拟关龙逢行歌》、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及陶渊明《拟古诗》九首、《拟挽歌辞》三首、《怨诗》等。相比于模拟风气极盛的西晋,东晋被认为是文学传统的“断层”。刘宋时期出现大量拟作乐府旧题以及“拟古”“效古”“古意”等诗歌,表现出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浓厚兴趣,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回顾过去”的历史时期。这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模式,首先由于刘裕北伐将大量中原音乐带回宫廷,使朝廷雅乐格局日趋完备,也使相和三调、清商乐歌等音乐传统得以接续,丰富了当时的音乐艺术,推动了文人拟乐府的复兴。
据《古今乐录》所引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以下简称“张《录》”)和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以下简称“王《录》”)所载相和歌辞,当时歌唱、传播的情况(依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沈约、江淹在文学史上虽归为梁代文人,但其旧题乐府的创作基本在刘宋,故将其归入一并统计)具体如下:
张《录》记载的吟叹曲有:《王明君》(鲍照拟作1首),《楚妃叹》(袁伯文拟作1首),《王子乔》(江淹拟作1首)。
王《录》记载的平调曲有:《长歌行》(谢灵运拟作1首、沈约拟作2首),《猛虎行》(谢惠连拟作2首),《燕歌行》(谢灵运、谢惠连各拟作1首),《从军行》(颜延之拟作1首、江淹拟作2首),《鞠歌行》(谢灵运、谢惠连各拟作1首);清调曲有:《苦寒行》(谢灵运拟作1首),《豫章行》(谢灵运、沈约各拟作1首),《相逢行》(谢惠连拟作1首),《相逢狭斜间》(孔欣拟作1首),《长安有狭斜行》(谢惠连、荀昶、沈约各拟作1首),《三妇艳》(刘铄拟作1首),《塘上行》(谢惠连、沈约各拟作1首,沈约拟作衍生为《江蓠生幽渚》),《秋胡行》(谢惠连拟作2首、颜延之拟作9首);楚调曲有:《白头吟》(鲍照拟作1首),《泰山吟》(谢灵运拟作1首),《梁甫吟》(沈约拟作1首),《怨诗行》(汤惠休拟作1首),《东武吟行》(鲍照、沈约各拟作1首)。
除张《录》和王《录》外,其余文人拟作相和歌曲还有《蒿里》《挽歌》《采桑》《日出东南隅行》《置酒高堂上》《饮马长城窟行》《孤儿行》《门有车马客行》《江南思》,基本来源于前代旧题,继作者不仅有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沈约等士族文人,也有类似于鲍照的寒庶之士,共计14人41曲73首。
当时杂曲歌辞的制作呈现复兴状态,杂曲中有一部分可归于相和。王运熙说:“汉代的杂曲歌词,风格跟相和相同,因其歌辞未被中央乐府机构采习或年代久远等原因,后世不详它们属于何调,故被列入杂曲。”[5]具体情况如下:《出自蓟北门行》(鲍照拟作1首,出自曹植《艳歌行》首句),《君子有所思行》(谢灵运、谢惠连、沈约各拟作1首),《悲哉行》(谢灵运、谢惠连、沈约各拟作1首),《白马篇》(袁淑、鲍照、沈约各拟作1首),《升天行》(鲍照拟作1首),《松柏篇》(鲍照拟作1首,拟傅玄乐府《龟鹤篇》),《齐讴行》(沈约拟作1首),《会吟行》(谢灵运拟作1首),《北风行》(鲍照拟作1首,出自《诗经·邶风·北风》),《苦热行》(鲍照拟作1首),《春日行》(鲍照拟作1首,属自拟新题),《堂上歌行》(鲍照拟作1首,属自拟新题),《前缓声歌》(孔宁子、谢灵运、谢惠连、沈约各1首拟作),《结客少年场行》(鲍照拟作1首,出自曹植《结客篇》首句),《鸣雁行》(鲍照拟作1首,疑出《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空城雀》(鲍照拟作1首,属自拟新题),《自君之出矣》(宋孝武帝、刘义恭、颜师伯、鲍令晖各1首拟作,出自徐干《室思诗》第三章首句“自君之出矣”),《长相思》(吴迈远拟作1首,出自《古诗》“客从远方来”),《长离别》(吴迈远拟作1首),《杞梁妻》(吴迈远拟作1首),《淫思古意》(颜峻拟作1首),《行路难》(鲍照拟作18首)。与相和歌辞相比,杂曲歌辞的来源比较复杂,不局限于传统,有前代旧题、旧题衍生新题、模拟前人乐府、化用诗歌首句和文人自拟新题等,共计13人24曲56首(含《乐府诗集》不载的鲍照《阳春登荆山行》《居边行》《少年至衰老行》《邦街行》[6]),其中鲍照一人就有35首,占一半以上,且很多曲题为其首创。除鲍照外,出身寒庶的继作者还有刘宋王室诸成员及吴迈远、袁淑等。士族文人也有杂曲,但数量较少,如谢灵运、谢惠连相和歌辞各有12首,基本为相和三调,杂曲歌辞分别只有4首、2首。
刘宋文人拟作乐府有以下特点:第一,在曲题使用上,士、庶文人都作有大量的相和歌辞,且庶族文人更偏向杂曲的创作(这与西晋士族文人陆机非常相似,陆氏拟作相和歌辞21曲,杂曲4曲),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士庶分流的情况。第二,刘宋文人普遍对建安文人离题悖乐的改制新作乐府诗不感兴趣,如《乐府解题》所载“曹植拟《长歌行》为《鰕》”“曹植拟《苦寒行》为《吁嗟》”“曹植拟《薤露行》为《天地》”“曹植拟《豫章》为‘穷达’”“曹植拟《善哉行》为‘日苦短’”等,以及以“当”为题的《当来日大难》《当欲游南山行》《当事君行》《当车以驾行》等,刘宋文人拟作乐府较多承袭的是乐府古题古意。第三,主要沿袭陆机乐府,采用亦步亦趋、跟随式的模拟方法,重视体制、宗法。此外,还上溯至汉晋乐府、汉赋和古诗,甚至融合晋宋山水、行旅诗的写景艺术、修辞风格等,在规步前贤的同时并未受其约束,而是自由驱使传统资源,从中选取适用部分加以改造糅合,追求多层次的复合行文结构,有一定的文本制作程序,多方位继承各种风格、文化渊综广博的特点。
当军事上的胜利带来音乐文化的输入之时,学术上也经历了蓬勃发展,特别是由文化世家谢氏家族领导的时尚潮流,呈现出对既往文学经典的回顾、继承的强烈兴趣。如谢混和族子谢灵运、谢瞻等构成了“乌衣之游”,谢灵运与族弟谢惠连、友人何长瑜等组成了“山泽之游”,他们组成了许多讨论文学的排外小圈子。当时的士族对文化资源有一定垄断地位,有较多机会接触古代的抄本等文献。《新唐书·艺文志》载谢混针对作者别集所作的选本,编有60卷的《集苑》,其《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残)曾引用古乐府《从军行》中的一句“苦哉远征人”。谢灵运于426年至428年间担任秘书监,被委派整理皇家藏书,曾作《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微,自称“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7]1664,其《杂诗》二首也是此期建康高门模拟古风的代表。刘宋王室如南平王刘铄作有拟乐府、拟古诗,其“《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8]。作于刘宋末期的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模拟汉至刘宋30位代表作家的作品。鲍照存诗约200余首,其中86首为拟乐府,25首是对无名氏古诗和阮籍、陶渊明等的拟作,堪称刘宋时期最热衷模拟的作家。除拟乐府和古诗外,人们对汉大赋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如谢灵运作于425年且自注的《山居赋》,规模宏大,以谢氏庄园媲美皇家园林,其写作手法以司马相如《上林赋》为学习对象。可以说,士族对文学遗产的占有与学习,也是此时“回顾历史”兴趣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融合汉晋乐府、汉大赋、文人诗片段的新型书写范式
刘宋文人在规步前贤的同时并未受其约束,而是自由驱使传统资源,从中选取适用部分加以改造糅合,最明显的即有意识糅合汉晋乐府、汉大赋、文人诗等“记忆、文本片段”。从此点入手,下文详论如何将这些压缩的文本构建成为层叠、交叉的行文结构。
首先,刘宋文人普遍不满建安文人所作的离题悖乐的乐府诗,多依古题古意,“且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9]。如在语言体式上,除吸收西晋铺排结构、繁缉雕饰之外,还反映出有意识存留古辞之体的倾向,如谢惠连《鞠歌行》及谢灵运、谢惠连《顺东西门行》使用“三三七”句式,谢灵运《上留田行》“上留田”、《相逢行》“忧来伤人”反复出现,《折杨柳行》其一写弟远行,与兄嫂离别对话,“神情高朗,直逼汉人”[10]37,颜延之《秋胡行》其五、六首叙述“遇于桑下,秋胡子下车,与之以金也”[11]等故事片段。相对于西晋傅玄、陆机故事乐府继承汉乐府体式及向乐府表演艺术功能的回归[12],刘宋诸人的创作无疑也属于此种创作倾向的有意继承。这些乐府诗是否与现实乐曲配合,情况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其自觉靠近汉乐府歌诗产生之际的原生态形态,使“歌”的成分远大于“诗”。
其次,乐府诗受汉赋程式影响和发展,有以下几点:第一,对汉赋的铺排结构、辞藻对仗的大量接受和发展。这种创作手法始于曹植《名都》《白马》之作,陆机在此基础上排比铺张,遂开出排偶一家。“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凡譬喻多方形容尽致之作,皆乐府遗派也”[13]。“士衡五言,如《赠从兄》《赠冯文罴》《代顾彦先妇》等篇,体尚委婉,语尚悠远,但不尽纯耳。至如《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门有车马客》《苦寒行》《前缓声歌》《齐讴行》等,则体皆铺叙,语皆构结,而更入于俳偶雕刻矣。”[14]88-89乐府体比徒诗体更适合事物的铺展。谢灵运更进一步,其《长歌行》十联除尾联“幸赊道念戚,且取长歌欢”不对外,其余九联都很工整,其《会吟行》十六联中九联对仗,远高于陆机《吴趋行》。时人不满陆机乐府“一味排比敷衍,间多硬语”[9],即那些不凝练的口语化诗句,逐步放弃以散文写诗的方法,以赋法原理写诗。同时创造性地铺排融合词语错置的“丫叉句法”[15],如谢灵运《悲哉行》“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二三句相承,一四句呼应,造成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相反,取得生新的艺术效果。这种通体用俳的作法以至铺叙过多、忽于剪裁,被讥为“作体不辨有首尾”[16]624。鲍照在谢灵运基础上,形成了许学夷所说的“凡不当对而对者,为渐入律体”[14]116。第二,大量排偶对句使其自身具备完整性和独立审美价值,可从上下文摘取,且以事形为本,省略汉赋“劝百讽一”的规谏之言,大大缩短了乐府诗的结构。如《苦寒行》,魏武帝“北上篇”六解,明帝“悠悠篇”五解,谢灵运拟辞仅五言六句。他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五言六句,通体用俳,完全略去古辞、陆机有关罗敷采桑的本事,用工笔画手法专咏有限范围(眼前)的美人,实开齐梁咏物一体。由于乐府与汉赋的天然渊源,古辞皆带汉赋讽谏戒惧之义,如陆机《齐讴行》拟左思《三都赋》,《文选》张铣注:“其终篇亦欲使人推分直进,不可苟有所营。”[17]颜之推评:“陆机《齐讴行》,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18]看似失败的写法皆脱胎于汉赋曲终奏雅、“归之于正”的惯常手法。然沈约《齐讴行》八句但赋齐地风土,缺少点睛题旨。再如《相逢行》,《乐府解题》称“古辞文意与《鸡鸣曲》同”[19]508,《乐府原》释《鸡鸣曲》“以桃李相依戒此篇”[20],陆机《长安狭斜行》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19]508,仍有“义正”之辞。谢惠连八句表现贵族生活方式及功业意识,沈约六句仅写贵游之士的奢华生活,皆失“言之助”。
再次,由于与音乐的疏离,文人将山水诗的手法移植于乐府,如时人继承了陆机乐府(如《从军行》《悲哉行》)相对独立的景物描写,大谢以山水诗见长,陆机乐府中的景物描写激发了其热情,纷纷将山水诗的手法移植于乐府。相对于以亲身登临的写实手法创作山水诗,乐府的山水描写主要源于学识和想象,如谢灵运《泰山吟》,作者从未亲临泰山。大谢山水诗常使用与登高相适应的观察方法,建立高位视点,描写的山峦多“有岩石的险峻高山,而且重点描绘的是山顶部分”[21],且善用双声叠韵字,以视觉、听觉增强对景物的直观感受,如《泰山吟》“岞崿既崄巘,触石辄千眠”仅截取泰山高耸入云的顶峰,从“岞崿”“崄巘”这些带“山”字旁的“联边字”的排列和塞擦音,就可感受到泰山之巍峨神秘。孙月峰评鲍照《代苦热行》:“形容苦势处不遗余力,胜士衡《苦寒》,然尚不及魏武。彼就实事写来,神采自溢,此自凿空撰出,安有真味?”[22]159可知均为想象之作。谢灵运《会吟行》“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运用山水诗一行写山、一行写水的对偶艺术,试图通过诸种细节传达完整的画面。其《苦寒行》只有六句,只沿袭陆机之作的纯写景部分。另外,还将山水游览和乐府中及时行乐、感时伤物的写法结合起来,用天道四时的推移观照人世的盛衰变化。汉乐府中就有类似写法,如《乐府解题》解《伤歌行》:“古辞伤日月代谢,年命遒尽,绝离知友,伤而作歌也。”[19]897只是乐府诗中景物多为阐述题旨的概念化描写,而非实景。时人将晋宋行旅诗的写作模式与乐府感慨时光易逝、亲友分离的题旨结合起来,如谢灵运《悲哉行》从冬春之变而触物兴怀,陈祚明评:“感时物而思友生也。”[23]谢惠连《塘上行》“沾渥云雨润,葳蕤吐芳馨”,近于张协“巧构形似之言”[24]之作。谢惠连、沈约《豫章行》均由行旅写景到友人别离,最后感叹“寿短景驰,容华不久”[19]501。
相比于时人山水诗情景分离的三段式结构,此时的乐府诗有意识糅合汉乐府、赋、文人诗三重成分,在三者转换过程中遵循“杂而不越”的结构方法。
第一,如上文所论,使用汉乐府、赋、文人诗等文本片段,依然按照原文本的写作方法,表现出维护各自文体的倾向。
第二,使用的汉乐府、赋、文人诗,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孤立的片段(也是被遗忘的文学传统),但又有易于交叉、重叠的结构,刘宋文人通过叙述、串联将其形成逻辑严密的稳定结构,保证了过去的文本在跨历史的共识中被阅读。如鲍照《阳春登荆山行》首句“旦登荆山头,崎岖道难游”,用山水诗的登临模式,中间写景“花木乱平原,桑柘盈平畴。攀条弄紫茎,藉露折芳柔”纯为文人诗写法,结尾“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则继承了乐府诗的歌唱传统,从而将晋宋山水诗与乐府音乐合二为一。颜延之拟西晋傅玄《秋胡行》作同题五言九首,比原作长了两倍多,作品内部呈现一定的写作方式和叙事原则,如第二首以秋胡视角叙述,从“驱车出郊郭,行路正威迟”到第三首结尾“悲哉游宦子,劳此山川路”,纯为晋宋山水行旅诗写法,叙旅途之劳顿及景色之荒凉。何焯评:“题是《秋胡诗》,然重在洁妇,今诗中详述秋胡宦游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顾略焉,体制殊不可解。”[25]即乐府体夹杂大量行旅诗句,重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轻故事情节。第四首以秋胡妻为视角,独守空房,四季变化触发思君之情,类于张协《杂诗》之作。第五、六首转换为秋胡视角,写桑园相遇。第九首“自昔枉光尘,结言固终始。如何久为别,百行愆诸己。君子失明义,谁与偕没齿?愧彼《行露》诗,甘之长川汜”,转换为第三人称,代妻作责夫语,承袭汉乐府道德褒贬的写作模式。这九首诗每部分尽量保持各体的独立性,整体追求句式整饬、声律和谐,隶事用典则尽量使叙事雅化。乔忆《剑溪说诗》言:“《秋胡行》,如曹氏父子,乐府体也;傅休奕、颜延年,古诗体也。”[26]值得一提的是,《行露》取于《诗经·召南》,写女子反抗欺凌,将诗题写进文章,点明寓意。这种创作手法较早见于汉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再如谢灵运《山居赋》“卷《叩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秦筝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旧受还”,将新兴的江南民歌纳入。时人在诗中时常使用这种手法,如沈约《王昭君》“始作《阳春曲》,终成《苦寒歌》”,刘铄《拟青青河边草诗》“楚楚秋水歌,依依《采菱》弹”,都可见汉赋的影响。这种融合多种传统资源的写法,多方位促进了乐府古诗化进程,如鲍照《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除尾句外,写宫阙亭台、声色伎乐全为对句,几乎看不出是乐府体。吴淇将其与陆机原作对比,认为:“此叙事处,伦次一些不乱,然只是平衍,固是古诗之体。”[27]
第三,汉乐府、赋、古诗片段是不稳定和易于变化取舍的。有些片段随着文学思潮、评价模式和作者取舍的变化而变化,以前重要的片段后来不再重要,甚至消失。比如汉赋的道德评价模式,在刘宋以后的文人乐府作品中几乎被抛弃。沈约《江蓠生幽渚》从陆机《塘上行》首句“江蓠生幽渚”衍生,只在末句“愿回昭阳景,时照长门宫”以陈皇后冷落长门宫比附甄后见弃而稍有古意,主体以香草象征女主人公的高洁,赋咏铺排江蓠,这就从题目上脱离了乐府写作传统,使诗题与内容相符,以散文式的行文概括,趣味优美文雅,体现了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
三、从书写范式转型看拟乐府之士庶分流
这种融合以往多种风格的文学资源,建构复杂的行文结构,成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士族文人“集体的文学选择”,从拟作对象的选择、审美取向等方面反映出一种新的乐府类型——士族文人乐府的审美趣味。所谓“士族文人乐府”,乃指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由门阀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乐府诗,此类作品在承继前代乐府诗贵族色彩的基础上,表现出鲜明的士族意识[28],从而与庶族、平民文学相区别。
首先,士族的根本文化属性即经典性和仪式性。经典性在刘宋拟乐府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上文所论,针对文化传统的断裂,重构那些不流行、被遗忘的文学片段,使之在诗学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
第二,用典繁密。以谢灵运为例,“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康乐之诗不易识也,徒赏其富艳”[29]3,主要针对其山水诗用典富艳,以至“不易识”。实际上,他的乐府诗也遵循同样的用典原则,其《善哉行》“滔滔武夫”用《诗》“武夫滔滔”,只更改顺序,“阴灌阳丛”,张来山曰:“阴灌阳丛句,非深学《易》者不能达。”[29]16《陇西行》“鸟之栖游,林檀是闲。韶乐牢膳,岂伊攸便”,用老、庄道家之言。《顺东西门行》“挥斤扶木坠虞泉”,出自《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贵族由于占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倾向于大量用典,以表现其阶层的知识修养。在印刷术流行之前的南朝,抄撮、抄撰之风为当时文化的一大特色,帝王之崇文,藏书之丰富,导致了征事、策事之风行,出现了专门的抄撰学士,如“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驎士应选”[16]943。此类群体常以贵族子弟担当,如谢混曾编60卷的《集苑》;元嘉三年,谢灵运曾为秘书监,“使整理秘书阁书,补足阙文”[7]1772,“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30],他们作为朝廷及王府的文翰之士,主要从事整理典籍、治礼撰史、吟诗作赋等。刘宋时期士庶关系的变化,“上升到公认的大族地位的寒人还是极少数,但寒人与皇权结合的事实毕竟意味着高位被士族垄断的局面已有解冻”[31]。具备文学才能的寒庶人士,也可跻身权力核心。如徐爰曾撰国史,被归为寒人掌机要的“恩悻”类。临川王刘义庆曾招庶族文人之有“词章之美”者如何长瑜、鲍照等,引为佐吏国臣,何长瑜还与谢氏家族成员有“共游”经历。可见,除了士族之外,具备较高文化修养的寒庶文人也有机会接触高门文化圈,士庶存在交往、融合,并不尖锐对立。
第三,文学趣味偏向于模拟经典,且在形式上趋同,遵从程式化的写作范式。经典性表现为大量拟作乐府旧题,“沿袭古题,唱和重复”[32]。特别是相和三调,汉魏相和歌辞或歌咏大众的普遍心理,或宣传个体独特的情怀,在后代积累了许多题材资源和文学传统,更符合文人心理及其艺术需求,在刘宋早已被官方视为“正声”。相比于士族,庶族文人表现出对杂曲歌辞的浓厚兴趣。如鲍照拟旧题乐府37首,除少量为琴曲、舞曲歌辞之外,杂曲歌辞有19首,占一半多。杂曲歌辞“亡失既多,声辞不具”[19]885,缺乏文学传统。时人对脱离传统的建安乐府不感兴趣,鲍照却从其中衍生新题,如《代堂上歌行》拟曹睿《堂上行》,《代苦热行》《代升天行》《代陈思王白马篇》直接模拟曹植,《代出自蓟北门行》《代结客少年场》分别化用曹植《燕歌行》《结客篇》首句。还有出于《诗经》的,如《代鸣雁行》出自《邶风·匏有苦叶》“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代北风凉行》出自《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其余如《代阳春登荆山行》《代居边行》《代少年至衰老行》《代邦街行》,因过于脱离乐府传统而为《乐府诗集》所不收。同为庶族的吴迈远,其《长相思》《长离别》题目及内容均取自《古诗十九首》之《客从远方来》“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仅用其相思绵绵之意,缺乏乐府因素。汤惠休乐府虽多用相和歌辞,但体式上明显受流行音乐影响,被颜延之讥为“委巷歌谣”,实为宫体描写女性之先导。出身武力强宗的刘宋王室还创制了两个影响较大的乐府新题,即孝武帝《自君出之矣》和刘铄《三妇艳》,前者属杂曲歌辞而出自徐干《室思诗》之第三章首句,后者出于《相逢狭路间》,两者同属“摘句法”新制,有明显的艳情倾向,显然也是新声影响下的产物。
其次,拟乐府之仪式性主要表现为文本形式上的一致性,受制于规范。如陆机《遂志赋》所谓“拟遗迹于成规,咏新曲于故声”,涵盖了士族乐府的两种主要创作方法,即形式上的重复和差异。
先看重复。沈约《梁甫吟》拟陆机,同为五言二十句,陆诗“蒸”“青”换韵,沈诗通押“青”韵,以下用黑体将趋同语标出,以见模拟情形:
陆: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沈:星钥亟回变,气化坐盈侵。
陆:冉冉年时暮,迢迢天路征。沈:寒光稍眇眇,秋塞日沉沉。
(按,此二句有意颠倒词序并有意用对仗法模拟。)
陆:悲风无绝响,玄云互相仍。沈:飚风折暮草,惊竿霣层林。
陆:年命时相逝,庆云鲜克乘。沈:奔枢岂易纽,珠庭不可临。
陆:履信多愆期,思顺焉足凭。沈:怀仁每多意,履顺孰能禁。
陆: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拊膺。沈:哀歌步梁甫,叹绝有遗音。
由上可见沈约对陆机步趋如一的模拟,包含了反复和不断使用的文本。再如鲍照《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悲哉行》均模拟陆氏,在题目、内容、修辞、押韵方面完全一致。士族将古典资源中繁文绮合的文本制作程序与个人情思及家族情怀结合起来,构筑“杂而不越”的复合文本,使之成为主流文学样式。庶族文人要想成为文化士族,必须小心翼翼地贴近模仿,鲍照的模仿就是士族文学传统巨大影响力的反映,他也进一步开创了一种更严格的“限定性文学”范式,《松柏篇》序明确表明模拟傅玄《龟鹤篇》,《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代曹子建白马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拟作范本。这意味着唤起了具体语境中拟作者的共鸣,对原作传递信息的充分接受,拟作过程中对体制、措辞、声律等都要以“得体”为原则。士族制作的文学文本就像合同一样具有约束力,意味着无条件向高难度看齐,苛求他人但值得追求。在制约的基础上施展才华,在文本制作上提出更高要求,更需继作者在学识积累、诗学技巧方面长期磨炼,即《文心雕龙·体性》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才能“得其环中”,这种拟作方法被誉为“文之司南”。王夫之评价陆机《拟古》说:“步趋如一,然当其一致而成,便尔独抒高调。一致则净,净则文。”[10]174这也可作为对后人模拟陆机的评价,追求一致从而突显“文”的特色。文本的一致性也允许、鼓励差异性的存在,文本在传统延续过程中,有些文本不免被抛弃、遗忘,新产生的文本不得不与旧文本一较高下,那些“存留”下来的文本被视为更悠久、珍贵和权威的文献。继作者在原作与文学传统面前,有一种担心名声、作品不被人传诵的焦虑,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将自己和作品纳入“传统之流”,另一面试图使作品以奇特、新颖的形式成为新奇、陌生的东西,与耳熟能详的传统并驾齐驱,甚至一较高下,因而绝对不能重复别人已说过的话。从沈约对陆氏的模拟来看,将其句式的颠倒、用更高级的修饰词汇替代即是。可以说,重复性、差异性的模式化写作并不妨碍文学的呈现,反而可充分调动拟作者的积极性,使得文本向深度开掘,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成为文化结构、知识得以传承的“桥梁”。与传统完全断裂的创新无疑等于遗忘,曹操的乐府诗、曹植以“拟”“当”形式改制的新作被南朝人抛弃,就说明了此点。在这个意义上讲,南朝人对“步步蹈袭”的作品不仅不排斥,反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金楼子·立言》评陆机为“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即赞其才华横溢而“不逾矩”[33]。
再次,在描写女性方面,庶族文人发挥乐府艳情一脉的传统,士族文人则试图在文学创作与士族礼法之间寻找折衷的平衡点,向往伦理和审美协调的美学风格。汉乐府《陌上桑》本身就存留描摹女色一脉,庶族诗人拟作时将其作为描写重心且日趋艳情化。鲍照《采桑》描写采桑女子冶容,“采桑淇澳间,还戏上宫阁”“卫风古愉艳,郑俗旧浮薄”借用《诗经》“桑间濮上,男女相悦”“淫奔”的典故,将其引入艳情。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悲歌吐清响,雅舞拨《幽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中丽人表演的七盘舞,是歌颂西晋盛世安宁的郊庙朝飨的大型雅舞,透露着贵族奢华生活及其“雅而艳”的欣赏趣味。傅玄《艳歌行有女篇》“容华既已艳,志节拟秋霜。徽音冠青云,声响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与王”,以女性坚贞相配公侯,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傅玄《艳歌行》,全袭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盖欲辞严义正,以裨风教。”[34]其《秋胡行》《秦休女行》亦大肆宣扬伦理道德。此种写法对南朝士族影响极大,一面重视女性姿容刻画,另一面引入儒家礼法以融合调节,竭力刻画美貌端庄、贤良贞洁的女子,为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谢灵运《日出东南隅行》中的女子“怀兰秀瑶璠”,不仅外表美,还有“皎洁秋松气,淑德春景暄”的美德。谢惠连《捣衣诗》“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深夜思念良人的美女仍严装正服。颜峻《淫思古意》亦曰“贞洁寄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庶族诗人也有许多重情的描写,如鲍令晖《古意赠今人》“容华一朝尽,惟余心不变”、吴迈远《长别离》“蕙草每摇荡,妾心空自持”等,主要继承的是《古诗十九首》及汉魏古诗的人性情感而非伦理道德。
更重要的是,由陆机提倡的“雅而艳”的士族审美理想,经过“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特质浸染,改变了东晋南朝士族的审美追求。他们没有西晋士族所追求的那种浓烈的美,他们喜爱的是一种简淡的透露着高雅趣味的美,即谢灵运《山居赋序》所谓“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将富艳之辞与寡淡折中调和,这是对孔子“绘事后素”儒家美学思想的变相继承再加上“礼后”的约束。以《三妇艳》为例,其变化反映了士庶阶层的审美差别。《三妇艳》为军功出身的刘铄首创,“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写丈人与儿媳在庭中享乐,有些不伦。其后王融、沈约、萧统将“丈人”改为“丈夫”“良人”,去掉了暧昧意味。乐府诗中涉及的女子,即便冶艳而充满性挑逗,最后也尽量归于守礼持正、以礼节情,即陶渊明《闲情赋序》所谓“始以荡以思虑,而终于闲正”。
最后,乐府诗反映的士族功名意识,多与贵族生活方式及家族荣誉相关。陆机《长安有狭斜行》“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将古辞改为贵族的奢华生活。谢惠连拟作缩短为八句:“帟帟雕轮驰,轩轩翠盖舒。撰策之五尹,振辔从三闾。推剑凭前轼,鸣佩专后舆。”仅保留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功业意识。沈约四句只写炫富的贵游子弟。有些也透露出诗人的处事心态和家族传统,如谢灵运《折杨柳行》其二:“否桑未易系,泰茅难重拔。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此诗用《易》典:“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又: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语或默。”[29]28包含着对人生出处进退的思考。若遇“否卦”(时运蹇劣),虽有“休否,大人吉”(停止行动,对贵人来说,仍可得吉利),却并无把握;遇上“泰卦”(时运顺利),也未必能“征吉”。他在出处选择的犹豫之中,始终在归隐和庙堂之间徘徊,其《善哉行》“善哉达士,滔滔处乐”,遂将古辞游仙转变为隐居以求其乐。谢氏一族有家族隐遁传统,谢灵运《述祖德诗序》称:“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赞美谢安隐遁东归的高情远志。心中的“达士”即《述祖德诗》其一所云:“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他们对待社会现实,持父祖“贵自我”“济物性”的清高生活态度。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他们也不像鲍照等庶族文人那样不平则鸣,而倾向于老庄的守静自遣,如谢惠连《顺东西门行》云:“哀朝菌,闵颓力,迁化常然焉肯息;及壮齿,遇世直,酌酩华堂集亲识。舒情尽欢遣凄恻。”强调的是士族的情感节制和抒情品格。
再看庶族文人阶层参与文化的方式,多将文化作为社会问题来对待,反映下层民众生活,格调哀怨悲凉。如鲍照多采用汉乐府描写底层民众苦难的题材,《代东武吟》写艰苦战斗的老兵,《代东门行》写被迫分离的贫贱夫妻,其自创新题《代贫贱苦愁行》不遗余力赋写人世苦难——贫、贱、苦、愁。又如陆机、孔宁子、鲍照、吴迈远的同题拟作《棹歌行》,陆、孔用宏大场面应制颂赞,鲍、吴赋写孤苦沮丧的行役旅程等,充满了“贫穷和死亡的主题”[35]。他们更需要抓住自身生存的基点,发出更强的呐喊和抗争,同时为了接近王侯、谋求仕途,也需在主流之外另辟蹊径。更重要的是,士族文本要求的约束力,使某一个特定的乐府古题展现出普遍性的题材传统,即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谓“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32],而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差别较大。文人遵从这种原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个人的权利,必然忽视叙事内容的充实与创新,刘宋文人拟乐府被评为“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9]的原因正在于此。与按古题古意索骥不同,庶族阶层多反映真实的个人行踪和志向等人生层面,表达对现实的看法,蕴含着自身的切肤体验,也就是以往文学史评价极高的“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除鲍照外,庶族如孔欣、袁淑等人,其乐府之作虽少,但其中灌注着深厚的情感,努力使其反映现实。袁淑《白马篇》虽效仿曹植,但多流露个人胸襟,“嗟此务远图,心为四海悬。但营身意遂,岂效耳目前”,刚正不阿、忧心国事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因在刘邵弑逆之举中不屈而被杀害)。孔欣《相逢狭路间》写归隐志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抒发自我情志的乐府,“此诗高趣,可并渊明。欣早岁辞荣,不负其言矣”[36]。
总之,以鲍照为代表的庶族乐府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的特点,备受后代评论家的极高赞誉,如刘熙载言:“明远长句,慷慨任气,嘉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37]而在当时,其代表的寒庶“险俗”诗风,不符合士族推重的受制于前代规范、雍容典雅的一派,虞炎在编集的序文中评其“虽乏精典”[22]1即是。萧子显也评其为“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16]908。可谓毁誉参半。他们挣脱了文学传统,尽情表达本人情感,仅此一点,也完全迥异于诗歌主流。当时鲍照派的流行,也主要是其中“雕藻淫艳”的一类,其拟古诗和拟旧题乐府,并无太大影响力,虽汲汲于主流诗风,实际上并未得到时人认可。
四、余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的社会动力
上文详论刘宋时期拟乐府的转型,是由于士族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企图驱使各种传统资源,从中选取适用部分加以改造糅合,追求多层次的复合行文结构,多方位继承各种风格及多元文化导致的。士庶乐府在当时树立了典范,庶族的写作方式既有贴近士族的一面,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转型的社会动力无疑来源于当时社会阶层的变动,以下简要对其进行探讨。
首先,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取决于其经济、政治地位。魏晋以后,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载体的门阀士族,其社会地位急速上升,成为不可低估的掣肘作用强大的社会群体。其经济地位依靠大田庄产业,主要是山川与耕地相关联的多种经营。谢灵运《山居赋》注“非无田以立”,可见这类产业是门阀士族的物质基础。且许多士族以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要分割山泽之内的本属朝廷的自耕农民户口,经济上的矛盾一直存在[38]。经济地位的霸权,相应必然追求学术文化方面的优势。不注重文化修养必然为世所轻,地位难保。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在社会的比例较小,以血缘为纽带,在印刷术流行之前,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各项特权,同时运用垄断的知识、文化对社会进行管理和统治。因此,在知识精英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导致社会分层,向纵横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在纵向上,将受过教育的上层与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区别开来,贵族制定了与庶民隔绝的种种规矩作为游戏规则,使文学成为表现其知识、身份、修养的礼仪文学,通过高难度的用典、精致复杂的对偶等技巧及对形式美的追求,将其与文学能力粗糙的庶民文学区分开来。由于精英文化向底层渗透力很弱,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层次——贵族的说话、写作必定文雅高尚、引经据典;庶民则发言通俗、言之无文。庶族想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必须小心翼翼地贴近、模仿,而且自身原本文化形态的“鄙野”也必须抛弃。
精英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能够促进身份的认同,那些文本的约束力、规则、价值取向能够维持和助长特定的、集体的身份认同(形成集体的“心照不宣”)。本来追求本文一致性只是一种“中性”的写作模式,但此时却变成了强化身份认同并显示优越性的充分条件。规范性的文本教导人们判别是非、做正确的选择,同时也传承着未来知识、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刘宋拟乐府写作范式转型为例,将断裂的不同形式的文学传统、文本痕迹编织成新的文本,沟通从过去到现在并通往未来的连续文学线索,让过去的文本变得“陌生化”。这种新的“文化一致性”即通过集体反思而形成的对某种文化的绝对信仰,成为天下的“公共经典”。这种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的形成,其必然结果是其掌握者也会被推上神坛。更重要的是,精英文化掌握者并不认为自身拥有的是一种“特殊”“代表性”的文化,而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全方位仲裁者,承载着“整个”文化,如王、谢等世家大族,将其锋芒不仅剑指一般士人,甚至刘宋王室。刘宋王室是军事上的胜利者,但不是学术文化的胜利者,学术文化与政治地位并非同步发展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精英文化已不单纯是上层文化,而是通过纵向上的团结、一致试图越过士庶的鸿沟而实现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也产生了文化的“归属”意识——通过共同的价值观监督、管理个体化的倾向,个人也通过群体的认同、在群体中的角色扮演来确立身份、实现自我。
再看社会分层的横向发展,“一体化”的文化“归属”意识,也在不断消解纵向的社会阶层,庶族文人代表如鲍照、何长瑜及梁代何逊、吴均等出身底层的士林可以凭借后天的学习、修养而跻身贵族文化圈,两者相处融洽,并不存在尖锐对立。底层人士习得这种贵族文学技巧,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用富艳的辞藻、典故组织成文,在句数、句法、押韵、修辞上极尽能事,甚至比贵族阶层的文学要求更高。只有这样,贵族文学圈才会对其敞开门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文化上的高等阶层。如出身北府兵将领的刘宋王室凭借军功夺取皇权,但文化上并不占优势,他们仰慕世家的文化威仪,“颇慕时流”,逐渐成为具备文化修养的次等士族,士庶阶层进一步转化、分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的排他性不仅针对下层的寒庶人士,也包括不能遵从“贵族性”写作的贵族。从这个角度说,精英阶层能够不断吸纳符合要求的底层士林进入,士庶之间不断融合,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贵族阶层随着历史而消亡也成了必然趋势。再从庶族角度看,他们不仅努力接近士族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自身寒庶写作方式从而形成了一股“反经典”力量,从写作方式、审美取向等不同方面对经典的反叛、背离,但并不表现对“公共经典”的颠覆和取代,“经典与反经典的‘正反’关系,成为对经典的必要补充,形成‘合力’”[39],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形式,顺应人们新的审美需求,也形成了后代经典与反经典之间的兴替往复。如鲍照“代乐府”,在当时不被主流接纳,但在萧统时代,编纂《文选》“乐府”类收录八首,成为除陆机之外收录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不仅成为士族乐府的补充,而且也升任“新的经典”。
总之,以王、谢等世家大族将以往的文化资源、多层次的复合行文机构、具体情事和王朝话语权结合起来,企图凭借文化的规范性、礼仪性来维护家族门户的地位,在当时的士庶文化圈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刘宋树立了皇家政治权威,严格意义上的门阀士族已不复存在,但其经济实力依然存在,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并不自动引退,企图将这种贵族写作模式保留下来,仍旧在学术、文化方面占据上层,并凭借文化优势反过来巩固其岌岌可危的地位。同时,为了保持稳定,刘宋的皇权政治也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造成了客观上一方面通过学习士族的文本写作方法来保持某种平衡,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代表自身喜好的欣赏趣味纳入文坛主流,重建新的文化模式。可以说,齐梁以后士庶文学的分流和融合就是这几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对后世诸如齐梁诗歌的新变、宫体诗的出现,也具有必然的源流关系。
[1] 牟愿相.小辦草堂杂论诗[G]//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78.
[2] 丁福林.东晋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M].西安:世界图书西安有限公司,2014:155.
[3] 王志清.论刘宋文人乐府的复兴[J].乐府学,2007(总2):198-216.
[4] 文晓华.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J].北方论丛,2011(1):9-13.
[5]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3.
[6] 郭晨光.刘宋新旧乐更替的音乐背景与鲍照代乐府创作——兼论其音乐表演属性[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0-106.
[7]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395.
[9] 黄子云.野鸿诗的[G]//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95.
[10] 王夫之.古诗评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5.
[12] 郭晨光.从拟作角度谈西晋故事乐府对汉乐府体式的复归——兼论汉乐府经典地位的定型[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4):130-134.
[13] 施补华.岘佣说诗[G]//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10.
[14] 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5] 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15.
[1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7] 萧统.六臣注文选[M].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522.
[18]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27.
[19]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 徐献忠.乐府原[M].内府藏本.集303:754.
[21] 小西升.谢灵运山水诗考——自然素材的选择与审美意识[G]//宋红,编译.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7.
[22] 鲍照.鲍照集校注[M].丁福林,丛玲玲,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3]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0.
[24] 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84.
[25]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894.
[26] 乔忆.剑溪说诗[G]//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29.
[27]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340.
[28] 孙明君.两晋士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1.
[29] 黄节.谢康乐诗注 鲍参军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0]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906.
[31] 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0-151.
[32] 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292.
[33] 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966.
[34] 谢榛.四溟诗话[M].宛平,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
[35] 苏瑞隆.鲍照诗文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6.
[36] 杨慎.升庵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刘熙载.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268.
[38]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36.
[39] 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J].文史哲,2010(2):5-16.
——以《登大雷岸与妹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