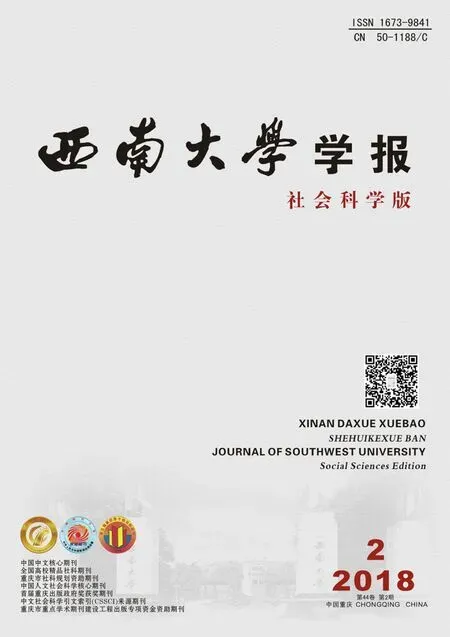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
——法国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再发现”
刘 怀 玉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西方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彻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史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历史。即有多少种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解,就有多少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1]59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二战前后法国思想界包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解。
近现代法兰西民族文化的传统,总体上说是擅长于文学艺术科学探索而稍短于哲学理性思辨精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19世纪的法国是政治发达而“哲学贫困”。曾几何时,在19世纪德国哲学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与之相比,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则显得有些苍白*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有关19世纪法国哲学发展概况,可参看[法]丹尼斯·于斯曼主编:《法国哲学史》,冯俊、郑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9-320页。。于是,黑格尔被法国人接受与理解也就是相当困难而晚近的事情了*20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拒斥与无知状态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对此,萨特有过一段著名的回忆。他说:“1925年,当我二十岁的时候,大学的讲台上不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否则就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当时学校里对辩证法十分恐惧,所以我们连黑格尔也不知道。”引自[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此所谓“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或如另有学者所说:“一个人的声誉史是一部各种分歧的记录书。某个人的所作所为与世人对他的看法之间,彼此总是相去甚远。这些分歧有的是时间上的,……有的是空间上的。”[3]这颇有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一般认为,黑格尔刚刚去世时的19世纪40年代,曾经是黑格尔主义影响如日中天的鼎盛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与存在主义(施蒂纳与克尔恺廓尔)的孕育期。但在1848年革命之后,黑格尔哲学逐渐被挤出思想舞台,而长期处于被人遗忘、受人冷落的状态。直到20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黑格尔逝世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哲学又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受到了法国思想界的青睐。这就是著名的“黑格尔思想复兴”现象,也成为20世纪法国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重要思想背景。为此,美国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法国人接受黑格尔,这是法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44年后,人们渴望社会、政治和知识完全更新。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票达到多数,知识分子梦想着即将到来的激进社会理想。在那些充满着希望但最终令人失望的战后岁月里,发现黑格尔式辩证法成为‘决定性的事件’。由此,在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崩溃、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和对黑格尔哲学兴趣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4]4
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他们所理解的“法语黑格尔”(French Hegel)是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之后即20世纪30年代由让·华尔(Jean Wahl,1888-1974)、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和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这三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联袂提供的。正是通过他们对《精神现象学》的重新解读,才使得黑格尔在法国得以复活。由于这三位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作为《精神现象学》作者的黑格尔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遇与融合的起点,也就是“有法国特色”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伊波利特与科耶夫的学说也是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4]5。其中,让·华尔的《黑格尔哲学中的苦恼意识》(1929)一书,为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他赞同克尔恺廓尔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必须抛弃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成分,而要突出其关于个人的自由与生存的辩证经验。伊波利特笔下的黑格尔则完全是一位个体化与主观精神化了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绝对精神的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当年所着重阐述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精神的哲学家。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克服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体对峙,克服法国哲学所面临的康德式的应有与现有、历史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等众多矛盾与危机而走向主客体统一的生存哲学的开端。当然,相对而言,科耶夫与海德格尔比较接近,而伊波利特与萨特比较接近。科耶夫的“黑格尔”是“主奴辩证法”的哲学家,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则是“苦恼意识”的哲学家[4]26,33。这两个著名的隐喻与命题,成为战后法国思想界所有激进思想家解决许多基本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的经典“公式”或锁钥。
一、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与“历史终结论”
亚历山大·科耶夫是一位来自俄国的移民,1947年他以一部《黑格尔导读》而蜚声学界,而晚年则担任了欧洲共同体的高官。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因其于1933年至1939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进行的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系列讲座,引起了法国人文学界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运动。在他的课程听众中有许多即将成为法国知识界弄潮儿乃至大师级的人物,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他引导了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天主教者、小说家、共产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瓦解了法国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唯我论的僵化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结束了新康德主义与柏格森主义的思想霸权地位,形成了一种将个体的生存与历史活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起来的全新思想视野*关于科耶夫《精神现象学》讲座的历史效应,可参看[法]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美]伊森·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法]多米尼克·奥弗莱:《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Bruce Baugh, French Hegel: From Surrealism to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科耶夫的成功其实是以过分简单化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为代价的,是以一种“平装本”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流行为代价的,这导致了后来结构主义彻底宣布“人之死亡”式的反动。许多并不赞成科耶夫观点的思想家事后都承认,他们的青年学生时代其实是生活在科耶夫所造成的时代气息之中的。正像索绪尔是靠“述”而不是“作”,是靠一本讲义结集而成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深刻而模糊地,但又强烈地影响着战后思想界。科耶夫也是靠一部厚厚的“课堂讲座记录”而扬名巴黎、泽被后学的。这就是连同他的一篇专门讨论黑格尔主奴关系辩证法的文章在内结集出版的《黑格尔导读》(1947)*我们主要参看了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9;[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对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和政治的一种回答。黑格尔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回答了关于“人是谁”“人如何变成社会的”以及“社会中的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这些问题。从洛克到穆勒,那些自由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都是脱离社会的一种抽象自然主义界说。按照自由主义的传统,一种超历史的静止的人类理性地盘算着自己的长处,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小资产阶级风格,雕刻着自己的现实。这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鲁滨逊”式孤独个体发家致富、独创天下的故事。这类故事不同于当代中国武侠小说中那种孤胆英雄:他们似乎并没有自己明确的近代市民阶级基础;也不同于俄国白银文学时代那些无所事事的“多余人”:他们这些人无法融入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科耶夫批判了那种没有斗争便获得相互承认的理想的启蒙的社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假设,而着重解释了黑格尔通过主人与奴隶之间斗争而赢得相互承认的辩证法。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先验的单子或无历史的前提,而是相互斗争导致的自我意识。社会共同体的瓦解或异化,历史地导致了自我意识的产生。贯穿整个《精神现象学》一书,人、历史与社会是一体共存的。在这里,没有抽象的个体,即没有鲁滨逊。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一劳永逸地终结了那种将自我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这种错觉,终结了将个体的行为与个体的阶级想象为全人类的这种错觉。
在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中,他主要根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自我意识中主奴相互依赖的辩证法思想[5]122,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阶段与前景做出如下概括:伴随着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之间的最初斗争场面的出现,人类诞生了,历史开始了。“就是说——在最初——人要么是主人,要么是奴隶;仅仅在有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人。……世界历史,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是作战的主人和劳动的奴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因此,当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消失,当主人不再是主人,因为他不再有奴隶,以及奴隶不再是奴隶,因为他不再拥有主人,并且也不会重新成为主人,因为他将不会拥有奴隶,这个时候,历史停止了。”[6]202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7]。
按照这个概念,历史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或相互作用。这个概念可把历史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如果历史始于一个主人得以统治一个奴隶的斗争。那么:
第一个时期必然是人的存在完全由主人的存在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人通过行动实现其存在的可能性,从而揭示自己的本质。但如果历史只不过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那么奴隶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从而也完全地显现自己。第一个时期必须由第二个时期来补充。
在第二个时期,人的存在是由奴隶的存在决定的。如果历史的终结是主人和奴隶的综合,和对这种综合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时期必须在这两个时期之后出现。
在第三个时期,可以说中立化的、综合的人的存在主动地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从而向自己显现。不过,“这一次——这些可能性也意味着充分地和最终地,即完全地理解自己的可能性”[6]203。
科耶夫所理解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就其性质而言,是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历史观混为一体的结果。其论证过程很是复杂,其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过程[6]3-31:
(1)人的存在根本上是以欲望为前提的,是欲望的“我”,是否定的欲望或者虚无/空洞。但若要有人类欲望,首先就应该有动物欲望的多样性。而要使人真正地成为人,要使他从本质上和动物真正地区别开来,他的人性欲望就确实应该战胜他的动物欲望[6]4-7。
(2)人是自我意识的,但这种自我意识不是认知的、理性的,而是欲望的、实践的,而这种欲望要成为自我意识,还必须通过与另外一个欲望进行社会斗争才行。换言之,所有人类的人性的欲望,即产生自我意识和人性实现的欲望,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承认”的欲望的一个功能。谈论自我意识的起源就必定要谈论为了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死亡之战。没有这场为了纯粹的声望所进行的死亡之战,地球上就不会出现人类。人类历史等于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用马克思的话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人的基本社会关系或人类的普遍历史就是主奴互动关系的历史:历史的辩证法就是主奴的辩证法[6]7-9。
(3)因此,要承认对方就是要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主人来承认。而要承认自己就是使自己作为主人的奴隶而得到承认。换言之,人在诞生之时,他绝对不单单是人。从本质上说,他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隶[6]9。
(4)要使人性现实形成为被承认的现实,交战双方在战斗后都应该活着。因此,战斗中的一方杀死对手毫无益处,他应该辩证地扬弃他的对方,也就是说,他应该让他的对手活下来,让对方保留着意识,而只是毁掉对方的独立性,仅仅在对方反抗他、与他作对的情况下,他才应该扬弃对方,换言之,他应该奴役对方[6]14-17。
(5)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不是抽象的意识,而是“关系中的依赖着奴隶的意识的”这样一种现实的自为存在[6]17。
(6)因此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就不是所谓“对等”的“承认关系”。主人是被他所不承认的人所承认,就他的处境而言,这是不充分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主人的态度是一个存在性的绝境。一方面,主人之所以是主人,只是因为他的欲望不是指向一个物,而是指向另一个欲望——因此它是一个需要承认的欲望。另一方面,当他最终成为一个主人时,这个主人就是他应该渴望被承认的主人,他能被这样承认仅仅是使他者成为他的奴隶。但是这个奴隶对他来说是一个物或动物。因此他就被一个物所承认。这样他的欲望最终指向了一个物,而不是指向了——像他最开始看上去的那样——一个(人)欲望。主人因此处在一条错误的路上。非本质性的或者说奴隶的意识是主人的对象,这对象构成了他对他自身的主体确定性的真理。因而这个对象同其概念并不相符合。这就是说主体的真理是奴隶与奴隶的劳作。实际上其他人将主人认作主人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奴隶,而主人的生活就在于消费奴隶劳动的产品,并且就依赖于这种劳作而存活[6]20。
(7)结果,独立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主人的根本现实是他所想要的东西的颠倒或逆转,奴隶也是如此。在其完成过程中,他可能变成了他直接现实的反面。作为一种被压迫的意识,奴隶将自己逆转成为真实的独立性。如果懒惰的主人导致了死路,与之相反,勤劳的奴隶就是所有的人类、社会与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就是奴隶劳作的历史。人们只有从奴隶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人的角度,去思考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就是说,去思考人类、社会、历史的首次结果。
(8)通过劳动,奴隶消除了自然存在,成为自然的主人。表面上,奴隶在劳动过程中受自然、物、原材料的奴役,主人对这些物来说是绝对的自由,但实际上这都不是事实。“因此,最终说来,一切奴役劳动并不实现主人的意志,而是实现奴隶的——尽管最初是无意识的——意志,奴隶——最终——在主人——必然——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6]31
科耶夫通过综合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以及海德格尔,而形成了作为欲望主体、苦恼的主体相互斗争与“承认的政治”,特别是“历史终结论”等著名学说[8-9];进而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弗朗西斯·福山,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霍耐特以及后现代主义者拉康、鲍德里亚,新尼采主义者巴塔耶,后殖民主义者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及其先驱法侬,甚至女性主义者们竞争的思想资源[10]*关于科耶夫的讲座的总体效果史研究著作可参看[法]多米尼克·奥弗莱:《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以及[加]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对主奴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可参看[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拉康主义与主奴辩证法的关系研究可参看[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关于后殖民主义与主奴辩证法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著作可参看[法]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女性主义思想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关系问题研究最深刻的著作可参看Judith 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二、伊波利特的“苦恼意识”的辩证法哲学
让·伊波利特生于法国容扎市,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受过教育,服过军役,1930年代末在巴黎一所公立中学教书。按照波斯特的看法,伊波利特在向法国思想界介绍黑格尔方面比科耶夫完成的工作更多[4]18。作为巴黎大学教授以及随后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伊波利特从1930年代后期即写作有关黑格尔的论文并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于1939年至1941年间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精神现象学》法译本,并因此而跻身于法国哲学界(正像后来的保罗·利科第一个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1》译成法文版,而成为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一样)。二战之后,伊波利特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1946年的《〈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1948年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导论》、1953年的《逻辑与存在》,特别是1955年的《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研究》一书。伊波利特于1960年代教过一些已经成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学生,比如阿尔都塞、德勒兹、福柯还有德里达等人。显然,伊波利特在使法国的“黑格尔复兴”运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关伊波利特的生平与业绩,可参看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pp.18-20。。
与科耶夫的讲演不同,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评述试图尽可能减少评述者本人的主观引申[4]20。在不断地克制自己个人理解偏见的过程中,伊波利特一步步地将读者引向黑格尔复杂曲折的哲学思想过程,即如何从对客体的最简单的意识知觉走向最高形态的绝对精神阶段。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解读变成整整一代想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更多精神满足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的可靠的黑格尔思想文本。
在伊波利特所提供的《精神现象学》文本解读中,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被一种个人意识的自我探险历程所取代。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苦恼意识主宰下的追求自由的探险航行过程。正像笛卡尔的《论方法》一样,伊波利特向人们介绍了一种黑格尔形成自己思想的方法。被黑格尔描述为意识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模式,不再适用于世界历史,而只是黑格尔“个人的”思想发展的阶段。如意识的发展,从主奴关系到斯多葛派,从怀疑论阶段和苦恼意识阶段之能够被解释,这是和黑格尔个人所经受的理智教育密切相关的[11-12]。在伊波利特看来,《精神现象学》之于黑格尔,犹若《爱弥尔》之于卢梭。
虽然《精神现象学》预先按照黑格尔个人思想内在独特的必然发展逻辑而无意识地展开,但它毕竟也是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历史进入到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进入到《精神现象学》之中,这也是个人的内心自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历史与理性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赖的。正因为如此,从黑格尔开始,不再像笛卡尔那样,不再有一种自明性、确定无疑性之类的绝对真理性的逻辑出发点,而是通过一个不断的试错与误认、因而是反思的重新塑造或否定与自我扬弃过程,通过自我认识的历史过程,而不是自我逻辑证明的阶段,而展开自己的哲学体系。黑格尔通过现象学的、即自然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及其自我批判,而不是以绝对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静止的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而是一个主客体矛盾统一的历史认识反思过程。他认为反思的开端与终点就是一个通过意识的历史而自我发现的过程。
除此之外,黑格尔以人类自我认识与反思的哲学史方式而赋予人类以历史的观念。在他那里,哲学的历史与历史的哲学完全是一回事。自我认识的历史逻辑阶段与哲学史上的哲学发展阶段基本一致。伊波利特认为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误导,历史发展被黑格尔个人的自我认识逻辑所必然化、神秘化了。《精神现象学》的主要意图是描述如何从经验意识向绝对认识的逻辑提升。
按照伊波利特的解读,人最危险的问题就是他不得不成为他自己认识中的一个对象以便成为其自己。人必须通过外在化自身,使自身脱离自己,否定自己,异化自己以便认识自己进而成为自己。为了变成对自身现实的意识,人不得不将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才是可能的。只有通过变成“为他”,人才能变成“为己”。个人必须通过否定他的意识的既定的直接性,把自身投射到自然物的世界中去和其他人身上,才能带着自身的知识而返回自身[4]24。
有了这样一种承载着异化的人性观,伊波利特自然而然地被引向了一种极度夸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被称作是“苦恼意识”的这样一个变化环节[5]140。正像科耶夫发现主人-奴隶关系是《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一样,伊波利特则把苦恼意识提升为《现象学》的“根本主题”[4]26*有关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哲学在法国的影响史,可参看Bruce Baugh, French Hegel: From Surrealism to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Judith 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苦恼意识由于出现在斯多葛派与怀疑论的死胡同与绝路上,它象征了人最终认识到绝对精神是可以体验到的,却是处于人类“之外”的地方的这样一个环节或时刻。在最普通的意义上,苦恼意识是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即生命的意识是对生命的一种脱离,一种对立面的反映。伊波利特将黑格尔认识论上的一个环节的苦恼意识放大成为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一部犹太人的犹太教的历史就是一部苦恼意识的历史。因为它们的绝对真理即耶稣就是一个不可接受与到达的他者。与之相似,中世纪基督教的主体性,还有罗马人的感性同样承受着苦恼意识的折磨。他们都在渴求着一个永远弃它们而去的神灵。在伊波利特之前,让·华尔已经在夸张地解释与利用早期黑格尔神学著作中有关苦恼意识笼罩人类整个历史的神秘主义观点。华尔将黑格尔打扮成一个类似于克尔恺廓尔式的神学家,他将人类的基本状况描述为一种有限的悲观的人的生存意识反抗位居其上的无限的上帝的统治。
在伊波利特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哲学,主要不是一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生存哲学或生命哲学,这就是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基本结论。伊波利特的最基本看法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具有一个与现代存在主义相似的存在观念。正像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有着与海德格尔一样的存在观念一样!伊波利特认为,《精神现象学》是一部人的意识到达绝对的知的历史。这部历史所描写的远远超出它建立的意识经验的范围。不应该将黑格尔的经验理解为仅仅是理论的知,而且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一个包括整个人类的经验与存在方式的概念,它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就是存在方式[13]。黑格尔对本质的一种过程性的体验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很为相似。黑格尔的生命意识即苦恼意识,就是生命的全新的存在方式。
伊波利特与科耶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认真翻译与解释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且还比较深入地甚至是专门地研究了马克思的书,并写出了名著《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14]419。总体而言,伊波利特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评价不高,认为黑格尔具有更为根本的生命哲学意义,这样便超越了克尔恺廓尔对黑格尔所谓“不关心个人的生命”的偏执攻击,而把黑格尔“克尔恺廓尔化”[4]26了。伊波利特认为,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一书[15]对黑格尔的全部批判,除了重复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之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他可能没有正视这种分歧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卢卡奇不理解黑格尔为什么使矛盾永存和异化永存,而没有同时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历史与技术条件。相比于马克思试图找到解决矛盾与异化的现实历史条件而言,黑格尔哲学不仅没有表现出它的无能,相反却表现出它的伟大。卢卡奇的分析从历史上证明了“黑格尔的正确”。“黑格尔的体系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他的体系的缺陷则在于没有力量超越他的时代。”[14]445“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在中介的内部保持对立的紧张状态,马克思的真正的辩证法则努力要完全消灭这个紧张状态。……黑格尔与马克思从奇妙的也是可解释的相反角度来看问题的。”[14]469黑格尔曾经一度与马克思一样想要在实际中消灭异化,而在后来鉴于某些历史事件而不得不推翻这种想法,他看到的是一种永远无止境的辩证运动过程,理念在其中熠熠发光,而马克思则预见到了历史的一种终结[14]469。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比马克思还要“马克思”,还要“后现代”。“黑格尔在历史存在的悲剧中发现了理念,而马克思则相反,他在消除这种悲剧的过程中,在实际的和解或实际的合题中发现了黑格尔理念的真正等同物。”[14]470青年马克思过分简单化了黑格尔的法哲学问题——官僚主义其实是无法消除的。总之,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而穷尽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潜能,相反却导致对黑格尔的简单化理解。黑格尔的存在论与自我意识哲学的意义,远不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体及其追求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所能穷尽的!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伊波利特对马克思的理解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严重失实的。众所周知,晚年恩格斯早已经说过,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精神被其封闭的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我们不妨引用前述的马克思学家费彻尔正好相反的观点作反驳。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历史观上:前者是一种抽象观念支配下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是从作为历史发展暂时结果的现实出发的社会批判理论。二者的对立表现在他们各自核心概念的差别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体系,从而是一个必然被瓦解的历史环节;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神秘化的绝对统一体系。前者表现为具有统一性而实际上是对无法克服的现实客观矛盾进行掩盖的虚妄性;后者则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从而是自由的主体的历史生成过程[1]16。
我们认为,从科耶夫到伊波利特的著作中能够发现一个后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现象,这就是首先把整个马克思哲学“青年马克思哲学化”,然后又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加以青年黑格尔化,进而又把青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加以“存在主义化”(或“生命哲学化”)。且不论这种思想解释套路多么违背历史的真实性,因而需要严肃地批判。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思考,那就是法国人接受马克思与黑格尔几乎是同时的,而这个时期恰恰是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西方被发现与重视的时期。
三、阿希洛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主义式解读
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除了有波斯特所形容的“黑格尔的复兴”[4]3-35这个重要因素之外,还有波斯特于同一著作中所说的“马克思的被再发现”[4]36-71这个更直接的因素。就在法国人刚刚开始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即在20世纪三十年代,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公开发表,这也成了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决定性事件。正是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手稿》的创造性误读,才活跃与丰富了战后法国的思想界。按照波斯特的概括,当时法国学界对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三方:第一方是来自天主教的让·耶夫·卡尔维兹,第二方是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第三方是法共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三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通过《手稿》来否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教条。可以说,法国人几乎是在“同时”接受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所以,把青年马克思解读成为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就并不奇怪了。
正像波斯特精彩地描述与总结的那样,二战前后的法国思想界,“所有可以想的到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宣称拥戴马克思的思想,或最起码,向他的观念的力量和丰富性表示敬意。和法国广大读者着迷于存在主义的程度相当,马克思的思想成功得到了整个巴黎的热情赞扬。使共产党理论家懊恼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成一种异化哲学。法国到处充斥着关于异化的讨论”[4]50。所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成为时尚,而把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直接解读为存在主义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方面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很多。诸如:天主教徒皮埃尔·比戈(Pierre Bigo)195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Marxismeethumanisme);吕克·萨姆豪森(Luc Somerhausen)194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行动》(L’humanismeagissantdeKarlMarx);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47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由,论对卡尔·马克思思想的认识》(Marxetlaliberté,pourconnatrelapenséedeKarlMarx)和埃米尔·巴斯(Emile Baas)1947年出版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论文》(L’humanismemarxiste:essaid’analysecritique);马克思学家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于194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片段:一个社会伦理学》(PagesdeKarl.Marx:pouruneéthiquesocialiste);亨利·列斐伏尔194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LeMarxisme);让·拉苦劳瓦(Jean Lacroix)195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Marxisme,existentialisme,personnalisme);经济学家亨利·巴尔托利(Henri Bartoli)1950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学说》(LaDoctrineéconomiqueetsocialdeKarlMarx);天主教会信徒让-伊夫·卡尔韦兹(Jean-Yves Calvez)195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PenséedeKarlMarx);吕贝尔1957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思想评传》(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卢卡奇主义文学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Librairie Gallimard)1959年出版的《辩证法研究》(Recherchesdialectiques);法共代表人物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1961年出版的《人的前景》(Perspectivesdel’homme);特别是来自希腊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考斯塔丝·阿希洛斯(Kostas Axelos)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技术思想家:朝向征服世界的人类异化》(Marx,penseurdelatechnique:deI’aliénationdel’hommeàlaconquêtedumonde)[4]50-51。
似乎有必要专门一提的是,在使法国人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亨利·列斐伏尔。他是马克思《巴黎手稿》最早外文译本即法译本的翻译者与导读者,从而也是法国最早把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加以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正像法国人是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著作导读》讲座而接受与理解了黑格尔一样,法国人也是通过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16-17]*《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辩证的矛盾”,主要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特别是集中阐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第二部分“人的生产”,重点解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部分《人类的产生》已经被译成中文,参见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及其所编辑的《马克思著作导读》(1934)[18](其中就包括法文节译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现与理解马克思的。甚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理解所借助的版本也是列斐伏尔主持翻译的另外一本《黑格尔著作导读》(1938)[19]。
考虑到关于列斐伏尔在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的贡献我已经另有专著详细介绍过*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3页。,也限于篇幅与目前研究能力,本文仅仅简单地介绍一下希腊裔哲学家阿希洛斯(也译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这位法国争鸣学派*争鸣集团(Arguments groups,又译作“论据学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由的独立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圈子,因其刊物《争鸣》而得名的。这个圈子包括哲学家列斐伏尔、考斯塔丝·阿希洛斯、埃德加·摩林,社会学家阿兰·图林纳以及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该学派一方面致力于结合利用其他社会思潮的成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反思与发展;另一方面也试图对战后法国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行研究,包括科技影响、大众媒体与消费问题的研究。代表人物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主义化理解(他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罕为人知,但近年来在英语学术界声誉日隆)。他曾经模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二条而写下了一篇“反读”的论文《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批判》。这可以说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实践本体论“提纲”或“宣言”了。
在其中的第一条,阿希洛斯这样写道:
所有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的)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物质,只是从生产对象、物质现实和劳动资料的形式去理解;它们固然是这样地被有效地把握了,但这些东西缺少根基和视野。这就是为什么另一面由唯心主义哲学以形而上学方式(即与朴素的或精致的实在论相对立的方式)加以发展了。自然地,唯心主义哲学既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称之为实在的世界:它是各种形式、各种力量,以及已经构成的、具体化的和已经固定了的世界的脆弱点的总和;同时,它也是正处于构成中而开放未决的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的另外一面。马克思想使感性对象高于观念对象,但他并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当作成问题的活动(problematic activity)来把握。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哲学的贫困》中,他同样把物质生活看作唯一真实的人类生活,而思想和诗只是在其有条件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才被把握。[20]97-98
在第十一条,他模仿马克思的《提纲》第十一条,这样写道:
技术专家们只是以各种普遍的、但又无差别的方式改造着世界;而问题在于要去思想与解释这种改造世界的高深莫测的方式,去体察与经验那种与虚无联为一体的差异性存在。[20]101
按照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青年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不知道能动地把世界理解为对象化存在物,而让能动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发展了。阿希洛斯则以同样的方式,指责青年马克思只是将世界行为主义地理解为一种对象化而不是意向性或视野性的世界。结果更根基的世界方面,被更精致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加以神秘抽象地发展了。正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是从犹太人的卑污的经纪人交易的庸俗形式理解实践概念一样,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则反过来批评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概念过于狭隘庸俗,而无法理解人类的无限能动的创造性。如果说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原则并不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实践,即人的世界本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同样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过于抽象与本质主义,而无法理解感性的生存世界的根基性意义。所以公平而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想重新争夺被海德格尔哲学所抽象地发现与揭露了的现代世界的“另外一个方面”,并试图对其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对生存的重新发现,其实是对被存在主义所神秘化了的现代生活突出现象的一种历史性批判透视与反思重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化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融合与解释过程,其实是用存在主义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原则,同样又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批判存在主义的自明的非反思的存在本体论。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存在主义视野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把马克思所突出的宏观而客观的社会异化现象显化为一种主观而微观的生活异化,同时又把存在主义所神秘直观到的人类生存虚无与危机的“永恒”命运,历史地解释为一种现代性的颠倒之社会现象。在存在主义看到的神秘直观的精神异化方面,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的主观表现形式。马克思求助于宏观而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与自由的批判理想,被他们改造成为主观而内向的精神解放。在他们那里,诉诸于客观性的社会内在矛盾危机与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不再具有真正的批判基础意义与方法论意义,只有个体主体的非理性的生命生存意义世界,才具有彻底的批判价值与参考意义。客观世界瓦解与虚无了,只剩下主观的生命意义世界的原始性、辩证性、本真性批判的本体论意义。康德的理性是“隐性的上帝”,是“不死的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抽象的上帝与同样“不(会)死的人”。黑格尔把实体,即真实-真理,理解为主体与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则把绝对精神这个抽象的上帝理解为人的“类存在”。马克思则进一步把绝对精神及其世俗化版本的人类理解为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人。从此,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主体人消失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与它同时萌芽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存在主义,都不再把人看作顽强的绝对的理性人,而是现实的有限的存在者。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把现实的个人理解为总体性的个体的生存实践过程。(当然结构主义很快又把主体的人理解为“被结构了”的存在物,理解为非历史的共时性的结构与无意识,理解为非本质非所指的符号,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人是一个近代发明”*参看[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05页。)。
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根基上”而只是从“内部的”某个层面批判现代性,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海德格尔神秘化了的形而上学根基处总体性地揭穿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本质——这种本质不是现代的物质生产实践平面所能发现与理解了的。在他们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结论,不足以理解比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这种现代性基本维度“全面得多”的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完成的本质。而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本义”正是要为作为“形而上学完成与实现”因而“终结”了的现代性文明与哲学寻找一种新的出口与道路。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总体性历史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即基本本体论,不是工业化历史逻辑,而是更深层的诗性实践或生存论实践逻辑。工业化逻辑并不是自明的、无罪的本真状态,而是异化的、次生的历史物化现象,是需要自我解构的辩证法。这种具有真正的颠覆意义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仍然是原则性的,而有待于进一步阐明,需要后代人不断地明晰与激活。这是想象中的现代性的另一方面。这也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世界中所试图发现的新的可能的世界。
[1]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3] 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M].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
[4] POSTER M.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7] 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M].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2.
[8]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M].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1] 平卡德.黑格尔传[M].朱进东,朱天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2] 董特.黑格尔传[M].李成季,邓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74-181.
[14] 张世英.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M].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6] LEFEBVRE H. Le materrialisme dialectique[M]. Paris: Alcan, 1939.
[17] LEFEBVRE 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M]. Translated by John Sturrock.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68.
[18] LEFEBVRE H , GUTERMAN N. Morceaux choisis de Karl Marx[M]. Paris: NRF, 1934.
[19] LEFEBVRE H , GUTERMAN N. G. W. F. Hegel: morceaux choisis[M]. Paris: Gallimard, 1938.
[20] AXELOS K. Introduction to a future way of thought: on Marx and Heidegger[M]. Translated by Kenneth Mills. Lüneburg: Meson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