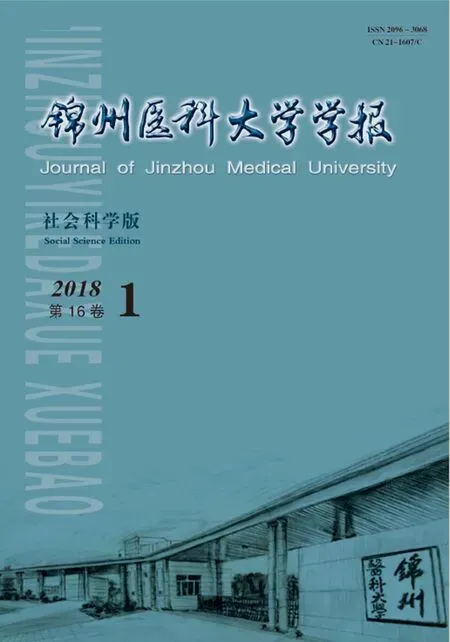理雅各《四书》翻译之得失分析研究
王亚敏
(皖南医学院 外语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儒家学说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而《四书》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儒学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发展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迄今西人翻译的《四书》译本有约18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则是来源于19世纪与20世纪两位传教士理雅各和韦利。本文通过译本细读,拟就理雅各《四书》翻译的特点,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探究,分析其译文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的得与失。
一、理雅各翻译之得
1.凸显学术性的注释。好的译文应该尽可能做出详细的解释,并对研究活动提供便利,然而这也会引发读者的不满——其往往更喜欢具备轻松性和简约性的译本,然而这样的译本却极难被学者所满足。如注释与前言均以长篇形式出现的理雅各译本——其此两种内容的文字总长度和原文相比多出很多,也就是作品已经成为了原作者和译者的“合著”。他所撰写的前言涉及文本介绍、背景解释、正本清源及考证评论。其对《论语》的各时期版本、权威性、作者、最早成书时间、古代学者的论著之类都做出过研究。他甚至发现了在某些问题上中国学者所依据的解释或文本并不可靠[1]。理雅各还大量使用脚注,在脚注中他用简明精炼的语言概括出各章主旨。另外对文中开始出现的一些关键词语,他都给予注释,而对于一词多义,他都是认真研究,保证翻译的准确无误。同时,他依据汉字四声的发音,通过语境选取相对应的词汇,有时还探索词源,旁征博引,力求精确。理雅各还对读者难解之处做出了必要的解释。例如,理雅各译《论语·学而第二章》时,自行增加“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 are the foundation of all virtuous practice”这一小标题,这种增益性的解释总领了孝与仁的关系,突出了主题。
理雅各自己在注释这一问题上也曾经表示,他本人意欲在《中国经典》的翻译活动中公正地对待自身。或许十有八九的读者对他的“评论式注释”过于冗长这一问题嗤之以鼻,但只要有人肯定,他觉得就值。作为“学者型译者”,理雅各愿意在汗牛充栋的儒经解释作品中整理出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2],可以用长篇的注释和前言来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给读者——这也是其作品中最引人入胜的内容,而在他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译者给研究者提供同样多的信息了。
2.贴近古文的句式特点。理雅各在翻译《四书》时采用了大量贴近古文的句式,从而尽可能保证译入译出两种语言结构方面的相通性,甚至不惜字斟句比。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其将“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译为“The wise are free from perplexities,the virtuous from anxiety and the bold from fear.”译文使用对仗句式,与原文结构一一对应,而且译文也属于原句的警句风格。理雅各作品中依据原著直译这一做法,也保证了其翻译作品可以最大程度上贴近原文。[3]
而当代译者翻译中国古经时,往往是先由其他专家学者将古文翻译成今文,再根据今文翻译,这样的译文很难像理雅各的译文那么贴近原文句式。这是因为译者所依据的现代文虽易理解,但结构繁琐,不如古文言简意赅,行文精练,由此产生的译文之语言结构与原文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三章》)鲍时祥译成现代文为:“花言巧语,善于作态的人,很少有品德完美之辈。”老安英译为:“Those who are capable of sweet words and fine appearance are rarely men of true virtue.相比而言,理雅各译为“Fine words and all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老安的译文明显是依据了鲍时祥的今译文,不如理雅各的译文简洁。[4]
3.求其真的异化翻译策略。异化翻译意味着保留译文的异域性,翻译文化研究的文献常用此法。而归化翻译则注重翻译的流利畅达。辜鸿铭常用归化译法,而理雅各多用异化译法,两人的译法各有千秋,但译文的功能则截然不同。比如,理雅各把《论语·乡党》 的“入太庙,每事问”译为:“When he entered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state,he asked about everything.”辜鸿铭采用归化译法,把“太庙”译成“Great Cathedral”(大教堂)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但却未能传递中国佛教的宗教氛围;相比之下,理雅各的译文较好地传递了原文的东方宗教氛围。辜鸿铭在其译文中除了孔子外,基本不用其他中国的人名与地名,而使用《圣经》中常见的人名和地名取而代之。他把“颜回”译为“孔子的福音使徒约孔”;又将中国古代君王分别比作《旧约全书》中的西方古代君王,因此,辜鸿铭的译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但理雅各的译本更精确,更具有学术性。[5]
又比方说,理雅各《大学》翻译为“伟大的学问”的做法曾受到中国研究者辜鸿铭先生的反对,而提出应将之翻译成“高等教育”更为妥当。但是,现在《大学》的通用译法却是援用理雅各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首先了解“大学”的含义。“‘大学’指的是‘博学’和‘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要在十五岁的时候在大学当中进行哲学、政治、伦理之类学科的学习。故而两种含义实际上是彼此解释的。”由此可见,“大学”的意思与理雅各的翻译是相契合的。那么,辜鸿铭的翻译“Higher Education”为什么反而没有流传下来呢?笔者以为“Higher Education”的译法过于西化和现代化,“高等教育”一词在西方的含义与儒经中的“大学”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西方的高等教育有文科、理科之分,因此该词未能精确地译出“大学”的真正含义。[6]
二、理雅各翻译之失
1.行文呆板,可读性弱。关于理雅各的译文,辜鸿铭曾经评价说对于那些对文学和哲学有敏锐洞察力的学者型的研究者来说,会对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里的这些文化内涵有所察觉,透见其真相。但是对于其他普通的国外读者来说,他的这些蕴涵着中国人智慧和道德的文化内涵的译著也许会令人产生怪异的感觉。而理雅各坚持认为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他必须要把忠实的翻译原则放在首位,而这种原则可能就导致了译文的呆板。理雅各追求形似,且鲜有增益,这就必然使得其译文古涩生疏,与孔子亲切自然的文风有着一定的差距。[7]
2.理解有误,翻译有失。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洋洋洒洒数以万言的译本,不出差错几乎不可能。古代中国的经典作品连中国人都未必能看懂,就算是中国的“顶级学者”也未必能够真正敢对疑难之处做出权威性的翻译——将之译为外文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翻译必须经历理解与表述两个阶段。理解为翻译之本,理解错了,译文当然也是错的。理解之后,译者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对原文的理解表述出来,这是译者面临的第二个考验。
理雅各作品中有不少误解误译的情况。如:“礼之用……亦不可行也。”这一段中(《论语·学而第一》) 理雅各把“和”译为“ease”(放松,不紧张的意思),并注释说:“In ceremonies,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但“和”的实际意思是“适当、恰当”,杨伯峻把此句今译为“礼的作用,以事事做得恰当最为可贵。过去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也以礼仪恰当为最好,小事大事都这样做。但其中难以行通之处也为数不少——就是其并未真正保证‘法制化’而仅仅是‘为恰当而求恰当’,这样的做法自然是不行的”。由上下文来看,译成“appropriateness”较为恰当。[8]
“意不在言中”是古经语言当中的一个颇为常见的情况,很多时候语言的深层结构难以被译者所理解,故而其深层意义也难以体现出来,翻译中“貌合神离”者自然不少。不难想象,要一个外国人不仅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字面意思,还要理解其内在的深层意思,难度是很大的。如,理雅各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话以“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的形式体现,这里的“不知”其实指人不解(comprehend)自己的内心(the inner self)。理雅各的译法未译出深层含义,而只停留在原文的表层结构上,因而使得外国读者无法充分理解原文的真谛。[9]
然而,在研读理雅各的《四书》译文与学者的相关研究时,笔者也发现学者提出的意见实际上并非全都合理,有些汉学家对理雅各译本的批判有时是本身水平不够造成的。例如,有学者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四书》翻译进行对比后提出下列看法:认为理雅各在译文语气的处理上不如辜鸿铭来得精确。如,理雅各将“回之为人也……”译为“This was the manner of Hui…”,辜鸿铭译为“Hui was a man who…”;学者认为辜鸿铭的译法要比理雅各的译法语气准。其本来的意思应理解为“颜回这人有某种性格”,本文则以为:两种译文没有太多的语气方面出入,而仅仅是理雅各做出了一个“视点转换”,是合理的语言转换手段。所以这样的例子很难有说服力。[10]
3.语篇缺乏衔接。语篇的衔接手段非常的重要,往往在文章中起着起承转合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令语篇连贯,整体沆瀣一气,而且能够有效地补充一些含蓄的隐含信息。在这一问题上,对比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人的译著,很明显能感觉到,辜鸿铭要优于理雅各,这可能也与其“绝对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有很大的关系。[11]
综上所述,通过对理雅各的《四书》译文得失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理雅各不仅是一名传教士,更是一名东西方的文化传播者和语言解码者。他通过大量的诠释、解义与加注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严谨而详尽的研译,为中国典籍传播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与支撑。然而,人无完人,译本也是如此,不可能完美无缺。他的译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理解不当乃至误译的地方,但是我们评判的目光应该是宽容的,因为理氏的《四书》译本犹如一个大宝藏,正等待着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和深度去挖掘,只有经过不断地研读、研究和修改,才能更加完善,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学术和文化传播价值。
[1]Pfister,Lauren F.Strivingfor“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M].Germany:Frankfurt am Main,2004:47,43.
[2]Pfister,Lauren.“Mediating Word,Sentence,and Scope without Violence:JamesLedge’sUnderstandingof‘ClassicalConfucian’Hermeneutics”inTuChing-I,ed.ClassicsandInterpretations: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M].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371-372.
[3]樊培绪,楚至大.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J].中国科技翻译,1999,(3):50-52.
[4](英)理雅各英译,杨伯峻今译.四书[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6:151,597.
[5]杨晓明主编.五经·现代版[M].四川:巴蜀书社,1999:40.
[6]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编.论语[M].山东:山东友谊书社,1992:27.
[7]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7:85.
[8]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9]杨翠翠.理雅各《大学》英译本中厚重翻译的应用[D].河南:河南大学,2014.
[10]高生文.语域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比较[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11]江晓梅.《中庸》英译研究:基于理雅各、辜鸿铭、休中诚、陈荣捷、安乐哲和郝大维译本的分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