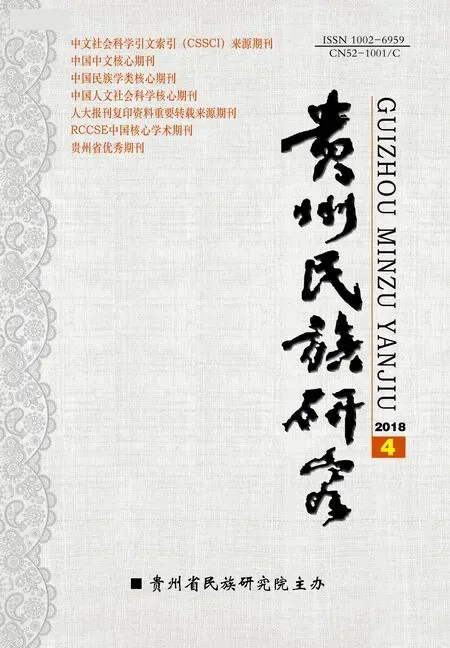大众传媒视域下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变迁
乔志龙 滕 驰
(1.内蒙古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81
2.内蒙古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一、价值观念嬗变
我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思想意识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媒体时代,各种传播媒介迅速地将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人们联系起来,表现出巨大的辐射性和渗透力,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沿动态,大众传媒同时也改变着少数民族的日常消费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发展迅猛,变化日新月异,少数民族在大众传媒影响下不断调适着生活方式,传统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仅满足于有效性、实用性和舒适性,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扩张,购买能力不断增强,日常消费行为中蕴含的审美、时尚、道德、意义等文化因素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在进行消费时,对商品的占有和使用不再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而是在确保其使用价值的前提下,更多地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意义: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购买实力、表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彰显自己的品位和价值。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消费观念更符合消费的符号化意义,这种符号化意义与传统消费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使“消费者通过对商品形象和品牌的崇尚,达到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可,更加关注商品所带来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把消费的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1]大众传媒本身即是一种消费文化,人们在消费时能够自觉地兼顾诚信、节约、环保等道德伦理因素,开始理性思考自己的消费行为与他人的关系及给环境、社会带来的影响,逐渐接受和效仿大众传媒中倡导的消费理念和行为,进而促使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与大众文化格调相一致的消费观念。少数民族消费观念的转变促成了民族地区消费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另一方面颠覆了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类型,使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引导民族地区由重生产、重积累的生产型社会向重消费、重流通的消费型社会转变。
大众传媒激发了少数民族积极进取的信心。大众传媒中展现的现代化生活能够创造出更高的经济利益和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际遇,这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年轻一代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家乡,到更发达的地区寻求生活机会。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主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获取工作机会,在其引导和浸润下,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与不同民族进行交往互动、团结协作,以获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大众传媒中宣扬的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理念强化了少数民族的个体意识,激发了他们积极进取的信心,促使他们迅速融合成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分子,“城镇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和网络效应能够快速有效地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更有助于提升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城镇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载体,能够容纳、接受和创造更加多样化的文化和人生,相应地,人口的进一步集聚为各种文化和各自的人生提供了展示的机遇。”[2]留守在家乡的少数民族也不再完全依靠地缘、血缘、亲缘构成的熟人社会维系生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电视、网络的全面覆盖,电视、广告、网络等大众媒体在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尽可能多地掌握新信息、新技术,希望能够为个人、家庭及子女后代拥有更先进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即便是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也可以充分通过大众传媒消除偏见、开阔眼界,主动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可以说,大众传媒凭借与时俱进的优势,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正逐渐深入到少数民族的内心,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促使他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众传媒使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互动日益增多,当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流碰撞时,首先感觉到的是我族与他族的差异,本民族的优势特色和不足使他们深感自豪或倍感失落,这便促使他们转变价值观念,形成对本族文化的自觉认知与转型,并对他族文化做出真实客观的评价,同时大众传媒的宣传教育功能能够进行有效引导和整合,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平等、公开、透明地帮助各民族分析差异的原因,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确定自己民族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这种文化认同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本民族共有形象归属感的认知和认同;二是在多元文化中保持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分享。”[3]大众传媒通过提供民族文化交流的多种途径来引导和整合各种价值观念,不但引导少数民族对我族文化的自觉认知和转型,形成对本民族归属感的认同,并且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使各民族获得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认知,鼓励民众参与到国家政务中,使其对主流社会和国家的向心力也逐渐增强,身份认同意识更趋于融入到主流社会中,进而对中华民族形成趋于一致的文化认同。
二、风俗习惯转型
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规约,是约束个体行为、维系民族感情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凝聚力。“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4]民族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使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本民族一些特有的传统习俗或消失殆尽或被束之高阁保存下来,与现实生产生活渐行渐远,总体来说向着现代化、大众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型。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变迁首先体现于日常习俗的显著变化上。大众传媒推进了民族交流的不断深入,使得各少数民族在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巨大改变,除了保持本民族传统的饮食习惯和烹调方法外,基本接受了当地汉族居民的饮食习俗,我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具有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服饰,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对现代城市服饰产生认同,民族传统服饰除了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旅游接待中出现外,基本淡出了日常生活,并且民族服饰在图案、材质、风格上也发生了变化,朝着美观时尚、简约大方、富有个性的方向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传播媒介的普及,少数民族的日常休闲时间不断增多,休闲空间有所扩大,休闲内容更加丰富,休闲生活中的知识性和科学性成分日趋明显,人们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多种途径的精神文化活动,甚至进行科普宣传、商业贸易等科技技术和经济洽谈事项,对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日习俗通过相对固定的流程和不断重复的仪式实现了民族内部的相互沟通、理解和认同,展示了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受多种因素制约,传统节日习俗覆盖面狭窄,内部吸纳功能相对较弱,影响力逐渐式微。市场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实现了与大众传媒的深度合谋,内在功能得以充分释放,主动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影响力不断扩大,传统节日习俗的民俗性特征符合大众传媒民众性、通俗性的特点,大众传媒能够展现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习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其提供更广阔的阵地和平台,通过有效引导和快速传播,使以前只在本民族内部小范围举行的特有的节日习俗,实现了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交融和整合创新,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盛会。“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节日进行丰富多彩全方位的报道,既可以采取报纸刊登、电台报道形式,还可以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把民族节日的盛况,直观地告诉观众,引起共鸣,实现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共同参加某一民族节日,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感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5]大众传媒形象直观地将世代居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呈现出来,过滤掉了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使少数民族迅速提高觉悟,满怀热情地尝试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果,体会和吸收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内容,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相一致,达到与国家主体性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精神风貌。
少数民族祭祀习俗产生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沿袭和传承构成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各少数民族许多祭祀习俗已不复存在,现存一些传统祭祀习俗也随着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文化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巨变,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存在态势:祭祀周期正在缩短,仪式程序有所简化,祭祀活动从整体上向商品化、形式化、世俗化、观光化的趋势发展,相应地,祭祀习俗的文化功能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少数民族祭祀习俗的变迁与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的全面渗透和强势兴起不无关系,各种传播媒介以方便快捷、图文并茂的方式将现代科技信息和教育理念传播给大众,动摇了祭祀这一集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于一身的传统习俗存在的社会基础,使其逐渐失却了社会所认可的属性,随着少数民族思想意识的根本转变,大多数人对自然、社会及自身具有了科学性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使得一些原来起着重要作用的“神灵崇拜”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在祭祀习俗上投入的时间和心力大大减少,祭祀传统逐渐淡化,变迁在所难免。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转型还突出表现在社会交往习俗的转变上。在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交往关系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和感情因素起主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人身和地域等的依附关系,大众传媒拓展了少数民族的交往空间,打开了他们认识事物的眼界,使其逐渐接受并内化了传播媒介中展示的现代交往方式,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交往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转变,从重人情关系的封闭式交往向重利益关系的开放式交往转变。在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交往时,少数民族穿着现代时尚服饰、遵循大众通行的交往礼节已是普遍现象,社交手段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社交的内容和目的越来越趋于理性化。除了感情因素外,人们开始考虑交往对象能否为自己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注重交往的成本与效益,谋求交往的长远打算,在处理交往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时也能够采用理智的方式方法加以解决。交往习俗的变迁给个体的人的发展带来了显著变化。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营造遵循的平等竞争氛围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冲破了以往“人情关系”的观念,给每一个人提供了自由和平等竞争的环境,有力地激发了人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进而孕育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使人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普遍而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日趋丰富和全面。
三、审美意识流变
审美意识是各民族在长期审美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审美个性,包括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是居于民族审美模式核心部位的内在性格,具体体现在音乐、舞蹈、服饰、饮食、建筑、雕塑、文字、绘画、风俗仪式等民族审美实践活动中。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载体之一,审美意识确定着本民族特有的审美价值取向。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都是与传播媒介密不可分的,审美的发展与传播必须借助于媒介,尽管审美的变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媒介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口耳相传到甲骨、竹片、纸帛等器物传承,再到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媒介的变化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说,现代信息技术时代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审美意识从单向流动转为互动交流,由陶冶情操转向载道教化,由精英审美转向世俗情怀。
少数民族传统审美实践是一种相对单向、稳定的模式,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中的经典作品,这种单向、稳定的审美模式都存在着许多不自由。大众传媒时代,审美的创作和接受走向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世界,审美创作者可以摆脱等级、身份、职业、年龄乃至性别的差异,更加自由和随意地进行审美创作,受众也不再单纯地受制于传统审美形式,可以依靠丰富的媒介资源自由拓展,获得充分的审美选择权。大众传媒介入民族审美以后,新的审美样式层出不穷,在媒介提供的互动空间里,传统单向、稳定的审美模式被打破,审美朝着多元化、立体化方向发展,审美的创作、鉴赏、批评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关系。因为有了一个可以互动交流的理想平台,使得参与者能够在不同的角色转化中体味审美带来的自由境界,达到一种更为自我、更为本真的审美状态。
尽管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审美意识并不相同,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表现为豪放雄健的阳刚美,而南方农业民族则体现为温顺坚韧的阴柔美,但总体来说,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审美意识形成于对善和恶的审美判断基础上,突出特征是以自然为美、以善良为美、以智慧为美,其审美意识的最高价值判断是人格精神。这种审美意识绝少带有伦理教化的特点,也并不依从于统治者或官方的意愿,而是基于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生发形成沿袭至今。[6]经济建设促进了民族社会的更新发展,改革开放拓宽了少数民族的审美视野,大众传媒使信息文化跨越时空局限,打破了各民族传统审美模式,为审美活动提供了普及性和可流行性的需要,审美阈限和创造方式发生了空前的位移,不但促使少数民族审美模式的外在样式和表层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迁,逐渐形成与大众审美趋于一致的态势,位于深层结构和内在意义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流变。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传统文艺作品在审美对象上侧重于对民族自然风俗的描摹与赞美、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讴歌赞扬,大众传媒视域下的审美对象透过自然风俗的表层转而关注本民族在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对社会变革取得的成果的歌颂以及少数民族个体或群体的困惑和抉择。
少数民族传统审美意识集中体现于音乐、舞蹈、文学、雕塑等经典性的审美活动与实践中,随着市场经济和传媒时代的发展,以高雅艺术形态呈现出来的精英审美逐渐被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或准审美的活动所取代。审美场所从高雅的艺术馆或舞台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审美活动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装、广告、流行歌曲等都可以承载美、表现美,审美的世俗化和世俗的审美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们越来越注重内心精神世界的体验,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调个性的体验和感受。大众传媒将人们的目光投向娱乐性、消遣性的审美活动,高雅严肃的审美活动逐渐让位于平凡的世俗情怀,审美倾向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迁。开放性、自由化充满世俗情怀的审美更受大众欢迎,而受众的青睐反过来又促使越来越多关注现实、注重当下的审美活动的产生和兴盛。从审美创作的角度,审美的世俗化倾向改变了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对“美”的固有认识和界定,创作者们经过选择、调适到投其所好,使原本相对纯粹的审美活动与文化消费融为一体,物质与精神、享乐与艺术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的精英审美在媒介的影响下不得不让位于文化消费。新的时代、新的传播媒介、必然形成新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意识,随着民族社会的变迁,少数民族审美视觉不断拓宽,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逐渐形成。
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的文化阻力较之经济因素显得更为复杂和艰难,尤其是少数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变革相对缓慢滞后,而变革又必将牵动或改变少数民族长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一旦改变其固有的价值观念或思维习惯,很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大众传媒自产生以来,就呈现出迅速壮大的态势,各种传播媒介凭借其强势的表现形态、独特的话语结构、商业化的经营理念和工业化的运作模式,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最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在于消除了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的壁垒,使族际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但同时也极易使人的思想观念受到所传递的信息的控制和影响;大众传媒构建起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空间和发展方向,缩小了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了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融合,但也在逐渐消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大众传媒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但现代媒介聚焦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过多地被强调其华丽的外在表现或新奇内容,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独特的伦理道德和文化意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逐渐被颠覆,价值取向、传统习惯和心理情感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被简化或异化,很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文化迷失。针对此情形,大众传媒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真实反映少数民族在面对社会变革和外来文化时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抉择,对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播不应只是非黑即白式地简单呈现,而应深入挖掘其中复杂、深刻的底蕴和内核,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少数民族宣传变革的必要性,展现变革带来的伟大成果,对少数民族在变革中出现的迟缓滞后状态引起高度重视,使之尽快适应并自愿接受社会变革,如此才能引发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深入认识,发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才能够真正实现大众传媒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1]王埃亮.消费向度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转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5).
[2]滕驰.内蒙古牧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转移与对策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3]刘艳萍.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J].人民论坛,2015,(11).
[4]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5]王埃亮.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嬗变[J].贵州民族研究,2016,(3).
[6]邓佑玲.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模式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