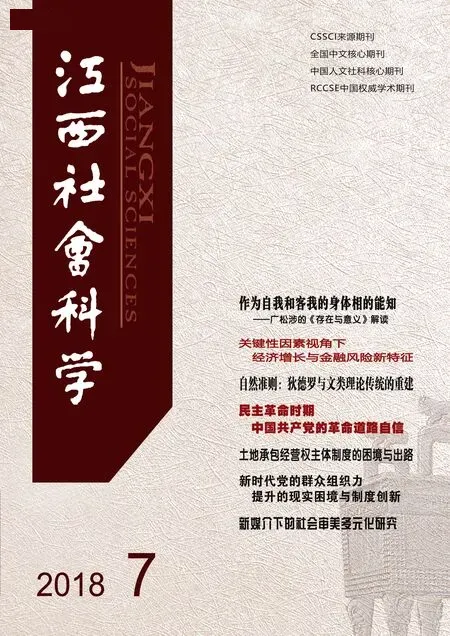南宋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
■程海伦
随着宋金、宋元之间战事的发展,游边逐渐成为一时风气。江湖文人①不惮险远,纷纷前往江淮、荆湖、四川地区,并汇聚于升、扬、润、鄂等边地要郡。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即在这种地域文化与时代背景下展开,是江湖文人在游边的历程中创作的与边地相关的文学作品。本文将在全面考察南宋中后期江湖文人游边经历的基础上,分别从时间指向(回望六朝)和空间指向(北望中原)两方面具体论述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以期更全面地认识江湖文人的生活状态与文学写作,并进一步探讨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在唐宋边地文学发展中的位置。
一、江湖文人游边行实考述
南宋时期,边塞地区主要指两淮、荆襄、四川三边。这其中又有极边与次边之分,据《宋会要》记载,楚州、盱眙军、滁州、濠州、安丰军、光州、随州、郢州、光化军、均州、信阳军、金州、洋州、凤州、西和州、成州、阶州等沿边州军属于极边,其余沿江诸州军则为次边。[1](P4436)总体来看,江湖文人游边的地域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区与荆襄地区,尤以江淮地区为多,而至四川者则较少。江湖文人游边一般是进入位于边地的幕府。据笔者统计,约有18位江湖文人曾任职或行谒于宣抚司、制置司、安抚司等具有军事性质的边幕。除此之外,以其他原因赴边地的江湖文人亦有30位之多。按游边时间的不同,南宋中后期江湖文人游边情况可分为前后两期。
第一,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至宁宗开禧北伐(1206)之前。这段时期是江湖文人游边的准备期,人数不多,代表人物有刘过、姜夔、周文璞等。此期游边风气尚未盛行主要是由于隆兴和议签订之后,边地多为太平场景,留给江湖文人一展抱负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此期疆场比较平静,故而江湖文人能远行至极边州军。如刘过曾漫游京湖、两淮诸地,足迹遍及盱眙、襄阳等边城。
第二,宁宗开禧北伐(1206)至宋亡(1279)。宁宗开禧北伐之后,宋金战事再度开启,边地压力陡增。嘉定和议后,金朝为补偿对抗蒙古的损失频频南侵,淮襄地区战事不断。而随着南宋端平入洛的失败,金朝虽亡,与蒙古的战事亦拉开序幕。此期疆场多事,为江湖文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刘克庄在《跋杨公节论语讲义》中写道:“当赤白囊交驰、戎马满郊之际,盖辨士说客、奇才剑侠奋发功名之秋。”[2](P450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湖文人游边的风气逐渐兴盛。此期江湖文人游边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几大战区,除了四川因为比较偏远较少为江湖文人所涉足外,京湖与江淮地区成为主要的目的地。由于战事紧张,襄阳、盱眙等极边之地已少见江湖文人的行迹,沿江的次边之地则多见江湖文人驻足。这一时期,送人游边诗也在江湖文人的笔下大量出现,如周弼的《送人游边》《送人之汉上》《送人之京口》《送人之荆门》诸作即是其例。在这些诗中,不见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而是弥漫着乱世的悲音。征途的遥远、边地的残破,都为游边文人的前途蒙上一层阴影。这种悲凉的情调,显示着国事蜩螗之下士人们渴望为国立功却常感前路渺茫的心理。
江湖文人游边的目的,固然有谋求生计的考虑,而实现“谈兵”②理想更是促使其身临边塞险地的精神动力。南宋中后期埋首场屋、困于选调的文官生涯对于士人逐渐丧失吸引力,不少江湖文人选择投笔从戎的游边生活。如游边文人的早期代表刘过在《盱眙行》一诗中比较了“起草黄金闺”“侍宴白玉墀”“生死困毛锥”这几种人生道路之后,指出“何不夜投将军飞,劝上征伐鞭四夷”。[3](P2)在其之后,理宗朝的盛世忠有《胡苇航寄古剑》诗:
有人尺锦长安来,远寄宝匣手自开。红云紫气灿虚室,铗中青蛇鳞生苔。诚携掌握一挥动,瞬息天地兴风雷。少年志气老益壮,惟愿圣诏下九垓。廐中我有汗血马,与汝直北清氛埃。丈夫当为国雪耻,笑指经生真不才。[4](第59册,P36827)
诗题中的胡苇航即胡仲弓,也是本文所讨论的游边文人中的一员。在此诗中,盛世忠敏锐地捕捉到“古剑”一物所蕴含的深意,并指出丈夫应该为国雪耻,肃清边患,而非如经生般皓首场屋。由上举二诗可以看出,许多江湖文人对于科举颇有微词,甚至放弃士大夫传统的仕进荣身之路。这种人生道路的转向,出于南宋选官制度的制约,也受到时局的影响。学界关于南宋中后期士人中举之不易、仕途之缓滞已多有研究,本文不拟赘述。对于不少仍具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江湖文人来说,游边成为一种更为可行的政治参与方式。宋代文臣将兵本是祖宗家法,文武兼备的普通士人也不在少数。在南宋国势倾危的时局下,“谈兵”更成为许多江湖文人的政治理想。而南宋日益紧迫的边事在使游边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同时,也为其赋予一种豪壮的色彩,这恰与江湖文人本身具有的“侠气”相吻合,因此对江湖文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边地经历到底为江湖文人实现谈兵的理想创造了多少可能?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实际问题。对于进入边地军幕的江湖文人来说,参与军事谋议,甚至亲临战阵都是很有可能的。如刘克庄嘉定十二年(1219)在江淮制置使李珏幕时曾“与同幕王中甫辈至龙湾点视舟帅,虏旗帜隔江,明灭可数”[2](P5203)。又如方岳端平二年(1235)在赵葵幕为淮东安抚司干官时平定高邮军乱,被赵葵誉为“儒者知兵,吾巨山也”[5](P673)。而对于未进入幕府担任正式官职的江湖文人来说,多数只能如戴复古“军前献筹策,第一守光山”[6](P63)那样针对战事献上自己的建言。总的来看,江湖文人参与军事决策与行动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在军幕之中,江湖文人往往无法处理文与武之间的平衡。方岳在《次韵范侍郎寄赵校正》中云“朱轓挟武将,白眼轻儒生”[5](P477),刘克庄在《祭余子寿尚书文》中回忆李珏幕的经历时亦云:“早客阃幕,方议进取。嗟我与公,扣阖四五。流涕诸侯,根立势举。众指而笑,两生不武。”[2](P5491)都指出文士身份的尴尬。除此之外,弥漫朝堂内外的萎靡士风更是造成江湖文人壮志难酬的深层原因。如黄大寿的《公安》即是一首典型的“谈兵”之作。黄大寿曾游历荆湖地区,因此对于边地的地理形势有切实的感受。在此诗中,黄大寿强调了公安一带的战略地位,指出朝廷应该“善卫保其吭”“更能用吾长”,以对抗外敌。然而全诗以“休兵不敢论,凄咽含余情”[4](第57册,P36092)作结,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的景象一笔画出,而诗人的壮志难酬,也成为意料之中却又无可奈何之事。这种失落心态在江湖文人的笔下并不罕见,由于政治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的极大反差,江湖文人游边的结果往往是不遇而归,这也为其游边文学染上一层黯淡的底色。
二、江湖文人游边文学中的历史反思
江湖文人在游边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咏史怀古题材的作品。以建康幕府为例,此地文风之盛即与登览怀古活动的举行分不开。刘克庄曾惋惜地说:“顷游江淮幕府,年壮气盛,建业又有六朝陈迹,诗料满目,而余方为书檄所困,留一年阅十月,得诗仅有二十余首。”[2](P4180)所谓“诗料满目”,正是指建康地区的历史遗迹,为文人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金陵幕士多作咏史怀古诗,这些作品除了对于历史兴亡的感叹,更多地体现了江湖文人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极的《金陵百咏》。《金陵百咏》的题写对象是建康附近地区的历史遗迹,其主旨并非泛泛地抒发黍离麦秀之悲,而是在“距南渡尚未远”的时代表达一种“仆悲马怀之叹”,即对于国事的关切与感怀。试举数首为例进行说明:
冰玉摩尼如鹄卵,大千世界倒悬中。何人提向江头照,照见神州一半空。[4](第50册《水精大珠》,P31516)
青山四合绕天津,风景依然似洛滨。江左于今成乐土,新亭垂泪亦无人。[4](第50册《新亭》,P31506)第一首题咏水精大珠,为本朝事。据《方舆胜览》记载,水精大珠为“真庙所赐,照物皆倒,又物影沉在下,上段无影”[7](P257)。曾极借前朝所赐之水精大珠写出南宋朝廷只剩半壁江山的现实,语含微讽。第二首所咏之新亭是南宋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的事典,本意是东晋时王导认为周侯诸人只知楚囚对泣,而无恢复之志。南宋诗人在使用这个典故往往又更进一层,意图说明南渡君臣不但比不上王导,连周侯那样的对泣之人都没有了。曾极此诗化用陆游之意,更进一步指出“江左于今成乐土”的苟安之状,表达了对于朝政的不满。四库馆臣认为曾极的《金陵百咏》“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画江自守,无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颇为深远”[8](P1381),正点出这组怀古诗的主旨。
在前代历史中,由于六朝与南宋偏安一隅的处境极为相似,因此南宋出现大量研究六朝历史的地理类、史评类著作,如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李舜臣的《江东十鉴》、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等。这些著作大都是“专为南宋立言者”[9](卷八八,P753),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在这种时代风潮的影响下,江湖文人对于六朝历史也给予较多的关注,方岳即著有《重修南北史》一书,惜已不存。而在江湖文人的诗词创作中,更鲜明地体现了“十年怀古恨,多在六朝中”[4](第63册释斯植《金陵道中》,P39313)的特点。借古讽今,通过吟咏六朝旧事,表达对于国事的见解,是其中常见的主旨。试以陈造与方岳感慨佛狸旧事的两首诗为例进行具体说明。南宋诗人登临瓜步,常常会忆及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之事。陈造的《魏帝庙》[4](第45册,P27978)即从拓跋焘陈兵瓜步写起,指出祭祀魏帝乃“事雠”之行,并不会得到庇佑,由此发出“云何此山椒,遗像俨高殿”的诘问。陈造认为,与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拓跋焘相比,南宋抗金的义士赵立、薛庆、魏胜更应该被立庙纪念,这不但能够使“顽懦”之人振奋,亦可避免“后嗣忘敌怨”的悲剧重演。陈造此诗写于开禧北伐之前,其用意当是借批判为拓跋焘立庙之事,提醒南宋朝廷不可安于对金之和议而忘记恢复旧日河山。方岳的《登瓜步山》亦是借拓跋焘之事发出感叹:当年拓跋焘并未渡江,如今蒙元却不会满足于此,而瓜步正是其入侵江南的第一站。因此南宋朝廷应该吸取前朝的教训,不可仅仅倚恃长江之险,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5](P358)这两首诗皆以议论为主,然词旨含蓄、感慨深沉,无生涩枯槁之弊。方岳在《深雪偶谈》中评论晚唐与宋人怀古诗时认为:“本朝诸公喜为论议,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隽永有味,然后为胜。”[10](第9册,P8886)可知其趋向所在。
江湖文人的咏史怀古诸作是在游边的实际经历中所写,因此也将边地的见闻融入这些诗作,增添浓重的乱世情调,怀古实为伤今。如吴惟信的《凤凰台怀古》云:“凭高北望旧神州,江绕秦淮万古流。塞草寒沙埋战血,更无林叶共伤秋。”[4](第59册,P37083)唐宋诗人咏怀凤凰台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而吴惟信的这首绝句却显得十分独特。此诗写登凤凰台北望,只见边塞战场的秋景一派凄凉萧飒。题为“怀古”,却只用“江绕秦淮万古流”一句轻点怀古之意,全篇用意实在感怀现实,对牺牲在边地的战士深致哀悼。又如陈允平的《多景楼》:
怀古心情独倚楼,荻花枫叶满江秋。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流。铁瓮百年春雨梦,铜驼万里夕阳愁。西风历历吹征雁,又带边声过石头。[4](第67册,P42010)
此诗吟咏登临多景楼所见之景,颈联的“铁瓮”指的是三国时孙权所建的坚城,然而亦逃脱不了铜驼荆棘的命运,仿佛春雨一梦,尽化乌有。尾联的“边声”将怀古的思绪拉回现实世界,提醒着诗人此地现已接近战场,国事日非,前朝覆亡的悲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重演。可以看出,这些咏史怀古诗并非套路化的感慨兴亡之作,而是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隐现出对于时局的焦虑与不安之感,充满伤悼的气氛。而这种伤悼的气氛在南宋后期江湖文人的作品中表现得愈发强烈。柴望是一位由宋入元的江湖文人,其《石头城和王宁翁韵》诗云:
怀乡吊古易伤心,绝顶危亭共客临。朝市曾经兵火后,山川转觉树云深。百年歌舞空台沼,六代豪华漫陆沉。惟有乱鸦归去晚,夕阳无限暮城阴。[4](第64册,P39908)
此诗吊古伤今,情调悲凉,置于晚唐人集中,几不能辨。可见在南宋后期江湖文人的咏史怀古诗中,抒情一体似乎又占了上风,反思的意识逐渐被浓烈的感伤情绪所淹没。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末世情调于此重演,昭示着王朝落幕时刻的到来。
三、江湖文人的北望情怀及其文学书写
北望,是江湖文人游边文学中重要的空间指向,北望的对象则是南宋丢失的领土——中原地区。北望情怀从南渡伊始即在宋人的作品出现,如陆游即有以北望为题之诗③。由于江湖文人游边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江淮与荆襄地区,而又以游淮为普遍,因此其北望的对象即以中原地区为主。游边的经历为江湖文人提供了接近边境线的机会,使其对于中原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正如朱继芳的《淮客》诗所云:“长淮万里秋风客,独上高楼望秋色。说与南人未必听,神州只在阑干北。”[4](第62册,P39075)如此近距离面对神州故土的体验是长期居住在南方的士人无法拥有的。地理距离的缩短带给江湖文人的是心理上的极大冲击,戴复古的名作《频酌淮河水》即描述了这种情感体验: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6](P24)
行至濠州,中原已不仅是在望中,而是只有一水之隔。酌取淮河之水,中原之气也似乎可触可感。淮水中的“英雄泪”,既是北地英雄的无尽憾恨,也蕴含着作者对于苟安时局的悲愤。“频酌淮河水”对于南宋文士来说是罕有的机会,戴复古游边的特殊经历,使其获得超越时人的沉痛感悟。
由游边经历出发,北望情怀在江湖文人笔下得到集中和深刻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局日渐倾危,江湖文人北望情怀中的感情取向也在发生转变。刘仙伦的《题张仲隆快目楼壁》是江湖文人表达北望情怀的早期作品:
天上张公百尺楼,眼高四海气横秋。只愁笑语惊阊阖,不管栏干犯斗牛。远水拍天迷钓艇,西风万里入貂裘。面前不着淮山碍,望到中原天尽头。[11](卷六,P24)
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一(1184)、十二年间,宋金之间处于隆兴和议签订之后的休兵阶段。刘仙伦在同期所作的诗中写道:“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12](卷六,P24)可见其对于南宋未来的判断还是颇为乐观的,因此借着题写快目楼之机,表达恢复旧疆之愿,全诗情怀振奋、豪气健举。不过这种乐观进取的心态在江湖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当收复故土的希望在南宋中后期的政治局势下变得日渐渺茫之时,北望的行为与内在动机之间便产生矛盾,江湖文人由渴望极目中原而逐渐产生不忍望、不敢望的情绪。如刘克庄《冶城》诗云“神州只在阑干北,度度来时怕上楼”[2](P49),张蕴《维扬即事》诗云“愁来莫上城头望,西北浮云接太阳”[4](第63册,P39380),方岳《水调歌头·九日多景楼用吴侍郎韵》词云“莫倚阑干北,天际是神州”[5](P604)等,都以相似的语气表达了矛盾的心态,可见这种情绪在江湖文人间极具普遍性。在这些作品中,又以戴复古的两首绝句最为出色: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6](《江阴浮远堂》,P240)
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6](《盱眙北望》,P241)
这两首绝句都作于戴复古游淮期间,诗意的表达十分曲折。尤其是第一首诗,首二句写出浮远堂所处的地势,起调甚壮,然而这登高极目之地带给人的却是“万里愁”。为了避开万里之愁,诗人不但不忍北望,更希望有山能遮挡住远望的视线。至此为止,诗人皆未明言忧愁的起因,直到末句,作为回答:只因淮南之北尽是神州故土。此诗将沉痛之感以宛曲之笔写出,较之刘克庄、张蕴等人的作品更为耐人寻味。从刘仙伦的“面前不着淮山碍,望到中原天尽头”到戴复古的“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可以看出江湖文人北望诗词中表达的情绪从欲图恢复的豪情壮志逐渐转向恢复无望的痛苦哀伤,北望的姿态虽一,但其中包含的情感内蕴却是极为复杂的。
表达北望情怀的作品多出现在登览之作中。江湖文人的边地登览有一些特定的地点,在江湖文人的游边诗词中,仅以“多景楼”为题的就有赵汝鐩、高翥、吴惟信、陈允平、张蕴、王琮、柴望、刘过等人所作十多首,数量十分可观④。多景楼位于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乾道年间有题记云:“登者以为尽得江山之胜,盖东瞰海门,西望浮玉,江流萦带,海潮腾迅,而惟扬城堞浮图陈于几席之外,断山零落出没于烟云杳霭之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12](卷十二《宫室》,P278)多景楼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登者可以将神州故土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地理空间的相近与政治空间的阻隔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昭示着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所谓“使人慨然有恢复意”,正是由此而生。在南宋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多景楼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逐渐成为江湖文人抒发“北望”情怀的最佳地点。如刘过的《题润州多景楼》:
金山焦山相对起,挹尽东流大江水。一楼坐断水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渐脱人间秋。烟尘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见双泪流。君不见,王勃才名今盖世,当时未遇庸人尔。琴书落魄豫章城,滕王阁中悲帝子。又不见,李白才思真天然,时人未省为谪仙。一朝放浪金陵去,凤凰台上望长安。我今四海行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下无人独登览。楼高思远愁绪多,楼乎楼乎奈汝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3](P6)
此诗作于开禧元年(1205)⑤,首四句描写多景楼的形胜之势,点出其地“收拾淮南数千里”,为下文北望中原做了铺垫。“西风”句以下记叙游踪,“烟尘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见双泪流”二句抒发由北望旧都而产生的中原阻隔、恢复无望的悲愤,情绪的表达十分强烈。接下来诗人引王勃、李白作比,感叹自己也遭逢不偶,四海浪游,如何能与前人一般名垂千古。最后以“楼高思远愁绪多”统摄全篇,沉郁悲凉。从此诗也可以看出,与滕王阁和凤凰台这类古迹不同,多景楼的意义是在南宋时才被发现的,而经典作品的产生亦从此时开始,刘过此诗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值得注意的是,多景楼的修成在北宋时期,本身并不具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但多景楼所在的镇江地区却具有丰富的历史内蕴,祖逖击楫中流、刘裕北伐中原等六朝旧事均可引起江湖文人的兴感,这就极大增添了多景楼的文化意义。如张蕴的《多景楼》诗:
假日此登临,凄凉北望心。戍烽孤障杳,塔影一江深。黠虏投鞭想,将军誓檝吟。所嗟人事异,天险古犹今。[3](第63册,P39380)
此诗首联点明“北望”之情,“凄凉”二字则为全诗定下情感基调。颔联叙登临所见,“戍烽”“孤障”,绘出边塞实景,表明此地靠近前线。颈联转入对于苻坚、祖逖故事的叙写,尾联承接此意,抒发英雄难觅的嗟叹。江湖文人游边文学中回望六朝的时间指向与北望中原的空间指向于此交汇,而多景楼的特殊意义也得到完全地展现:历史与现实的感怀超越欣赏风景的需要正如柴望《多景楼》诗所云:“昔日最多风景处,今人偏动黍离愁”,这种黍离之愁即由于“关河北望”而产生。[3](第64册,P39908)
四、结 语
在宋代的边地文学中,学界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北宋的使辽诗及南宋的使金诗⑥,有关两宋使北诗的写作特色及其相较于唐代边塞诗的变化,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然而,对于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学界尚较少论及。与唐代、北宋及同时期官僚士大夫的边地书写相比,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在作者身份、题材表现、情感取向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江湖文人在身份上属于中下层士人,与同时期官僚士大夫的使北之作相比,其游边文学常常将家国之思与身世之感相结合,对国事既有理性的思考,也包含着不平与悲愤的强烈情绪,反映出这一社会群体感时忧世却又报国无门的复杂心态。
其二,江湖士人能够亲至边地,尤其在宋末战事频仍的背景下,正常的交聘已成历史,江湖文人的边地经历无疑更为难得。这使其边地书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在表现的广度与思考的深度上,都具有边塞诗所无法比拟的价值。
其三,江湖文人的边地写作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随着南宋中后期政治局势的发展,江湖士人恢复中原的壮志逐渐被对国家前途的无力感所取代,其游边文学中的情感色彩近于晚唐边塞诗的萧瑟悲凉,而忧患意识与危机感更为强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总体来看,江湖文人的游边活动涉及的地理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创造了数量众多的诗词作品。其游边文学在继承前代写作经验的基础上亦形成自己的特色,对我们全面认识宋代的边地文学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江湖文人包括江湖诗人与江湖词人,分别采用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和郭峰《南宋江湖词派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一章第二节“江湖词派的界定”中的界定。本文之所以将江湖诗人与江湖词人统名之为江湖文人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将其视作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而非文学流派。江湖文人群体具有阶层与文化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身份并非显达,二是擅长文学写作。
②江湖文人作品中常出现“谈兵”一语,如“幕下相从若弟兄,当年曾悔误谈兵”(《刘克庄集笺校》卷四,第257页),“本无谋略强谈兵,每愧临边病未能”(周弼《秋日马上》,《全宋诗》第37770页)等。
③参看黄奕珍《论陆游南郑诗作中的空间书写》(《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④据李德辉《多景楼与两宋文学》(《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统计,《全宋诗》和《全宋词》中所收题咏多景楼之作约四十三人、五十五首。
⑤岳珂《桯史》卷二:“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饶幕庾吏,因识焉……独录改之《多景楼》一篇曰(略)。”
⑥如王水照《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张高评《南宋使金诗与边塞诗之转折》(《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诸葛忆兵《论北宋使辽诗》(《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曾维刚《南宋中兴时期士风新变与使北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