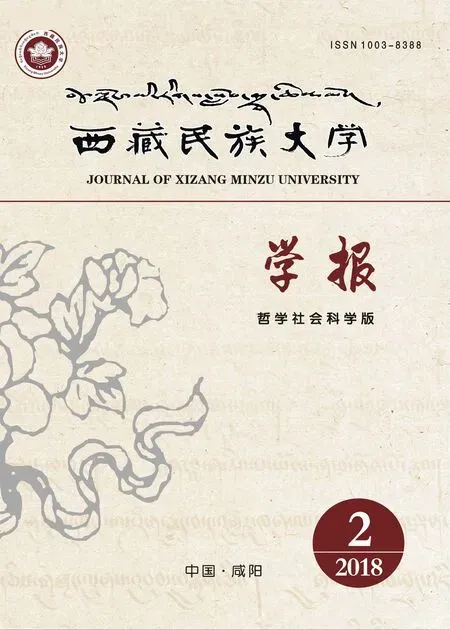唐朝、吐蕃、南诏西南战事与长安战略防御
——以代宗、德宗朝为中心
胡岩涛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唐代吐蕃是唐朝之劲敌,在安史之乱前,唐朝对吐蕃保持高压势态,令其无法实现觊觎中原之心,然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急剧转衰,吐蕃趁机对唐朝大举进攻,唐军连败,导致疆域缩减,州县罢废。吐蕃于历朝对外扩张过程中,模仿李唐天下秩序,逐步建构“以吐蕃赞普系天子下凡,入主人间”的概念为中心的吐蕃型天下秩序,用以对抗李唐竞逐与国。[1]唐朝虽饱受内战创伤,但面对强敌西来之际,君臣将士亦能奋起反击,持续抵抗,亦表明唐朝政治制度及组织在当时周边诸政权中的先进性。张达志先生指出,东亚世界东端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和稳定是唐朝全力应对吐蕃军事压力的基本前提。[2]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蜀川设剑南道,管辖今四川中部与云南北端,目的是“南抚蛮獠,西抗吐蕃”[3](P1503)。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所以又有南宁、戎州、姚州三都督府对地方部族政权实行羁縻统治。自唐高宗时起,吐蕃与唐朝关系恶化,双方在西北互相攻伐。而后吐蕃又向西南进犯,公然挑战唐朝在西南地区建立的政治秩序。为阻止吐蕃在西南地区扩张,唐廷在开元年间全力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实现了笼络南诏对抗吐蕃的战略构想。但南诏强盛之后,又引起唐朝的戒备,最终双方爆发战争,致使南诏倒向吐蕃。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入蜀川,南诏也趁机扩张,唐朝西南局势骤然紧张。代宗、德宗朝时唐朝、吐蕃、南诏西南战事错综复杂,与当时唐蕃战争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为此有必要结合史料进行进一步探讨,并考察唐朝西南战场对长安防御中发挥的作用及蜀川之地位。
一、吐蕃攻入蜀川与唐军被动防御
吐蕃与唐朝相接壤的地区有安西、河西、陇右、剑南等地。安史之乱前,唐朝“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4](P6895),强大的军事布防使吐蕃无法挑战唐朝在西域建立的政治秩序,亦不能突破河西直接进攻关陇腹地。在西南地区,唐朝长期奉行结南诏而抗吐蕃的政策,剑南节度所在蜀川是唐之西南对抗吐蕃的大本营,令吐蕃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安史之乱前,唐朝对抗吐蕃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河陇和蜀川,两地如同一把扳手,牢牢地将吐蕃锁困在青藏高原。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直扑长安。唐廷“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5](P5236)。原河陇地区防御吐蕃的精锐部队纷纷内调,前往平叛,导致唐朝在河陇地区的军事部署被打乱。叛军攻下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经安史战乱,唐朝由盛急剧转衰,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势力过大,唐肃宗深知这对于国家的危害性,所以当唐玄宗返回长安后,唐廷立即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两川,西川治所依旧为成都府,管辖除了东川以外原剑南道属州,东川治所在于绵州。[6]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7](P44)。十月,吐蕃进攻泾州,直过邠州,又指向奉天、武功,京师震骇。随着吐蕃对唐朝西北地区蚕食的完成,也开始大举进攻蜀川。广德元年底(763),史载“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7](P47)。
杜甫曾指出,“吐蕃今下松维等州,成都已不安矣”[8](P2193)。吐蕃应早有预谋,趁唐朝大乱方平,攻占河陇后又在关陇地区、西南地区两线同时出兵。安史之乱未殃及蜀川,时任剑南节度使高适没能阻止吐蕃进攻西山地区,纵然有军事指挥之失误,实质上背后还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剑南道分治导致蜀川唐军御敌能力下降。安史之乱刚平定,唐肃宗派人迎接唐玄宗回京时,玄宗却流露出“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9](P3641)的割据意图。唐肃宗是在灵武被追随的朝臣私自拥立为帝,事后才昭告天下,令唐玄宗心中别有滋味。玄宗晚年倦政导致边地节度使久任,藩镇做大,但是他对剑南道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松弛,这让肃宗对玄宗在剑南的势力有所忌惮。[6]剑南道分成东、西两川,势必削弱整体实力,而且无形中为军事行动的协调造成很大阻力,导致御敌能力下降;其二,蜀川因防范南诏被迫分散兵力。南诏强盛之后,“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5](P5281),令唐廷不满,故采取阻止南诏统一滇池的政策,南诏也意识到唐朝的戒备,暗中备战。皮逻阁逝世后,其子阁罗凤即位,唐朝曾企图用阁罗凤的异母弟来取代阁罗凤为云南王,并加倍征取税赋,迫使南诏服从唐朝利益。南诏对唐朝的步步紧逼以及唐朝边疆官员横行不法的行为极为不满,双方矛盾发展到了尖锐地步。[10](P134-135)吐蕃趁机拉拢南诏,南诏也积极投桃报李,北臣吐蕃。天宝战争使南诏最终实行倒向吐蕃而敌视唐朝的政策。吐蕃进攻河、陇之时,“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11](P269)。唐廷不得不派大量军队进行防范,势必分散了蜀川的兵力。
随着吐蕃在蜀川的不断攻扰,唐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河陇的丢失使得吐蕃对长安形成战略攻势,若成都被攻占,则意味着蜀川沦陷,长安战略防御相当于两臂全被斩断。若是吐蕃攫取蜀川的战略意图实现,必然会在土地肥饶,人口富庶的成都平原获得巨额战略资源补充,然后配合它的西北军以钳形攻势再次寇入长安,或是沿江而下,其后果将不再是长安第一次陷落时那样被轻易收复,唐廷很有可能被迫迁往洛阳。更何况此时藩镇割据之局面已然形成,唐朝的命运面临着不可想象的危险。
二、代宗朝唐军的抗击与蜀川政区变动
广德二年(764)正月,唐廷意识到剑南道分立的弊端,不得已又将两川合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严武任用崔旰的西山人马,积极部署,在西南很快扭转了与吐蕃对抗的败势。史载,“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5](P3398)。随后,严武又指挥唐军乘胜追击,“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十月,取盐川城”[5](P3396)。严武幕府中的杜甫在《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中写道:“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生动描叙了当时战役的情况。唐军虽取得大胜,却没有收复军事重镇维州城,吐蕃占据此地,可以随时发起进攻,唐军来自吐蕃的军事压力依然很重。此时的关陇地区,“(十月)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7](P48),长安戒严。
永泰元年(765)九月,在关陇地区,“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7](P49),长安又一次陷入危险。同年,严武卒,剑南诸将在节度使后继人选上产生了矛盾:一派是以西山都知马使崔旰为首,请立大将王崇俊;一派是以节度使府都知马使郭英干为代表,支持其兄郭英乂。[4](P7187)唐中期以后,一些跋扈的藩镇节度使一般由部下所立,然后唐廷只能被迫承认,这样一来,唐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就有所削弱。王崇俊属于蜀川地方武人,代表地方军将势力。郭英乂是名将郭知运之子,有平叛安史之乱之功,历任陇右节度使、潼关防御使、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等。唐廷希望选出一位对中央忠诚的人,于是派郭英乂出任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到任后,“严暴骄奢,不恤士卒,众心离怨”[4](P7187),“肆行不轨,无所忌惮”[5](P3397),百姓怨声载道。郭英乂设罪诬陷王崇俊,将其杀害,又妄图招崔旰回成都加害。他在断绝西山军粮饷,囚禁崔旰家室,崔旰仍拒命不回的情况下,以协助防御吐蕃为名调集重兵攻打崔旰,结果惨败。崔旰率领西山军乘胜攻入成都,郭英乂仓皇出逃时被普州刺史韩澄所杀,一时“数州牙将纷纷举兵讨旰,蜀中大乱”。[4](P7187)
唐廷为了控制蜀川局势,于大历元年(766)二月“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4](P7190)。同时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以崔旰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御使”[4](P7191),试图互相制衡。但唐廷显然低估了以崔旰为首的西山军事集团的实力。三月,张献诚与崔旰战于梓州,献诚大败,旌节被夺。[4](P7191)杜鸿渐名义上为山南三道副元帅,能直接指挥的兵力却有限,他深知武力介入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所以到成都后,改变了戡乱的意图,满足崔旰一些要求,不但不谴责还向唐廷大力举荐。唐代宗为了安抚崔旰,亲自为崔旰“赐名曰宁”,取蜀中安宁之意,明确表达对崔旰的信任。大历二年(767)七月,崔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两川才实际分治。[12]
大历三年(768),唐蕃关陇战场上的战线已经基本上稳定在陇山至六盘山两侧。吐蕃以西侧为阵地,不时向关中发动猛烈进攻,曾迫使长安数度戒严。六盘山山脉古人称之为“陇坂”,北面与荒漠接壤,南面与秦岭相连,是关中战区的天然防线。大历八年(773),吐蕃再次入寇,朝臣们主张放弃泾州,宰相元载反对这项决议,认为“陇坂”“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5](P3412)。“陇坂”以东是军事要地凤翔,凤翔是防御吐蕃的重镇,也是连接关中与蜀川的枢纽。“凤翔、陇州和宝鸡构成关中平原西面防卫的三角地带,而凤翔因控陇关道与陈仓道并间接控制回中道,地位尤为重要。”[13]吐蕃已经吞并了河陇地区大片土地,如果此时蜀川再被寇陷,凤翔将会受到两面夹击。[14]凤翔在长安以西,是阻挡吐蕃进攻长安的重要屏障,若是凤翔被占领,长安基本无险可守,有再次沦陷的危险。值得唐廷庆幸的是,崔旰镇蜀期间多次打败吐蕃的进犯,使唐朝在西南战场暂时遏制住吐蕃的进犯。在大历九年之后,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远不如先前那般凌厉。这其中的缘由应与西南战场上唐军屡次获胜,成功牵制吐蕃对长安的进攻有关。史载如下:
大历十年(775),“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数万于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7](P57)。
大历十一年(776),“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7](P58)。
大历十二年(777),“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冬,十月,乙酉,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于望汉城”;“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十二月,“丁亥(初九),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7](P58)。
与此同时的关陇地区:
大历十年(775),九月,“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7](P57-58)。“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破之于百里城。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7](P58)。
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7](P58)。
大历十二年(777),九月“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7](P58)。十月,“吐蕃寇盐、夏州,又寇长武;郭子仪遣将拒却之”[7](P58)。
大历十三年(778),“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7](P59)。七月,“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7](P59)。八月“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7](P59)。“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与段秀实共却之”[7](P59)。
吐蕃与唐朝在关陇战场上处在胶着拉锯状态,而大历九年之后西南战事明显升级,表明吐蕃也意识到进攻长安受挫与蜀川唐军掣肘有很大关系,故而在西南战场投送的兵力不断加大。大历十四年(779)十月,吐蕃联合南诏,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进攻蜀川,“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峡关”[5](P6271-6272),并狂傲声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7](P60),企图夺取成都后挥师北上进攻长安。崔旰时在长安,代宗担心崔旰回蜀地后不服唐廷管制,于是遣大将李晟率四千禁军,大将曲环率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火速驰援,东川与山南兵亦前来助战。李晟、曲环等作战经验丰富,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史载,“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7](P60)。此役的后果使吐蕃与南诏的联盟开始关系发生逆转。先前,在吐蕃与南诏联合进攻唐朝中,一般是以南诏军为前锋。南诏虽然在名义上与吐蕃平等,但是吐蕃对南诏“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7](P71)。这次吐蕃与南诏的联合进攻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让双方关系出现裂隙,吐蕃改云南王异牟寻为日东王,地位从兄弟之邦降为藩属之国。异牟寻惧怕,乃“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7](P60),对吐蕃不满与日俱增。对于唐朝而言,此役“唐王朝稳定了剑南西川的边界,阻止了领土的进一步丧失,并且还使这种和平安定的局势维持了好些年”[15](P99)。
三、德宗朝唐朝、南诏重新结盟与吐蕃的溃败
唐德宗时是吐蕃进攻唐朝最为严峻的时期。贞元元年(785),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审时度势,积极谋划,一到任就尽其所力招抚有归化之心的东蛮等诸界蛮族及东女国、西山八国羌族,“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力”[7](P71)。韦皋先招抚东蛮中的勿邓、两林部落,用它们引诱其他部落归顺,又对招抚的诸蛮族首领恩威并施,并且充分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16]这些蛮族诸羌深受吐蕃压榨,敢怒而不敢言,而唐朝此刻向它们伸出橄榄枝,加之韦皋治理蜀川有方,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南诏又在吐蕃与唐朝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出于自身考虑开始逐渐归附于唐。唐德宗即位初期奉行的是对蕃友好的政策,但泾原兵变后,唐廷以吐蕃助国讨逆不彻底为由,拒绝割让西域的安西、北庭之地,导致彼此关系又急剧逆转。平凉劫盟事件让唐蕃关系再次彻底撕破,吐蕃随即对唐朝发动新一轮进攻。史载,贞元三年(787)八月,“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7](P76)。
面对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德宗不得不检讨自即位以来“有意奉行而连遭挫败的和吐蕃而仇回纥的基本国策”[17](P147),逐渐接受宰相李泌所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7](P77)的战略。关于南诏,李泌认为,“次招南诏,则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为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7](P78-79)。南诏主异牟寻就曾说:“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7](P6272),从侧面表达了他对生产技术先进地区的向往。异牟寻的清平官郑回也认为“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7](P71),劝异牟寻归附唐朝。唐军在关陇战场上长期与吐蕃作战,虽仍是以防御为主,但抗击能力却是在不断增强。吐蕃久攻长安不下,进攻重心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德宗采纳这一战略,虽然未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历史的演变却充分表明这是唐、蕃关系再次发生历史性颠倒的重要契机。[17](P147)
韦皋是唐朝与南诏关系修好的关键人物和政策的执行者。他绥服东蛮,一面利用东蛮力量,武力进攻吐蕃,一面利用东蛮为耳目,看是实行争取南诏的方针。[16]贞元四年(788),南诏王“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4](P7513)。唐廷宴之麟德殿,“赐赉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4](P7513)。同年,“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虽内附唐,外为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7](P81),韦皋深知异牟寻犹豫不决,“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报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导致“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两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回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7](P81)。吐蕃“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7](P81)。清溪关道在黎州之南,连山带谷,夹涧临溪,倚险结关。清溪道是连接川滇两地重要通道,明人杨慎在《犯星歌·其二》中写道“飞鸟不飞愁羽堕,行人何事远来游”,说明此道之险峻。扼守清溪关对于保卫成都意义重大。韦皋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联合东蛮迎战,“大破吐蕃军于清溪外”[7](P81)。吐蕃不甘心失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7](P81)。最后“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7](P81)。经此役后,唐蕃战争的主战场由关陇地区开始逐渐转向西南地区。
南诏的外交战略是视唐蕃势力强弱开展交往,因而张九龄有“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去”[18](P1284)的判断,吐蕃也深恨南诏挟唐朝为轻重,责骂南诏为“两头蛮”。贞元五年(789)二月,韦皋致书异牟寻,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7](P81)。为了促使南诏早日归降并打消顾虑,同年十月,“皋遣其将王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7](P81)。此役不仅使吐蕃锐气受挫,而且“数年之内,终复巂州”[5](P3823)。巂州城在大渡河与沪水之间,是巂州都督府所在地,唐廷曾设昆明军、宁远军、会同军,控扼沪津关,足见对其之重视,收复巂州城对唐朝西南战场意义极大:首先,唐军的防线往南推至巂州一带,避免了成都直接暴露在吐蕃兵锋之下的危险;其次,占据巂州后的唐军由于在地理上取得优势,开始主导西南战场,吐蕃渐渐处于被动状态;最后,唐朝向南诏展示了唐军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使其加快归唐的步伐。韦皋虽然屡次致书异牟寻,未获得异牟寻正式答复,但“吐蕃每发兵云南,云南与之益少”[4](P7524)。
贞元七年(791),韦皋遣讨击副使段忠义劝异牟寻并复次至书。吐蕃得知后派人质问异牟寻,异牟寻回答道:“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它谋也”[7](P83)。经此事后,“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7](P83)。贞元七年后,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明显减弱,唐蕃战争主战场已经完全转向西南方。
贞元九年(793),唐德宗下诏在盐州修建防御工事。盐州在长安以北,“地当要冲,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5](P3923)。吐蕃占据盐州,就会对庆、宁、邠等州实现居高临下的战略姿态,可由北向南直接进攻长安。唐廷担心修建期间吐蕃来袭,于是“诏皋出兵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5](P3823)。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结果又被击败,唐军“杀伤数千人,焚定廉城”[5](P3823)。同年,异牟寻遣三批使者贡献方物以示对唐赤心。
贞元十年(794)正月,韦皋遣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至南诏都城。当时有几百名吐蕃使者也在,异牟寻不敢得罪吐蕃,他想暗中与唐朝结盟,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城,遭到崔佐时拒绝:“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7](P87)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史载,“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7](P87)。崔佐时劝说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7](P87)。异牟寻一一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将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率其子寻梦凑等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誓文云:“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云南志校释附录)。[16]
同年,南诏突袭吐蕃神川都督府,“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7](P87)。这标志着诏、蕃结盟关系结束,随后唐朝与南诏友好关系全面开始。[19]
贞元十一年(795)正月,“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邛南驿路由此遂通”[20](P50)。此役,唐军进一步加强对巂州的控制。“十月,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7](P88),表明唐朝再次联合南诏的战略初现成效,吐蕃在西南战场上开始陷入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
贞元十二年(796),“韦皋于雅州会野路招收得投降蛮首领高万唐等六十九人,户约七千,兼万唐等先受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5](P5284),这实质上预示着云南诸部开始纷纷背叛吐蕃而归附唐朝,吐蕃在西南的苦心经营面临瓦解的危险。
贞元十三年(797)“五月十七日,吐蕃于剑山、马岭三处开路,分军下营,仅经一月,进军逼台登城”[5](P5258)。吐蕃此次进攻目的在于重新夺回巂州。巂州刺史曹高任率兵与东蛮接战,“自朝至午,大破之,生擒大笼官七人,阵上杀获三百人,余被刀箭者不可胜纪,收获马畜五百余头匹、器械二千余事”[5](P5258-5259)。此役仅用半日,战果虽不大,但击碎吐蕃的企图,也显示出蜀川唐军战斗力之强盛。
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巂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返”[7](P89)。巂州在西南战场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唐朝与南诏合力御敌,再次证明了唐朝“南通云南”战略的正确。
贞元十六年(800),“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巂州,吐蕃怒,吐蕃遂大搜阅,筑垒造舟,潜谋寇边,皋悉挫之”[5](P5259-5261)。唐军一连串的胜利导致吐蕃的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率领其部下将领八十七人前来投降,吐蕃在西南战场上人心涣散,陷入崩溃的边缘。
可见,由于韦皋成功联合了蛮羌和南诏,“吐蕃失云南之助,势始弱矣”[7](P81),在西南战场的优势逐渐丧失,开始节节败退。
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馀户又降。赞普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5](P3824)。自河陇丧失后,唐朝在西北防御上的“都域之襟带,畿辅之堑防”[21](P2477)优势不复存在,朔方军所在的灵、朔之地逐渐成为长安防御之右臂,号称“国之北门”。为牵制吐蕃进攻灵、朔,唐德宗令韦皋出兵深入蕃界,“以分其势,纾北边患”[7](P90)。
维州位于蜀川西川西北部,自茂州向西南取维州,出滴博岭道,可达于吐蕃。[22](P937-975)唐人认为,“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州之冲,是汉地入边之路”[5](P4524)。由于地理位置较为靠北,从西山地区向西北可达青海,向北可到达洮水流域,向东北可进关中,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其州南界江阳,眠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吐蕃得之,号曰‘无忧城’”[5](P4524),唐军如果收复维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里之地”[5](P4524)。维州对于唐蕃双方都极为重要。贞元十七年(801)、十八年(802)韦皋发动维州之战,以缓解关陇战场的压力,史载如下:
皋遂命镇静军兵马使陈洎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率兵一千出龙溪石门路南,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两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进逼吐蕃维州城中,北路兵马使邢玼并诸州刺史董怀愕等率兵四千进攻栖鸡、老翁等城,都将高倜、王英俊等率兵二千进逼故松州,陇东路兵马使元膺并诸将郝宗等复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巂等路。又令邛州镇南军使、御史大夫韦良金发镇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与三部落主赵日进等率兵三千进攻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过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三部落主苴那时率兵四千进攻昆明、诺济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拔其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一万余级,遂围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余里,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王师万余众,据险设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也,悉众来追,入于伏中,请将四面疾击,遂擒莽热,虏众大溃。[5](P5260-5261)
维州之役是安史之乱后唐蕃战争中唐朝取得最为辉煌的战役,亦是唐蕃战争间一次转折意义的大战。唐军虽然未收复维州,但却给吐蕃极大重创,致使吐蕃在西南地区再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四、唐军最终守住蜀川的原因
南诏归附唐朝,极大削弱了吐蕃的军事力量,减缓了唐军西南战场上的压力。唐与南诏再次联合攻吐蕃,必添胜算,这是唐军守住蜀川的原因之一。
吐蕃人虽善骑射,作战常以骑兵为主,而在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的山地作战,骑兵的战斗力很难完全发挥。在西南战场上,吐蕃将帅可以说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骑兵的劣势不可能不清楚。所以,吐蕃联合南诏进攻蜀川很有可能采用骑兵、步兵搭配的方式,根据不同交战区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此蜀川地形制约骑兵作战不是吐蕃失败的主要原因。
吐蕃自青藏高原进入唐之西南地区,战线过长,且始终在蜀川交通落后,较之贫瘠的地方行动,后勤补给应该主要倚靠盟友的支援。唐军与之对比优越性明显。蜀川民殷物富,“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5](P5022),历来为中央重要的财政支柱。安史之乱后,唐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各地节度使“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5](P3838)。面对这种情况,唐廷只能设法对赋税重地江淮和蜀川严密控制。蜀川财力虽然不及江淮,而地近京畿,“然河南、河北贡奉未入,江淮转输,异于难时。唯独剑南,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腴腆,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8]。西南地区最富饶的区域莫过于蜀川之地的成都平原,安史之乱未波及蜀川,唐玄宗避难于成都还刺激了蜀川经济的发展。髙适任彭州刺史时,在上疏论西川三城事中说,“自卭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赋税者,但成都、彭、蜀、汉四州也”[5](P3330)。见之蜀川财赋之雄厚。
韦皋治蜀时,(剑南)兵力约在3.72万人,以后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目左右。[23]将士作战需要巨额军费,以西川军为例,这部分军费给的开支来源于正税,《册府元龟·邦计部·赋税二》载,大和四年(830)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当道两税并纳见钱,军中支用及将士、官吏俸、依(衣)赐并以见钱给付,令若一半折纳,则将士请受折损较多。今请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纳疋段及杂物。准诏每贯加饶五百文,计优饶百性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其时,西川军中支用及将士衣赐都以现钱支付,这也许与西川两税“并纳见钱”有关。此外,西川军费来源也有增盐估供军、采铜铸钱支度军用、屯田补给、茶利赡军等临时措施。”[23]
蜀川的盐税给士兵的衣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9](P1377)。据统计,元和二年(807),西南井盐收入约为50万贯。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时,“度支使皇甫传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9](P1379),足可说明蜀川盐赋之丰裕。
在西南战场中抚恤阵亡将士也是一个而不小的开支。韦皋在西川21年,其时西川兵卒约2至3万人,假如21年内每人享受一次抚恤,共需40至60万贯,每年用于此项费用在2至3万贯之间。[23]当然,军用物资的运输、战马等牲畜的供应、士兵的赏赐、兵杖器械亦是军费开支。此外还有在山地修建军事防御工程,此项费用在蜀川之军费中虽不占太大比重,却是不可或缺的。[23]统治者对蜀川的搜刮虽让民众苦不堪言,但是过度征敛税赋的做法为缓解战争中物资供应紧张和提高军队战斗力有一定的作用。如严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5](P3396)。持续稳定的后勤保障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利于唐军在蜀川与吐蕃长期作战。吐蕃与南诏交恶,导致重要的后勤补给力量丧失,战斗力自然日益下滑。此外,吐蕃军队惧怕炎热,在剑南道不能持久作战,故其人虽健,戟虽利,却不能长久为蜀地之患。[24]士兵一旦染疾,后勤又供应不上,势必导致疾疫传播扩散开来,无论是对于防御还是进攻,都极为不利。
余 论
安史之乱后,唐朝内有藩镇林立割据,外有吐蕃西北、西南进攻,令其疲于应对。就西南战事而言,唐朝一方面要防止蜀川产生割据势力而二度将剑南道划分东、西二川;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蜀川唐军迎战吐蕃以牵制其对长安的进攻,此外还要极力争取南诏及蛮族诸羌,可见唐之西南局势错综复杂。严耕望先生指出,“安史之乱,陇山以西尽为蕃有,两军拒守之边界去长安不过五百里,致蕃军常入郊甸,而唐都长安仍能屹立百年十年不动摇者,固赖西北朔方军及其分滋诸军之坚强拱卫,亦恃剑南节度在西南之犄角也。吐蕃一旦来逼,则剑南、朔方南北呼应,故吐蕃虽强,亦殊难得志。”[25]试想,吐蕃如果攻占蜀川,很有可能挥师北上,关中亦必危,长安不保亦,唐朝国都必然要被迫东迁或南下,更何况此时已经面临着藩镇割据之局面,唐朝的命运将有着不可想象的危险。吐蕃亦有可能沿长江东进攻。历史时期,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莫不是先攫取蜀川,而后以疾风扫叶之势,击吴楚之腰脊,一统中夏。吐蕃崛起后能与唐朝、回鹘、大食、南诏以及天竺同时作战,地域扩至幅圆万里,足可说明武力之强盛。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此之时,吐蕃正是赤松德赞主政期间,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不可能不会意识到蜀川“北渡汉水以窥秦地,东顺江流以震荆、扬”[26](P355-356)的战略地位。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21](P2502)吐蕃一旦控制蜀川和关陇,就会对唐朝形成完全性的高屋建瓴之战略优势,继而横扫中原,撼震天下,历史很有可能被改写。蜀川之安危,系中原之大局,代宗、德宗朝时唐朝与吐蕃在西南鏖战三十九年,最终守住蜀川,实属不易。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安史之乱令唐朝元气大伤,亦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吐蕃的全面入侵,致使唐朝“只有招架强之功而无还手之力”[27](P185),带来最恶劣的后果是唐朝失去了战乱后整顿天宝政治积弊的大好时机。唐朝之衰落影响此后两百多年东亚局势之更迭却为赵宋以降新局面肇始新开端。
[1]林冠群.唐代吐蕃构建天下秩序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2]张志达.安史之乱后唐蕃边境的进退——泛东亚视域的角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4).
[3]杨慎.全蜀艺文志[M].北京:线装书局,2003.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陈乐保.唐肃宗时代剑南道政治地理研究(757-767)——以东西两川的分合为中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7]苏晋仁编,李加东知译.《通鉴吐蕃史料》全译[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
[8]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1]岑仲勉.隋唐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马剑,孙琳.唐代剑南道之分合[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4).
[13]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J].文史集刊,1987(2).
[14]彭起耀.试论剑南道在唐蕃战争中的地位[J].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
[15]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6]王永兴.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17]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18]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9]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冶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20]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1]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3]贾志刚.唐代剑南道军费刍议——以剑南西川为中心[J].魏晋南北朝唐史资料,2002.
[24]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J].历史研究,2004(5).
[25]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1(12).
[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