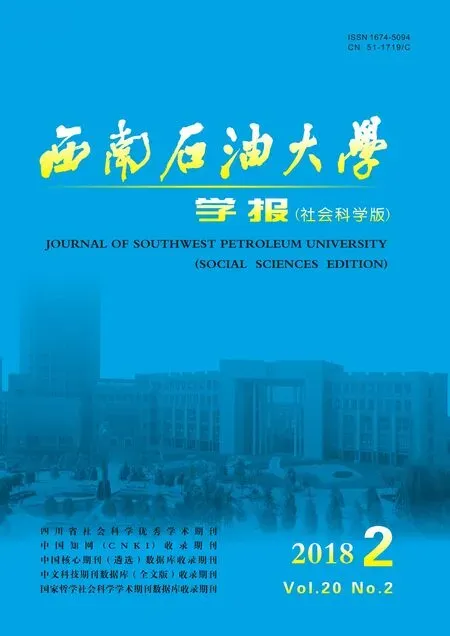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黄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引 言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籍徽州歙县长塘,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桐乡乌镇。鲍廷博年轻时曾参加科举未中,后绝意仕途专门从事藏书活动,他曾言:“物无聚而不散,吾将以散为聚耳。金玉玑贝,世之所重,然地不爱宝,耗则复生。至于书,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着古昔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甚伟也。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为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惧其书之不能久聚,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1]128鲍廷博在藏书过程中遍交江浙各地文化名人,例如与黄丕烈、陈鳣、卢文弨、吴骞、钱大昕、金德舆和方熏等人经常把酒言欢、互通有无。但是,真正让鲍廷博“海内荣之”的是他藏书事业得到清廷官方的高度肯定。1773年四库开馆,鲍廷博响应号召向朝廷进献家藏秘本626种,居各私家之首。1774年乾隆帝赏赐鲍家《古今图书集成》《平定回部得胜图》及《平定两金川战图》等。1775年《四库全书》完工发回原书,乾隆帝在《唐阙史》和《宋仁宗武经总要》上题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阙史》两篇传摭拾,晚唐遗迹见规模。彦休自号参寥子,参得寥天一也无。”[1]1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民间藏书家,在封建社会能够得到统治者的奖赏是很稀有的。
吴骞(1733—1813),字兔床,号槎客,生于浙江海宁小桐溪,祖籍徽州休宁,性喜藏书,曾经建造拜经楼等以藏书。吴骞家族在浙江落籍后一直居住在海宁,鲍廷博先是居住在杭州,后迁至桐乡乌镇,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来看两人都在嘉兴居住。共同的爱好和乡友关系,成为他们日常交往的重要桥梁,尤其是以藏书为中心的活动,他们更是互相支持、互相影响。两人在搜集浙江当地文献的同时特别关注徽州文献,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就有不少徽州著述,而吴骞对徽州地方志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吴骞非常了解徽州《歙志》,他认为该书刊刻不久就销毁是有特殊原因的,“《歙志》之修,先告于城隍神,其文附刻卷末。然其书成之日,时论哗然,故不久即毁其板。观其体例,较他邑志颇简略,至列仇鸾于《国憝》,而于其过恶皆直书,不少回护,居然有斧钺在笔端,宜为乡里所侧目矣。唐咸通中,大芦禅师住锡大芦院,李玭招之入善卷,不赴,居大芦以终。谢少连谓:‘志之体实史,史之要在劝惩。’故《歙志》于《载记》后著《巢寇》《宋寇》《岛寇》《列女》后著《妒妇》《人物》后著《货殖》,皆创例也”[2]87。
根据吴骞日记及其相关诗文、藏书题跋记的记载,吴骞与鲍廷博的往来十分密切,这其中书籍自然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两人书籍交往过程中的诗文互动、互相赠书、传抄、借阅、校勘等活动一时成为藏书史佳话。吴骞也因此刻一方“知不足斋主人所贻,吴骞子子孙孙永宝”的藏书印,可见两人交往的密切。
1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诗文互动
鲍廷博与吴骞都是生活在清代中叶的中下层文人,且都是旅居浙江的徽商大家。虽然两人曾经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都没有取得显赫的功名。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藏书上面,在此过程中彼此作诗、赠诗,成为交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鲍廷博一生到底作了多少涉及藏书的诗,无人知晓,但他曾以书香、书味、书声、书橱和书灯等为对象作诗,使其“不蕲名而名自至”,阮元曾评价鲍廷博:“中年后尤耽吟讽,杖笠所至,一草一木,流连竟日,如‘夕阳’一题,多至二十咏,可谓极体物之妙矣。”[3]由于鲍廷博流传的诗除《花韵轩咏物诗存》外尚未有其他发现,因此无法看到鲍廷博对吴骞的和诗,但根据吴骞日记及其题跋记,却可以发现其中记录有关两人藏书活动过程中诗文互动的例子。
1774年3月24日,吴骞前往祖籍地徽州祭拜先祖,25日途径武林,当时鲍廷博去了绣溪,26日鲍廷博归来后驾船冒雨送吴骞,舟中鲍廷博出示最近新得的宋刊《九经白文》,两人谈书一直到深夜才作罢。吴骞作诗《雨渡钱江却寄渌饮》:“饱挂轻帆出乱峰,茫茫何处托离踪。银涛打岸春三折,碧海粘天雨万重。修禊兰亭人已远,探奇宛委兴徒浓。相知剩有孤飞雁,尺素休辞一再封。”[4]111776年初秋,鲍廷博与吴骞、奚冈过访心上人山舫,一边探寻石刻文献一边欣赏风景,吴骞作诗《同渌饮、铁生过心上人山舫》:“漫携三笑侣,言访六朝僧。竹暗还幽迳,云深最上乘。盔泉松火沸,香饭野蔬蒸。错忆同孤棹,流连晚兴增。”[4]18
1780年,鲍廷博与吴骞至武原访书,吴骞作诗记载《雨夜与渌饮自落星庵至武原》:“残星能化石,远溆转多风。一雨秦溪至,扁舟鲍叔同。披蓑惊宿鹭,灭烛听归鸿。不分征途上,犹馀两断蓬。”此次访书收获不小,回途后两人在海宁城外雨夜惜别,吴骞又作诗《海昌城外与渌饮别》:“握手辞滓水,移灯过海城。酒欺双鬓短,书放两船轻。不待鸡初唱,似闻潮欲平。东风和别恨,并作两千声。”同年,鲍廷博与吴骞同游茶磨山,并拜访当地先贤明代许相卿故居,吴骞作诗《同渌饮游茶磨山许九杞先生故居》:“振衣千仞俯孱颜,岳庙西来第几湾。东海至今通散浦,南云从古护青山。输粮鹤喜田多岁,解组人言鬓未斑。杜曲冈边空翠里,高风犹对碧萝间。”[4]291781年,鲍廷博与张燕昌等人在涉园集会谈古论今、考证书籍源流,吴骞因故没有参加,但有作诗《夏日闲居,闻渌饮、文渔诸君涉园雅集却寄》记载:“绿竹名园旧凤阿,沧江逸兴起酣歌。永嘉南渡才尤少,汉上题襟句孰多。花落几惊春婉娩,乌啼莫问夜如何。也知吴质新来病,不得絺衣挂薜萝。公子归来晚更忙,莺莺燕燕此相羊。桃源不似人间世,濠濮居然水一方。镜里芙蓉凄露粉,岩前松桧饱风霜。好留第五风流在,重醉陶家九日觞。”1782年初夏,鲍廷博同吴骞、陆绍曾、陈鳣西湖泛舟,吴骞作诗《初夏雨后同陆白斋、鲍渌饮、陈河庄西湖泛舟》:“玛璃坡前唤渡航,清游容易感流光。舖来弱絮堤浑软,洗尽秾花水更香。黛影也如云意淡,离愁莫共雨丝飚。只期鱼鸟邻同结,妻子琴书同一庄。”[4]31
1784年夏,吴骞去乌青访老友鲍廷博新近购书,吴骞在途中作诗《夏夕从小桐溪泛舟径硖石至乌青访渌饮道中即事》二首,其中有“渔火沿汀白,蘋香到枕浓。忽闻歌水调,知己出云峰。草没乌墩戍,风传宋堡钟。平明聊倚棹,隔岸见晨春”。当吴骞在鲍廷博处看到其为亡女作《泪珠》三首时不禁怅然,“桦烛辉生绮席霞,虚将好事向人夸。谁知红影双摇处,不是人间并蒂花”,“采药归来自怪迟,补天石在手难施。瑶池宴罢椒花落,消得仙翁一首诗”,“合浦明珠去不回,老怀更复向谁开?碧桃花下春长在,愿与仙人扫绿苔”。吴骞题诗三首以示哀悼,“鲍家小女离魂日,句漏仙人徙宅时。肠断青溪花下路,一棺秋雨瘗琼枝”,“月上归来月未斜,萋萎芳草奈天涯。维摩示病渠真病,始悟拈花是扫花”,“那复围棋伴谢公,青鸾一去渺无踪。彩云易散流离碎,也算麻姑小劫终”[4]36。
1787年,鲍廷博、张燕昌同访吴骞于南祠,三人趁月至金牛庵,并赏景论书,吴骞作诗《渌饮、文渔过访南祠,因同晚步湖塘即事三首》,其中有:“户凿烟霞窘,庭垂橘柚阴。往来逢二妙,臭味本同心。白鹭沧洲阔,青山碧里深。紫芝能共采,聊此散幽襟。”[4]461785年,吴骞的藏书楼拜经楼建成后,恰好鲍廷博游新安回来,购得明代书画家郑叹旼所绘《拜经图》,于是立刻赠吴骞。《吴骞日记》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初七日曾记载鲍廷博赠送自己《拜经图》的故事:“渌饮前岁游新安,见有以郑旼画《拜经图》求售者,买以见赠,因余有拜经楼也。予守而悬诸楼下。画法倪迂,有萧疏闲谈之致,上题诗云:‘治历当辰一荐芹,经延秦焰岂全焚。百篇删定教齐鲁,半壁留遗见典型。书考连丛疑自阙,冤沈掌故训谁闻。只将中道传心法,何事诸儒议论纷’。”[2]52其还创作绝句:“学古名楼事偶符,故人携赠出天都。只缘个里诗书气,不共去烟化绿芜。三径荒烟带草青,千竿纡竹自娉婷。主人未必全如我,不解穷经只拜经。”[4]45
鲍廷博曾有著名的“夕阳诗”,1804年吴骞为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题诗《题鲍渌饮茂才韵花轩咏物诗后》五首,其中有“玉尺纱橱汗简量,白头涵泳尚青箱。定香亭下清风在,争看诗人鲍夕阳”“唱和松陵偶寄踪,齐云采药悔疎慵。何时更把宣城句,吟上光明顶上峰”[4]141。1809年2月26日,82岁高龄的鲍廷博携孙子拜访吴骞,吴骞感慨其“精神巩固,真不易及也”,并作《试灯夕喜渌饮文学过访》“九裹遐龄叟,春王五夜灯。暗尘随杖屦,华发兴飞腾。酒借银花祝,诗凭玉漏增。素娥尤好客,先破早梅冰”[4]162,1812年9月11日,“尚能小楷,不异少年”85岁的鲍廷博还前去拜访吴骞[2]250。
2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传抄订补
书籍传抄订补是清代以来藏书家藏书的重要来源,鲍廷博曾经传抄汪氏振绮堂不少书籍,朱文藻言“余馆振绮堂十馀年,君借抄诸书,皆余检集”。而吴骞又多次借抄知不足斋的善本,1790年杨慧楼在吴骞处作客谈及《辽史拾遗》时称吴骞“慨举知不足斋赠本假钞,以数年愿见不可得之书,一旦得缮录全帙,登诸箧衍,快何如之”[5]49。吴骞和鲍廷博祖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并没有收藏书籍,他们完全是靠自身努力储藏书籍。然而仅仅依靠购买是不足以扩大藏书的,于是,传抄书籍并订补就成为积累书籍的重要方式。通过吴骞日记及其藏书题跋记可以发现,两人之间因书籍传抄而产生许多交往故事。
吴骞收藏的抄本《南部新书》十卷,就是从鲍廷博知不足斋借抄的。吴骞还照录各家本在借抄过程中订补,并补录首序、王闻远叔子及贞复堂二跋,又附录厉本延佑丙辰子贞子、洪武五年清隐老人、正德十年约斋、辛丑清常各校,雍正庚戍蝉花居士、乾隆乙酉贞复堂诸跋。1775年,吴骞还从著书斋借稽古堂本重校原抄本,跋云:“乾隆乙未闰十月又从周芚兮先生借得高寓公稽古堂刊本重校,凡抄本中有原字与刻本同者不复注‘刻作某’,有不同字而刻本显然纰漏者亦不复注。”1784年,陈鳣又以陈宋斋藏本互勘云:“此吴槎客先生手校本也,乾降四十九年三月,海盐馆中有苕人持抄本见示,乃家宋斋先生书巢旧藏。会予以寒食解馆,归语槎客先生,先生出此本,属为覆勤。因复携至馆中,自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夜半勘毕,凡紫笔者皆是。合诸先生所校,是书可称善本矣。”[5]53
吴骞拜经楼藏的宋代王铚撰《默记》抄本,陈鳣曾借拜经楼吴氏藏本抄出,原本为朱映漏、鲍廷博所校者都用朱笔。吴骞所校者先用紫笔,继用绿笔。吴骞1774年跋语“予借得以文本,吾友朱君云达为予手抄,且以意改其豕亥,藏之箧衍。今予又得朱、鲍二君从汪氏二本校过者。凡此一书,合四家藏本,经四人手眼,吾辈之好书可谓勤矣。他日以示云达,当更为之忻然也。甲午十月二十七日,横河舟次,兔床再志”。又跋“明日,海昌吴骞复从知不足斋主人借观”。朱文藻1774年的跋语写到:“鲍渌饮以此本嘱为校勘,因合汪氏飞鸿堂、汪氏振绮堂藏本互勘,三本皆善矣。”当朱文藻校完后归还,鲍廷博又取飞鸿堂本重勘,校出数十处。但是飞鸿堂藏本也不佳,尚有讹脱,无法搞定改定,鲍廷博非常遗恨。鲍廷博跋“《五总志》,南宋吴迥所撰。世多未见。予近始得之。因自叹躭书之癖不减昔人,所恨林宗、石君辈不见我耳。乾隆甲午秋日,廷博。”1776年陈鳣各依原色造录于上,其认为有未合者以黄笔改正,其跋曰:“从拜经楼借阅,因亟命胡生凤苞抄之,至八月二十七日抄毕。其诸家校本仍照各色书之。更有一、二改正处则用黄笔。合观之,恍似文通梦中五色笔矣。”又跋“吾乡有王性之庙,不知即撰《默记》者否?俟考。卷后有叶石君题跋。按石君名万,吴之东洞庭山人,晚家琴川,聚书数万卷,多手校过。余每思其人。近日修地志者不载其姓氏,殊恨事也。所云《五总志》,当更从渌饮处借抄”[5]112−113。近代收藏大家张元济认为,此书“既出名家所藏,所校又为名人之笔,洵可珍已”[6]360。
又如,吴骞《云麓漫抄》十五卷同样是从知不足斋借本传录,其亲手校正用朱笔,并属朱巢饮校用绿笔。十卷后有鲍廷博跋云:“《云麓漫抄》刻于商氏《裨海》者祗四卷。此本传自赵氏小山堂,较商氏所刻已多过半,而《宋诗纪诗》及《南宋杂事诗》所引李易安《投翰林学士綦崇礼书》不在焉,然则此尚非全书耶?更当觅善本订之。乾隆壬午瑞午后一日,知不足斋识。”鲍廷博认为,曹彬侯跋《清波杂志》说《云麓漫抄》二十卷,那么此书仅有其半,其后来又从小山堂得十一卷至十五卷,但是李清照启载十四卷中,从作者自序看此书只十五卷。曹彬侯所言恐未足据。吴骞在书后写到:“庚子夏日从渌饮借得《云麓漫抄》十五卷,因为传录,并倩朱君允达校而藏之拜经楼。按此书《书录解题》亦作二十卷,又续抄二卷,乃《中庸说》及《汉定安公补记》,然藏书家率未闻有,岂不传耶,俟续访之。”1806年陈鳣又从吴骞的抄本借抄,跋云:“嘉庆十一年夏日,从拜经楼借得是本,携至吴中,今年春始得倩人传抄,甫竟,遂手录渌饮前后三跋并拜经楼主人所跋所评,细校一过。至吾师朱子,则称‘师云’以别之。适渌饮扁舟过吴见访,相与把玩,为之一快。且谓余曰,此书尚缺图数页,故未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渌饮年八十矣,尚健饭,行不扶杖。时携书卷往来杭、湖、苏数郡间,其好古清兴正复不异昔日也。嘉庆十二年四月望日,勃海陈鳣记。”[5]110−111
3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校勘借阅
鲍廷博与吴骞收藏的书籍有不少善本也非全本,通过彼此间的校勘,可以使善本更加完善,对刊刻书籍也大有裨益。如1773年秋,鲍廷博从湖墅友人斋头得见明柳佥影宋抄本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驰告吴骞,吴骞喜不自禁,急借归校勘。因此,校勘书籍就成为他们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校勘过程中书写自己的心得或者书籍源流,勘误其中的不足自然也是重要的内容。因此,他们彼此都会在善本的后面写题跋,正是经过他们的校勘题跋,刊刻出来或流传至今的善本价值也就更能得到体现。
鲍廷博校刻《古文孝经孔氏传》时就邀请吴骞为其校勘并书写题跋,吴骞云:“《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世久失其传。武林汪君翼苍随估舶至日本访求以归,吾友鲍君以文得之甚喜,遂刻人《知不足斋丛书》。”[7]831812年,鲍廷博请吴骞为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作序,吴骞写到:“抱经卢先生之归道山,屈指十八载矣。方先生之殁也,骞走哭诸寝门,葬往视其窆,毕封乃去。及同人汇刻遗集,得之为独先。他日,鲍君以文过溪上之敝庐,而言:‘《抱经堂集》梓成久矣,未有序,环顾先生平昔交游,大半零谢,子其可无一言乎?’骞深谢不敏。既而伏念,辱先生之知垂数十年,每抠趋请业,无少厌倦,谬以直谅多闻之友见许,晚至愿言与夫子结为弟昆之语。且先君子碣墓之文,实出先生手笔。呜呼,是虽欲以不文辞,得乎?先生教人,首重论品而次学术......尝谓士不可顷刻离书,譬鱼不可须臾离水......先生著书满家,已足垂诸不朽,矧研摩经传,起废钩沉,尤有裨于圣贤......爱不揣固陋,聊抒梗概,以谂于鲍君云尔。”[1]232−233《金楼子》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时,鲍廷博曾经组织朱文藻、吴骞等学者对《金楼子》的文字进行校勘,甚至自己也动手写校记,这使《金楼子》的质量大大提高。由于《金楼子》辑录的底本《永乐大典》当时藏于深宫,吴骞校勘《金楼子》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其他书籍,如《记》《汉书》《说苑》《淮南子》等。吴骞认为“《金楼》杂采诸书”,故反用诸书来校勘《金楼子》,这也是吴骞校勘精确有据的重要原因。虽有诸多不足,但吴骞的校对是最早全面整理《金楼子》的成果,具有重要的价值。而鲍廷博将其刊入丛书中,并参与校勘,功不可没,且稿本二中有“四次校”“《金楼子》第五次补校”字样,可知吴骞、鲍廷博曾经多次校勘《金楼子》[8]。
吴骞收藏的《笠泽丛书》中有一本是乾隆年间吴门顾楗手校重刊本,即覆元本,虽然纸墨都好,然而错误仍然不少,且没有王益祥的跋语,于是吴骞访求更好的本子进行校勘。在此过程中,鲍廷博两次帮其借得更好的本子用于校勘。鲍廷博告诉吴骞,钱塘郁礼的东啸轩藏本非常好,于是1774年秋鲍廷博携吴骞前往拜访郁礼藏本借校用朱笔;后用拜经楼藏本校用绿笔。1775年春鲍廷博又购得林厂山本,吴骞又用蓝笔校。1776年秋仲,吴骞又从海盐吾太学以方,借其照宋本校正陆氏刊本用墨笔,并补录《小名录》序及跋。1781年秋,吴骞又借得秀水蒋春雨旧抄本,校勘仍用朱笔。但是蒋本只分上下二卷,无目录,前有樊开序及自序,卷末附陆龟蒙传、朱衮后序、德原跋。蒋本前后篇数与刻本同,只少《耒耜经》一篇。据此,可知吴骞当时根据各种版本校过5次,并补录《小名录序》、王益祥跋、陆钟辉跋,及明王良栋、康熙丁卯龚蘅圃、阮善长诸题识。周春曾经对吴骞的校本也进行复校,其云:“乙未正月初四日校起,初九日毕。其确无疑义者用圈,显然谬误者用掷,至字可两通者用点于傍。但心绪苦劣,匆匆或有未尽处,况风庭扫叶,此事本难,兔床其再勘之。松霭棘人周春记。”陈吾进也曾校勘过一次,其跋语云:“戊戌首春,兔床先生以此书属予校勘,勘法一遵松霭先生之例。其是正处,朱黄二毫为胜。然蹲鸱鸡尸,自昔为然。兔床其值本即校,勿以再三为限可也。竹素后人吾进识。”张燕昌题跋云:“《笠泽丛书》余向有碧筠草堂刊本,好友陆白斋又赠何义门先生校本,自喜所藏称善矣。今假兔床先生所校,集诸家之大成,较何本订正更多。按碧筠本为吴人王岐所书,笔讹尤多,先生一一改正,以《说文》为宗,且有益于小学......后之求《丛书》者,不得朱衮、樊开本,当以先生本为甲观矣。乾隆乙巳七月十九日,海盐张燕昌识于冰玉堂。”黄丕烈在观看吴骞此校本后也大为赞赏,于1805年5月17日跋语书中云:“《纪锦裙》一首,兔床先生引吴融诗为证,可破群疑矣。余谓‘裾’与‘裙’虽各本不同,而篇中‘曳其裾’者‘裾’字本不误,且‘曳裙’未见所出,断非‘裾’或为‘裙’之误也。承兔床借读,附著于此”[5]147−148。此外,吴骞另外还藏有陆氏刻本《笠泽丛书》,1777年鲍廷博又从慈溪毕氏帮吴骞借得所藏何义门本对校。
又如,吴骞拜经楼收藏厉鹗著《东城杂记》,有杭世黢及厉鹗自序。吴骞曾经从鲍廷博知不足斋借阅,但是鲍廷博说自己藏本并非足本,只有郁陛宣东肃轩藏本最佳,当有机会去校抄。吴骞在题跋中记载鲍廷博的话语并又跋语云:“乙巳岁,吴门宗人枚庵借绿,又为勘出数处”。陈鳣书云:“嘉庆十四年冬日,陈鱣借绿于吴门寓舍,并校一过。时方得樊榭徵君所著《玉台书史》,因与拜经楼主人交易而观,各抄副本云。次年春正月,鳣识。”[5]125吴骞拜经楼藏《容斋五笔》为旧抄本,原有朱笔评校,吴骞后借知不足斋所藏义门先生评校本过录,跋云:“乾隆辛丑春日,偕鲍君以文游武原,有书估谒予舟次,携抄本《容斋五笔》求售,有朱笔评校。盖陈宋斋先生笔也,因酬以直待之。复从鲍君借所藏何义门先生评校本,用蓝笔点次。鲍本末复有筠溪煦跋,不具录。壬寅冬日兔床吴某识。”[5]112−113
4 《吴骞日记》中的鲍廷博
刘尚恒先生大作《鲍廷博年谱》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成为研究鲍廷博的重要文献。刘尚恒先生曾对年谱多次补遗,足见其治学严谨。笔者由于研究的需要,发现鲍廷博年谱仍有遗漏,而《吴骞日记》中有多条关于鲍廷博的记载,此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原名为《日普》。目前出版的有2006年学苑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影印的《吴兔床日记》(历代日记丛抄),以及凤凰出版社2015年出版点校本《吴兔床日记》,另外国家图书馆亦藏有抄本①刘尚恒先生曾经发表多篇论文补遗,然未收入,2017年出版增订本不知是否依据吴骞日记补入相关内容。。现据此补鲍廷博行年如下:
乾隆四十五年(1780)②此年《鲍廷博年谱》中有此相关描述,作者参考了邓实、缪荃孙合编的《古学汇刊》。:二月十八日“黎明入城。雨中同河庄访渌饮于知不足斋。接朗斋京师书”。二月二十五日“得松霭书。同河庄过卢绍弓学士抱经堂夜饮。渌饮过谈”。三月朔日“渌饮以戴无忝诗画册及杨忠愍公书册借观”。三月初八日“晨起,自莱园还寓。午后同渌饮、河庄游昭庆寺山房,际晚入城。渌饮复以明高丽许篈所书其妹景樊诗借观,书法秀逸,颇类赵吴兴。景樊号兰雪,其诗苍浑悲壮,有须眉丈夫所不能道者。朱竹垞《明诗综》选五首,皆不在此卷内。余详河庄《武林寓目记》”。三月初九日“芝山、晋斋过访,予与河庄各出行箧所有金石书画鉴赏。别后复与河庄至昭庆寺山房,遇渌饮茶话,邂逅抱经、嘉树于段家桥。薄暮,与河庄步月入城。是日藉山过访,不及晤”。三月十一日“复与渌饮、河庄游湖上,重过昭庆山房,迨暮始还”。三月十三日“午后同渌饮、河庄过卢学士抱经堂,观新校定汉魏诸书”。三月望日“与河庄探晋斋。午后莱园牡丹盛放,因携觞招同人小集。在座者为卢学士文弨、鲍茂才廷博、张郎中培、项孝廉丰及其二子、沈茂才恩治、陈君鳣、儿寿恒”。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廿七日“知不足斋过。雨,还舟。是夕冲雨,访小疋嵩门,迨二鼓而别。翟晴江先生以《尔雅补郭》从金华属小疋寄赠,又从小疋借得孔荭谷刊《诗毛郑考正》,乃戴东原作”。九月廿八日“过渌饮贞复堂。魏叔子出示陈?兰竹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五日“偕渌饮过绍弓先生抱经堂,是夕小疋、广文来舟中夜话”。六月十二日“热甚。是夜泛舟至乌青,访渌饮新居”。六月十四日“与渌饮同访金鄂岩刑曹于桐乡。夜宿桐华馆”。六月十五日“渌饮先归乌青”。十一月初五日“自桐溪至乌戌,问渌饮疾”。乾隆五十年(1785):十一月十一日“至武林,寓祖庙巷。渌饮来晤”十一月十二日“晨起,偕渌饮同访程易田孝廉。易田名瑶田,歙县人,博学而长于考古,著《通艺编》,辨论古器甚析”。十三日“复与易田、渌饮、河庄过汪西庚明经十墨斋,观日本各种墨,皆其尊人翼仓从倭国购归者。规制不一,最奇者曰佛际石碑,碑为辽统和三年立石于和州,一面有诗十七首,赞四首,字细如绳头,非显微镜不能读。是日渌饮偶失手碎其一枚,余笑语坐中曰‘久不闻此碎玉声矣。’主人亦为之解颐”。
《年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六十岁,“春,鲍廷博同吴骞、吴翌凤访杨复吉,适逢王鸣盛同至”。吴骞有诗记其事。吴骞《同绿(渌)饮、家枚庵访杨慧楼进士于松陵,小集湖楼,王西庄光禄适至》诗(二首):“蹑屐下姑苏,扬帆迳石湖。为怜扬子宅,可钓季鹰鲈。屏拓峰千叠,楼高酒百壶。此中容啸傲,身世一菰芦。”(其一)“远塔垂虹外,孤城钓雪边。碧萝三迳雨,芳树五湖烟。客至巾初垫,春移景未迁。三高祠下水,相与定忘年。”补遗:《吴骞日记》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初三日“在吴门,偕渌饮、枚庵至吴江访杨君复吉。杨君字立欧,号慧楼,乾隆庚寅孝廉,壬辰进士。是夜于座间晤王西庄先生。茶罢,西庄别去,予与渌饮、枚庵小饮于慧楼新楼,黄昏而别”。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望日“儿寿照病目,久不瘥,掣之至青堆就治。是日渌饮同舟,抵桐乡,过爵余堂。适鄂岩以病不出,留饮于桐华馆,夜分而别”。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月初二日“至青堆,渌饮以《元统一志》九大册赠我,希世有也。志为集贤殿大学士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岳铉编上。《千顷堂书目》以孛兰肸为卜兰溪,张季才《补元史艺文志》作卜兰禧,《居易录》以为岳璘撰,并误”。十一月廿四日“至青堆访以文,不值而回”。十一月廿六日“以文偕禹新过访。禹新从云间来,携宋拓《圣教序》,后钱士升跋”。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初四日“鲍渌饮自青堆至杭,以夕阳诗见视,予为序而刻之”。五月初八日“雨中渌饮来道别”。六月朔日庚戌“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头斋二际,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际,以佐剞劂。而渌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六月二十九日“是日渌饮过访,赠予古剑一,长一尺二寸,土花绀碧,惜未知何代表物”。七月朔日“渌饮携石斋二际归青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四日“偕渌饮、绿窗父子游湖上,时渌饮将为楚游”。六月二十五日“鲍渌饮见过”。九月廿六日“同渌饮、小洲至葛林访汪容夫,不值。容夫名钟,江都人,丁酉拔贡”。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廿七日“至西湖访渌饮于醉茶轩书局”。
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十六日“过小如舟室,晤东谷学博。出城访渌饮,不值。是夕漏下二十刻月蚀,三鼓卢师山大火,沿及四条巷,际晓始熄。焚数千家,死伤不计其数。故老云:‘数十年目所未见’”。嘉庆二年(1797):五月十八日“过醉茶轩,与渌饮、鄂岩同游昭庆,观王昭平先生楷书《金刚经》石刻”。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十一日“晴。晨起登比部墓,送其下定,渌饮过舟中。饭罢,渌饮仍还梧桐乡,予亦解舟难归”。嘉庆十二年(1807):五月二十日“渌饮偕何梦华见过”。十月廿五日“渌饮偕其孙过访,商刻《谢山外集》,予资助十两。夜分解舟”。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廿六日“渌饮过舟次,晋斋踵至,剧谈而别。小舟以书画至,际晚别去”。嘉庆十四年(1809):一月十三日“渌饮挈孙自乌戍至,时年八十有二,精神巩固,真不易及也。至夜分观灯而去”。嘉庆十五年(1810):一月十三日“忆去年此日,绿饮自桐乡过访,留连竞日,迨夜小饮耕烟山馆,观灯至午夜而别”。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初六日“老友鲍渌饮过访,时寿八十有五,尚能小楷,不异少年”。
5 结语
“羽陵姓字九重闻,阙史题诗帝右文。正是夕阳无限好,白头携杖拜卿云”[9]425;“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架庋千元。生儿即以周官子,俾守楹书比孝辕”[9]436,这是叶昌炽对鲍廷博和吴骞藏书事业的高度赞扬和肯定。明清时期旅外徽州人在寓居地经济发达以后,开始深入文化领域,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的文化互动来实现身份认同。因此,他们与不同群体之间开始了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交往,在此过程中不同积淀文化的互动,加深了徽州文化的传播,而对于寓居地来说,也使当地人有机会了解相对封闭的徽州社会的风土人情。此外,通过吴骞的著书了解他与时人的交往,特别是了解吴骞笔下的鲍廷博形象和补遗《鲍廷博年谱》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资料的发掘,许多鲍廷博与吴骞交往的史料将得到开发利用,这对于研究清代中下层文人的学术活动及生平,特别是清代旅外徽州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刘尚恒.鲍廷博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10.
[2] 吴骞.吴兔床日记[M].张昊苏,杨洪升,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3] 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J].历史文献研究,2014(18):365.
[4] 吴骞.拜经楼诗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145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清]吴寿肠.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8)[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 周生杰,杨瑞.鲍廷博评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8] 陈志平.论鲍廷博、吴骞对《金楼子》的整理[J].兰台世界,2012(12):3−4.
[9][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