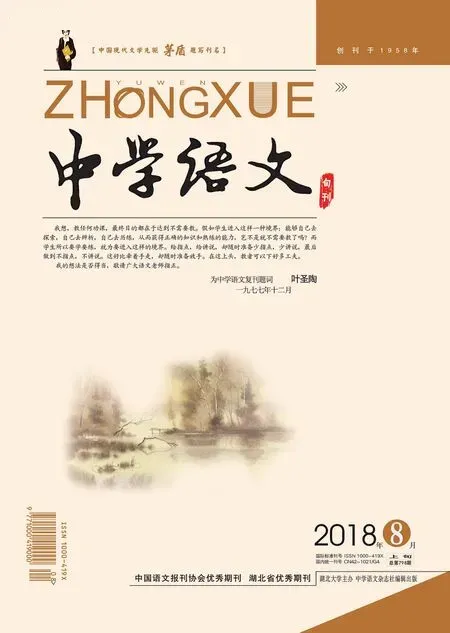知人论世:从文学意义生成到课堂教学建构
袁海锋
随着20世纪“文本中心”“读者中心”文学观的发展,特别是理论家罗兰·巴特宣告“作者已死”后,“作者中心”文学观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作者要素并没有、也不可能抽离于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文学力量,作者要素及其派生的“知人论世”观念对于文学意义的生成是毋庸置疑的。
“知人论世”最早由孟子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强调的是作者要素对文学接受的意义。事实上,“知人论世”存在更深刻的理解可能:在阅读观的“读者对于作者要素的了解”认识外,还有深化到创作观的必要——“作者/读者对自身外部世界的认知与主观世界的表达”。这种深化可以量化阅读中“知人论世”对文学意义生成的功能性价值,进而明确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存在依据。藉此合宜处置它的阅读教学效用,推进语文课堂教与学的各种可能,实现有益有效的课堂教学建构。
一、知人论世:观测文学意义的生成
所谓“知人论世”就是清晰“作者”存身的宏观时代背景与微观生活经历、创作的历史分期与文本风格、具体作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意图等。这里清晰的内容不仅关涉阅读行为的达成,也显示了“创作”的基本要素。因而“清晰”也应走出狭义的读者观,它既包含读者以“他者”身份对作者要素的返视与还原,更包含作者/读者瞬时语境下的自我审视与表达。打通这一阻隔,“知人论世”的理论力量,便可返溯作者创作,规束读者接受,由此观测整个文学意义生成的全貌。
1.作者维度与“知人论世”
文学创作不能凭空发生,它需要具体而微的触发,诱发作者的情感爆点,激发创作冲动。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他存身在与外部世界的时刻互动中;人是精神性的存在,外部世界变动不羁,必然与个体产生或顺或逆的关涉与交互,触发个体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礼记·乐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钟嵘《诗品序》)阐发的正是这种主客、内外、物我的交互关系,其中的“心动”“感人”便是文学需要的触发。作者“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诗品序》)“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大序》),运用个人的艺术造诣,完成作品由内而外、由精神到形式的原初生成。
启动文学发生的“心动”“感人”之物便是变动的外部世界,它可能是作者身处的宏观大时代,也可能是荣辱难测的个人小经历。外部世界与作者个体历时交互,影响着作者的性格特征、社会身份、写作风格等;与作者个体的瞬时交互,形成飘忽不定的个人生活,进而构成顺逆不一的具体背景性遭际及点状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物我交互中作者“知人论世”的艺术编码外化。它是作者对身处的外部世界历时状况的理性品评决断,涵盖天下治乱兴衰、时局由来去往、人事盛衰之道等;它是对个人瞬时生活遭际的真切体察,涉及人生顺逆、物我得失、人情冷暖、生老病死等生活节点的感性认知与幽微表达。
“知人论世”创作观从物我交互的视角解释文学发生,它为“知人论世”的阅读观提供了发生的可能。一方面,把文学理解为作者对外部客观世界与内部精神世界认知、品评,是他对作者本人的“知”与身处之世的“论”,读者才能穿越时空、超越个体差异返视还原激发原初创作的作者因素,以推动阅读的理解。另一方面,即使从非“作者中心”的文学观,承认文本、读者对文学意义的积极创造,作者的原初创作也是先发性、基础性的。它不能规定文学接受中具体点,却可以从先天的角度规束文学意义生成的方向与边界。这些,需要阅读观的“知人论世”来完成。
2.读者维度与“知人论世”
如果原初创作是文学的艺术编码,那么阅读就是读者对作品的艺术解码。非“作者中心”文学观认为,除了作者创作中原初意义生成,艺术解码也是文学意义的新创造,读者与作者一样都是意义生成者。
与作者在创作中生成文学意义不同,读者是在阅读中实现它的。读者作为存在的个人,无疑有对本人心性的“知”与身处之世的“论”——对内部精神世界的认知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品评。这可以理解为与创作观中作者“知人论世”遥相呼应的读者创作观“知人论世”。它是阅读的前提之一,也是文学意义再次生成的基础。读者带着这些当下“世界”认知进入文本,与作者创造的原初“世界”相遇,形成读者赋予的文学新意义。这与作者原初创作相似,差异在于阅读是非创作性创造。“非创作性”体现为阅读无须编码;“创造”体现为解码文本就是将读者“世界”认知与作者“世界”认知合宜而不冲突地融入文本,实现文学意义的二次生成。
如何“合宜而不冲突”的工作便需要阅读观的“知人论世”来打理。读者借助自我“世界”认知创造文学意义,不是不顾作者要素,不是肆无忌惮地改造,甚至铲除作者原初创建的文本意义走向和边界。这是孟子所谓的“说诗者……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如此原初意义尚且被戕害,更遑论新意义生成。读者必须以“他者”身份返视、还原文本的作者要素,并以这些作者要素规束读者“世界”认知的走向和边界。文本场域里,作者原初“世界”优先于读者当下“世界”。二者可以不相同,但底线是以作者原初“世界”走向边界为标的的不冲突。实现两个“世界”聚合大于单独“世界”的文本扩容,进而达到文学意义的新生。孟子“以意逆志”与此几乎是一致的。
阅读观的“知人论世”是指向作者要素的客观工作,它不肩负文学意义的生成,却是勾连作者、读者“知人论世”创作观的纽带。它既理清了作者原初创作的老底,又为读者意义创造廓清边界,指明方向。它可谓是文学意义的总军师——虽只运筹帷幄中,却能决胜千里外。这正是它的重要,“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但是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朱光潜所言甚是。
二、知人论世:建构有效的课堂教学
理清阅读观 “知人论世”(下文简称 “知人论世”)在文学意义生成中的地位,有助于它在阅读中角色的明确和效用的发挥。语文课堂教学,是教师组织学生围绕选文展开的文学接受活动。其本质是借助艺术解码,实现学生创造性把握文本意义的文学行为。学生是一类特殊的文学读者——无论是身体塑造还是心理建设,都处于未完成的不成熟状态,他们的人生经历有限,作者要素的百科知识掌握不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对“知人论世”的需求也就更急迫,课堂教学对它合理的运用也就更关键。
1.“知人论世”建构课堂教学要针对“这一篇”
教材由一篇篇选文构成,具体文本只是作者文学创作历程中的节点与剖面。构成作者因素的内容则是多元繁杂的,比如生平经历、性格特点、创作背景、创作风格、代表作品等。这些要素内部,如生平经历,又包含历时性与瞬时性的内容。“知人论世”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来建构有效的课堂教学,不是以量取胜的社会史与作家史的展示。它的有效性指向教材选文的“这一篇”,此时“知人论世”内容的选择也是指向文本的理解的,能帮助学生返视与还原“这一篇”原初文学意义的,能激发学生此时文本意义创造的,才是教与学需要,也才是“知人论世”应该包含呈现的。此正是“弱水三千”与“取饮一瓢”的关系。
以《梦游天姥吟留别》课堂教学为例。此诗是一首作于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的第二年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游仙诗,彼时李白将从东鲁南游吴越,故留诗作别。天宝元年,李白因道人好友吴筠帮助,借玉真公主之力被荐出任朝廷翰林学士。但在天宝三年,便因权贵排挤、同僚谗陷离开长安。此时李白正经历从锦绣庙堂到落寞江湖的滑落,内心波澜可想而知。教学中,如果让学生直接感受文本,无异于“盲人摸象”。此时还原出诗作的创作情境,无疑是为学生点亮一盏阅读明灯。但关于李白的作者要素是海量的,比如“诗仙”名头由来、神秘的异族血统、宫廷趣事杂闻等,都够噱头,有吸引力,但却很难指向选文的“这一篇”,也就难谈原初创作情境的还原,更别说教学有效性了。与“这一篇”有真实关联的是,李白从应诏入京到赐金放还的传奇仕途。教师以此为依托,再结合游仙诗的体裁形式,构建对诗作解读行之有效的作者要素。借助这些,学生才能“知”李白之人之世,“论”李白之诗之情。学生才有可能在梦境与现实、仙境与宫廷中找到理解的突破口,把握李白赋予诗作的原初意义,进而产生创造文学新意义的可能。
2.“知人论世”建构课堂教学要恰逢其时
“知人论世”何时出现在课堂,其中蕴含需要厘清的层级:一是它要不要出现在课堂教学;二是它具体出现在课堂教学的什么环节?
“知人论世”不是教学外在形式的需要,而是教学结构价值的呼唤。文学阅读的目的在于解读与延展文本意义,解读、延展的力量首先来自内部,也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创作观“知人论世”式意义生成。像《咏鹅》(骆宾王)《悯农》(李绅)之类作品,文本意义简明、普适,不需要借助作者因素,仅依托文本就能完成意义生成。此时“知人论世”之于课堂教学,便不是必需品。当作者原生意义解读,或读者创造意义延展陷入僵局时,“知人论世”才应运而生,勾连二者创造生机。可有可无看情况,这是它要“恰逢其时”的第一义。
因为不是教学外在形式的需要,课堂建构中也没有“知人论世”的固定出场时间。课堂教学中文本解读僵局出现的时段,需要作者要素为文本阅读助力的地方,就是“知人论世”现身教学现场之时。它可以作为文本解读的急先锋,出现在课堂教学之初,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教学开始阶段李白的创作背景介绍。它也可以出现在教学进程的中后段,由它深化对文本的深入思考,得出不同的文本意义解读,比如《秋天的怀念》课堂前半部分可以依托文本开展教学,到母亲病危那句“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处,提出教学问题:儿子是什么病,让母亲如此忧心;从女儿“未成年”又可以读出儿子什么信息。在问题讨论思考后,补充“史铁生21岁上山下乡时,双腿得病瘫痪,意志消沉”这样的作者要素,对于理解前文儿子的暴躁、期间母亲的忧虑、病危母亲的牵挂,进而把握全文的情感抒发,都有极大帮助。“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它要“恰逢其时”的第二义。
3.“知人论世”建构课堂教学的分治与通观
课堂教学的进程分为不同节点。不同的节点,有的可能形成阅读思维的僵局,有的可能是文本意义生成的热点,它们的教学又可能是前后分散的。面对这样的教学局面,就需要走出“知人论世”单点存在的思维局限。既然它能可有可无,前后不羁,自然也可以多点开花、分而治之。
教学节点归根还在文本,文本节点造成的不同阅读问题,“知人论世”在还原作者要素时必然有所选择、侧重,不必赘言。文本虽然表面有不同节点,但内部自有其统一的逻辑结构。在运用“知人论世”解决不同的阅读问题时,必须思考这些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而思考不同节点处需要的作者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在“知人论世”分而治之外,还要通篇以观。这样才能做到解决教学问题的同时,实现文本意义的最终生成。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教学中,游仙部分是一处教学难点,可以通过补充李白从应诏入京到赐金放还的仕途经历,引导学生认识梦境与现实、入仕与归隐的关系,这可以实现对文本思路的大体了解。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处,可以提出这样的教学问题:既然已经“且放白鹿”了,又为何“须行即骑”,引导学生思考“名山”的真正含义。此时补充“李白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受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延请,入幕为僚”的材料,展示这一时期《永王东巡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等作品。通过与前出背景资料的对比通观,学生便可隐约读出文本深处的难言之隐和李白身上强烈的仕隐纠结,感受李白的内心失落与不甘。
文学是复杂的,语文的课堂教学更是难的。还好,有“知人论世”这款武器。它让我们更加清晰文学意义生成的内部机制,同时又找到了阅读观的“知人论世”这样的外部手段,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建构上,可以有法可依、有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