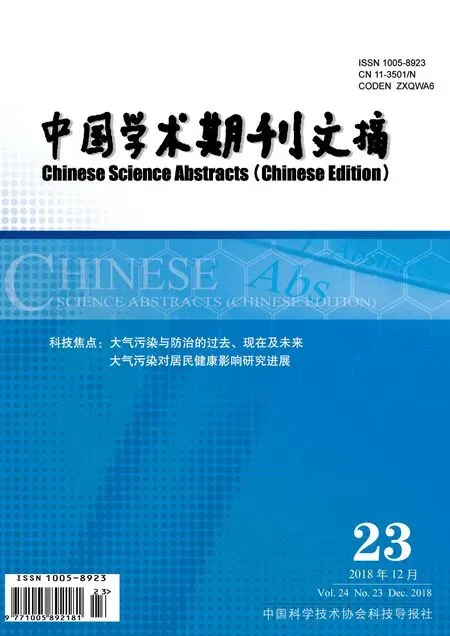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研究进展
秦耀辰 谢志祥 李阳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相继发生比利时马斯河谷、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英国伦敦烟雾和日本四日哮喘病等骇人听闻的大气污染事件,这不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吞噬着居民的健康与生命。面对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英、美、法、日等国纷纷采取优化产业结构、革新生产工艺、提升能源效率、推广清洁能源及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来防治大气污染,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空气质量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说明大气污染与人类活动关系极为密切,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步发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但由此也付出惨痛的环境代价,具体表现为以霾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事件发生频率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和危害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统计公报》指出,2013年中国平均霾日数约为35.9 d,达到1961年来的最高峰;雾-霾灾害风险热点区范围囊括96个城市,占据国土面积92.4万km2,波及人群数量高达5.9亿;北京市仅PM2.5污染就造成2万多人死亡,100余万人患病,引发经济损失约9亿元。
学术界关注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由来已久,但是由于知识和学科背景的差异,致使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开展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Ridker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估算出1958年美国因大气污染诱发的健康经济损失约为802亿美元,成为定量评估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的开端。随着研究的深入,从流行病学视角出发开展的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研究亦呈增多趋势,Dockery等通过追踪美国6个城市PM2.5浓度与8000名被调查人群的健康变化状况,发现PM2.5浓度最高城市的人口死亡率大约是浓度最低城市的 1.26倍。Seethaler等采用支付意愿法评估 1996年欧洲奥地利、法国和瑞典PM10污染引发的健康损失,得出健康损失的经济价值约为 270亿欧元,占据同年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7%。Katanoda等采用队列研究方法着重探究日本分项大气污染物对63520位居民的健康影响,揭示出PM2.5、SO2和NO2浓度增加均会导致居民死于肺癌和呼吸系统疾病人数的显著上升。Dan等基于加拿大空气污染物浓度和居民死亡数据探寻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健康危害,发现众多大气污染物之中O3造成的居民死亡风险最高,而NO2的死亡风险最低。流行病研究案例的增多为Meta方法的应用奠定坚实基础,Aunan等基于搜集到的42篇文献成果,借助Meta方法探寻中国PM10和SO2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PM10和SO2浓度每增加1 μg·m-3,人口死亡率分别上升0.03%和0.04%。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开始较晚,过孝民等依据1985年中国 SO2浓度和居民健康数据,采用修正人力资本法揭示出其造成的健康损失价值为37.64亿元。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的研究表现出数量上不断增多、方法上持续改进和深度上广为拓展的特征。陈仁杰等评价 2006年中国 113个城市 PM10污染的健康危害,发现PM10引发29.97万人早逝、25.49万人住院。Song等探寻 PM2.5对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发现 2013年中国 PM2.5污染造成 14.98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44.60万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此外,也有学者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判定不同大气污染物胁迫下暴露人群数量,为核算居民健康损失提供新的视角,但该方法总体较为粗略。归纳来看,当前研究集中在宏观区域层面健康损失核算和微观个体层面健康损失差异两个方面。为此,本文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归纳评述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推进大气污染健康损失核算提供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
1 研究内容
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毒性作用机制极为复杂,主要表现为长期慢性和短期急性效应两种形式。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效应,大气中的毒害物质主要通过破坏人体呼吸、免疫和血液循环系统等诱发致病或致死症状,进而造成健康或经济损失。目前公认的大气污染物致病效应主要表现在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方面,致死效应则主要表现在总死亡、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等方面。鉴于慢性效应与急性效应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分界限,不同学者对此认知差异较大。为此,可将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划分为宏观区域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两大部分。
1.1 宏观区域层面
宏观区域层面的研究聚焦在居民健康损失核算、健康损失的经济代价评估以及控制大气污染的健康收益等方面,实质上强调人体对大气污染做出的被动响应,优点在于能从全局把握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缺点在于这是以不考虑个体特性差异为前提的。
居民健康损失核算方面,目前主要是依据流行病学理论方法,通过追踪大气污染物和样本人群的健康变化状况,以此确定两者之间的暴露响应系数,在此基础上推算特定区域居民遭受的健康损失量。下面将从大气污染物类别、健康终端选取和暴露响应系数确定 3个方面展开阐述。从大气污染物类别来看,学者们最初关注SO2的健康危害,随后逐渐转移到NO2和PM10上来,随着霾成为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学者们意识到 PM2.5和 O3的健康危害更大,研究的兴趣点也转移到PM2.5和O3对居民健康影响方面。健康终端选取方面,最初研究主要探讨大气污染物与死亡率的变化关系,随着流行病研究案例的增多,研究大气污染物和分项健康终端对应的死亡或发病关系成为主流。暴露响应系数确定是核算居民健康损失的关键,也是开展健康损失价值评估及不同污染物控制情景下潜在健康收益分析的前提。从中发现,早期暴露响应系数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流行病实证研究,随着研究案例的增多,使得Met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求取案例区以外的暴露响应系数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流行病研究案例匮乏,导致国内研究多基于国外流行病案例,采用Meta方法求取大气污染物与特定健康终端之间的暴露响应系数。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产业结构、能源构成和环保投入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中国大气污染也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依据国外案例求取的暴露响应系数存在着不确定性。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从统计学视角出发研究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对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得出大气污染造成中国北方地区居民预期寿命比南方地区缩短5.5 a的结论。
健康损失的经济代价评估是指对大气污染物引发的健康损失量进行货币估计,以便能够直观认知大气污染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损失的直接和间接经济代价评估这 2个方面。其中,直接经济代价是指大气污染造成居民自身直接经济损失,包括早逝经济损失、治病费用支出以及误工收入损失。间接经济代价则是指大气污染诱发劳动力供应和医疗支出费用变化而对宏观国民经济产生的冲击。直接经济代价评估通常可分为以下步骤:首先根据暴露响应系数核算特定健康终端对应的损失量,其次,借助人力资本法(HCA)、支付意愿法(WTP)和疾病成本法(COI)等对居民健康损失量进行货币估计。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通常借助 HCA或 WTP法计算早逝经济损失,采用COI法计算治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因治病而造成的误工损失通常也采用HCA法计算。其中,住院费用支出由对应健康终端单位人次平均诊疗费用乘以平均住院天数求得,门诊治疗费用由对应健康终端单位人次诊疗费用乘以门诊总人数求得;因治病造成的误工损失则采用不同健康终端发病对应的平均住院天数乘以每天的人均 GDP。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产业间的关联性特征又决定着发病与死亡人群变化最终会反馈到宏观经济层面。间接经济代价评估主要包括3个步骤,除前2个步骤与直接经济代价评估完全相同外,间接经济代价评估还需依据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模型(I-O)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将大气污染物造成的劳动力和医疗费用变化数据等带入,以此估算大气污染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
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潜在健康收益方面,众多国家或组织纷纷意识到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于是出台或修订更为严格的空气质量控制标准。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也开展不同污染物浓度控制情景下居民健康收益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同地区模拟结果相差甚大,但毫无疑问均证实削减大气污染物能够带来巨大的健康收益。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借鉴健康损失经济代价评估的思路,采用货币化手段量化削减大气污染的健康收益,同样说明削减大气污染物可以获得极大的经济收益。以上开展的健康收益分析大多是基于不同国家或组织的空气质量控制标准为前提的,强调的是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假定被控制或削减到同一浓度水平下的理想化状态,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能源构成及环保投入等因素千差万别,导致不同地区削减大气污染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如若采用统一的污染物浓度控制标准,势必造成污染重灾区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导致“污染天堂假说”情形的出现。有鉴于此,部分学者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大气污染物削减分配方面,强调削减分配过程应在满足区域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确定区域内部单元的浓度控制目标,提出不同原则导向下的大气污染物削减分配方案。
1.2 微观个体层面
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认为应从人的生理差异、行为偏好、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属性出发,着重探讨大气污染胁迫下居民个体遭受的健康损失差异,更多强调的是居民个体具备主动降低或缓解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能力。
暴露于大气污染状态下的居民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大气污染给健康带来的袭扰,但是由于以下因素的差异,导致居民个体抵御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一是个体生理差异,包括种族、性别和年龄等。美国心脏协会研究证实黑人比其他种族的人群更多暴露于大气污染,大气中的毒素会导致黑人患心脏病的风险比白人高出25%。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中国每10万人中就有161人死于大气污染,且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另外,还有学者发现老人和儿童是易受大气污染危害的脆弱人群,其中老人构成了心血管疾病早逝的主要人群,而儿童则构成呼吸系统疾病早逝的主要群体。二是居民行为偏好,包括职业选择、出行方式、锻炼习惯、饮食搭配和健康意识等。职业选择与居民室内外活动时长紧密相关,2011年WHO发布的《室内空气污染与健康》指出,室内空气污染高出室外5~10倍,每年全球有约200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死于室外空气污染的人数在 130万左右。孙斌栋等认为出行方式由私人机动车向公交系统、体力型交通转变有助于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并据此提出改善社区设施可达性和减少居民个体机动化出行的建议。吴丹等对比南京市不同交通工具内部的颗粒物浓度,发现乘坐地铁遭受的空气污染程度显著低于乘坐私家车和出租车。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出行方式对健康的作用会随空气质量变化而变化,当空气质量状况较好时,步行或骑行带来的健康收益要优于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当空气质量状况较差时,情况则恰好相反。此外,具有锻炼习惯或注重膳食搭配的人群往往体质较好,因而抵御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能力较强。健康意识也关系着居民防范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能力,具有健康防护意识的居民可通过乘坐地铁、佩戴口罩及使用空气净化装置等降低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三是自然条件差异,包括大气污染物浓度、气象条件、地形因素和地表覆被等。Cuijpers等研究夏季烟雾暴露对儿童呼吸系统的急性影响,发现污染越严重地区儿童患过敏性病症的机率越高。气象条件在大气污染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温度、风速、日照、气压和降水等均会对大气污染起加剧或缓解作用。周亮等分析了 2001—2011年中国 PM2.5的时空演化特征,发现PM2.5污染严重区域集中在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明显的低地平原指向性特征。另外,还有研究表明植物能够削减大气污染物浓度,所以植被覆盖较高地区的大气污染程度往往低于植被覆盖较低的区域。四是社会经济水平,反映在居住环境、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居住环境包括土地利用混合度、距公交或地铁站点距离及社区绿化状况等,这些因素关系着居民出行、娱乐和休闲方式的选择,最终会反馈到个体健康层面。收入水平决定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高收入人群减少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支付意愿要强于中低收入人群。教育水平影响个体认知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能力,高学历人群大多具有较强的防范意识,因而遭受的健康损失相对较小。医疗条件对改善大气污染诱发的致病或致死效应具有重要作用,配套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广大人群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接受医疗救助成为可能,所以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也会影响居民个体遭受的健康损失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开展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研究的前提在于获取大气污染物浓度和特定健康终端对应的发病与死亡数据。大气污染物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空气质量实测数据,这类数据通常比较权威且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已相当完善,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时序过短、站点设置不合理、部分监测指标缺失及数据可获取性差等问题,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评价结果。二是研究机构公布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这类数据多是由学者结合地面监测站点数据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对卫星遥感影像进行校正,推算缺失年份或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浓度。该类数据优点在于有效解决部分年份或地区的数据缺失问题,为研究长时序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提供了可能,缺点在于受云层反射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的数据精度偏低。三是个人实测获取的污染物数据,这类数据利于精准反映微观尺度的污染物变化,缺点则在于获取数据的成本较高且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健康终端数据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如人口普查资料、卫生统计年鉴和疾病监测资料等,该类数据适用于研究宏观区域层面居民的健康变化状况。二是WHO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GBD),该报告详细提供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死亡与发病成因,与政府部门的数据相比,该数据覆盖面大,内容翔实,标准相对统一。三是医院调研获取的健康数据。较前两类数据而言,这类数据通常获取难度较大,样本容量偏小。此外,评估健康损失的经济代价时还需用到以下数据:一是统计数据,如投入产出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诊疗费用和住院日数等;二是调研数据,如居民为减轻大气污染健康危害的支付愿意等。
2.2 主要研究方法
早期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定性方法为主,重点在于探讨大气污染致病或致死效应的生物学机制。随着学科融合水平的提升,定量测度大气污染的健康及经济损失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确定暴露响应系数时,经常用到的是Meta分析和流行病研究方法。测算居民健康损失量时常用Poisson回归模型,但对于污染物安全阈值的设定尚无统一标准。评估健康损失的直接经济代价时,COI主要被用于求取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WTP和HCA则用来评估居民早逝和误工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有学者认为 WTP是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因此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存在着主观随意性;而采用HCA评估早逝或误工的经济损失时存在着伦理学缺陷,因此有学者主张采用修正的人力资本法进行估算。评估健康损失的间接经济代价时,常以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为依据,采用I-O或CGE模型将劳动力供应和医疗支出费用变化等数据带入模型,以此估算大气污染对宏观国民经济产生的冲击。大气污染物削减分配方面,用到的有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环境基尼系数等。归纳来看,这些方法均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和特定适用范围,不同方法的灵活组合极大丰富着大气污染健康效应方面的研究内容。另外,运用这些方法评估大气污染的健康和经济损失时,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能够对现存结果起印证作用,有的则与之相反,这主要是由研究区域选取、大气污染物类型、健康终端选择和阈值标准设定等因素造成的。
3 存在问题
(1)关注单一类型大气污染物的健康危害,缺乏同时考虑多种大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随着城市化推进、机动车普及和能源消耗量增长,复合型大气污染特征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居民往往同时受到多种大气污染物困扰,大气中的SO2、NOx、O3及颗粒物等均会给居民带来健康危害,因此在评价单一类型大气污染物诱发居民健康损失的过程中存在着忽略其它类型大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交叉影响的缺陷,而这会错估某些特定类型大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2)宏观区域层面研究集中在单一城市层面,微观个体层面研究以定性为主且发展滞后。众所周知,大气污染具有极强的空间传输特性,因此开展大的区域范围内不同城市健康损失差异研究对于明晰大气污染危害、识别暴露人群分布及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宏观区域层面强调居民对大气污染危害的被动响应不同,基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居民健康损失差异有助于针对特定群体(妇女、儿童、老年人和高收入群体等)定制个性化防范策略。
(3)较多聚焦大气污染诱发的健康及经济损失,对大气污染物的削减调控研究重视不够。定量评估大气污染胁迫下居民遭受健康或经济损失的目的在于为政府部门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科学依据,而污染物削减分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然而,现有研究仍大量集中在居民健康及经济损失核算方面,少有的大气污染物削减调控研究亦是围绕区域内部单元污染物浓度被削减到同一理想水平而展开的,这在不同程度上弱化着研究结果的应用性。
(4)数据可得性、阈值参数设置和健康终端选取等也会造成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内流行病实证研究案例匮乏,直接借鉴国外暴露响应系数结果会导致健康损失核算产生偏差。采用泊松回归模型测度居民健康损失量时需要确定污染物安全阈值,事实上,不仅不同类型大气污染物安全阈值不同,即便同类型污染物也无相同阈值标准,而这会影响最终评价结果。考察大气污染健康危害时多从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等入手,存在着忽略其它健康终端的缺陷。
4 未来展望
(1)加强国内不同类型大气污染物与居民特定健康终端的流行病案例研究。流行病案例研究是目前确定暴露响应系数相对较为科学的方法,它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不同类型大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造成的交叉影响,也是顺利进行多种大气污染物健康效应评估的前提。由于中国流行病案例匮乏,致使现有研究多采用元分析或统计回归方法求取暴露响应系数,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大气污染方面的差异制约着国外流行病研究案例的普适性,因此未来应积极开展国内流行病案例研究。
(2)更加注重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体层面健康损失差异研究的定量融合。长期以来,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体层面居民健康损失差异研究割裂现象明显,但两者对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和卫生健康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遥感数据、站点数据、调研数据和居民健康终端数据可获取性增强,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涌现,初步具备在大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特定居民群体遭受健康损失差异研究的基本条件,这有助于探寻居民健康损失的地域分异规律,深刻揭示其驱动作用机制。
(3)聚焦居民健康视角下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削减调控研究。大气污染极大危害着人群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国家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未来研究应立足于居民健康损失核算的基础上,将居民健康与大气污染物削减调控结合起来,提出健康收益视角导向下区域内部单元因地制宜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削减调控目标,这不仅能够给区域带来较大的健康和经济收益,而且也能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进而减轻大气污染诱发的健康及经济损失。
(4)重视大气污染物和居民健康终端数据库建设。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同时存在长短期效应,鉴于国内大气污染监测数据时序过短,所以建立长时序大气污染物数据库不仅是进行长短期健康效应评估的前提,而且也为综合评价多种大气污染物的健康损失奠定基础。另外,政府和相关组织公布的居民健康终端数据多是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的,忽略居民健康损失量的年内变化特征,这给大气污染的急性健康效应评估带来巨大障碍,因此建立精细化的居民健康终端数据也刻不容缓。
(《环境科学》2019年(网络优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