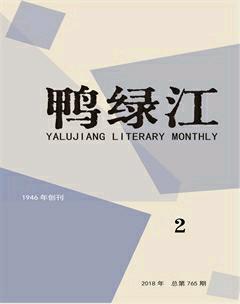复印者
[美]+依兰·斯塔文斯++译者+史国强
鲁宾·斯塔夫洛维奇犯案后,听说的人大感意外,纽约那些小报把他称为复印者,《哈泼斯》杂志又强调了这一称谓,但我与此案关联太小:不过是十五分钟的对话,不幸的是,我连这对话的内容也记不大清了。
最先听说他的名字,是在福科希复印社,这家复印社不大,旁边是一座战前的老建筑,我在曼哈顿的大好时光,有一部分就是在那幢建筑里度过的。复印社老板默瑞斯,五十几岁,为人大方,遇到客人光顾,他总是以礼相待,从不装腔作势,如此为人,在纽约城里实在稀罕。
我几乎天天光顾复印社,因为我有材料要按时复印按时发送,我可不希望把复印设备请进家来,所以只好花点儿复印费请默瑞斯代劳。
他总是张开双臂迎接我的到来,若是时间允许,还能在复印机后面的写字台旁和我聊上几句。我们的话题或是扬基队的比赛或是一周来纽约发生的丑闻,之后再为我复印材料,仿佛那些材料是他自己的。他读过我发在杂志上的文章,所以以我为荣,还把我视为他所谓“显要客户”里的一员。“你早晚能让我出名。”这句话他总挂在嘴上。
一次闲聊我大胆地问默瑞斯,来这里的客户,还有他们复印的材料,难道他对这些不好奇吗?
“为什么要好奇呢?”他马上答道,然后又改嘴说:“你真想让我回答你吗?请跟我来。”我随他走进后屋,里面有一个硕大的橱柜,默瑞斯顺手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复印纸,摆放得有些零乱。
他说:“布鲁克林有位老教师喜欢用生字。我买下复印社以后,想起了他用的一个字:paralipomena,大意是‘价值不大的东西。橱柜里正是顾客遗忘或丢弃的东西。”眼前的景象使我想起了犹太教堂约柜后面存放祈祷册的地方。不用的犹太书籍不能乱扔,因为里面可能印着上帝二字,生怕落入坏人手里被他亵渎,所以那些书要妥善保管才行,等到实在存不下了,才让长者埋到后院。
我说:“这里很像犹太人存废书的地方。”
他说:“唯一不同的是,有家公司每三个月过来一次,把东西收走。我希望废纸能循环使用,不然于心不忍。”
我翻了翻这堆复印纸。
他说:“垃圾,真的。上面印的几乎都是英语,唯独斯塔夫洛维奇先生留下的不是英语。”他说着,用手一指下面的纸堆。我仔细一看,发现纸上印的大概是古闪族语。
默瑞斯不喜歡谈论他的顾客,但所有的纽约人无一不是大大咧咧的,默瑞斯也不例外。他告诉我,鲁宾·斯塔夫洛维奇先生——根据我的记忆,默瑞斯第一次说出了对方的全名——很少说话。斯塔夫洛维奇中等身材,生得敦实,身着黑西装、白衬衫,一双乌光软皮鞋,无拘无束的胡子,一顶亨弗瑞·伯格特款式的礼帽。默瑞斯又说:“他隔两三周就来一次,手里拎个医生用的黑袋子,一般是要闭店时才来,晚上六点左右。他一个人占上一台复印机,然后从袋子里轻轻取出一册旧书,连续复印二三十分钟,之后把书放回袋子,将复印件装入一个塑料袋,结账后离开。怎么来的,怎么离开:闲话一句没有。”
我记得那天和默瑞斯还聊了些其他话题,但唯一吸引我想象力的却是斯塔夫洛维奇。默瑞斯接着说道:“要知道,在一旁看他复印,这是件奇妙的事。他复印东西,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一页纸也不浪费。不过,等他复印完了,总要从里面取出一张——就一张——然后扔掉。至于他的用意嘛,我也不知道。我又不好问他。但我出于同情,把他不要的纸都留了下来。”
我取出了橱柜里纸堆上的第一张。“这张纸给我行吗?”
“没问题。”他说。
我回去后,那天夜里一个人破解纸上的文字。我发现那是用拉丁文翻译的《困惑指南》,作者麦蒙尼德。
不久之后,我在百老汇遇见了斯塔夫洛维奇。默瑞斯对他的描述入木三分。要不是那顶帽子,斯塔夫洛维奇并没有特别之处,这正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模样:刻板的犹太人,特点并不鲜明,与迪兰希大街上的其他犹太人没有两样。他步履匆匆,神经兮兮的,右侧腋下夹着个塑料袋。我情不自禁地跟在他身后。他朝96街的地铁站走去,然后又继续走过几十个街区,最后来到犹太神学院的门外。他走进一道大铁门,不见了。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他出来之后继续朝城里走,这一次的方向是哥伦布大道,然后消失在一栋公寓楼里再也没出来。“他一定住在里面。”我对自己说。我真希望与他见上一面。他神秘的身份让我感到着迷:他结婚了吗?他独自生活吗?他以什么为生?他为什么执着地复印旧书?
等我再次遇到默瑞斯的时候,我把跟踪斯塔夫洛维奇的事告诉了他。默瑞斯说:“我感到愧疚,你要找的人未必有灵魂。”
一个月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完一天的课,从校园出来时,与斯塔夫洛维奇进行了一次十五分钟的对话。他正要走进116大街的地铁站。我们二人碰巧一同朝下走。我转身与他打招呼,佯装意外邂逅。“我见过你,不是吗?你是不是福克希复印社的顾客?”
他的回答闪烁其词。“是吗,不见得。我对街坊不感兴趣……怎么?你在复印社里见过我?”
我马上就听出了他的拉美口音。后来报纸,尤其是电视台,也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你是从阿根廷来的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
“我自己也是墨西哥的犹太人。”
“是吗?我不知道这边还有。或者……”
斯塔夫洛维奇显然是要摆脱我,从身上取出一张月票,从十字门走了进去。我没有月票,只好排队。还好,我在站台又找到了他。他站在站台的另一端。地铁慢慢入站。我走过去继续搭讪。“我发现你在复印旧书……”
“你怎么知道?”
当时我们到底都说了什么,对此我已记不大清。但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斯塔夫洛维奇向我解说他所有的神学观点,等他被捕之后,他又对不同的记者解释了这些观点。我记得脑海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不少想法。我们生存的世界,或者往好里说,我们被迫生存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丢了原著的复制品。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的,不过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他还说,我们被偶然性所左右,上帝是个疯子,对纯粹的东西不感兴趣。endprint
我记得还问他为什么来曼哈顿,他回答说:“这里是20世纪的首都,犹太人的记忆就存放在这里。但存放的方式令人烦恼,没有人性,要马上改正才行……” “不人性”三个字使我颇感意外。斯塔夫洛维奇显然是要强调这三个字,似乎他希望我牢牢记住其中的含义。
他最后说:“我有个使命:一部著作要表达上帝不可改变的意志,在这部作品里,我要扮演代言人的角色。”
我问道:“你住在上西区?那天我在犹太研究院看见你了。”
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耐烦了,开始嚷嚷道:“我不和你说话……别来烦我。我没话说,没话说。”
我退了一下,碰巧赶上火车进站。等我上车后,发现斯塔夫洛维奇转身朝出站口走去。
一周之后,小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标题:《复印出来的噩梦》《复印者:不折不扣的贼》,《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发斯塔夫洛维奇的丑闻。他被警察抓走,罪名是不停地盗窃并损毁犹太人的绝版著作。
显然,他通过极为聪明的技巧盗取了三百册左右世间少见的作品,其中有几版巴希亚的《心灵上的义务》《巴比伦-塔木德》、阿姆斯特丹出版斯賓诺莎亲笔签名的《神学政治论》、埃及印刷的插图版《哈加达》,无一不是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苏瓦等名校的私人藏品。最初记者报道说,他占有这些犹太文物的唯一目的是,以最戏剧性的方式销毁它们:黎明时分在河边的垃圾箱里烧掉。还好,他是在复印之后才下手的。引用一名警官的话说:“斯塔夫洛维奇是个复印狂。他就崇拜复制品。”
他的个人经历渐渐浮出水面。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正统的环境里长大。他被捕时,父亲是耶路撒冷有名的拉比,他总是与父亲发生龃龉,争论上帝的性质和犹太人在俗世里的角色。少年时代的斯塔夫洛维奇确信,非正统机构拥有犹太典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他并不想为那些典籍搬家,他要通过精心安排,制造混乱,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他80年代初在布鲁克林的一次骚乱中明白的道理。监狱的心理学家说:“在他那里,无序才是秩序。其实他早就与正统的犹太人脱钩了,这不免令人感到滑稽。他确信,上帝并没有真正统治宇宙,上帝允许宇宙万物自由运转。模仿神祇的人类应该复制这一方式。”
警察搜查他在哥伦布大道的公寓后发现了不少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复印的材料。箱子上既没有写名,也没有编号,就那么扔在那里,但里面的复印件并没混乱。斯塔夫洛维奇一案就版权和图书馆借阅制度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正统犹太人的敌视,因为他们拒绝走入现代。
等公众的关注稍稍消退之后,我又在复印社里见到了默瑞斯。他告诉我:“这么大一个案子,但警察没来找我。我猜测,斯塔夫洛维奇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一定还找了其他的复印社。他公寓里的三百册图书,我见到的不超过十二册。”
我和默瑞斯继续谈论他这位最著名的顾客,但这件事我越想越不明白。我能想象出关在牢房里的斯塔夫洛维奇,他独自一人,但又并不孤独,不知道他对这些复印后的典籍都做了什么。
数月之后,等《哈泼斯》文章出来之后,一幅完整的画面才变得清晰起来,至少在我的眼里是如此。文章作者几次在狱中独家采访斯塔夫洛维奇,提到一些他不为人知的经历,如,他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与纽约的关系等。斯塔夫洛维奇告诉采访者:“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憎恨正统的犹太教育。教育内容无一不是派生出来的。说西班牙语的拉美人都是模仿者,模仿欧洲,模仿美国,但总也赶不上人家……”他还就纽约发表了一番评论:
母亲死后,我靠她的遗产维持生活。我总以为这座城离上帝最近,不是因为这里纯粹——显然这里并不纯粹——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座大都市要复印这么多东西。曼哈顿一天复印的纸张不计其数。不过,其他的东西也都是模仿品——建筑、艺术、文学,虽然表面上挺风光。纽约与拉丁美洲不同,纽约不用模仿别人。纽约就模仿自己。这才是原创性的所在。
文章的最后,作者请斯塔夫洛维奇开诚布公地说出他的“使命”,我读到这里才想起,那次在地铁站斯塔夫洛维奇不是对我反复强调他的“使命”嘛。
斯塔夫洛维奇自言自语地问道:“我公寓里的复印件都少点东西,警察发现没有?每册书里都少了一张复印纸,他们检查没有……?”
“你把那一页扔掉了?”对方问。
“当然是我扔的。我要在身后留下一个更清晰、更令人信服的宇宙,我要完成这个使命,但总也没法完成。”
“那些复印件哪儿去啦?”
“呃,这才是秘密所在……要创造一部大作,如实反映上帝不可更改的意志,这卷书要偶然拼成,内容取自其他书籍,在编辑的过程中,我要担当使者,这是我的梦想。但这个使命怎么也没法完成,所以在我光顾复印社之后,就把抽取出来的页码扔进了垃圾桶。”
读到这里我马上想起默瑞斯后屋的橱柜,还有斯塔夫洛维奇的使命:他的目的不是复制,是创造。我匆匆赶到默瑞斯的复印社,他是精明的人,必定不忍扔掉那些复印过的书页。原来那一张还在我手上,但我希望把手放在其他复印件上,十万火急!研究这些材料,研究斯塔夫洛维奇津津乐道的混乱。我自言自语:“这是他给我留下的遗产。”
默瑞斯不在店里,他的助手说,几天之前废物回收公司来过,把后屋橱柜里的废纸收走了。
作者简介:
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美国安姆赫斯特学院拉美文化教授、诗人、小说家,曾出版《借来的文字》《编字典的日子》《西班牙语环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等作品,能用英语、西班牙语、意第绪语写作,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最大胆的批评家,最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学者和作家”。
译者简介:
史国强,山东莱州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中心教授,出版《喜福会》《赛珍珠》《格利弗游记》《上帝知道》《布什自传》《普京自述》《简·方达回忆录》《灼痕》《暮光地带》《时光倒流》《塞林格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 》和《对话潘基文》等多部译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