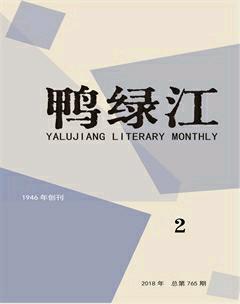理论何去何从
唐诗人
1
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时,她说:“我们给予别人怎样去读书的指点,就是不要听从什么指点。”①
她以这话开始,建议撇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批评家等中间人/因素,可是如托尔斯泰批评评论家却自己也写评论一般,悖论也出现在伍尔夫身上,她写了一本《普通读者》之外还觉得不够,继续写《普通读者∏》。这些作家式的评论难道不是中间因素吗?冒充普通读者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吗?她批评各种中间因素,但自己却成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中间因素,这不是作为普通读者来充当中间因素的,而是作为作家和评论者来充当的。作家和评论者同样可能是远离文学文本的干扰因素,是妨碍读者自由感知文本的“杂质”——但它们真的是杂质吗?
在经历20世纪的文学、文化理论磨炼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感知可谓深入骨髓了,批评从各个角度进入文学文本的血肉,或者文学文本的血肉通过皮肤表层的各种元素向各个角度敞开。比如对于《哈姆莱特》这部莎剧,我们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分析文本中真的觉着了什么趣味吗?即使有,这种剖析是理论的还是文学的呢?当然我们可能难以区分是理论的还是文学的,就像难以把赫什的含义与意义进行区分一样,也许在理论家看来,正是因为这部文学文本具有这样的含义,才会做这些意义的解析、演绎。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阅读文学文本的乐趣和阅读理论文本的乐趣并不是一样的。“乐趣”怎么区分呢?对于文学文本,也许我们可以从场面的渲染、从人物的性格变化、从对话的进展以及各种故事来获取乐趣;对于理论文本,乐趣在于发现意义方面,发现了一种理解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看到了这部文学文本的另一番含义,这是发现的乐趣,而不一定是阅读的乐趣。由此,是不是需要一种思考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之间关系的理论呢?这类理论当然也是汗牛充栋了,批评在评论着文学也在评论着自身,它们展示阐释也展示关系。它们展示的关系于当今已呈现了一种被普遍批评的现象:理论压制了文学,文学感知被各种理论扼得毫无生机。
把理论看作恶魔,或者相反把它看作救世主,这些一刀切式的观点在我看来都是不明智的。视作恶魔的指责可能过于哗众取宠,但哗众取宠也往往是因为出现了问题才能被“哗”或者“宠”出来。理论对于文学感知的束缚主要表现在许多批评文本内理论套文本的现代八股论文中,它们不仅仅把文学的趣味抛弃了,也把自己美好的审美感知细胞给遗忘了,看到的只是某种理论的架子,把这架子拿来框文学文本也把自己框住了,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人性化,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文学和理论都成了僵尸,自然要被抛弃。当然,抛弃的是僵尸,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鲜活的生命依然存在,像幽灵一般不可能被轻易扔弃。就像德里达所言的马克思精神,马克思像幽灵般存在于当代世界,他的精神依然存活于现代社会。因此,对于理论,需要的依然是理智,或者借鉴钱穆先生对历史学习的看法,需要的是历史的智识,而不应局限于材料和知识,理论也要有智性成分,在理智中处理文学与理论的关系。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并不认为之后就意味着可以抛开理论,相反,他认为我们还生活在理论的影子底下,各种理论都在影响着我们,理论几乎成了不是我们想离开就能离开的事物。我们先认可伊格尔顿的这个观念的话,那么我们能够满足于被影子遮着吗?或者我们能够不去认识影子本身而居安不思危吗?或者,如果我们不认可伊格尔顿的说法,只相信理论确实过时了,可以不需要它了。可是,这些观念从哪里来的呢?言说这些观念的人士是居于何种位置去言说的?在这样的分析下,我以为作为学科研究者,轻信任何时髦说法都不可取,相反,研究者甚至需要用心去研究这些争议颇多的理论,根据各自的研究和思考去悟出相应的心得。因此,重新思考理论问题也可以成为一个话题。
2
文学与理论有什么关系吗?这个问题不是谈论文学理论问题,而是询问我们如何处理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关系问题。20世纪以来,甚至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文学已经离不开理论了。这不仅仅是文学研究方面的离不开,而且是文学创作方面的不可忽略。至今,依然有很多人认可这样一个观念,即文学创作跟那些理论是无关的。认为作家写作要是跟着理论走肯定写不好,认为理论是在大量的文学文本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必须承认这在很早以前确实如此,但是20世纪以来,继续持有这种观念是片面的。
先不说叙事理论对于现代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就讲那些看似与文学形式方面无关的纯理论问题,比如福柯的权力观以及相关的很多后现代思想,它们已经在无形中渗入了活跃的作家作品中,这是塑造现代人思维方式的思想资源,因此它们不是被硬生生地使用,而是吸收之后的转化。这种转化我觉得是可以存在的,并不能借此判断这个作家的创作缺少自己的发现。比如,我们当代著名的作家格非,先锋倾向异常明显,后来的《春尽江南》等小说都有颇多细节以及描述性段落有明显的哲学因子,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则更为浓重,还有王小波、莫言,这些人的作品背后都很容易看到时代思想的影子。而这些思想又并不是他们自创的,而是学来的。如果我们熟悉中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各路哲学思想的话,会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自然而然地想到哪处哪处有什么思想,等等。当然,他们把思想转化到文学文本里面,转化得灵巧而恰切,这些也暗示了作家的写作功底。外国作家比如戴维·洛奇、威廉·福克纳甚至于伊塔洛·卡尔维诺,当代思想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实践。
可是,文学创作对思想的吸收是转换了形态的,那么文学研究呢?文学研究如何处理文学文本与理论的关系?如前面提及的,理论可以提供角度、发现更多层面的意义等。这毋庸置疑,但这些角度如何处理?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每个角度都可以是一套理论。但是这样的套法解释真的有价值吗?而且,在我们将理论一个一个地认识完之后,很多理论体系其实是相悖反的。遇到这些情况如何是好?角度可以多,分析理解也可以多,也就是说初步的作品评论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文本所呈现的意义世界真的需要用那么多的理论视角去挖掘吗?这样挖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在?文學研究如果仅仅靠着许多理论方法的力度去试探,那么文学文本是被凌虐还是被抬高为张力丰富的意义世界呢?也就是如葛教授所言的这双刃剑该怎么处理。对此,无论做什么判断来区分孰对孰错都是片面的。它没有答案。因此,思考这个问题应该转化到理论方法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也就是遭遇某个文本后,使用什么理论以及怎么使用理论也该是个问题。endprint
南帆说过理论是一种修养,我很相信它确实是一种素养。荀子很早就有言:“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在有几千年的思想发展之后,我们如果想思考,就必须借助前人的思想再去思想,必须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去探索和再探索,不然就很可能陷入自以为是的无知状态,陷入一种可怜的重复境地而不自知。如今,很多人每学到一种方法就急急忙忙地想来个小试牛刀,于是看到任何文本都寻思着怎么往他的理论方法靠拢。而且,如果他够较真的话,还可能用得有模有样,讲得头头是道。但是,退一步想,真的有必要这样吗?或者说如果我们还有点感性悟性细胞的话,是不是会对这样的阐释有所排斥呢?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读文学文本的时候都不会没有感觉,不会是为了对文本条分缕析才去阅读的。如果是,那即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对于作品如此,对于阅读者亦如此,甚至对于原作者都是。因为它扼杀了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最最基本的感性体验。文学世界是情感的世界,甚至是情绪的成块表达,它是关于内心世界关于灵魂世界的语言艺术,它不是古董或者什么机械,不是用来考古和拆分肢解和仿制提炼的标本。
3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求真,而该怎样求真又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个基本的路径问题,路径本身出了毛病,那结论不管看起来多真,都终究会是看起来而已。“真”不应该成为看起来的“真”,而是在合理的材料发现上论证、求证出来的结论。那么,在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能到达“真”吗?或者说哪些理论更值得信任?比如,我们当然可以从弗洛伊德的潜性意识理论去研究李商隐那些隐喻性特别强烈的诗,但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解释为真吗?或者,我们可以从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解释人类族群之间的通婚问题,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部机制,但我们会相信这些作品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精致的瓮才进行的吗?也许在人类学视野里它确实抵达了某种程度上的真,但在文学世界,即使结构再“真”,我们也不满足于这样的技术分析。我们还会感受到一些触动心灵、激荡情感世界的质子,会对这些触动心灵世界的作品思想是怎么回事感到疑惑,或者询问文本呈现出来的一些语言或者叙事现象等都是怎么回事。
也许,这就是文学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它在这个时代有着特别意味,批评不能够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感性表达。它还是一种专业,一种行业。这在19世纪的法国批评家蒂博代那里就开始说了。蒂博代认为19世纪是一个总结的世纪:“批评之所以是一种总结,因为它是针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批评是由亚历山大的一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创建的,它产生于一种保存、整理、清点和复制某些文献的努力。……我们因此可以补充说,在批评家的两大分类中,一种,即教授的批评,用于总结历史;另一种,新闻记者的批评,用于剖析现实。”②批评的“总结”特征无可置疑,只有对过去的作品做出评价,才能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也因此,批评总需要有某种历史感,没有历史感总显得单薄,或者说无凭无据就无法做出评价,如此,做好批评写作所需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博闻强识,在这基础上应付新出现的艺术作品方才能够显出眼力,得出比较理性的批评见解。
若要总结,自然要有一种对过去的评价,这种评价该怎么产生呢?这就是批评专业化后面临的学术问题,成了一种带有总结意味的学术研究了,它的写作就需要有学术的严谨和学问的证伪精神。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目标,是以史为鉴,为当前的文学创作、理论建设或人们的精神需要提供资源与养分。这是一种思想史的途径,而思想史在当下看来,其实是经受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熏陶后的文化研究思路,而文化研究思维里的思想史研究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中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很多学人,但是很多人还是将思想史研究看作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把文化研究当作狭义的文化現象解释,而不清楚作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文化研究是怎么回事,不清楚思想史研究在现在早已不是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著名人物的观点史,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史,时代的复杂性让这个思想内容变得繁复冗杂,它是跨学科的,是时间和空间汇聚起来的,做好思想史研究,其实就是把一个时代上上下下和前前后后的许多问题弄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那个时代内部的文本问题,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当然,文学文本也可以是成就一个时代思想史谱系的分子。
在解释和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和文本阐释这些问题上,应用思想史的方法更具备合理性。陈寅恪先生所言的“了解之同情”,其实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是我们要在了解这个时代氛围和思想背景以及各种现实处境问题的基础上去发现和研究问题。解释不能凭空捏造,评价也不能无所凭依,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苛责过去时代的作品,或者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过去的人。比如我们今天看现代作家的作品,很多作品思想简单而且技法笨拙,但是在一开始创作新文学的时代背景里,它们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依然不可动摇,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就不能依据现在的审美标准去否定它们的价值和影响。用思想史的视角去研究解释文学问题,可以研究出文学文本思想的时代背景、语境问题,可以看到这一文本在谱系中处于哪个位置,它的价值可以不是现在读者阅读的审美价值,但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文学案例,甚至思想案例。
思想史的方法还不仅仅是解释问题的根基,还可以是生产思想的根基所在。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寻找权力话语的运作机制,考察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合谋关系,进而通过对历史上被压抑的、埋没的、处于边缘地带的话语、事件的挖掘,来反抗那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和知识话语。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特别指出:“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③谱系学是批判思维,它通过对某一对象(比如性话语、监狱现象等)进行线性的历史考察,在这考察过程中挖掘被历史话语所忽略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边角料以及演变过程中的偶然性事件,进而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事物之构成的一种历史形式,这种工作构成对当下权力话语的批判,这种批判是话语生产,也是理论生产。总之,相对于考古学形成的话语“生成空间”,谱系学提供的是知识的“生成过程”,对这种权力话语“生成过程”的考察和批判,是挖掘被压抑、被支配的历史知识、话语的工作,也是批判当下权威话语的生产资源,因此,福柯说,谱系学……是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由此,可以看到谱系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梳理,或者不是复杂的思想观念溯源,而是一种不断发现和重新创造的过程。endprint
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思想史研究成为一个不断发现和重新创造的过程呢?怎样在过去的思想中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学术研究更为高端的去向,走向这个阶段就是一种创造力的发挥,是一种学和问的结晶,我以为这可以看作学术研究和问题意识的熔铸,学和问可能是鸡和蛋的关系,学问探究能不能生出健康的小鸡呢?这就是思想生产的问题,是创新。我们可以不追究鸡和蛋孰先孰后,但必须追求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在我看来,能不能孵出小鸡是一个活的问题,创新是要和时代接轨或者引领时代的,如此,当下性问题就是思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题中之意,利用思想史的方法去探究过去的文学文本问题,这就需要当下的视野和最新的眼光,否则就会流于重复或者落入意义危机处境。那何谓当下呢?
4
“当下”是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被引用的次数够多了,但很多人却言行不一,做起来总是拿客观性来为自己撑腰,总以为自己的研究不带有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甚至以为脱离了他们自身的主观意识,这也未免成了自欺欺人。1919年,28岁的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上来就声称刚刚演讲过的52岁的章太炎先生所讲的东西都是消极的,并在演讲中用英语讲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虽然不觉得章太炎的观点就一定消极,但胡适这里明显地强调了积极方面的时效性问题,也就是当下他们所需要的观念、建议是什么的问题。我想,这种从当下出发的研究视点现在也不过时。当然,注重当下的思维并不意味着“当下”这个词语要时刻放在嘴边。它更多是一种潜在意识。
“当下”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对它的界定必然涉及“过去”和“未来”。如果把这种时间性概念做哲学的处理,那会有很多相关的知识,比如存在、在场、历时性、共时性、延搁、延异,等等。从古希腊到当代哲学,对“时间”的分割问题总是兴趣不减,论述也历久弥新。这里暂且不讲这些,而取甘阳的看法谈论。甘阳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④,立足于“当下”,然后对过去和将来进行描述。这三个时间概念即是甘阳对“传统”一词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当下”来理解他的“传统”观。
甘阳认为,传统并不是过去,如果把传统当作过去,那就牺牲了“现在”,甚至也牺牲了“未来”。这是因为把传统看作过去的观念总是以“过去已经存在”这一观念来衡量“现在”,甚至预测未来。也即是说,现在和未来的文化是否符合过去的文化成为判断现在和未来文化的依据。因此,它把现在和未来都纳入了过去的文化结构、意识中。这种观念是不是有些悲哀呢?我虽不赞成死板的进化论,但我却也不敢苟同于希望维护千万年不变的“道统”观。甘阳批判这种观念,认为这种“过去式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缺乏现实感,缺乏自我意识,有种阿Q的病。
传统并非一种固定的文化结构、意识,它其实始终处于流动变化过程中,正如时间永不停息地流动一般。过去总是由现在构成,无数的现在构成源远流长的过去。我相信传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结构,但这种稳定只是相对的,并不是恒久不变。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曾经冷静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劣根性。阅读此书似乎令我们感到自卑,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书对于自省性太弱的国人来讲还是深有价值的。从此书来看,如果我们一切都以过去来衡量,那么很多东西似乎要流于悲哀。
传统,应该理解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所生发出来的种种可能性/可能世界,而这些可能性/可能世界也即成为我们的未来可能性的起源。这是一种立足于“当下”的思想态度。这种“当下”是立足点的此时此刻,它不可固定,它向未来敞开,也向过去敞开。甘阳这里明显借用了西方哲学中的时间观念,恐怕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尤甚。用这种立足于“当下”的时间观来看“传统”,那么,“傳统”则必然始终处于流动的未完成状态,始终是一种形成过程,过去也就不再是一种僵死固定的既成之物了,而是“不可穷尽的可能性之巨大源泉”。
甘阳这一“传统”的观念是80年代反思传统文化时形成的,但它似乎于今天还有参考价值,虽然“80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了。但进入21世纪已经十七年的今天,它也显然不再属于“当下”的观念了,而成为了“传统”观念,对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热情的人士是不是忘记了这一“传统”呢?如果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传统观念,那我们今日又如何能够全面理解“传统”?因此,我依然觉得,“当下”是个涵括着现实感、责任感的立足点,从“当下”出发去理解传统,从而不把传统辖域化,而将传统不断生成化。
总而言之,我们时刻都需要反思理论本身的价值,简单地抛弃理论很不可取,沉溺其中也不是理论研究所希望的。作为思想的理论是活的,它引导问题的产生,与问题意识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同时,在思想和问题的背后,有着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具体的思想史。思想史不仅是研究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的根基,而且是发现新问题和生产新思想的土壤。我期待这样一种研究,通过“当下”问题,沟通起理论与思想史知识,提供值得信赖的意义判断,也生成新的知识话语。
【责任编辑】 邹 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