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物理之美
陈竹沁
2017年4月,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上,被问到如何向外星人介绍人类取得的最高成就时,霍金说:“告诉外星人关于美,或者任何可能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形式都是无益的,因为这是人类特有的。我会告诉他们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费马大定理。这才是外星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霍金说:“告诉外星人关于美,或者任何可能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形式都是无益的,因为这是人类特有的。我会告诉他们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费马大定理。这才是外星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我对这段问答印象极深。在采访国际量子信息领域领军者潘建伟团队前,物理之“美”也是最早浮现在我眼前的字眼——很多年前有报道写道,中科大前党委书记郭传杰评价潘建伟实验室是“自豪和美的团队”,而潘建伟在评价学生实验时也常这么说:“这是一个有美感的实验。”
当我向他和他的学生求证时,这个“大词”似乎反倒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一言以蔽之,“团队之美”是团结互补、共同实现美好的科学目标;“实验之美”则转换成创新的程度和水平。一个对科学概念全凭朦胧想象的文艺女青年,显然无法对这样的平铺直叙感到满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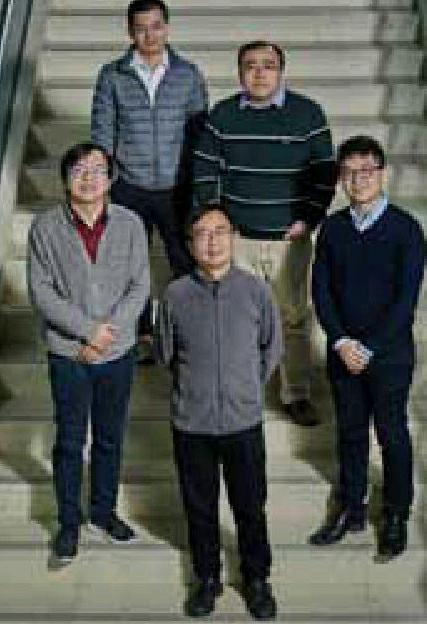
好在量子力学本身的玄妙是最好的弥补。1925年前后,一群年轻的欧洲小伙,在牛顿、麦克斯维尔经典力学体系的废墟之上,建造了量子理论的大厦。在你打开箱子前,“薛定谔的猫”既生又死;海森堡则告诉我们,你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而爱因斯坦从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讽刺量子纠缠特性是“幽灵般的远距效应”。
多亏“量子隐形传态”和“多世界理论”,我们有了那么多描绘“超时空传输”和“平行时空”的科幻片,加上通俗科学史著作的传播,似乎现代世界的每个人都对量子力学一知半解。
起初我给自己的封面报道取了一个副标题:今天我们如何认识量子物理?逐渐深入才发现,这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命题,涵盖理论演进和产业前沿,无论从报道体量还是个人科学素养,这都是我无法完成的任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指出现实中的谬误,借助科学家的思维和话語,来厘清纠缠在量子力学周围的“科学、伪科学、宗教”三者的边界。
量子信息领域国际权威尼古拉·吉桑写过一本小册子《跨越时空的骰子》(潘建伟为之作序),里面有段话讲得特别好:“对量子物理的讲述总是充满了长篇累牍的说教和含糊其辞的哲学评论。为了避免这种误区,除了‘基本事实以外我们什么都不借助。当物理学家做实验时他们是在对永恒的实在进行探寻。物理学家会决定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什么时候提出。比如研究一个发着红光的灯泡时,物理学家不会纠结于灯光到底是不是真是红色的,或者这来源于一种错觉。他们会认为:灯泡是红的,仅此而已。”
但事实上,有人文关怀的物理学家总是难免会走远一步。比如对自由意志和量子波函数坍缩的理解,潘建伟也曾引申认为,“量子力学从哲学上讲,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概念”——你睁一下眼去看,粒子原本的叠加状态才确定了;因此“我们个人的奋斗,对这个世界是有影响的。”但这显然只是个人的一点浪漫主义感悟罢了。
当潘建伟对我说,量子物理最美妙的是包容,我确定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甚至还想到一些他未必抱有的“言外之意”。他的多光子纠缠操纵、他的量子卫星宏图,在国内的科学环境下曾饱受非议,被抨击为“异想天开”甚至“骗局”。但今天他和团队取得的国际成就,早已让那些批评声沦为笑话。与之相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却不愿以科学的“权威”去“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
潘建伟和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有过一段对话。潘建伟说:“生命真的太短暂了,我真想活得长一点,搞清楚量子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那样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朱清时回他:“活那么长干什么?你活着,思想就会僵化,不仅自己搞不明白,还会妨碍下一代前进的脚步。”
如今看来,潘建伟一直都是那个清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