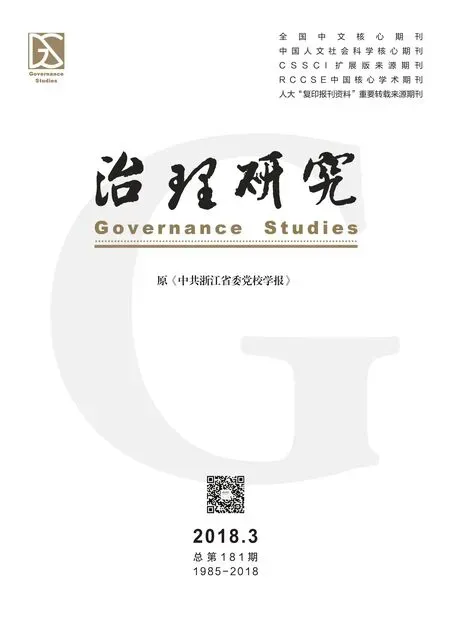十八大以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
□ 周文华
中共十八大以来,美国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行了广泛研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跟着领袖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的《中国的挑战》、李成(Cheng Li)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和中国新一届政府》等。他们既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又分析了毛泽东至习近平时期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执政特点以及中国政治结构和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刻变化。美国还出现了大批介绍和评论性文章,以更加宽广的视角探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当下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外交事务》《当代中国研究》《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众多智库的网站上几乎每月都发表数篇相关论文,研究主题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一、主要研究内容
中共十八大以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挑战、习近平的领导风格等。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11月在杂志封面(美国本土版除外)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上“中国赢了”! 这是《时代》周刊封面第一次出现两种语言。内文《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其作者布雷默指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实力的国家。布鲁金斯学会李成等人充分肯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及其成就,也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存在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等挑战,需要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认知度等。
第一,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李成认为,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人们对腐败行为的不满以及对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尤其是低收入者改善经济状况的需求,大胆地推进经济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绘制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蓝图,其重要性不亚于邓小平1978年实行的经济改革。*Cheng Li.(2017).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0-12.波士顿大学陆伯彬(Robert S.Ross)认为,中国拥有一批很专业的经济改革人才,他们能力很强,知道中国怎样向新的增长方式转型,但他们可能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他说,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革表明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经济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但推进改革议程面临更大的挑战。*Robert S.Ross & Jo Inge Bekkevold.(2016).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70-271.
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戴慕珍(Jean C.Ol)等人认为,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争论的话题,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以及快速城市化影响了中国改革时代的发展,并将有力地塑造中国的未来。他们认为,错综复杂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和经济治理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延缓经济增长。中国在走向全球前沿之前,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劳动力应该做好提高生产率、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准备。*Karen Eggleston, Jean C.Ol, Scott Rozelle, Ang Sun, Andrew Walder & Xueguang Zhou.Will Demographic Change Slow China's Ris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3).波士顿大学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地方官员考虑更多的是利益和经济因素,而不是提供公共产品。尽管权力下放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但如果缺乏对地方政府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就会增加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的机会,普遍存在的土地征用问题尤其如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也认为,启动改革和巩固改革之间有重要区别,二者所需要的领导技巧很不相同,执行新政策需要增强政府行为的有效性。*Robert S.Ross & Jo Inge Bekkevold.(2016).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M].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70-271.
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Shang-Jin Wei音译)着重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他基于大量研究数据认为,中国有惊人的经济增长,但现已走到了十字路口。自2012年以来,中国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工资压力,现在必须采取一种以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的方向或许应该是让所有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扩大参与创新活动的公司数量和创新企业的创新强度。尤其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中国企业在应对薪资压力和全球机遇方面表现出了更具创新性的能力,没有理由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内在能力感到悲观。*Shang-Jin Wei, Zhuan Xie & Xiaobo Zhang.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1).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需要加强对周期长、成本高的产业进行创新支持,以弥补一般投资人逐利行为下的产业导向。
华盛顿大学沈大伟在《中国:不完全大国》中说,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认知度还不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在海外成功运营的公司也不是太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斯坦福大学魏昂德等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第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魏昂德(Andrew G.Walder)说,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多党制才能带来善治,但是很多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治理的并不好,尤其是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魏昂德还说,有些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对美国自身的政治并不熟悉,1830年代的美国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曾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腐败问题也不是多党制所能解决的,多党制只会给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不利影响。*Kenneth G.Lieberthal & Cheng Li.(2014)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12-216.李成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发展变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中国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威权主义的韧性”,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寻求新的工作机制、制度性规定、政策措施、政治规范来解决内在缺陷与不足,在党内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西方观察家们的预期。*Cheng Li.(2016).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7-9.
第二,中国民主应该有自己的特征。
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认为,为满足国内治理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往往采用不同类型的民主。民主可以缓解社会冲突,增进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民主可以给创新性思维提供更大的成长空间,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类型的民主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以及社会和政治环境,美式民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民主应该有自己的特征。*Kenneth G.Lieberthal & Cheng Li.(2014).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reface xii.纽约大学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也认为中国不应当迷信竞争式民主,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自我政治分裂。他还认为,由于语言障碍、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不足等原因,西方理论界很难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于简约浓缩的概念;中国当务之急是用外部世界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政治制度。*魏南枝:《差异与合作——帕斯奎诺教授谈当今中国政治》,《求是》,2013年第19期。
(三)关于外交与国际地位
美国研究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但面临大量不对称关系;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还不是完全大国;尽管许多地区大国都有区域排外的门罗主义,但中国并没有。
第一,中国加速走向世界。
霍普金斯大学大卫·兰普顿认为,习近平明确表明要加速推进中国走向世界,他是第一个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进行认真阐述的人,目前的中国表现得更像一个全球力量,二战以后世界还未曾面对一个如此活跃的中国。*江玮:《“要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赋予内容”》,《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9月27日。李侃如认为,美国和其他各国欢迎习近平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阐述,并希望看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更多具体行动。宾夕法尼亚大学金骏远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存在,但对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有更大的潜在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民众希望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有强硬表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照顾民众的心理需求,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外交政策的外部影响。
第二,中国面临大量不对称关系。
弗吉尼亚大学布兰特利·沃玛克(Brantly Womack)认为,中国面临大量不对称关系,既在G2框架内决策也在G20框架内决策,情况比较复杂,对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举动都会在其他邻国中引起反应,因此要非常慎重。就中美关系,他认为,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因预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美国作为一个衰落的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受到批评。事实上,艾利森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认为要考虑中国崛起的综合因素,美国对衰落的恐惧,以及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了霸权怀旧,特朗普呼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美国没有能力扭转历史或阻止中国崛起。同时,美国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特朗普和中国都不能改变这些基本事实。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将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鉴于此,布兰特利·沃玛克呼吁,面对当前的全球政治危机,中美应该保持冷静和包容,关注问题而不是对抗,并建立地区和全球机制。*Brantly Womack.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 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J].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4).
第三,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国。
沈大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尤其如此,但是,如果综合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情况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国。他认为,中国可以被看作澳大利亚、巴西、英国、法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那样的具有较大地区影响力的中等程度的强国,距离美国那样的大国地位还有一定的差距。*David Shambaugh.(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9-310.赵穗生2017年7月底做客“凤凰大学问”时指出,中国已经是现存国际秩序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中国还没有能够取代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还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投入到现存国际秩序中。他认为,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要改变的主要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在游戏过程中的地位、代表权和发言权。
第四,中国没有“门罗主义”。
针对某些国外媒体对所谓“中国门罗主义”的指责,宾夕法尼亚大学史蒂文·杰克逊(Steven F.Jackson)认为,尽管许多地区大国都有区域排外的门罗主义,但中国并没有。他援引约翰·米尔斯海2015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当遥远的对手将军事力量转移到某个大国的邻国时,该大国的反应是严厉的,更不会让一个国家与该大国的边境国家结为盟友。史蒂文·杰克逊认为,任何美国领导人都不会容忍加拿大或墨西哥加入由另一个大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尽管美国是少数几个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实现完全地区霸权的国家之一,但其他国家也在寻求这样做。如,苏联积极寻求通过“有限主权原则”排除美国在东欧的影响。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印度特别引用了门罗主义,试图将南亚作为印度统治的一个地区,这一努力最终被称为“英迪拉主义”。尼日利亚周期性地发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陆管辖原则”。1968年勃列日涅夫学说则正式阐述了苏联对一些试图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的“国际主义义务”。 史蒂文·杰克逊认为,中国可能会效仿此类国家的模式,并正式宣布一种区域排外主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一直强调亚洲是开放的,欢迎外部力量在亚洲所起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这是一种与门罗主义根本不同的立场。他认为,中国没有门罗主义的第一个可能的原因类似于路径依赖:它在过去明确谴责了任何这种区域排外主义,并以官方的方式声明,它永远不会采纳这样的教条。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对区域排斥理论的反感。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被认为是门罗主义的体现。第三个潜在原因是为自己与南亚和中亚的关系树立榜样。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在沿线地区发展,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如果将其他国家排除在东亚之外,无疑会招致虚伪的指责和抵制。第四,原来的门罗主义现在已经正式失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2013年11月在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讲话,正式放弃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认为,中国对邻国的态度实际上比其他地区霸权国家的行为更为温和,中国没有公开干涉邻国的内政,其军事力量的使用是有限的,并没有公开宣布区域排外主义。*Steven F.Jackson.Does China Have a Monroe Doctrine? Evidence for Regional Exclus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2016(4).
(四)关于中国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要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明智的策略并不是易事。中国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获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因为当今世界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关注度,而关注度取决于公信力。他说,软实力的发展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所有国家都可以从寻找彼此的吸引力中获益。*[美]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70-72页。美国研究认为,中国在着力加强软实力建设,但要改进建设方式以提升建设效果。
第一,中国赢得关注和吸引力的同时,还要增强说服力。
布兰特利·沃玛克认为,中国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投入巨大资源,“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一部分,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的支柱。他认为,中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安全的政治领导和不同政治制度相容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吸引力。2017年7月在乌拉圭举行的拉丁美洲政治科学协会会议上,23篇论文的标题有“中国”,6篇有“美国”,5篇有“印度”,1篇有日本。他援引约瑟夫·奈的话说,软实力是一项微妙的资产,中国赢得关注并增强吸引力的同时,还要增强说服力,而说服力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双赢框架。他认为,在全球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拥有稳定的优势,但它必须让合作伙伴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是低风险和符合自身利益的。兴起的大国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于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中国的崛起不太可能成为这些缺陷的牺牲品,然而,也要警惕民族主义的自大情绪。中国主张的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政策很好地适应了全球化,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必须是自由的,并且能够连接世界其他地方。*Brantly Womack.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 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4).
第二,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仍然不够广泛。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基于对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民调数据,于2017年6月发布有关中国软实力的报告,认为在全球范围来看,更多人视美国而非中国为世界经济领导者,但美国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和盟友认为平衡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百人会”发布《2017年美中公众认知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以普通成年民众为主,同时包含了商界领袖、政策专家和媒体人。报告发现,近五年来中美两国民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增加,但彼此信任度却在降低。对于“20年后谁将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选择美国的人数较五年前有所增加,选择中国的在减少,说明美国人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在上升。另外,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仍然不够广泛,美国普通民众、商业领袖和政策精英群体中,都有约一半人从未看过中国电影,同时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够准确。五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表示观看过中国电影后对其好感会增加,而看过展览或艺术演出后有此感受的受访者则达到45%。这些调查数据将有助于中国更加精准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英]乔纳森麦考利、唐磊:《2017年海外对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评估》,《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五)关于当前面临的挑战
陆伯彬等人认为,中国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挑战;雷默等人则着重强调了中国形象等方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面临多方面的综合性挑战。
陆伯彬认为,除经济增长、反腐败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展现自己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对此寄予较高期望。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未来十年极为关键,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成熟和智慧的领导人。同时,陆伯彬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与发展经济的关系。*Robert S.Ross & Jo Inge Bekkevold.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6,Introduction,xiv,p.278.李侃如2013年“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国际研讨会上认为,中国的挑战主要有人口结构转型、资源短缺、技术革命对国家治理所带来的未知影响以及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压力、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多样化等。李成认为,除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环境外,中国还面临资源短缺以及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和沿海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等。他认为,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向消费驱动型、创新引导型、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Cheng Li.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p.24.戴慕珍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衡、快速城市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并深刻挑战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Karen Eggleston, Jean C.Ol, Scott Rozelle, Ang Sun, Andrew Walder & Xueguang Zhou.Will Demographic Change Slow China's Ris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3).大卫·兰普顿认为,中国的挑战主要包括保持经济增长、进行政治改革、为人们提供干净的水和空气、向外界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等。*David M.Lampton.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p.1-2.柯伟林在《中国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序言中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反腐败、密切党群关系。
第二,中国面临国家形象等方面的挑战。
“北京共识”首倡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近年来一直强调,国家形象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之一,其他挑战也都与此相关。他认为,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中国在进行国家形象塑造时,要注重真实地展示其特有的复杂性。
马里兰大学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M.Pearson)等人认为,中共中央所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是地方政府无处不在的“自由裁量权”。地方自由裁量权是世界各国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对北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行为一直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来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地方自由裁量权并不总是服务于中央的目的,它经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辖区内的竞争以及经济过热。有些自由裁量权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而采取违规行动。因此,如何在不影响地方创新的前提下准确制约地方的负面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Ciqi Mei & Margaret M.Pearson.Killing a Chicken to Scare the Monkeys?Deterrence Failure and Local Defiance in China [J].The China Journal, 2014(2).
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认为,进行当代中国暨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应该局限在政权更迭的走向与前景上,尽管这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常有的倾向;面对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过程和极富生命力的制度韧性,其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应被视作一个政权在走向成熟进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增长的痛楚。*[美]裴宜理:《中国高层面临的新挑战》,《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
(六)关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
十八大以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一般都涉及对习近平本人的研究。他们高度肯定了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并强调了习近平的转型色彩与政治确定性。
第一,习近平获得广泛赞誉。
2014年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根据30个国家的受访者对10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的知名度、关注度、认可度、信心度等方面的评价,习近平得分最高。*领导人形象调查:习近平国内国际认可度排第一,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7/c70731-26227944.html。陆伯彬认为,习近平执政之初,中国面临着维持社会稳定、提高治理水平、平衡国内经济以及处理动荡的东亚局势等挑战,在内政外交方面,习近平更自信,更有决断力,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主动。他说,习近平如果能通过必要的改革推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保持地区稳定,将作为一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而被载入史册。*Robert S.Ross & Jo Inge Bekkevold.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M].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6,p.278.
第二,习近平既具有转型色彩又具有政治确定性。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认为,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风格稳重自信,促进中国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取得成功,获得全球思想领袖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全球决策需要中国参与,习近平在其执政期间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美国前大使:习近平将成中国首位真正的全球领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29日。伊丽莎白·伊科诺米说,习近平不是第一位呼吁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为民族复兴提出了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即“一带一路”计划,旨在复兴古丝绸之路和海上商路,从而加强中国的中心地位。她认为,习近平的复兴叙事在今天的中国人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唤起了人们对中国获得世界赞誉的历史记忆,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一流的创新源泉,不需要使用武力,仅凭成就和美德就能赢得他人的尊重。*Elizabeth C.Economy.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ow China's Imagined Past Shapes Its Present [J].Foreign Affairs,2017(4).
布兰特利·沃玛克认为,特朗普具有明显的政治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矛盾和不断变化的观点;团队的不确定性;对奥巴马政府的广泛批评给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带来了不确定性;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抗的不确定性。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政策上是谨慎和一贯的;他的团队具有凝聚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在很多方面保持连续性。此外,他还显示出重新思考一些棘手问题的政策性能力。*Brantly Womack.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 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 [J].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4).
二、主要研究特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呈现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范式各不相同、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并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等特点。
(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2015年1月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发布的《美国知华派评估报告》对158名美国专家的影响力进行评估,大卫·兰普顿名列榜首,沈大伟、李成、傅泰林和李侃如、金骏远以及多位中生代学者跻身前20名。美国的中国学领域人才济济,英才辈出。既有仍然活跃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麦克法夸尔、基辛格等老一辈中国通,也有沈大伟这样的中坚力量,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康奈尔大学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等。尽管有些年轻学者在中国还不具备较高的知名度,但在美国已有相当影响,他们师出名门、年富力强、成果丰硕,是未来美国中国学的中坚力量,其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主要倾向及发展动态需要我们提前了解、密切关注,并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交流。
此外,以李成为代表的一大批华人华裔学者异军突起,他们的研究态度和研究倾向与美国本土学者有所不同,其研究成果在中美均有较大影响,值得我们关注。目前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人群除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智库、政界、商界和媒体人员等。他们有更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以更独特的视角对中国某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
(二)研究范式各不相同
美国历来存在不同的中国研究范式,尽管有些范式并不是最近才形成,但是,直到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范式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美国要竭尽所能延缓中国的崛起。哈佛大学保罗·柯文(Paul A.Cohen)的“中国中心观”范式则从中国人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惯用的“西方中心观”看中国的发展,他强调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包括“移情”研究中国。另外,美国部分青年学者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整体研究,专题式研究较为普遍和深入。比如说,他们对城管问题、法律制定、利他主义、民族主义、家庭结构、中医等都有比较详细的研究,沈大伟和李侃如都曾对这种侧重微观分析的方法表示忧虑,他们认为过于注重细节和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容易失去对宏观和重大战略问题的把握。
(三)研究方法有所侧重
十八大以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在方法上更为侧重比较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
在比较研究中,一方面,把今日中国与前苏联进行多方面比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比较。比如,魏昂德认为中国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比较重视政治稳定,但中国无疑具有较好的政治体制改革条件;还有学者通过对比苏联解体前申请入党人数与中国当今的申请入党人数,论证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把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比较,其中习近平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尤为多见,认为习近平坚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又大胆创新。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中国与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比较研究,体现了较为宽广的视野。
定量研究在美国中国学中得到较多应用。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对定量研究有所侧重,另一方面,定量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呈现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四)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美国对中国现实问题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反映迅速。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愈加频繁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了解更为及时,他们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研究也呈现出更强的时代性特征。围绕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中共十九大以及每年的“两会”等重要会议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围绕“中国梦”“四个全面”“五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亚投行”,甚至“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9·3阅兵”等重要议题都有所关注和研究。部分重要议题的研究与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同步进行。与时效性直接相关的是政策性,美国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即时研究,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其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策变化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合作研究逐渐增多
十八大以来,中美合作研究逐渐增多。2014年,中美24位学者合作完成《中国的政治发展》一书,由俞可平、何增科等12名中国学者就中国政治的某一个重要领域进行深入分析,由托马斯·赛奇、魏昂德、墨宁等12位美国学者分别就其中一个问题进行评论。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系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利益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再如,李侃如、王辑思等中美学者就中美战略互信等若干重要问题,通过书信体的方式进行交流探讨,最终结集成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外,中美学者就环境问题、经济改革、外交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出现不少论文和专著。
美国还尝试通过MOOC推广中国学研究成果。2013年,哈佛大学发布了由包弼德和柯伟林主讲的MOOC课程《中国》,邀请哈佛大学对中国有所研究的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教授参与授课,从思想、社会、经济的变迁等维度对中国进行解读,吸引了170多个国家的43万名学生注册学习。包弼德说,开这门课一方面是想告诉人们怎样思考历史,另一方面是想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打消他们对中国的疑虑和偏见。该《中国》课程认为,“当代中国具有双重形象: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确立全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都有多种传统资源。中国社会和政府将背负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包括它的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运行逻辑与方式。要理解21世纪的中国就不能不理解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Peter K.Bol& William C Kirby,China,https://www.edx.org/course/harvard-university/sw12x/china/920.
(六)研究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既存在客观公正的认识与评价,也存在片面性认知,甚至存在误解与曲解的成分,其中尤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最为典型。观点的多样化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往来使他们希望中国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第一,中国威胁论不断发展。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并在新中国成立时和苏联解体时分别有过较大发展,近年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以来,中国威胁论再起,并在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方面分头推进。有人认为,中国梦可能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他们没有全面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就武断地将国家梦与个人梦、中国梦与美国梦、中国梦与世界梦对立起来,执意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外界的威胁。有人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视为中国施展全球影响力的工具。有人煞费苦心创造出“锐实力”概念,攻击中国通过开设“孔子学院”等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与建设活动。尽管有些观点危言耸听,不足为信,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混淆视听,需要给以特别关注并积极应对。
第二,中国崩溃论仍有影响。
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时,中国崩溃论也在不断发展。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以来,中国崩溃论不断发展,尽管预言从未成真,但至今为止中国崩溃论者并未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十八大以来,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在国内外均引起热议。这种唱衰中国的论调,即使在美国国内也不占主流,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影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一方面以中国的客观事实对其中的曲解成分进行反驳,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研究成果的警示作用。
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并行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冷静客观的分析。一些研究者对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及症状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借鉴作用,但其最终研究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就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呈现出一幅复杂的改革图景,美国要努力读懂中国,充分利用中国改革所带来的机遇,追求美国自身的政策性目标。*Elizabeth C.Economy.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reface xi.
总体来看,美国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在研究队伍、文献资料、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广泛深入的特点,但是,在研究范式和具体结论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受西方价值观、国内外政治气候、社会舆论以及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改革开放新实践缺乏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可能会产生误读、曲解和偏见。另外,语言的障碍增大了理解复杂的中文资料的难度,影响他们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科学性。但是,可以预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将会持续升温,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热点和研究重心。
三、结论和对策
美国正逐步加大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力度。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较强的话语权,其研究状况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尤其是加强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一)大力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海外研究者的目光,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对中国进行研究,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这一状况也得到了国内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2010-2020年)》以及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海外中国学研究既有重要的资政作用,也有重要的育人作用,对维护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建言资政。海外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人员及机构往往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并具备智库的作用。了解他们的研究状况和政策倾向以及研究动向与趋势,可为我国相关党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助于我国的咨询型智库的建设。另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来自海内外的诸多挑战,其中海外意识形态渗透是一个主要方面。通过对海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纠正那些片面的甚至明显错误的观点和言论,对帮助人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通过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有效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判,有助于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二)重点加强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
美国在当今世界具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评价。加强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可以起到正视听的作用,而且有益于在国际范围内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内对美国关于中国共产党及主要领导人的研究给以较多关注,并对部分代表性成果加以译介、研究,基本上搭建了整体研究框架,从研究机构、成果类型、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等方面进行分类梳理和评析。初步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机构、研究团队、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也从最初的资料搜集整理向专题研究转化,从评述为主向资政转化,从注重译介向国内外研究相结合转化。但是,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美国的研究状况还关注不多,至今研究性成果仍不够多,这种局面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很不相称。
(三)加强中美对话与交流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均发生较大变化,中美两个大国各个层面的有效对话与沟通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共同推动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在加强中美对话与交流中,我们需要注意,由于美国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学术经历、研究背景不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起点和立场也不同。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以开放的学术环境、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开展交流。我们既可以借鉴美国研究中的建设性内容,也要对其中的谬论和误解进行回应和批判,减少其错误观点对我国民众的不良影响和冲击。例如,针对部分美国人指责中国使用“锐实力”对美国的政治和信息网络领域渗透,试图影响美国各界的认知与决策,并进一步谋取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学者应以充分的事实依据进行反驳,并为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对策。同时,加强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正面宣传,适时推出外文版,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积极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