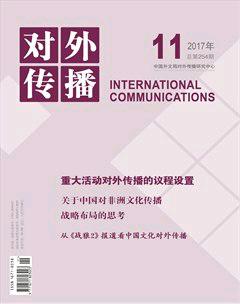《白毛女》故事走进日本的启示
杨珍珍+诸葛蔚东
2016年11月19日至20日,在日本东京南青山松山芭蕾舞团的演练剧场举行了新编大型历史史诗《白毛女》的公演。在中日关系处于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人们愈发认识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性的今天,该剧的上演似乎具有特殊意义。
电影《白毛女》1952年流传至日本后,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广泛欢迎。然而,不同社会阶层对《白毛女》的理解各有偏重。左翼知识分子及产业工人更多地从阶级意识、革命理想出发,希望日本也能效仿《白毛女》中展现的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道路;农民阶层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将其视为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松山芭蕾舞团以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改编的芭蕾舞《白毛女》在日本获得了好评,为中日两国建立邦交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民间基础。
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日之间并无官方交流。1952年,历经艰辛摆脱日本政府阻挠、成功访华的政界友好人士帆足计、宫腰喜助及高良富来到中国后,从中方获赠电影《白毛女》,并将其带到日本。当时虽然承诺不公开放映,但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努力下,电影《白毛女》经常在东京的小型集会上播放。
《白毛女》的公演在当时的日本面临巨大的挑战。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再加上双方分别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战后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中国官方交往几乎处于完全断绝状态。1952年4月,日本政府与台湾方面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合法地位。然而,日本民间却对中国非常关注。以日中友好协会为代表,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及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阶层对新中国的革命斗争模式及成功持赞同、憧憬的态度;而朝鲜战争过后,日本作为美国军用物资基地给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呈现颓势,经济界人士希望与中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以此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新推动力。如此,日本民间建立起深厚的对华友好基础,主张中日尽早建交的呼声也是首先发轫于民间。
1952年,中方將电影《白毛女》交由帆足计等三位政界友好人士带回日本,其实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歌剧《白毛女》最早上演于1945年4月,其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及中国人民面临着走向哪条道路的抉择。在当时中国农民占国民数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能否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更改为“耕者有其田”,规定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赢得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最终掌握了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电影《白毛女》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便是宣传土地政策,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掌握了土地所有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在以农民为主的人民的支持下获得的,是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在此时期将《白毛女》交由帆足计等人带回日本,主要并非像山田晃三所言,“把正确的新中国形象传达给日本”①,而是包含着向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宣示自己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意图。
二
帆足计等人将电影《白毛女》带回日本后,随即在日本各地展开小规模的放映。据统计,从1952年秋天到1955年6月,在日本观看电影《白毛女》的观众达200万人②,放映范围覆盖东京等大城市及地方的农村,非常广泛。1955年12月6日,电影《白毛女》由“独立映画株式会社”正式发行,由此得以公映,观众范围进一步扩大。
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称不知为何东京大学会播放《白毛女》。竹内是在东京大学驹场大礼堂观看《白毛女》的③。该电影当时尚无日文字幕,是由懂汉语的人手持话筒在播放过程中同步翻译。没有日文字幕,收取租金,但仍能多次在会议上放映,这本身就体现出日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关注。
日本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对《白毛女》的反应不同。如当演到大春被红军战士救下并来到解放区的场面时,鼓掌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参加工会的非基础产业的工人。中农、贫民、外地工人和城市的产业工人则只是放心地舒了一口气,掌声稀疏。当演到喜儿和大春在山洞里见面的场面时,农村观众中响起暴风雨般掌声的同时,还伴有激烈的哭泣声。在城市却没有什么反应,到了下一个人民审判的场面才有掌声④。
在探讨《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时,必须从当时日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考察。20世纪50年代,产业工人阶级在日本共产党及工会的领导下,从经济斗争上升至政治斗争,对于日本“事实殖民于”美国的现状不满,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运动,抵制《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及受工会教育的产业工人,从《白毛女》中看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看到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巨大改变与日益强大。因而他们会对大春参加解放军、人民公审地主等具有明确革命意义的事件产生共鸣。然而,他们对喜儿和大春重逢却并无感动,穆仁智在杨白劳尸体面前把土地契约展示给农民看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应⑤。他们并无在农村生活的实际经验,不懂得地契对于农民是何等重要。通过《白毛女》,他们看到了通过武装斗争打倒剥削阶级、解放被剥削阶级的重要性,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确立政权的正当性。他们是从权力话语层面来观看《白毛女》的,这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向日本输出电影《白毛女》的意图。
与左翼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不同,农民在观看电影《白毛女》时,更多的是关注大春与喜儿的个人情感、影片中每一个人物(包括黄世仁)的生命权。比如,当喜儿走到河边时,农民都发出“啊啊……”的声音表示担心,看到喜儿往山里爬去时,他们又发出“太好了”“得救了”之类的庆幸;当演到杨白劳喝卤水自杀的场面时,农村的观众同时发出“啊,死掉了”的感叹;在判决黄世仁时,他们又感慨“不用那么过分吧……”⑥。
他们对审判地主表示同情,对于杨白劳与喜儿悲惨的命运,他们也表示同情。可见,农民们在欣赏《白毛女》时,是从个人情感出发,将其当作描述个体命运的故事,其中的武装斗争、阶级意识等该影片最主要的创作意图并未很好地传达给他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地改革的形式。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其中针对农村最主要的是推行农地改革:由政府出面强制收购地主的土地,再以低价将土地出售给更多的佃户。这种温和的自上而下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形式使得未曾受过阶级教育的日本农民对于地主并没有斗争的意识。endprint
从上可见,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及产业工人在观看《白毛女》过程中,很好地领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该影片试图传达的政治意图,他们意识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成为可以与美国、苏联抗衡的大国,也激发了他们效仿中国,通过武装斗争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实现完全独立的理想。而农民阶层则未从政治上的权力话语层面观看《白毛女》,而是将其视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对每一个遭受不幸的人表示同情。可以说,吸引到农民阶层的是故事情节和情感因素。
三
1952年,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中观看了电影《白毛女》,深受感动的他携夫人即知名的芭蕾舞艺术家松山树子再次观看,随后二人决定将电影版《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版《白毛女》。1955年2月,松山芭蕾舞团的芭蕾舞版《白毛女》在日本公演,受到日本观众的广泛好评。
松山树子在之后的回忆文章《从歌剧到芭蕾》中表示:“妇女解放等大主题也多少有些,但最主要的还是朴素氛围中令人感动的故事。”⑦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最初版本中,他们做出了如下几个重大改动:一是将由杨白劳买给喜儿的红头绳改为由大春买给喜儿,这也成为后来大春认出变成“白毛女”的喜儿的关键道具;二是对于黄世仁的处理是将其“驱逐出境”,而未将其处决;三是在结尾处,大春高举喜儿,青年农民也将各自的情侣高高举起,以爱情昭示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从上述改编我们可以看出,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是将大春与喜儿的爱情作为叙述线索,弱化了原歌剧及电影中着重表达的阶级斗争色彩,这种处理方式更加符合普通日本人的审美趣味,“观众们都被主角喜儿在任何环境中不灰心、不气馁、生机勃勃、英姿飒爽地生存下去、与时代斗争的精神所感动,认为她即便青丝变白发也非常美丽,首演因此大获好评并取得巨大成功”⑧。可见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让日本观众感动的主要并非阶级斗争,而是喜儿的坚强与韧性,是喜儿与大春之间的爱情。
1958年,松山芭蕾舞团携芭蕾舞版《白毛女》首次来华演出,在中国也引起极大轰动。然而松山芭蕾舞团所做的改编尤其是对于黄世仁的处理方式让对《白毛女》故事耳熟能详并深受阶级教育的中国观众感到“颇为不解”⑨。但是,我们不应要求松山芭蕾舞团跟中国观众以同样的情感看待《白毛女》,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观众的审美意识会相应有所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与改编使得《白毛女》能够打动日本观众的心,至今仍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看家剧目之一。
当松山芭蕾舞团之后再携《白毛女》来华演出时,《白毛女》反而成为他们表达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的文化手段,所以他们将其做了更为符合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改编。如1971年第二次来中国演出《白毛女》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之前的1966年,上海舞蹈学校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被确立为八个样板戏之一。
松山芭蕾舞团在中国公演《白毛女》时如果继续以大春与喜兒的爱情为主线的话,就无法让中国观众满意。所以,他们顺应时势做出调整,“从学习江青女士指导、在‘文革中完成的《白毛女》中学到很多,更主要的是贯彻毛泽东思想,基于《延安文艺讲话》,将松山芭蕾舞团《白毛女》改编为以解放日本人民为目标的日本《白毛女》”⑩,将原来版本中由大春交给喜儿的象征着爱情的红头绳改为由大春母亲给喜儿,从舞蹈动作及面部表情增加喜儿的反抗色彩,让喜儿与大春一起参加革命等,这些改编迎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及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而2011年,第13次访华演出之际,松山芭蕾舞团第三次改编《白毛女》,将这些迎合政治形势做出的修改复原,主要仍然表现以喜儿为代表的穷苦人民在任何恶劣环境中都不妥协、抵抗到底的精神。
松山芭蕾舞团在面向日本观众将中国歌剧版《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版时,做出了符合日本人审美趣味和情感倾向的改编,在面向中国观众对自己的芭蕾舞原版进一步改编时,又考虑到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及观众的情感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使得两个国家的观众都对松山芭蕾舞团版《白毛女》充满感情,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宣传意图,更使得松山芭蕾舞团能够在两国尚未建交之前,通过艺术的形式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为官方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民间基础。
四
由《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和在不同社会阶层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效途径。而优秀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对海外受众市场的了解和作品是否满足海外受众的需求。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的改编能够打动日本受众的心也说明了这一点。《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对今天的文化产业“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首映70周年,11月7日,由文化部组织复排、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新歌剧《白毛女》从延安开始了巡演之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形式的《白毛女》都以自己的艺术魅力和充沛情感感染着不同国家的观众,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人民心灵的桥梁。
《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案例,其中的成功经验仍有待分析和整理,这对于推动中国故事在海外的传播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日)山田晃三:《<白毛女>在日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②(日)山田晃三:《<白毛女>在日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③(日)山田晃三:《<白毛女>在日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4页。
④久松公(1953)「白毛女」合評会のメモ(J),ソヴエト映画4(1),P24。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松山樹子(1992)オペラからバレエに--「白毛女」の場合(J),悲劇喜劇45(3), P25
⑧森山洋子(2013)日中国交正常化のかげにバレエ外交あり(N),http://www.focus-asia.com/socioeconomy/economic_exchange/360687/。
⑨白秀峰:《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与中国》,《炎黄纵横》2011年第5期。
⑩清水正夫(1970)バレエ「白毛女」の創造(J),アジア經濟旬報(802),P1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