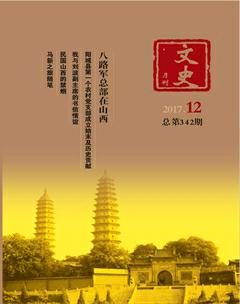民国山西的禁烟
介子平
193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二期《山西据毒月刊》上一则发自太谷的消息《女科犯被捕——粉头低垂泪双流》写道:“驻谷毒品稽查第二路第一队,于十四日下午四时余捕获女科犯一名。该犯系太谷县东北小常村杨姓某之第三妾,身穿粉红色丝布短袄,外套黑缎背心,下穿青缎镶花边棉裤,年二十余,姿色颇佳。在众目之下,粉头低垂,羞泪双流,颇有羞愧之意,倒绑两背,左右及背后有武装稽查跟随,武装稽查后,尚有怀抱皮褥毛毯之家人数名,垂头丧气,紧相追随云。”当时的祁太秧歌编有《劝戒烟》:“家住太谷住城北,自幼儿许配给了念书的,奴男儿把洋烟吃,水里营生懒待做,嫁一个吃洋烟的男人气断奴的肠子。”类似歌谣,全国遍唱。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名县志》载民谣曰:“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破席摆过照尸灯,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锈成一根棍,老婆暗与旁人混。大烟鬼,心中忿,要说打他吧,浑身没有劲;要说杀他吧,刀子卷了刃;再说禀他吧,官府封了印。到此时,常发闷。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1931年2月19日,阎锡山在指示太谷县长时特别提及该县现状:“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普遍,田野荒芜。”可见烟害在山西之严重。
从清道光初年,到国民政府成立时,鸦片流毒中国已有百年。为此,民众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非敌国外患所同日而语,其结果导致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军事孱弱,外交昏聩。从宫廷到民间,到处迷雾缭绕。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载:“内廷凡遇庆节演戏,召王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以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至,媵以烟泡三枚。犒赏之额,视官缺之肥瘠为等差,自十金至百金不等。光绪庚辰,俄人以索还伊犁事,几启衅。于时办理海防,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驻山海关。雷抵都,适孝钦万寿,得拜入座听戏之命。雷烟瘾极大,闻命深以为忧,乃浼人与内监商明,每小时必送茶一杯,每日六茶,每茶索犒千金,雷不得已从之。计听戏三日,而茶赏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为第一阔烟茶也。”徐珂《呻余放言》云:“山右之太谷、介休、祁县多富室,而男丁不蕃。相传保富之法,于男子之将届成年者,为其娶妾,并授以鸦片吸具,则为烟色所困,而无用财之他途。于是黄标紫标,绵延弗替,然烟色二者,为伐树之双斧。断丧既甚,生殖力锐减矣。”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中,曾描述清末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形:“中国人一般将鸦片称为洋烟。我的妻子说:‘访问中国家庭时,他们常常向我递上烟枪,妇女们见我拒绝就会表示惊讶,说她们还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呢。”郭嵩焘临终遗嘱竟有“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条:“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可见当时国人吸食鸦片之普遍。
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与英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海关税则》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翌年,民人买食鸦片亦得允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清廷曾统一对土药实施税厘并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筹集“庚子赔款”,又对洋土药也推行了征收政策,这使信誓旦旦、奔走呼号的禁烟者莫衷一是,不知所措。夏颂莱填词的《何日醒》痛心地写道:“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临。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实行“禁烟新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初三颁布了禁烟谕令:限种罂粟以净根株,分给牌照以杜新吸,勒限减瘾以苏痼疾,禁止烟馆以清渊薮,清查烟店以资稽察,官制方药以便医治,准设善会以宏劝化,责成官绅以期督进,禁官吸食以端表率,商禁洋药以遏毒源。据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载:“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除连颁谕令,要求各省督抚、将军严厉禁烟外,还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将禁烟方法、措施具体化。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清末,全國大部分地区鸦片种植已根株净尽,烟馆已全部关闭,鸦片吸食者显著减少,鸦片进口与销售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因逊清政府之政令不行,而革命军政府则无暇顾及烟禁,故各省愚民因贪图小利,多偷种烟苗,致鸦片毒卉几有复萌之势,即已报禁绝之省份亦复种植。至于吸食及兴贩,更随处皆是。1912年3月2日,孙中山颁布禁烟令:“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而嗜者不察,本总统实甚惑之。自满清末年,渐知其病,种植有禁,公膏有征,亦欲铲除旧污,自盖前蛊。在下各善社复为宣扬倡导,匡引不逮,故能成效渐彰,黑籍衰减。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锢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中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本总统有后望焉。”此外,他还要求内务部“迅查前清禁烟各令,其可施行者,即转咨各都督通饬所属,仍旧厉行,勿任弛废。其有应加改良及未尽事宜,并著该部悉心筹划,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政府即发议案要求:“各省情况不同,应由督抚提交各该省咨议局妥慎斟酌办法,作为本省单行规则,一律施行,务以能达禁烟之目的为止。”各省也相继成立禁烟处,负责督办禁烟事务。随后又提出销烟限证管制,烟民登记制度,设立戒烟所等一系列措施。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歌唱集》收录有华航琛作词的《戒鸦片》:“叹鸦片输入中原,流毒正无穷。看年年无数金钱,输出实可痛。愿我同胞快禁绝,富强甲亚东。叹鸦片弱国病民,贻害实无边。看人人曲背扛肩,憔悴实可怜,康健乐天年。”戒毒在民间也得到了积极响应。endprint
然各省军阀挟兵自重,包揽地方税收,苦于筹饷乏术,乃视鸦片为其绝大利源,于是勒民种烟,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而裕饷糈,以致烟祸危害丝毫未减。此风一开,大小军阀群起效尤,演成国内争战滔天大祸。四川因各军皆以烟税为重要财源,全省一百四十余县,不种烟者,殆不及三、五县。至1930年,全国鸦片总产已达1.2万吨,七倍于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遥居各国之首。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无非两大原因,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改;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后者尤胜。
罂粟的种子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云南,后又传至川、贵、甘,再传陕、晋。19世纪中期,山西种植罂粟就已经相当普遍了。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十九年(1839年)在一份上谕中指出:“朕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最初山坡水湄偶尔播种,后来近则沃土肥田。晋省形势,南路重山复岭,绝少平原,北路固阴冱寒,每忧冰雹,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安得不匮。这样使得“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米粮”,“粮食渐缺,粮价日增”。道光元年,道光帝在上谕中曾指出:“山西太谷、介休等处竟有富商大贾贩此牟利者,著成格饬属严查,将贩卖之人拿获,按律惩治,勿令渐染成风,有伤民俗。”咸丰九年(1859年),山西巡抚英桂于省城设立筹饷局,规定行商“外来洋药、土药于入境之卡,土产药料于出境之卡,每百斤抽银三十两,再于落地行销处所抽银九钱三分八厘”。同时又规定本地有栽种罂粟者,计其药料收成多寡,在纳完正赋之外,按两纳厘。政府采取加征厘金税的办法,实际上使得种植罂粟合法化,纵容和助长了罂粟的种植和继续泛滥,鸦片种植业便以空前速度在各州县蔓延。同治年间,山西广种罂粟造成粮食产量减少,粮价上涨,引起清廷重视。到光绪初年几于无县无之。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曾忠襄公奏议》云:“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光绪初年,曾任山西学使朱酉山幕僚的许珏初入晋时,已为那里的罂粟种植之害所触动,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再到山西时,“亲见连畦接畛,遍种罂粟,視光绪初年增多且将十倍”。且“今内地自山陕陇蜀以至滇黔,遍种土药”。对于种烟日多的原因,其认为有三:一是种烟比种粮利厚,“晋民谨愿不敢亏国赋,而自昔年大祲之后,人民凋落,雇人种田率不足偿佣值,恃有罂粟始可酌盈剂虚,以致愈种愈繁”。二是当时社会上流行“以土药抵制洋药”的说法,“议者妄谓藉此可以抵制洋药,乃外洋贩运如故,而内地种植益繁”。三是地方官吏贪图土药税厘而鼓励种烟,在山西“自大同南至省城,沿路所见膏腴之地,遍栽此毒人之物。讯之土人,皆云官吏许民种植,但令少种路旁,多种僻地而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西全省的鸦片种植面积,据当时《农学报》记载:“山西莺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其中“太原一百七十六村,共种土药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七分;榆次一百五十村,共种土药三千零十三亩三分;交城一百四十五村,共种土药三千五百七十三亩八分;文水一百七十五村,共种土药四千三百零二亩五分;代州一百九十四村,共种土药五千零九十六亩七分;归化一百六十一村,共种土药四千八百八十五亩一分。”合计共30503.8亩。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统计数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西全省每年产鸦片30000担,居全国第5位,合计为300万斤,若以亩产20两计,约占耕地120万亩之多。至宣统元年山西产鸦片11620担,居全国第4位。在湖北省于1912年11月发布禁烟新令:“凡云贵川晋四省土药,一律不准运入鄂境。”山西烟土以“味好劲足”而名世。
瘾民数量少,种植面积小;瘾民数量多,种植面积广。另据《中国宣教会百年史》记述:“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国内地会于成都设有戒烟所101处,于太原(指山西全省)设立71处。”晋商以经商著名,为牟取暴利,开设烟馆竟也在其列。烟馆处有联曰:“一呼一吸精神爽;半吞半吐气味长。”“灯光不是文光,偏能射斗;文将并非武将,亦善用枪。”晋省烟土之多,烟民之众,言之骇人听闻。1904年10月16日,天津《大公报》记载:“晋省土药出产甚多,男人之吸烟者几居十之五,女人之吸烟者几居十之三。吸者半属苦力之人,古晋地虽贫瘠,工价甚昂,缘工人每日所入除衣食外尚须筹烟资也。”吸食品的花样且在不断翻新。种烟日繁,必致吸烟日盛。许珏《复庵遗集》云:“每询诸人,不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室而九,即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人而五。以予度之,当不至若是众也,意者十户中必有二三,十人中必有一二欤。或曰山西吸烟有‘留人不留户之谚,谓间有不吸之人,断无一家全不吸者。”
罂粟自印度南洋传入至民初为鸦片时期,民初至民十五六年间为金丹时期,之后为器械泡时期。全省上下,上至官吏士绅、富贾地主,下至差衙走卒、贫下中农,染此瘾者,数不胜数,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而风尚所及,争相效尤,不念前途,甘心沉湎毒窟,虽蒙斯害,尚不知有所警惕,故山西为禁烟的重点区域也。清源县有民谣曰:“鸦片烟,吃上瘾,辫子结成饼,腰里捆草绳,婆姨跟别人,田产卖干净,衣裳不完全,卖儿又卖姻,他说不心疼。”又:“鸦片烟,上了瘾,头上发,缠成毯,儿姻不过问,婆姨跟别人,家产都荡尽,死在墙脚跟。”按县禁烟考核办对散发药饼数目的统计,清源县有烟民3081人,其绝对不止此数,因一烟民领饼后,会有数人分食,估计数字在三倍以上,且还有吸食器械泡及海洛因者,尚不在其内,而吸食芙蓉膏者,绝对不吸食器械泡,吸食器械泡者兼打高射炮者。
中国数十年来致今日贫弱之弊者,其咎安在?盖在民间吸食鸦片烟而已。许珏《复庵遗集》认为鸦片烟毒之害,首先是耗银甚巨,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其次是毒人身心,败坏风俗,“士大夫一经耽此,则志趣卑污,习为苟且,而人才日坏;小民一经嗜此,则身家倾荡,流为匪僻,而风化愈漓”。再者是病民贫家,“今则一朝耽好,终身废弃;一夫成瘾,八口皆饥。种植愈广,受祸之人愈多”。“向之力能作工者,既种则无有不吸,未几而不任作工矣;向之有田可种者,既吸则所入无余,未几而并鬻其田矣”。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随笔》载:“一日至戚家,见其夫妻反目。询其故,戚告曰:‘余吸洋烟,拙荆为我煎烟不善,故至反目。予曰:‘贤哉!此司炊之主妇也。居中馈有人矣,胡反目为?戚曰:‘目下烟土价昂,不敢浪费,令其酌量搀和烟料。乃彼不善调和,或搀入太多,不能过瘾;太少,则多费烟土。训之不服,以是反目。予曰:‘搀和匀停,此须有料量之学。孔子为委吏,料量平。此圣人之学也,妇人乌能之?戚大笑,其妻亦掩口而笑,和好如故。”这则故事反映出了烟土对吸食者家庭的财务压力。endprint
烟害戕兵耗财,危及国本,山西作为烟毒大省,从曾国荃到张之洞,历任巡抚皆力主禁烟,且取得一定成效。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曾将曾国荃的禁烟奏折与山西制订的《查铲罂粟章程》向全国推广,勒令各地“一体严行查禁”。张之洞主政山西后,上奏请求在查铲罂粟之时,设戒烟局,劝戒吸食,移风易俗,加强综合治理。然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云:“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宣统二年(1910年)夏,曾在交城、文水一带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交文禁烟案”。清廷于宣统元年通令禁绝私种罂粟和吸食,但到次年时,交城、文水一带不仅未禁,且广为种植。时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居然向朝廷诳奏“晋省完全禁种,吸食者亦即绝迹”。为此,清廷于四月间欲遣钦差大臣来晋察勘。文水县令刘彤光为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翌年,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遂派夏学津率兵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图画日报》以“是豺狼也”为题,对其进行了叙述:“山西交城文水一带,居民因种烟苗,被官兵惨剿,刻已敉平。当统带夏学津驻扎交城时,城内西大街有郝某者,为人愿谨,家仅中资。二月十一日,突有兵数名,闯入其家,调戏妇女,肆行非礼,郝某上前恳阻,被一兵劈头一刀,立时毙命。”《晋阳公报》因揭露丁巡抚以禁烟之名,屠杀两地百姓暴行,遂以“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的罪名遭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出逃。
民国之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于1916年提出了“用民政治”,其以“六政三事”为中心,禁烟乃“六政”之一,同时还设立了“禁烟考核事务所”。之后发布的《人民须知》专设《戒吸烟》一条:“洋烟毒人的利害,人人都知,不必细说。如今又添了各样玛非、金丹等物,毒化比洋烟还大。从你们吃烟的一个人说,吃得熏死;从吃烟的一家说,现在洋烟金丹都是很贵,必定要吃的穷了,甚至于家败人散;从一省上说,每年买外处洋烟玛非金丹等项,大概费洋钱一千万元,所以近年来各县都少现洋现银,多是不兑换的纸票,弄的粮食很贵,百物都涨,连好百姓也跟上你们受害了。本督军结实告说你们:这洋烟、吗啡、金丹非禁不可,要不听本督军的话,就是枪毙你们,也不爱惜的。因为你们吃烟,害了自己一人其害还小,害的一家老老少少受累,害的国家和地方都受穷苦,这真是罪孽太大,不能宽容的。”仅1918年,即“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烟丸(金丹)共四千多起”。阎锡山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称:“窃查中英禁烟条约内载:‘民国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为全国种烟禁绝期,六年三月至六月为全国吸烟完全禁绝期。山西禁烟一节,早经呈报肃清,运烟、吸烟,亦各依据条约期限,次第禁绝在案。惟以向系产烟最旺省份,吸食之户,比较他省尤多,六年六月吸烟禁绝以后,官厅赓续查禁,不遗余力。而前此烟民,因戒后犯病断而复吸,或吞服代用药品者所在多有;又兼以山西北界内蒙,西邻秦地,近数年来盗匪骚动,出没无常,黠民乘机窃种,奸商无赖,藐法输运,希图渔利;贩运一日未绝,则吸食一日难净。近复以烟价奇昂,由外阜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实繁有徒,非假借洋商名义,即冒充入口货物,稽查既难,破获非易,纵即发觉,因罪行甚轻,不足蔽辜,侥幸之心,未能消除。查吗啡之毒:施打,则残毁肢体;吞服,则腐烂肠胃;其害更烈于鸦片。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及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各县因无现款,纯用纸币交纳省库,名为收入,其实废纸。综上各情,不得不通盘筹划,另图禁烟方法,以扫除余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副,一律按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办;于治疗期间内,发觉吸食毒品、施打吗啡及吞服含有吗啡之药丸者,仍依法分别治罪。至于禁运一节,迭据平阳镇守使,河东道尹,暨荣河、兴县知县,离石驻防连长,及本署密探报告:‘陕西匪徒,本年大种鸦片,拟运入山西售卖,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1920年,破获案件1.8万起,比前年增加四倍。据《介休历史纪事》载:1923年,介休县知事杨瑞鹏在城内关帝庙及三官楼巷、温家巷民宅设立戒烟所,各村烟民分批前来检查,轻者由村长领回,重者服“曼陀罗戒烟丸”,强制其戒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不得不面对痛遭国人谴责的鸦片毒品泛滥问题。1928年7月,颁布《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会议,研究各项禁烟问题的症结,厘订切实有效的禁烟措施。11月,全国禁烟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议决有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各种议案44件,并发表宣言,指出要“毅然痛割寓禁于征之秕政,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厉行铲除烟毒之计划。”随后,山西省政府颁发了《禁毒烟事告谕人民文》,要求烟民:“由民国二十五年起,按年岁分五年戒烟。一、二十五年年终止,三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二、二十六年年终止,三十一岁以上三十九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三、二十七年年终止,三十九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四、二十八年年终止,五十一岁以上六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五、二十九年年终止,六十一岁以上者,一律戒绝。”处罚也十分严厉:“在应当戒绝年岁,而不戒绝者,处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自己愿意投戒,戒绝后又吸食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百元以下罚金,并限制交医勒令戒绝,经勒令戒绝而后又吸食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并限制交医勒令戒绝,三犯者处死刑。”对贩卖或運输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其数量在五百两以上者处死刑,贩卖或打算贩卖而持有或运输罂粟种子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另有对“打算营利以房屋供人吸食鸦片者”“利用限期戒烟执照而供人吸食以营利者”“帮助他人犯吸食鸦片之罪者”也都有规定。虽屡申禁令,犯者仍不绝。endprint
禁烟乃苏民气、疏财路,发展民族工商业之基础。许珏《复庵遗集》云:“吾意始禁一二年后,食必果腹矣;又一二年后,衣之破者完,屋之颓者整矣。时则民气渐苏,民心渐奋,惰者思勤,弱者思强,向之贫者可免于贫,富者日以益富。方是时也,太原以东之铁路已成,盂平、泽潞之矿产渐出,晋民见矿路股票可以获利,必将出其积年所蓄悉数购归。计其时,总在五年以后、十年以前,固无俟远期也。”烟禁虽不绝,只是稍有成效,尽管如此,不出十年,正太铁路经过三年建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线竣工通车。第二年,集煤铁于一身的保晋公司成立。1920年,保晋铁厂用现代化技术工艺炼钢成功。1924年,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1928年,太原兵工厂以为北方之最。1933年,西北实业公司成立。贯穿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1933年5月开工,1935年12月即竣工。中国欲求富强之术,其速而易效者,无过于禁烟。
然山西禁烟后,使毒品价格猛升,周边省份的烟土纷纷流入市场。据1918年7月18日上海版《民国日报》载:“陕省陈树藩前以要求地丁押款不遂,乃大开禁烟私种烟土。曾经内务部派员查办,而该督尚诿为土匪所种,非彼势力之所能及,故电使空驰终归无效。近更私连各地,充斥晋边。闻阎督军恐此项烟土运至晋省影响民间,特于前日订定禁烟条例十二条,凡能拿获烟土一两者赏洋二十元,携带者处死刑云。”刘镇华督陕时,每年烟税收入都在1500万元以上,超过全省田赋的一倍。其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从者增收“白地款”13元。军队不仅给鸦片商贩充当保镖,且组织贩卖。陕西鸦片入晋通道有三:南部由大庆关入蒲州、解州,中部由兴县、离石、中阳、石楼渡口入,北部由河曲、保德入。当初公子夷吾是得到秦穆公的帮助才得以继位为晋惠公的,所以包括秦穆公在内的秦人都认为晋国欠秦伯一个人情。惠公四年(前647年),晋国发生旱害,国内粮荒,晋国遂向秦国借粮。秦国内部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仅不应借粮,还应趁机发兵于晋;另一派认为,应实行仁义,借粮予晋国。秦穆公采取了第二种意见,发送义粮给晋国。两年后,秦国也发生了饥荒,秦国则向晋国借粮,晋国内也是两派对立,结果晋惠公背信弃义选择了出兵。晋人欠秦人的那个两千年的情,在刘镇华时期算是抵平了。丹料则自河南输入,抗战时期,日本人在河南博爱、辉县、林县、武涉、修武等地相继设立了金丹制造厂。博爱大辛庄一所名曰“中和记”的金丹制造厂,日产红丸5000袋,日收入可达5000万元。丹料进入路线也有三条,晋城一路,高平一路,长治一路。鸦片出自印度,虽地属英国,而英人严禁吸食,无一犯者。日本亦然,其严禁国民吸食毒品,自割我台湾之后,也禁台湾之民吸食,但对中国却倾销之。山西境内的吗啡、丹药等高纯度毒品,即由日本公司设在天津租界的工厂生产,每日自正太铁路入晋的毒品达2万元。对于洋药,晚期时的许珏曾提过全国各省齐力“以土抵洋”的主张,认为应“诚仿山西《议禁章程》,各省老病之废人均吸本地土药,则洋药来华无过问者,势将不禁而自绝。纵或沿海省份不能照腹地省份一律办理,然吸者既少,则洋药之来源必衰。”在提倡禁毒的同时,却建议以土毒攻洋毒,真乃无奈之举。鉴于此,有人规劝阎锡山开禁烟片种植,阎在1932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政府亦当有所不为,有劝余开种烟禁,借以减社会之输出,并可救济财政之不足者,是不知为之道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更是怂恿其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并公卖毒品,开设烟馆,先前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日本人还特设了经营毒品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致使毒品迅速蔓延到所有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1939年10月,“兴亚院”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毒化政策,奖励吸食毒品,借以达到增加税收、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收的资料,“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在沦陷区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以南京为例,当时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在浙江吴兴一县,就有烟馆200余家。
1939年,伪山西省公署规定每县必须种烟3000亩,并以“罚款”的名义,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伪市长苏体仁对其民政厅长宋澈、财政厅长宋启秀说:“现在绥远大种罂粟,进入我省做成料面,一出一进,漏卮很大。不如我们大开烟禁,一则可以以毒攻毒,二则可以活动农村经济,你们看如何?”(见《日伪时期的山西省政府财政厅》,《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平遥、崞县、代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还强迫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可将毒品私运对方,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出一条无粮带,并在此区域设立制毒工厂。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
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因鸦片毒品致死者达1500余人。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在运城,其毒化工作由日本宪兵队附属的密探队进行。密探队员皆当地不务正业者,且为瘾君子,其报酬不是薪饷,而是日军按月发放的海洛因,这些无耻之尤为获得毒品,甘心做任何事情。中国人好赌、好抽的心理,日本人很是了解。太原的一些私贩毒品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则摇身变为公开贩毒的“商会”或“公司”的老板,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其目的在于把中国人永远变成“东亚病夫”,以便长期奴役之,同时实行经济上的掠夺。日本军方曾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中国近代的开端自鸦片战争始,国家的衰败与兴起竟皆与此有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自甘堕落、昏昏噩噩的国民,不知有多少志士为之泣血宵呤,扼腕长叹。呜呼!精神無根,随风摇摆,闲散寂寞,百无聊赖,凡事缺乏判断,只愿随俗而行,鸦片似可医此等空虚,殊不知沉溺既久,适得其反矣。倚之如身家性命,视之如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由此勤农转懒汉,富家变破产,民籍卖妻鬻子,官吏吞挪公项,人不可救药,国病入膏肓。文明在启蒙,富强在启智,禁烟何不然。否则,烟是禁了,但烟瘾还会以另外的形态不时出现。启蒙与救亡,启智与强盛,是那个时代未完成的主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