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森?怀特黑德:我想虚构,充分地虚构
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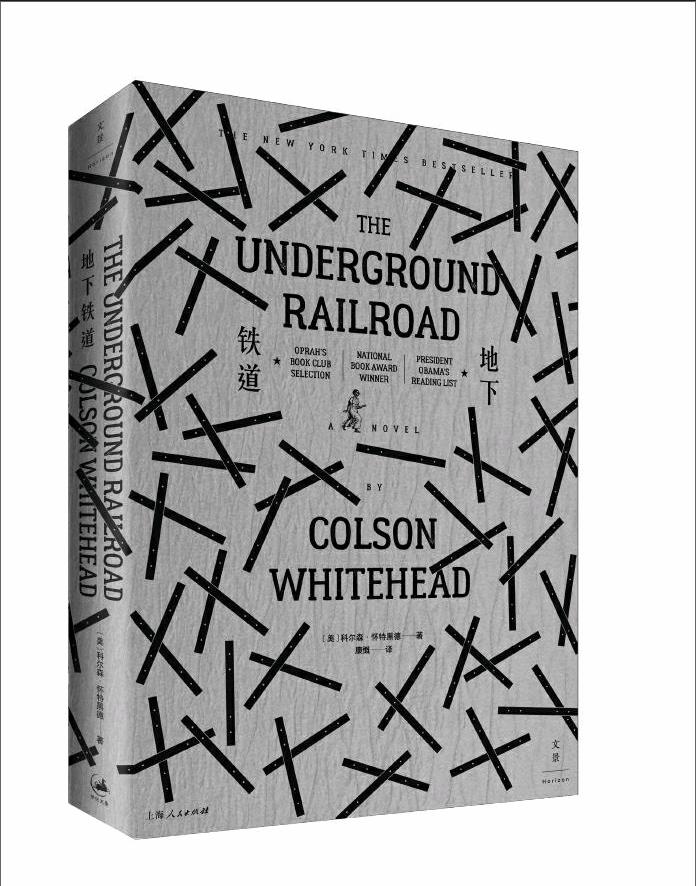

1980年代,纽约上东区,有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在杂货店里买啤酒,准备随后去参加朋友的派对。一个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没有废话,直接要求他把双手放在背后,再把这茫然的男孩带到警车旁,拷上了手铐,理由是:几个街区外有位白人女士被抢劫了,而这个男孩是警察发现的第一个黑人少年。幸好白人女士摇摇头:不是他。男孩这才被警察放走。事实上,男孩并不是很惊讶,因为父亲早就告诫过:我们一出门就是显眼的目标。在那个年代,有好些年轻黑人在城区里闲逛时遭到殴打,甚至被打死。但对这个男孩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切身体验到种族歧视。
虽然住在上东区,但这个男孩的家族史绕不开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他的祖母在1920年代从巴巴多斯岛来到美国,那个岛就是一个很大的种植园,产糖;而且,众所周知,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压迫更为残暴。他的外祖父也曾为奴。只要往前追溯一百年,就会发现:黑人家族中会经历不同形式、不同区域的奴役。“我的父母不会把黑奴历史天天挂在嘴边,但他们会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有多么严重,问题在于你要如何面对这种状况,并在这样的国家里拥有幸福的生活。”反种族歧视的进程迂回、漫长又艰辛,但始终在往好的方向走。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有一天他为了参加活动特意打了领带,十一岁的女儿很高兴地说:爸爸你看起来就像总统!这话在他听来别有意味:说明女儿这一代已不再認为有色人种当总统是天方夜谭了……但他还要跑遍全世界强调种族歧视依然严峻的事实。
如今,这位名叫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大男孩依然生活在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娶了一位美貌聪慧的白人太太(她是一位成功的文学经纪人),养育了两个孩子,并因描述黑奴女孩逃离种植园的小说《地下铁道》勇夺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再于2017年摘得普利策奖,并入围布克奖决选。
《地下铁道》势如破竹,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书还没上市,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就选定了此书,激动的经纪人在科尔森·怀特黑德的语音信箱里(当时他在飞机上)只留下“奥普拉”一个词,飞机落地开机后,怀特黑德听罢留言,当即大声爆了句粗口(激动时的本能反应),引起乘客们的一致侧目。《地下铁道》上市后仅用四天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两周后便升至榜首,并持续占据数周。不久后,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此书列入夏季书单。仅仅过了半年多,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的编剧、导演巴里·詹金斯就宣布参与本书改编的美剧制作,将本书引发的“现象”推向新的高潮。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不是“双奥”的推荐——在于怀特黑德巧妙地改写了史实,缔造了文学性的地下铁道。在美国历史上,“地下铁道”本是比喻性的说法,指的是美国内战前民权活动家们为帮助南方种植园中的非裔奴隶逃往北方自由州和加拿大而设立的秘密路线网络及避难所,延伸至14个州以及加拿大。
怀特黑德在17年前写John Henry Days的间歇躺在沙发上打瞌睡时突发奇想——如果真有一条在地下的铁道呢?用文学手法塑造出与史实大同小异的另一个平行世界,岂不是很赞?但又觉得这仅仅是个idea,太单薄。事实上,他在四年级时以为那条铁路真有其事,长大后才得知那不过是比喻修辞,顿感失望。这个灵感显然源自儿时的失望,得益于常年写作后的文学思维方式。 但当时的他觉得自己功力不够,人也不够成熟,不见得能驾驭这个题材,所以搁下,忙于别的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想起这个题材,自问能否开始?答案都是No。直到三年前……
事实上,怀特黑德此前已出版了七部作品,但奥普拉都没有读过,奥巴马大概也没有。
有些读者是循着僵尸的足迹(Zone One)追到他这本《地下铁道》的,还有些(更聪明的)读者循着他的第一本小说Intuitionist(直觉主义者)到后来的Sag Habor、John Henry Days,一路追到黑奴科拉,才能确定怀特黑德十多年创作光谱中的主色调:黑色——黑人在当今美国社会、中产背景中遭遇到的或明或暗的偏见。
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黑人作家身上,我们看不到流行文化领域中的黑人明星常有的浮夸、饶舌或愤世嫉俗,恰恰相反,他给人以一种“二次元交往会更有趣”的错觉。他坦言自己不爱出门,教创意写作课只是为了挣钱再回家死宅;他写了很多扑克牌手的故事,尤爱描写在室内都戴墨镜的poker face;他和在中国、在日本的七零代一式一样,都是伴随电子游戏和漫画书,在二次元英雄主义(夹带恐怖暴力)的熏陶下长大的。
在2012年6月的《纽约客》上,怀特黑德发表过一篇名为A Psychotronic Childhood的自传体长散文,标题可暂译为“精神力的童年”,但重点在副标题:Learning from B-movies,从B级电影中的所学所得。
开篇就点明自己从小就宅,有点小病态: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别人家的男孩都跑去家门外运动,他只喜欢瘫在客厅地毯上看恐怖电影。那是VCR和DVD和网络电视都尚未普及的1970年代,对那时的小孩来说,这无疑是很前卫的爱好——夹杂着某种早熟的忧虑,害怕此时不看,就再也没机会看到这些制作拙劣的低成本恐怖片了。恐怖延伸到惊悚,惊悚延伸到外星球,四年级时,他已把《星球大战》看得滚瓜烂熟,从此陷入科幻魔域,至今无法自拔。
那时候,纽约城里播放这类影片的影院通常都很破烂,后座有人抽大麻,地板上有臭虫爬。多年后怀特黑德写了自己的恐怖僵尸小说,回头再看,原来童年时已留下了最原初的恐怖教养,从小就已懂得“怪物,就是不再伪装自己的人”。1979年看过《活死人黎明》后,他开始做一系列的僵尸主题噩梦,情节随着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活重心而有更新,但总是在被僵尸追赶。直到他写完Zone One才意识到:除了梦境,这些僵尸还可以有个好去处。
1981年怀特黑德搬入了新家:位于五十七街的一栋崭新的公寓楼,并添置了家庭影院。小宅人就有了新任务:去租碟。他和弟弟很快就独霸了家庭影院的播映权。“我们把火鸡大卸八块,大快朵颐,吃完后就重聚在起居室里,看(电影中的)某些人被大卸八块,或大快朵颐。我们看到那些套路就会笑:黑人总是先死……”
提及恐怖教养,不得不提到怀特黑德的母亲,娘家在弗吉尼亚,家族经营着一家葬仪社,也就是说,在家里的地下室里完成整理死者仪容和防腐的工作,继而操办葬礼,活脱脱是美剧《六英尺下》的黑人版。如今,这家葬仪社在新泽西,仍由怀特黑德的姨母打理。不难想象,这家人常常谈论死亡的话题,而且都很喜欢看恐怖電影——感恩节的保留项目就是吃完火鸡,看两三部恐怖电影。
1980年代有很多“失血过多”的电影,尽管怀特黑德还不能给好电影、坏电影下定义,但显然已经熟悉了类型创作:库布里克翻拍了斯蒂芬·金的《闪灵》,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奠定了变态连环杀手的原型,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衍生出一系列惊悚佳作,包括怀特黑德一向钟爱的《魔鬼雨》。这些电影教会了怀特黑德一件事:艺术家可以将各种元素拼贴组合。八年级,他就写了一篇论述《录像带谋杀案》小说化的论文,作为英语课作业交掉,并拿到了A。到了高中,怀特黑德也不太约会,弟弟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却越来越宅……最爱的书包括电影史上的奇作:Michael Weldon所著的The Psychotronic Encyclopedia of Film,涵盖了三千多部另类小众电影,好比是前谷歌年代的信息源,立刻成为他爱不释手的案头书,也教会了他一点:就算是看起来超离谱的一个idea,也有可能获得生机,成为一部佳作。
过了二十岁,怀特黑德基本上跨过了B级电影阶段,成为有创作意识的青年作家。毋庸置疑,早年的这些影响深深镌刻在他的头脑里了。这应该可以解释他为何一出手就是脑洞很大的科幻政治隐喻小说,又为何念念不忘类型小说:“在创作《直觉主义者》的时候,我本人就是个不可理喻的怪奇生物……之前我写过一稿,但被位高权重的经纪人毙了,所以我就再写一遍,有点愚公移山的味道。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继续写,如果这意味着远离普通受众的领域、进入精神力者的另类世界,那就这样好了。”
就这样,直到三年前,那个超离谱的idea依然脉动在怀特黑德的头脑里。
去年一年,怀特黑德东奔西跑为这本书做宣传,完全奉献给了媒体和读者,光一个夏天就赶去了苏格兰、挪威、丹麦、瑞典。九天里跑遍四个国家,对于一个从小就宅的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旅行,前所未有的高能社交,但他应付得不错——衣品时髦,每一套都有亮点,足以上照;应对自如,针对这本书的每一种问题他都已回答了千百遍,索性把问题汇集起来,完成了在上海的唯一一次公众演讲。为了避免出错,他把iPad搁在膝盖上,时不时地看一眼预先写好的讲稿,就连笑话也好像是预先写好的。
他穿着黑衬衫(花边袖口和领口)、镶黑边白皮鞋(配红黄格短袜),略带拘谨,以标志性的自嘲开场:“现在是美国时间的中午,通常我都在家里,回想自己曾有的失败痛哭不已。所以这个礼拜来到中国,备受礼遇,感到特别高兴。”
然后,他告诉大家这本传奇的小说是怎样从idea变成屠榜神作的:“婚姻生活中总需要制造话题,免不了和太太讨论自己的写作,她认为:相对于布鲁克林作家的中年危机,地下铁道这个idea好太多了!我又和合作十八年的经纪人谈起这个idea,经纪人也说好,还前所未有地在周末追了电邮过来:这个主意特别好!最后一票来自我的心理医生,她反问我:你是疯了吗?大家都知道你很疯,但这件事真的值得做!”
三十岁不到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就是个loser
Q:《地下铁道》让更多人认识了你,以及之前的七部作品,但我们还不太了解你。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以写作为生?
A:十岁开始我疯狂地看《蜘蛛侠》那类漫画,还有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还有The Twilight Zone——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知道这部黑白电视剧……总之,我十岁就认定:当作家是个很酷的职业,随心所欲地编造吸血鬼、机器人的奇幻故事,多好玩啊!而且可以待在家里!
Q:那么早啊!所以是有目的地进入高等学府,为了完成自己的文学梦想?
A:当然,一直到读大学,我才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梦想,主修英美文学,但我不只是想写纯文学,也想写科幻,写了一大堆吸血鬼……
Q:从作品年表上看,你的文学梦之路还蛮顺畅的,如果拿到布克奖,坊间就会赞你是大满贯得主!
A:这个嘛,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写下去会得奖……三十岁不到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就是个loser,写了部长篇小说,但人见人不爱,被二十五家出版社拒了。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再写一部——虽然已经写了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期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总之,我不会再去法学院之类的地方进修,我别无选择,只能从头再来。
Q:真的想过去法学院?
A:唉,父母都希望你有份正经的工作,当律师、医生、银行家……都是衣食无忧的好选择。我明白父母觉得写作不太靠谱,所以毕业后我先去《村声》杂志社当记者,当编辑,那段经历教会我如何与人合作,如何编辑自己的作品,如何保持自制力,如何按时交稿——以便按时采买日常用品。
Q:第一本书没卖出去,也没有找“正经工作”,那你从何时开始确定自己可以完成文学梦?
A:第一本书没人买,写第二本(《直觉主义者》)时我就想在情节上多下点功夫,把结构支起来,可以玩转人物和情节。重点是写一个不像我自己的主人公,所以我写了女性主人公,也做了些重要的尝试:不用第一人称,不融入自己的形象和声音,注重结构和情节。那之后,我决定当一个好作家。
Q:你似乎一直很刻意地要求自己不要写自己的故事,譬如说,很多人会对你母亲家族“六英尺下”的故事很感兴趣吧,但你不想写。
A:事实上,我的第五本书是自传性质的,写了1980年代的纽约。至于家族故事嘛,其实我并没有涉入很深,葬仪社是我外祖母家的企业,我小时候去过几次,也许有朝一日我真的会想写一部母亲家族的故事,那我得先去外婆家好好了解一下。
Q:同样,你也一直很在意设计结构。《地下铁道》让人想到《格列佛游记》和《奥德赛》这样的经典史诗的结构,有趣的是,也有人会觉得更像是《行尸走肉》《饥饿游戏》这类当代影视作品的结构……
A:《格列佛游记》《奥德赛》都是经典的叙事结构,远在《行尸走肉》和《饥饿游戏》之前,不过,这里有一条不变的脉络:经久不衰的故事里会有一个主人公经受一项又一项考验,始终坚持一个目标:回家,或寻找自由的新世界。你可以说这是古老的经典结构,但事实证明,新世纪的网络游戏也常用这个结构。
我记得,当年确定了《地下铁道》的结构后,我跟好多朋友讲过:主人公会一个州一个州逃亡下去,每一个州都有不一样的危机和场景,但很多人都觉得那挺傻的……我想他们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还是比较赞同前一个看法,确实更像奥德赛式的。后一个看法表面看也没错,主人公总是经受生死考验,幸存到下一站,又是崭新的生死决战,科拉被救,再被抓,再躲藏……这是保持悬念的叙事方式,悬念在于:她能不能逃掉。
Q:十七年前你先有了“把地下铁道写成真实存在的铁道”的idea,但三年前才正式动笔成文。这么长的创作过程里,有过哪些设定上的重大变化?
A:一开始主人公是逃往北方的男性,也许是为了寻找失散的爱侣,也许是为了追寻双亲,后来发现母女关系是我未曾尝试过的,所以决定挑战一下自己。
Q:有传闻说,是因为你有了女儿,对母女关系、家族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才把主人公定为年轻女孩……
A:为人父母确实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但把本书的主人公改成年轻的女孩,并不是因为我有了女儿(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前两本书都是男性主人公,不希望这本还是那个调调。我想让自己的几本书有截然不同的区分。
另一方面,Harriet Jacobs的自传也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阁楼里被迫躲藏了七年。她在书中写道,当女奴从女孩变成女人,所经历的奴役内容就会成倍增多:要生养更多孩子,给奴隶主带去更多收益……从这个层面讲,女奴和男奴的境遇是不同的,当然,都很凄惨,但用女奴做主角,会给故事带来更多的维度。
Q:很喜欢书中提到:对黑奴的压迫事实上从截断非洲语言就开始了,从根上斩断了黑奴的身份意识;自然奇观展示那段充满了画面感,也极具寓意;这些都能揭示媒体、教育会在根深蒂固的层面制造歧视,你如何得到这部分的灵感?
A:自然奇观的部分并不需要灵感:美国黑人在嘉年华、世界博览会等诸多场合都曾被展示过。这是史实。他们被迫穿上非洲衣饰,假扮土著人,而那就是白人们的娱乐项目。但我也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一些情节,增添了一点自己的想象。那是19世纪后半叶发生过的事,我让这段历史提前了。
科拉不知道“乐观”的意思,只是因为从没在种植园里听到过,也没人讲过,这也是个事实:他们没机会接触到这类词汇。还有一个事实是:我读书那会儿,历史课上可能用十分钟来讲奴隶制,四十分钟来讲林肯,跳过了很多惨绝人寰的事实,这也是美国教育的一部分真相。
我坚持的是真相,而非事实
Q:你曾坦言:“当我允许自己将‘地下铁道写成真实的铁路,我顿时感到自己可以自由地将(历史事件的)时间线前后挪移。(发生在黑人身上的)梅毒‘坏血实验其实是之后很多年才发生的事情,但为何不将它往前提一些呢?为何不让一些优生和绝育运动——这些看似善意的政府项目——发生得更早?将‘地下铁道这个隐喻进行艺术加工,使得我拥有了这样的创作空间。”由此把你的文学原创性发挥到了一个至高点。有没有担心这种虚构历史的文学手法会触怒一些忠于历史的读者?
A:我不担心啊(笑)。这是两码事:如果你不知道史实是什么,那说明教育机构出问题了。如果小说中的虚构、对史实的更改调动了你的兴趣,让你去探究历史的真相,那就是好事情。
科拉躲在阁楼的章节会让大家想到《安妮日记》,因为跨种族和文化的迫害是有源头的:先有1850年代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再有194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样,20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血统纯正主义,其实美国从19世纪就开始了。所有白人至上主义者读的都是同一种垃圾读物。
Q:就像奥普拉初读此书时曾把历史书翻出来,校验“地下铁道”是不是真的,这是文学的一种力量吧:唤起读者对某一个主题、某一种命运的再度关注。
A:是的。小说是虚构。我不是在写历史书。我坚持的是真相,而非事实,尤其是发生在某一个奴隶身上的事。
Q:为了搜集素材,大部分时间要泡在图书馆或资料馆里吗?
A:哦,完全不用出门,不用泡在图书馆里!美国政府从1930年代开始做了一系列黑奴访谈纪实项目,这些可以说是书中种植园故事的蓝本。都是公开存档的文献,在各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网站上都是公开的,数码化的。在正式写小说前的几个月里,我大概每天都会上网查阅资料,几个小时吧。老实说,这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不想出门。也不需要采访,因为涉及的那个年代的人都不在人世了。我只是去了一次南方的种植园,两天而已,去看看。
Q:虽然你的书也要翻拍成电视剧了,但眼下就有一部名为Undergroud的电视剧,也是讲黑奴逃亡的,其中有提到William Still,这引发出另一个有关史料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写与这个地下组织相关的真实人物?
A:因为我写的是文学作品。我没看那部电视剧,但我知道这个人物,在很多口述历史中都会提到他帮助黑奴逃离奴隶主。他是真实存在的。我没写他,但电视剧会写到他,这就好像……你看过多少二战的电影和书籍?永远不嫌多。我不写他,或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就是因为我想虚构,充分地虚构。
Q:这是否也是虚化地下铁道建造者组织,但强化埃塞尔、斯蒂文森这些小人物的原因?
A:只写一个故事的话,就无法表达在很多事情上的思考,也无法纳入不同时代美国的问题,我想可以把它们mix&match在一起。那些专门描写配角的章节,我称之为“小传”,希望它们能辅助主人公,用他们的人生照亮科拉看不到的世界,拓展这本书的时空跨度。写这些辅助人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导演,允许很多人来试镜,譬如埃塞尔,她代表了19世纪主流社会中的女性,受到当时社会准则的约束,她就很适合出演那个章节。
Q:对你而言,黑奴的主题在你八岁、二十岁和现在的意义是不同的,你是否把自己思想递变的过程融入这本书的写作?
A:我并没有刻意地把自己不同时期对奴隶制、对自由的想法灌输到这本书里。因为结构的限制,我不可能在一本书里谈论所有的议题、人物和主题。十七年前的闪念过后,我结婚生子,写书谋生,步入中年,对很多事才有了真正的思索,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考虑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或伤痛。对你这个问题,直接的回答是NO,但我也承认,假如二十岁时写这个故事,肯定和四十出头再写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四十岁的这次写作很节制:我强迫自己用六页写完了外祖母的生平,自然奇观那段控制在了两页里面。
Q:身为美国中高产阶级的有色人种,对于种族歧视等美国社会问题,你认为文学有怎样的推动力?
A:悲观地说,文学不能改变或推动现实。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社会仍有种族歧视的现象……自弗格森案件后,2013年开始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运动,但这些事并不新鲜,只不过人们会忘掉,直到下一次悲剧重演——从19世纪到现在,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多改变,甚至压迫有色人种的白人依然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系统:拦下奴隶的猎奴者,与拦下黑人的警察羞辱黑人的语言是一样的……我们进步得很慢很慢,也确实希望情况会向好的方向改变。
想当年,Upton Sinclair 的The Jungle、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之类有革命意义的作品让北方人看到了南方种植园里的残酷真相,虽然我写的书可能会改变当下某些人对奴隶制、对美国历史的想法,但注定不会再有当年那些书所产生的振聋发聩的效应。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迟钝的,很难快速地改变……(数秒钟的沉默)至今还没有。
现在的美国……当然,黑人有投票权,但种族歧视依然是个大问题。讽刺的是,这本书刚拿奖,就把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送上了总统宝座,美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有种族歧视的总统。总体来说,针对有色人种的不公平政策变得越来越有策略性了,可以说,“奴隶制”像是改名换姓后继续存活在各个领域。
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能维系住同一批读者
Q_《小说界》杂志
A_科尔森·怀特黑德
Q:说点轻松的话题吧——这么多年都是在一家出版社出书,你们如何维系这种有趣的、多样化的合作?
A:第一本书是被拒的,但我很幸运,《直觉主义者》出版了,他们从那时起就知道我是个不走寻常路的黑人作家,所以一直很支持我……毕竟,有些书卖得动,有些书卖不动,但我写的书刚好可以卖到让他们继续支持我的程度(笑)。
Q:看你的作品会发现主题、类型的多样化,觉得你挺任性的。不怕这样会无法积攒读者群吗(虽然现在已没有这种困扰了)?你会规划自己的事业吗?
A:我一直在变化体裁和类型,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可以维系住同一批读者!从来都不信!这件事也没法规划的。有些人喜欢我写僵尸的末世小说,但很不喜欢写扑克牌的那本;有些人喜欢写1980年代纽约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不喜欢写黑奴的这本……要说写作方面的规划,倒确实有一脉相承之处:城市文化,流行文化,种族问题——我的写作基本围绕着这三点,但不一定每本都涉及到。
Q:就是说:虽然表面类型不同,但骨子里有共同的原则和主张?
A:我希望始终能找到不一样的方式去描述、去探讨这个世界。我唯一的原则大概就是:不要翻来覆去地总是用同一种方式讲同一个故事。我希望自己能用上从小就热爱的漫画书、奇幻故事里的元素,让另一种叙述主题变得与众不同。我会选择不同的文学类型,挑出自己喜欢的,并用于我想写的题材之中。
像我这么大的美国作家,小时候都是清一色看七八十年代的漫画书长大的,人生第一次面对“故事”就是X-man的故事,你会去想:故事是怎么写出来的?更有趣的是,我们这代人已经长大了,变成了写书、拍电影的人——从消费者、阅读者变成了内容制造商——结果,我们的孩子是看电影版的X-man这类的作品长大的,这简直就是生命的循环啊。
Q:僵尸也好,黑奴也好,都算长盛不衰的主题类型,你如何保持自己的原创性?像《宠儿》《根》《为奴十二年》以及Frederick Douglass、Harriet Jacobs的传记等已有的杰出作品给过你哪些启迪和压力?
A:有时候,你打算写一个东西,肯定会去看别人、前人是怎么写的。27岁时我读完《宠儿》,觉得完蛋了,无论如何不可能写得这么好。后来呢?我想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你想写的题材,之前有人写过,而且写得很好,但你还是想写,那就写出自己的特色来吧!因为你永远无法和托妮·莫里森同场较量,事实上,这也不该成为一种较量吧?否则,你想着那些前辈,那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你必须要有这份自信,创造出崭新的作品——僵尸是个老梗,我就得找个与先前那些不一样的主人公;种植园里的黑奴要逃亡,这也是个老梗,我就得找个新的结构、新的虚构重点去讲述这个故事。
Q:坊间还有传闻,说科拉和西泽的名字颇有隐喻性:Cora好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地下世界女王,你是故意的吗?
A:呃……科拉的名字来得很偶然:就是朋友聚餐,席间有个女孩叫Cora,我觉得挺老派的,就拿来用了。Caesar本意是凯撒,没错,因为我想奴隶主会喜欢给奴隶起一些好大喜功的名字,其实是为了彰显自己有多能耐。真的没有别的深意……这算一次过度诠释吧。
Q:可以谈谈你在几所大学里教创意写作课的事吗?
A:我有一阵子没去教书了。我会和学生们谈自己失败的经验啊(笑)……我们会尝试各种各样新鲜的方式:就算你是18岁的姑娘,也别害怕把自己暂时变成27岁的小伙子,换个声音、身份來写作,你会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写作,或是不擅长。去教写作课,当然会花时间和学生们讨论写作的内容和技巧……但我只希望教一年的工资可以让我在家宅一年(笑)。
Q:全职宅家搞创作,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缺少社会经验?
A:对,我喜欢宅在家。家就是我的工作室。可以打个盹,再给自己做个三明治,但基本上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是我的固定写作时段。一周写好八页,大概这个速度,一年下来就有一本书的量。但我不是每天写的,有的时候一天写三页,隔一天再写两页。至于社会经验……我虚构了很多职业呀,这也算一种体验吧。
Q:喜欢旅行吗?
A:这一年,为了这本书没少跑。平常也有旅行,但都是家庭度假——我是绝对不会抛下妻子、两个孩子独自去旅行的!
Q:新书是以纽约为背景的吧?
A:现在该说是:1960年代的佛罗里达。没错,上次采访我说是以纽约为背景,但说完就改主意了。因为我还没开始写,所以可以尽情地改主意——下一本书我会写沙俄前夜,会写到很多很多白人,有探险,有爱情……也可能是科幻,更贴我心的类型;我想在星球大战的宇宙里添加我的版本,探索未解之谜:新死星怎么会比恒星还大?太空偷渡客的生平故事?R2D2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说话?——到底哪一本,大家拭目以待吧,也许两本都不会写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