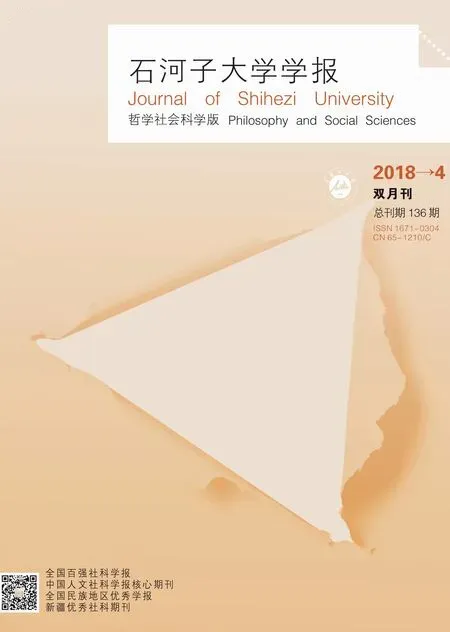稀见甘肃民间藏清嘉庆年间缉捕文书研究
赵兰香
(西北民族大学 图书馆,甘肃 兰州 730030)
最近,笔者有幸在一民间收藏者手中见到多件清嘉庆年间抄写的缉捕文书。这些文书被粘贴在一部道家经书《太上元始天尊说宝月光皇后圣母孔雀明王尊经》的背部,主要起衬纸的作用,是道教弟子为防护道经折损而特意粘贴上去的。从当时粘贴者的眼光来看,这些缉捕文都是无用的废纸,时至今日,却成了研究清代缉捕制度的珍贵文书。缉捕文数量约130多件,其中内容完整者约有60多件。本文仅择取11件进行研究,并就这批文书的主要价值和内容作一阐述。
从文物和艺术价值上来看,这些缉捕文书都是清嘉庆三年抄录下来的最原始的手抄文稿,完整的文书纸张大小约50×33厘米,白麻宣纸、墨书、小楷字体,书写工整秀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
从资料价值来看,这批文书为我们研究清代缉捕制度提供了一手资料,呈现了当时缉捕文书的基本格式和主要承载内容,保留了清政府处理逃犯的基本立场,反映出了清代社会的弊政,也体现出当时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本文举几例来说明:
1.一件为详请分咨通缉事,嘉庆叁年拾月拾肆日接准
浙江抚部院咨缉鄞县程国奇家被窃银钱,案内贼犯逃走;又萧山县董发先家被窃银两洋钱,案内贼犯逃走;又乌程县王规之母坟墓被贼损见棺,案内贼犯逃走;又龙游县吕长宝受伤身死,案内罪犯逃走;又仙居县张七因勒伤张成选身死案,拟流脱逃时年肆拾陆岁,身中面赤,微须;又乐清县安置因陈氏身死,案内流犯陈合贵于嘉庆叁年贰月贰拾玖日脱逃,时年叁拾叁岁,身中,面黄,无须;又会稽县安置军犯;又宁海县船户叶顺利被盗取人船牌照,盗犯逃走;又宁海县船户吴金万被盗取人货,盗犯逃走;又石门县安置因跌压张梅枝肾囊身死,案内流犯刘运实于嘉庆叁年叁月拾伍日脱逃,时年柒拾岁,身中面紫,有须;又嘉兴县程源泰家被窃花米银钱等物,案内贼犯逃走;又嘉兴县顾裕堂被窃银钱洋钱等物,案内贼犯脱逃。
此文书为浙江抚部院发向甘肃的缉捕文书。案件涉及浙江鄞县程国奇、萧山县董发、嘉兴县程源泰和嘉兴县顾裕堂被窃银钱案;乌程县王规之母坟墓被损案;龙游县吕长宝、仙居县张成选、乐清县陈氏和石门县张梅枝身死案;会稽县军犯案;宁海县船户叶顺利和宁海县船户吴金万被盗案。
《大清律例》:“凡犯罪拘捕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流三千里。殴人致折伤以上者绞,杀人者亦绞①〔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101页。。以上案件,罪犯皆在原罪之上罪加二等。
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人去世后往往陪葬一定的实物用品供逝者在冥间享用,珍贵的陪葬品也引发了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前去盗墓。《大清律例》规定:“凡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绞(监候)。”②〔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1页。
2.一件为遵例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拾月初肆日接准
江西抚部院咨缉宜春县拐犯刘森九,逃走时贰拾刚捌岁,身矮,面白,无须。逃妇钟氏时年贰拾玖岁,身中,面赤,脚大;又宜春县拐犯黄瑾一逃走,时年叁拾岁,身中,面白,无须。逃妇黄氏时年贰拾伍岁,身矮,面圆;又流丐王添生被殴伤身死,案内凶犯未允照脱逃,系乐平县人,均未缉获。
这是江西抚部院发向甘肃的缉捕文书,涉及江西宜春县拐犯刘森九和黄瑾一两个逃案以及流丐王添生被殴伤身死案。
对于诱拐案,《大清律例》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流三千里,被诱之人不坐。”③〔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8页。
3.一件为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伍月拾壹日接准
江南抚部院咨缉祥符县儒学衙置被窃衣物银两,案内贼犯逃走;又项县鲁玉九图奸白氏致氏羞愤自尽,之犯脱逃时年叁拾肆岁,身中,面白,微须,系项城人,均未缉获。
这是江南抚部院就祥符县儒学衙置被窃衣物银两案和项县鲁玉九图奸白氏案而发向甘肃的缉捕文书。
按《大清律例》:“强奸未成但经调戏本妇羞愤自尽者,斩罪。”④〔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9页。
4.一件为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柒月初柒日接准
福建抚部院咨缉宁德县安置因诬指凌扭为窃拷打致死,案内军犯郑鹏飞于嘉庆叁年陆月贰拾壹日逃走,时年叁拾伍岁,系安徽凤阳县人,尚未缉获。
这是福建抚部院就宁德县安置拷打凌扭致死案和军犯郑鹏逃案而发向甘肃的协缉文书。按《大清律例》:“凡诬告人因而致死,诬告人绞罪。”⑤〔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4页。
5.一件为禀明事嘉庆叁年柒月初捌日接准
河南抚部院咨缉汝阳县人唐敬被殴身死,案内凶犯逃走;又平阳县无名男子受伤身死,案内凶犯逃走;又鲁山县安敏车厂内被窃银两,案内贼犯逃走,均未缉获。
这是河南抚部院就汝阳县唐敬被殴身死案、平阳县无名男子受伤身死案和鲁山县安敏被窃银两案而发向甘肃的缉捕文书。
6.一件为遵例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拾壹月初叁日接准
江苏抚部院咨缉番县监生姚联索被窃银钱衣物逾贯,案内赃贼逃走;又如皋县吴继太被窃用刀砍伤左腿等去包袱银两等,案内船户四人逃走,时壹人王姓约年拾余岁,身长,面无有须。壹人约年叁拾岁方,面无须,无麻。壹人约年贰拾岁,身中,面瘦,无麻。壹人杨姓年近肆拾,面白,无须;又宜兴县吴三处被窃银两,案内赃贼逃走;又吴江县张广源被窃银两等。
这是江苏抚部院就番县姚联索、如皋县吴继太、宜兴县吴三处和吴江县张广源4人被窃银两案而发向甘肃的缉捕文书。
清代地方发生窃案,事主一旦报官,当地地方官必须立即派人准确核实失窃财物。《大清律例》规定:窃盗及掏摸得财五十两为首者,徒一年,八十两徒二年,九十两徒三年,赃至满贯者绞罪①〔清〕徐本:《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6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3-367页。。
清代以文职出身的总督或巡抚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总督辖一省或数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其衙门称为督部堂;巡抚辖一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其衙门称为抚部院。以上缉捕文皆以地方最高行政衙门督部堂或抚部院的名义发出。
从缉捕文的格式来看,以上六件缉捕文的格式基本相似。开头往往先书:一件为遵例(呈请或报明)详请分咨通缉事,某年某月某日接准。第二行书,某省或某局咨缉某案件中某贼犯逃走,注出贼犯的年龄体貌特征及缉获情况。
“遵例”指遵循《大清律例》之意。有清一代,法律严厉峻刻。州县官“身任地方,遇有盗劫案件,督率缉捕,是其专责”②〔清〕王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8《吏部·处分·地方缉捕》,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不论远近,州县官必须会同部下赴事主之家查验,当场讯取确供,填注通报文书。并向上司呈报案件发生的情况。如有迟延,计日论处或予革职。
如果要犯脱逃本境,则行文邻境,一体缉拿。任何省的地方官除了对自己辖区的人犯有责任缉捕外,对于隐藏、逃至本境的邻省逃犯也有协助缉拿义务。乾隆二十一年(1756)刑部规定:“凡命盗一切重案正犯脱逃,即行差役密拿,开明年貌、事由,详请通饬本省州县,一体协缉。倘未弋获,在初参限满之时,立即请求分咨邻省通缉,不能稽延致使人犯远扬”③宋国华:《清代缉捕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上述六件缉捕文来自浙江抚部院、江西抚部院、江南抚部院、江苏抚部院、福建抚部院和河南抚部院。除以上地方外,还发现见于广东抚部院、云河抚部院、陕甘督部堂、四川总督部堂、甘肃军需局、陕西抚部院、湖广总督部堂、广西抚部院、黄州抚部院、安徽抚部院、贵州抚部院、云南抚部院、直隶督部堂、湖南抚部院、湖北抚部院等20个省的督部堂或抚部院,几乎涵盖了清朝全国各地,证明当时若有罪犯逃脱未被缉获,往往由当地政府官员向全国各地发协缉文,协同缉捕罪犯。
接到外省的咨缉文后,地方最高督抚用下行文的方式要求下属官员协同搜查缉捕,各州县在文到之日,一面差捕认缉,一面填写印票,分给各乡总甲,遍行访察。如果遍缉无踪,年底出具印结,具文到府,府加具总结具文到按察使司,按察使司报督抚,由督抚咨部。以上六件通缉文书皆出自清代凉州府平番县一农户家中,说明此家人在清嘉庆年间曾为当地甲长,“有责任协助官府逮捕盗贼”④宋国华:《清代缉捕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7.一件为呈请通缉家丁事嘉庆叁年拾月贰拾捌日接准
四川总督部堂咨缉逃奴得柱,现年贰拾伍岁,圆面,无须,身中,于本年柒月贰拾日逃走,尚未缉获。
此例涉及到清代的逃奴法。清代官府和大家族皆豢养有大批奴婢。早在清入关前,就允许“旗下买卖人口,赴各该旗市交易”,入关以后,买卖人口更是盛行,如北京“顺承门(宣武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 ”⑤〔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人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6页。,《大清律例》中,许多罪都有发遣为奴的处罚。仅在乾隆初年,“各项发遣为奴之民人,律例载有三十余条”⑥〔清〕王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44《刑部·名例》,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
清代官私奴仆不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缴纳高额地租,而且身份极为低贱,“以奴婢与财物同论,不以人类视之,生杀悉凭主命”⑦〔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37页。,奴隶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往往选择逃离主人的控制。再加上缺食少衣,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逃亡往往是他们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才冒着鞭打斩杀的危险而逃亡求生。
奴仆逃离主人的控制,便是逃人。《顺治律·户律·户役》中有一条名为“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的法律①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专为逃奴设定。从顺治皇帝开始,清代历届皇帝都很关心逃人问题,《督捕则例》是清政府专门针对逃人问题而制定的法律条文,可见其重要性。顺治十二年(1655)刑部尚书刘昌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②吴伯娅:《试论清初逃人法的社会影响.清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139页。。清廷根据地方逃人多寡和查解逃人数量,针对地方官制定了具体的查解逃人功罪律例,加以惩罚和摧迁。各级官员为了逃避处分,争取奖赏,纷纷致力于缉捕逃人,不但百姓人人自危,就连官员也有朝不保夕的感受,一时间“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③〔清〕魏际端:《四此堂稿》卷35《移将军勿拿刺面逃人所扳窝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都文伦书局铅印本。。与此同时,清王朝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满族统治者试图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逃人缉捕事务。在利益的驱使下都希望在逃人问题上获得好处,设局图财、挟仇诬陷、指扳富室等种种诈伪极为普遍,逃人法的弊端也因此而凸显。
8.一件为报明脱逃兵丁事嘉庆叁年玖月叁拾日接准
陜甘督部堂咨缉出征固原右营马兵祁合,于嘉庆叁年捌月初肆日逃走,时年叁拾柒岁,身中,光面,紫色,微须,系固原州人;又出征西宁军标中营步兵张得,于嘉庆叁年捌月贰拾肆日逃走,时年贰拾肆岁,身中,光面,无须,系长安县,均未缉获。
嘉庆时期,清王朝吏治逐渐腐败,国库空虚,由治入乱,颓势已现,大小官吏贪赃枉法,因循守旧,难以振作,而武备废弛,军队纪律涣散,大量兵丁因为兵饷克扣、生活困苦,加之所派多为环境恶劣之地,无生命保障,逃亡事件也经常出现。嘉庆、道光时期,凡兵丁、盗贼逃亡,执行法律也为《督捕则例》。以上文书与缉拿逃兵有关。除了一般的刑事或民事案件,清代法律规定,如果军队内的兵丁逃跑,地方督部堂除差人缉捕外,也咨请外省协同缉拿。
9.一件为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拾月贰拾日接准
广西抚部院咨缉藤县黄嵩船内被盗窃去银两衣物,案内盗犯逃走;又安置行凶扰害,案内军犯李通于嘉庆叁年肆月贰拾陆日脱逃,时年肆拾壹岁,身中,面白,微须,系福建武平县人,均未缉获。
10.一件为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柒月贰拾日接准
陕西抚部院咨缉岐山县安置,因奸拐邵仁至妻胡氏同逃,案内军犯方胜才于嘉庆贰年拾月拾伍日逃走,时年叁拾贰岁,身中,面麻,无须,系浙江西安县人;又渭南县安置因砍伤张凤身死,案内流犯张得林于嘉庆叁年贰月捌日逃走,时年肆拾肆岁,身中,面赤,有须,系江南南涯县人;又盩厔县安置因殴伤尹妻李身死,案内流犯傅景秀于嘉庆叁年贰月贰拾日逃走,时年叁拾柒岁,身中,面黄,微须,系直隶遵化州人;又盩厔县安置因殴伤张杰身死,案内流犯张魁于嘉庆叁年贰月贰拾肆日逃走,时年肆拾柒岁,身中,面黄,微须,系直隶州人;又盩厔县安置因致伤周湖可身死,案内流犯戴伍文于嘉庆叁年贰月贰拾伍日逃走,时年肆拾壹岁,身中,面白,微须,系江南达贯县人均未缉获。
以上二件文书皆涉及到清代的安置政策。清朝沿袭明代刑律,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是为正律。在流刑和死刑之间,又加入非正律的军、遣二罪。军罪分附近2千里、近边2.5千里、远边3千里、极边4千里、云贵、两广烟瘴五等,称为五军。遣罪较军罪更重,“军罪虽发极边烟瘴,仍在内地,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④〔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0《刑九》,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36年,第7647页。。军犯被发配到边远地区进行屯田或从事苦役。从以上文书看出当时的广西、陕西都是清政府安置罪犯的地方之一。“安置”与军犯稍有区别。安置可以是无地移民、流民被政府有组织地安排在一处从事屯田劳动,也可以是罪犯被安置从事屯田劳动。而军犯完全是因犯罪而被派遣从事劳役的犯人。
11.一件为遵例详请通缉事嘉庆叁年捌月拾贰日接准
湖南抚部院咨缉长州县张二李被窃银钱等物,共估值钱贰佰零贰两玖钱捌分,赃贼逃走;又湘潭县观音庵僧道被殴身死,并焚烧庵内右屋,凶犯逃走;又黔阳县钱意侯被踢肾囊身死,凶犯黄移福逃走,时年肆拾岁,身中,面白,无须;又芷江县杨昌贵被殴身死,案内凶犯夏维明逃走,时年贰拾伍岁。
按大清律例:“凡放火故烧官民房屋及公廨、仓库系官积聚之物者,皆绞。”“若殴人至死,自当抵命”①闫晓君、陈涛:《大清现行刑律讲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
以上11例缉捕文中,涉及最多的案件是盗窃罪,其次是殴伤致死罪、微冒职官罪等,一方面反映出清代法律的严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清代底层普通民众生活困难。清人郑端引明人吕坤的话,阐述了清代盗贼产生多的原因:“盗非人乎?曰:人也。知为盗之必死乎?曰:奚而不知。知而为盗何也?盖有六流焉:饥馑之民苦于饥寒,无识之民牵于胁诱,游惰之民习于自奉,强悍之民敢于为恶,赌博之民迫于空乏,武艺之民偶乘便利。盗不出此六流矣。”②郑端:《政学录·弹捕盗贼》,《政书集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23页;吕坤:《实政录》卷4《弹捕盗贼》,《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48页。蒲松龄说:“盖年荒则盗易聚,天下之大乱多起于荒年,不可不早杜其渐也。”③蒲松龄:《聊斋文集·救荒急策上布政司》,《蒲松龄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04页。又如浙江巡抚王度昭说:“士兵的军饷被克扣,又困于饥寒,使之守汛,何能奋勇擒贼,所以江湖盗劫往往滋多。”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97折《浙江巡抚王度昭奏陈浙江情形》,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256页。
实际上,更多的逃人、盗贼的出现与地方官的不作为有关。如顺治十年(1653),直隶地区,大雨连绵,河水汛滥,沿河一带城郭庐舍漂没殆尽,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⑤《清世祖实录》卷77,顺治十年秋七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地方上贩济救灾、抚恤黎民等应办事情,畏于逃人混杂,自身难保,犹豫拖延。又如“山东一带流民复千百成群,携男挈女,蚁聚河干,望救无门,逃生无路。当此严风密霰,坠指裂肤之时,此辈衣不掩胫,食不充腹,流离沟壑”⑥〔清〕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3《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页。。流离失所的百姓生活无助遂“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⑦〔清〕魏裔介:《魏文毅公奏议》卷1《查解宜黄州县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李姻的《谏逃东疏》提到清代“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法愈峻,逃愈多”,“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⑧〔清〕蒋良祺:《东华录》.卷7,顺治十二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7-118页。。不但加深了各阶层的矛盾,而且根本没达到当初立法之目的。清代《督捕则例》制定保甲法、连坐法来全力缉捕逃人,但乡邻街坊互相检举,不单是情面问题,而对检举人的保护也缺乏制度性保障,其实施过程反而只会恶化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相互防范的心理,在客观上也给逃人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在严格的法律及政策的威迫下,推卸责任是最好的选择。清代《督捕则例》实行连坐法,“连累他一家,连累两邻,连累十家长,连累地方,连累县官、府官,又连累本道”⑨〔清〕李渔:《资治新书初集.文告部》,《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杜,1992年,第221页。。为了免于连累,民间只有将逃人隐匿不报,地方官也致力于遮掩,也就无怪乎“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什一”了。而且在连坐制度下,官官相护成为官场陋习,而这种陋习所构成的贪污贿赂、以权营私,使官吏们无心去防逃与缉逃。另外,清代《督捕则例》对于与邻近省府州县协同共济缉捕逃人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协调运作,如职责不清、不相统辖、没有统一指挥等。也有人为的缺陷,规避责任等因素。所以,清代地方官府当有缉捕逃犯案件时,立即只会他省协同缉拿,而相关省份为了推诿责任、规避麻烦立即张贴通缉文,只是应付,并无实质性进展。从上述通缉文中对案件的内容描述来看,无论是犯罪经过还是罪犯相貌特征的描述都很粗糙,实际上很难按照案件描述抓到原犯。而大量的通缉文书存藏于普通民众家里,也说明清代地方犯罪案件很普遍,老百姓不但没有起到被震慑的作用,反而见多不怪,将这些通缉文书作废纸使用,如此,则这些缉捕文书的法律作用也就如同一纸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