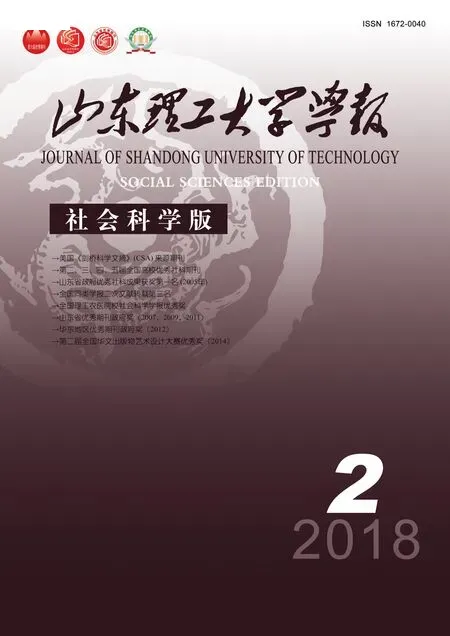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孙 景 鹏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9)对“新小说”的倡导,使人们对小说的启蒙、教化、新民等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小说创作的热潮,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与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提升小说地位
不少人认为小说(novel;fiction;story)源于西方,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不过,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屑的言论”或“小道理”,是其本义,与现代小说观念相差甚远。到了东汉,班固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就与现代小说的意义颇为相近了。到了唐代,小说正式形成——唐传奇就是非常成熟的小说体式。之后,宋元有话本小说,明清有章回小说——“四大名著”和“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彰显了中国小说的巨大成就。然而,在“经史子集”中,小说历来只能附于“子”和“史”,地位十分低微,难登大雅之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晚清,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独树一帜,满怀激情地指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以来被众人视为“小道”的文体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小说地位得以提升——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时间完全可以推移到“小说界革命”被正式提出(1902)之前的1898年。该年九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随后,梁启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提倡和翻译政治小说,成为中国小说地位提升与现代转型的开端和标志。纵观中国文学史,虽然一直不缺乏为提高小说地位而默默耕耘的人,但是,使小说的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深入人心、被世人所公认的举世之功当首归为“文界革命”积极奔走、为现代小说大声疾呼的有识之士——梁启超。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1]881898年底,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竭力称赞小说的重要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26显而易见,在多数人仍在“沉睡”的时候,梁启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现代小说多用白话,通俗易懂,基本不存在文言分离的情况,接地气,受众广;阅读起来无障碍,不吃力,甚至“很轻松”;具有启蒙、教化、新民等诸多重要功能,进行政治宣传时能够以一当十;往往能对人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一种非常强势的文体。虽然多数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认为小说是“下里巴人”,不把它当回事,但在普通民众那里,现代小说无疑是最受欢迎的。
正因为认识到了现代小说颇为重要的地位和不可估量的作用,梁启超才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2略略几句话,梁启超就指出了小说在道德、宗教、政治、民风民俗、学问艺术、人身修养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小说如今天的广告一样,受众面广,传播迅速,通俗易懂,老少皆宜,所以,梁启超把它当成一种政治宣传、教化国民、启迪大众的工具,强调它的“用”而不是“体”。当然,梁启超并没有偏执一端,而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小说的作用:“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3]4由此,不仅小说的作用被梁启超提到了新的高度,小说的地位也被其随之提高。
进而,在该文中,梁启超又指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熏”即熏陶、感染、陶冶、潜移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表明小说影响人的广度;“浸”即浸染、感化、使沉醉、使入迷,“入而与之俱化”,说明小说影响人的深度;“刺”即刺激、警醒,“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点明小说影响人的强度;“提”即菩提、顿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指明小说影响人的程度[3]3-4。这四种力的提出,有别于单纯的口号式的宣传,体现了梁启超独具匠心的识见与智慧。在总结时,梁启超说道:“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3]4再次把现代小说的地位提到了其它文体之上。
由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论断在当时颇为新鲜,且是由名人——梁启超提出的,很快便在社会上疯传,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对小说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梁启超所看重的,是现代小说在启蒙大众、教化国民等方面的作用。1923年,梁启超发表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在文中,他明确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4]263-264在这里,梁启超不仅把文化的衰落与中国的没落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把“文化”定性为民族进化、国力提升、国富民强的“根本”。孔子曾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梁启超之所以把小说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小说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言之有文,因而,定会行之久远。梁启超的此番言论,进一步巩固了之前所述的现代小说在人民幸福生活和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地位。
据统计,1902—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就创办了27种(含报纸一种)[5]242。报刊编辑们在栏目设置、体裁选择上均不约而同地偏向了“小说”。众所周知,报刊只有在栏目设置、体裁选择、题材取舍和主题取向上提高对大众的吸引力,才能销畅;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被人由地下捧至云端,变成了‘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6]226”[7]18,当然,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小说地位的提升上所做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明小说的重要地位,促进小说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身体力行,亲自创作了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在该部小说中,梁启超为了“发表政见,商榷国计”[8]4,图解其政治理想,特意安排了两个政治意味极强的主人公——黄克强(主张君主立宪,代表改良派)和李去病(主张法兰西式革命,代表革命派),让其就“革命与改良”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双方观点逐级呈现,几乎囊括了20世纪初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一论争的基本要旨。小说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虽然早已有之,但像《新中国未来记》这样与政治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在当时较为罕见。且不管该部小说的质量如何,起码可以说,这是梁启超提升小说地位、促进小说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发展小说理论
虽然梁启超在小说创作方面略有不足,但在小说理论方面,无疑具有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说语言文字的革新
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中指出:“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9]53后又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3]4在这里,梁启超之所以反复强调用俗语进行小说创作,不断倡导小说语言的变革,显然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小说之所以易于传播主要是因为其多用“今语”和“俗语”。当然,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欲使小说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以此实现其“政治改良”的目的。此外,梁启超还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作为四大文体之一的小说,用白话进行创作最宜,“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10]65-66。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尝试着创作了平生第一部白话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然该小说最终并未写完,且语言上杂以文言,并没有纯用白话,但毕竟是他运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的一种尝试,对小说语言的发展与革新功不可没。
(二)小说内容题材的拓展
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8]4-5诚如梁启超所言,翻开小说,里面充斥了大量的议论。不过,即便如此,小说仍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现实意义,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而且,随着小说的发展与转型,小说的题材日益繁多,法律、演讲、论说等,在现代小说中并不稀奇。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说不免影射时政,寄托作者的政治理想,但仍以虚构和想象为主,充满了大量的“预言”,可谓“预言小说”。比如,小说第一回写道:“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8]6-7梁启超预言(对新中国未来蓝图的美好勾勒)的实现(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在上海举办)虽比其预言的时间(1962)晚了近半个世纪,但终究还是实现了。从中看出的,不仅是他惊人的想象力与远见卓识,更是其在小说内容题材方面的有益探索。
(三)小说叙事技巧的探索
这一点最为重要。陈平原曾指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必须溯源到1898年——梁启超、林纾等一代‘新小说’家正式登台表演”[5]6。其中,梁启超的“表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仍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进行论述)。
首先,梁启超有意识地采用了“倒叙”的叙述方法进行叙事,使小说“一起之突兀”(梁启超语)[11]9,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线性”叙述模式。《新中国未来记》先在《绪言》中进行了大致的介绍,然后从第一回开始,便采用“幻梦倒影之法”[12]769(倒叙)进行叙述。叙述者先铺排六十年之后举行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然后回过头来叙述六十年前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的辩论及其游玩旅顺的故事,实则在叙述自1902至1962这六十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虽然幼稚,可还有把不同时空的情景拼在一起以产生强烈反差对比的艺术效果”[5]39,读之颇有新意。
其次,梁启超采用了多重声音的“复调”形式进行叙事。我们知道,无论从宏观看还是从微观看,复调小说都是一种“对话”而非“独白”,复调小说中的思想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十分复杂的,“思想在主人公的意识里具有独立的生命:实际上,活着的不是他——活着的是思想,而小说家描写的不是主人公的生活,而是他身上思想的生活”[13]23-24。《新中国未来记》共有一个绪言和五个章回,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叙事声音,如黄克强和李去病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演讲者孔觉民的声音、听众的声音、读者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形成了一种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的“复调”形式,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一的叙事结构,使小说更为复杂丰富。
再次,梁启超大胆地使用了“限知视角”。由于受“宋元话本”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往往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虽然叙述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剥夺了接受者的大部分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力”[14]250。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不落窠臼,摒弃传统的较易掌握的全知叙事,采用较为复杂的限知叙事,使小说忽明忽暗,既吊起了读者的胃口,又引发了读者的深思。例如,在小说第三回的结尾,叙述者写道:“至于以后有甚么事情,我也不能知道,等礼拜六再讲时,录出奉报罢。”[8]76在这里,叙述者不是像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一样胸有成竹地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是说自己也“不知道”;于是,很想知道“后事”的读者和不知“后事”的叙述者形成了一种十分平等的关系——二者共同期待着故事的发展,承受着迫不及待地欲知真相的“煎熬”。
最后,梁启超大量地运用了“非叙事性话语”。虽有研究者指出:“记叙文在文字的形式上要看不出有作者在,方能令人读了如目见身历,得到纯粹的印象。一经作者逐处加入说明或议论,就可减杀读者的趣味。……凡是好的记叙文,大都是在形式上看不出有作者的。”[15]127但从历史语境来看,非叙事性话语迎合了个性解放的浪潮,彰显了时代的精神追求,不仅能使读者的认识与叙述者的见解形成对话,促进双方的交流,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叙述者的叙事技巧”,“把握叙事性作品的内容和本质”[16]111。《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非叙事性话语比比皆是,例如小说第一回的开头,写到六十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大博览会时,叙述者写道:“阔哉阔哉”[8]7。虽然只有四个字,但叙述者的自豪与欢喜之情显露无遗。再如第三回的结尾,在黄克强指出天下事别的都还容易,只有养成人格一件“最难不过”时,叙述者不失时机地插入一句:“我辈不可不勉。”[8]61小说的写作目的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不胜枚举,虽然只有略略数字,但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只有抓住这些重点细细品读,才能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
综上所述,虽然梁启超对小说语言文字、内容题材、叙事技巧等方面的探索、发展与运用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已经见多不怪,但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相对于旧小说,他的“新小说”是颇有新意的,他为小说理论发展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三、促进小说转型
陈平原曾指出:“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17]364所谓“脱胎换骨的变化”指的正是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知道,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以上所述的“提升小说地位”“发展小说理论”外,还有译介小说、创办刊物、创作小说等。
(一)译介小说
有研究者指出:“翻译文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涵容了时空跨度较大的西方文学的精神本质,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异质的营养。”[18]39一提起晚清的译者,人们熟悉的往往是林纾、严复等,事实上,梁启超是和上述两人齐名的译者之一,周作人曾在《我学国文的经验》中将此三人相提并论:“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19]10不辱“代表”的称号,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翻译事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拿小说翻译来说,他不仅是中国较早的倡导者,而且是十分积极的实践者,前后翻译了《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与罗孝高合译)、《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中之人鬼》等多部小说。其中,《佳人奇遇》“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十五小豪杰》是十分典型的“豪杰译”,二者曾一并入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20]127-167。
有人认为原著的水平比翻译的水平更为重要,事实上,二者同样重要,相辅相成。如果原著质量很差,译者的水平再高,也不可能译出经典的作品,只会“侮辱”优秀译者的智商,浪费物力、人力。反过来说,“文学翻译水平不仅影响着文学接受者的层次,还影响着文学接受者的数量”[21]70,如果原著质量很好,但译者的水平不够,同样不可能译出优秀的作品,只能使原著“伤痕累累”,无形中局限了文学接受者的层次,减少了文学接受者的数量,削减了翻译作品的销量;更有甚者,将原著“糟蹋”得体无完肤,如此,很可能由之永久性地毁灭了原著。显然,对于“译介小说”,梁启超做得相当出色,既不属于前一种情况,也不属于后一种情况,而是像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一样,将本来优秀的作品翻译得更为出色,因此,无形中扩大了小说接受者的层面,增加了小说阅读者的数量,提高了小说作品的销量,从而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的现代转型。
当然,在翻译的同时,梁启超还吸收了西方的小说观念,学习了大量的小说理论,并将所学应用于中国小说的创作与研究,如引介并提倡“政治小说”、学习并运用“限知视角”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小说的快速发展与现代转型。
(二)创办刊物
晚清时期,报刊业蓬勃发展,梁启超和诸多报刊人一样,积极奔走,创办了多个刊物,如《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后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任主笔)、《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任主笔)、《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任主笔)、《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梁启超创办并任主编)、《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梁启超创办并任主编)、《新小说》(创刊于1902年,梁启超创办并任主编)等,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名副其实的奠基人。显然,这些刊物的创办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特别是《新小说》——虽也刊载了戏剧、诗歌和散文,却是中国较早的、主要发表小说的重要刊物,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就发表于该刊物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号。此外,该刊还发表过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小说。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极力强调小说启迪民智、改良社会的重要作用。该言论曾得到严复、夏曾佑、康有为等人的认可,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下同,只列年份)、《新新小说》(1904)、《小说世界》(1905)、《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白话小说》(1908)、《小说时报》(1909)、《小说月报》(1910)等专门刊载小说或以小说为重点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中足以看出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及其创办的《新小说》的巨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新小说》杂志所刊载的小说虽然主要是创作,但也有很多来自域外的译作。其他受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的影响而纷纷创办的小说刊物同样刊发了大量的小说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集束效应”,很快引起广大社会阶层对小说的重视。人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或打发了时间,或娱乐了身心,或开阔了眼界,或提升了素养;进而,不少读者在“获益”之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者,使小说读者的数量呈几何级数迅速增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提升了小说的社会价值。
(三)创作小说
有研究者指出:“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22]5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显然包括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梁启超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他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不仅普及了现代化的文学观念,使小说在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小说创作,使小说这一文体逐渐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大端”。因此,对中国小说的快速发展与现代转型来说,梁启超无疑是首位功臣。
这里所谓的“身体力行”主要指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并刊发于自己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我们知道,《新小说》的宗旨是:“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12]766显然,这不仅是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的目的,更是他“小说界革命”的目的,同时也是他创作政治小说的目的。《荀子·乐论》有云:“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事实上不仅仅是音乐,在梁启超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也具有这种“入人”“化人”的重要功能。由于政治小说不仅是小说,而且包含着救国救民的“大道”,其特点与梁启超“觉世”“启蒙”“新民”——即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目的暗暗相合,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最能传达政治思想、最易为国人所接受的“政治小说”,并大张旗鼓地加以倡导,以此来实现其伟大抱负。可见,“新小说”在梁启超这里既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
事实上,梁启超之所以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并让其中的人物口头完成他的政论,是因为他要实现自己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的“新政治”这一理想;虽然曹亚明指出“其思想意识仍无法摆脱‘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念”,王国维批评他“将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做法不足以仿效”[23]41,但是,他的政治小说连同他的政论文一起,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他们走上了救国图强的大道。
综上所述,虽然梁启超对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的倡导和推介略显矫枉过正(把小说的地位抬得过高,实际上,小说无法承担梁启超所说的全部功能),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狭隘性,但瑕不掩瑜,他不仅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乃至社会中的地位,拓展了小说理论研究的空间,而且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使小说在中国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虽然梁启超主要着眼于小说的社会功用(政治宣传和思想启蒙),不如徐念慈(觉我)在《余之小说观》中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来得更为客观(其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和王国维的“独立价值”之间,没有偏执一端),但他毕竟使小说开始跃居诗歌、散文和戏剧之上,逐渐成为最受世人瞩目的文学形式。此外,梁启超身体力行的创作与翻译虽谈不上“颇有建树”,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一言以蔽之,梁启超为中国小说的蓬勃发展与现代转型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M]//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M]//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陈春生,刘成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傅修延.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梁启超.变法通议[M]//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0]梁启超.小说丛话[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儒勒·凡尔纳.十五小豪杰[M].饮冰子,披发生,译.上海:世界书局,1930.
[12]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M]//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1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5]夏丏尊,刘熏宇.文章作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孙景鹏.论叙事学中非叙事性话语的重要作用——以长篇小说《无关声色》为例[J].昆明学院学报,2014,(2).
[17]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8]蒋林.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9]周作人.知堂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21]孙景鹏.论文学翻译与文学接受者的相互影响[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2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3]曹亚明.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受[J].中国文学研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