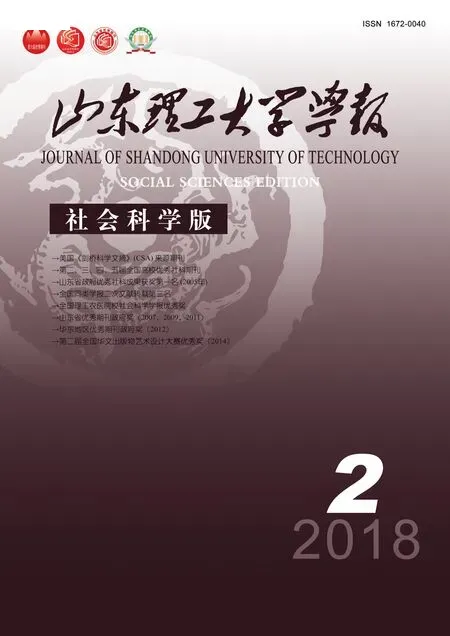信仰界说
——以与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为中心
陈 博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合作 747000)
信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虽常常触及,时时“遭遇”,却又实在不甚了了。即使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进行相关问题探讨的专家、学者,对信仰本身的理解和界定也往往是众说纷纭。然而,信仰问题却从根本上关涉到人的终极存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是在我们理性审视自身的存在和未来发展,还是在全面分析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状况,亦或是在忧思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文化传承问题的时候,无不必然地最终要触及到信仰这一问题。这便要求我们对其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只是浅尝辄止,而要必须对其本质内涵、属性特征做出积极的正面澄清和系统思考。
2012年凤凰卫视的一个关于“你有没有信仰?”的社会调查和中央电视台关于“你幸福吗?”的走访调查颇受瞩目。从结果可以看出,当下普遍国人的信仰状况和精神文化生活、幸福评价问题都是非常堪忧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有无信仰的问题时,除了少数被调查者回答有宗教信仰和坚信共产主义信仰之外,整体反应是,要么茫然不知所谓,要么说信仰自己或干脆没有信仰。这种状况实如一剂惊雷让人震惊,但却也正告出了这样一个让人无法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事实,那就是当下社会愈加严重的信仰危机。
若问,面对当前普通大众的信仰状况和精神生活,我们是否还要要求让其来承担全部责任?难道在我们的专家、学者当中就没有人思考过与信仰有关的任何问题?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专家们只该在做出人心的不古和社会的堕俗之叹后就只是隔岸观火或者说只是将就纵容,任其病变朽死吗?
其实,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由于信仰与个人、社会、国家以及民族等在各个层面、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从而使得对于信仰问题的探究是不可能被忽视的。无论古代、近代还是当下,在海内外学界,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大家、大学者中都不同程度地做出过回应和相关探讨,并且其中不乏有杰出贡献者。他们不但具有悲悯之情,同时更具有担当之责。如果我们用张载的“四为之说”来诠释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信仰的思考以及对于天地、人心的关照之心的话,那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既然这样,为何当下我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状况会如此参差不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交代清楚的,也不足以让人信服。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先在此做一这样的概括性答复,就传统而论,中国社会、文化在近代之前,是有其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基底的人文信仰思想体系的,并且也经历了一个极其艰辛的建构历程。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的时局走向和社会变革,这套信仰体系内部的一些缺憾与不足便被急剧地凸显出来了。从而从根本上撼动了国人的价值理想与信仰认同,以致迷失。可以说,当今国人的信仰危机就是近代以来在内外两方面所造成的文化、信仰问题的遗留和延续。以近代为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近代以前以致回溯到周孔之际,整体上都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文化人文信仰思想体系的建构、确立阶段。自近代以来以致当下,都可看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体系的反思、修正,积极谋求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相融通,旨在重拾国人之文化自信、人道尊严、坚定人文属性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阶段。虽然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作出过这一问题的相关探讨,但考虑到理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理论突破上的艰难性、长期性,就决定了信仰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完成。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在关于信仰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有继续讨论的巨大空间和深远意义。这也是笔者试图去进一步探讨信仰问题的目的与初衷。
一、信仰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为了使我们关于信仰的讨论尽可能详尽并且全面,从而能在此恢复文化自信、重塑信仰、重拾人道尊严的反思进程中有所发声,我们就不但需要系统回顾我国传统文化人文信仰思想体系的整个建构历程及其成熟形态,以兹来凸显其理论体系本身的优劣殊胜和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利弊得失,而且还要理性地审视近代以来主要学人的不同反思和各自努力,以兹来阐明我们关于信仰重塑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使如上的讨论和研究成为可能,我们首先应做的就是规范和明确信仰问题的讨论界域。对于究竟什么是信仰?有着怎样的效能、特征便成了我们首先必须正视和回应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信仰的严格界定和系统阐释,在古今中外的那些思想大哲的论述当中却显得并不厚实和充分。大多数时间,信仰总是以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解说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学术研究之中。我们于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信仰本身的不明晰和模糊理解,最终才使得信仰领域的问题不断滋生以致恶化。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明确信仰的实质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避免不求甚解的数量堆积和种类罗列呢?考虑到信仰与宗教的固有关联以及凝结在其中而根本无法肃清、撇开的文化因素,因而本文将从信仰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梳理中试图做出自己的思考和澄清。
(一)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西方社会由于深受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影响和熏习,因此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哲们都作出过关于宗教的专门讨论,虽然他们各自对于宗教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但仅就其所理解的宗教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来看,却都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解。那就是,他们将信仰全部归属于宗教,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核心与灵魂。甚至有些直接将宗教与信仰等同。认为信仰,其实就指宗教信仰,信仰的外在呈现就是宗教,宗教的本质内涵就是信仰。所以,于此我们便可以将其对宗教的定义和解释同样拿来作为对于信仰的理解和澄清。例如,门辛认为,所谓宗教(亦可理解为信仰,以下皆然)就是指人与神圣真实体验深刻的相遇,受神圣存在性影响之人的相应反应。康德认为宗教就是道德,是把所有的道德责任全部作为神圣命令的一种主观认定及其表现。那种靠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仅靠仪式,即外在的崇拜来取悦神灵的不是宗教而是迷信。在费希特看来,宗教是一种知识,它给人以对自我的清澈洞察,解答了最高深的问题,因而向我们转达了一种完美的自我和谐,并给我们的思维灌输了一种绝对的圣洁。费尔巴哈认为,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贪婪的占有欲,并在祈祷、献祭和信仰中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其职能是为了这个颠倒的世界提供神学的辩护、道德的核准和感情的慰藉。为苦难的现实社会罩上神圣的灵光,为套在苦难人民身上的锁链戴上虚幻的花朵……。施莱尔马赫认为,所谓宗教就是人对神的绝对依赖感。它可以主宰我们,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决定它。弗雷泽认为,所谓信仰就是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约翰·希克认为:宗教就是我们人类对超越的实在或诸实在——诸神、上帝、梵、法身、道等的不同回应[1]1。保罗·蒂利希认定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而被誉为现代宗教学之父的麦克斯·缪勒在谈及宗教与信仰的关系时则解说得更为直白和明晰。在其代表作《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缪勒曾明确表述:“1873年,我在皇家协会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宗教学导论的讲演中,力图明确说明宗教的主观方面即通常称作信仰的东西。”[2]15缪勒还说,“所谓宗教就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是属于有限形域之内的人所具有的并且展现出来的那种对于无限的企向”[2]15。因此,凭此理解,缪勒便将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中凡是具有一种超越有限界域而能显现出无限观念的精神文化皆归于宗教。中国的儒学也不例外。
在这里,我们无意在比较和分别陈述中论定具体哪种关于宗教的理解更好,只是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即无论对宗教做出如何的理解和诠释,都无法厘清其与信仰的联系。同时,信仰与宗教相比,要更为根本和不可或缺。人可以不是宗教的,但绝不能是没有信仰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信仰?其所具有的哪些本质特征与规定性让其对人显得如此重要?或者说究竟宗教本身具备了什么属性才使得其与信仰具有无法根除的莫大关联?
实际上,从如上各种关于宗教的定义陈述中可以看出,所谓宗教都是关于形域之外的那个无限的超越性的存在本身,同时在形域之内的人以自己的实际作为表现出了对于这一存在本身的信任、敬畏和依赖的一面,这才使得它与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也使得我们在对信仰的理解上有了必不可少的极具标志性的超越性企向和现实性经营这一属性认定。无论这一无限超越的存在本身是人格化的(我们称之为宗教的)还是非人格化的(我们称之为哲学形上学的或本体论的),其事实是都成为了人最后的终极性精神皈依和情感慰藉,都显示了信仰的效能和力量。因此才说,信仰可以是宗教的,但却不必然是宗教的。
与前一种在宗教氛围下的对信仰与宗教关系的理解不同,在人文、理性主义的传统中,信仰绝非专指宗教信仰,信仰也绝不是隶属于宗教之下的或直接与宗教相等同的。相反,信仰就其外延来说要比宗教大,宗教性的信仰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在一定社会占有较大比重的表现形式和载体罢了。而决不能顺此就将信仰与宗教信仰划等号。以中国为例,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无论是佛老亦或是其他类型的宗教形态,其并未取得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和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一种显赫地位。但却不能由此推断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从来没有过占据主体地位的信仰体系。以事实论,自西汉时期直至清末,在我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不论本土化了的佛教还是固有道教皆无法与之抗衡。自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信仰体系也就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价值理念为基底而建构起来的人文主义的信仰形态。就中国而言,信仰更多展现出的是理性、人文的色彩,而非宗教、神学的意蕴[3]21-23。同时对于宗教的理解从其构成元素上看,就不仅需要支撑信仰的宗教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一般我们称之为教义),还必须满足宗教要有它的创始人和膜拜对象(我们称之为教主),同时还要具有宗教的各种仪式、戒律等为特征的教职制度与组织结构(我们称之为教团)。只有在这三种元素同时具备的情形之下,我们才称其为宗教。
依此而论,中国儒学显然不具备宗教的全部要素,因而不是宗教。儒家思想虽深具天道性命的哲学义理和供人追求的君子风范与圣王人格的价值设定,也明确强调人所必须奉行的实践精神,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也当然有它的创始人,但终归来看,其并不提倡旨为凸出某一个人为目的的个人崇拜与英雄主义。更没有类似于佛老式的清规戒律和僧团组织。在中国,宗教早在周孔时代就已经被德礼文化所代替。信仰的依傍形态也已发生了人文的转向[4]148。因此在有关信仰之安顿与挂搭的讨论中才有了共产主义者以人与社会的现实经营与努力来滋养心灵、充实精神生活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主张,也才有了近现代新儒家以道德代宗教或以哲学代宗教的坚持和论证。至于那些认儒学为儒教的主张和提法,在笔者看来其根本用意旨在让极具儒学底蕴的信仰体系更加得到强调,信仰职能能够更加充分地得到发挥,从而彻底恢复国人之文化自信、信仰认同以及人道尊严罢了。
所以说,当信仰所展现出的形式、载体不同的时候,其所信仰的对象也就不同,甚至其对现实人生的关照和肯定也有所差别。
信仰如若以宗教的姿态来呈现以显示其力量和效能时,其信仰的对象便是人格化的上帝、诸神。信仰如若以理性、人文的姿态或哲学形上学的姿态来呈现以显示其力量和效能时,其信仰的对象只是那个超越性的绝对无限本身。作为宗教信仰,它需要信众对人格神、上帝的绝对服从与皈依,人在其所信仰的神面前永远是仰视的。绝对没有与其同参的理论可能和情感奢望。而人文信仰,则从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张扬与肯定。是对为人者的一种自觉、自豪与担当。其自觉于人在形域之内之现实状况(作为人文主义信仰的一种典型范式,共产主义信仰于此方面则表达得更为明显与透彻),自豪于人能超越形域之限而企向绝对无限,能有一种机会去与天地同参,赞天化育之理论设定。而担当在于明了这种精神的最终所达与兑现不是被动的祈求拯救、等候遴选,而在于自己的当家作主,自我成全。在理性不断开悟的觉解路程上去挣得性命与天道的契合和贯通,最终实现信仰的安顿和本我的呈现。作为宗教信仰,由其在人以外有一个人格化的肯定,从而无形中或多或少地对人自身的肯定便有所削弱。其虽然能够使人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而不肆掠,但却也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消极懈怠的处世态度,无法真正感受和体验到为人者所理应具有的那份尊贵与荣耀,反而隐含着人之异化的可能。相较来说,理性、人文的信仰于此却有着一定的优势,其不但同样能够给人以寄慰、安顿,而且由于其信仰对象的非人格属性从而有机会在使人保有一颗敬畏之心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张扬人的存在,实现和体验为人者的应有殊荣,进而避免了人根本性异化的可能。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我们所谓的人文信仰是有别于宗教形态式的信仰表达的一种人文理性主义的宽泛概念。是指在民族文化大融合基础上所建构、形成的,旨在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德性自觉,落实人道尊严与价值归属等精神性诉求的思想文化体系[5]132-133。因此从外延上讲,既包括历代以来的儒家成己成物,以通天人的传统人文理性主义的信仰,也含慑旨在实现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信仰。
理性、人文的信仰由其在人的肯定和信仰的安顿、实现诸方面都有着较为妥善的处理,因此也预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可期前景与雄厚价值。由于传统的不同,再加上思想文化本身在其转换上的艰难,特别是信仰对象与信仰表达在置换上的近乎绝望,才使得康德在面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泛滥以及在对人自身的肯定与对上帝的绝对皈依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和内在张力的时候就只能通过以对人的理性进行设防、划界的方式来为其信仰挣得地盘。这种艰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实可避免。所以对于今天的国人信仰危机的根本解决来说,不必非得让国人都去选择宗教的方式去皈依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其它来安顿信仰,因为让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文化基底的情况下去改变信仰对象和表达其实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即使勉强做到形式上的相仿一致,便也只是胡信、乱信,是迷信而非信仰。虽然我们的传统信仰体系并不完美甚至有着诸多硬伤和缺陷,但毕竟没有水土不服的文化排斥和不相匹配的情感认知诸问题。所以,只要我们对其能够报以理性的对待,进行彻底的反思、修正和再诠释,终将能够水土适宜地安顿心灵、重拾信仰和荣享人道尊严。
(二)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如果说信仰与宗教之所以有千丝万缕的莫大关联的话,那么究其根本,正是由于宗教本身所蕴含了信仰之为信仰所不可或缺的超越性企向和现实性经营特征。正如缪勒所说的:“所有的宗教,尽管在其它方面多有不同,可在这一点上恰恰一致,即它们的对象或是完全地或是部分地超出了感性和理性所能把握和领悟的能力。”[2]19“所有宗教知识的基本要素就是体验既不能由感觉领悟也不能由理性领悟的存在。这种存在事实上是无限的而不是有限的”[2]21。与此相较,则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便显得更为紧密。就信仰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信仰需求的产生和信仰需求的确立、落实以及对它的回应和安顿三部分。就第一部分信仰的需求产生而言,其根本上是与人的精神存在有关,用麦克斯·缪勒的话说,正是由于人有着一种想要突破有限的界限而产生一种关于无限存在的意识和观念,才使得宗教(主观面即为信仰)成为可能。“可以肯定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使脸孔朝天,只有人才渴望无论是感觉还是理性本身都会否认的东西”[2]11。凭借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本真和先天欲求,才使得整个世界被意义、价值化了的同时也必然地要求人自身生命的精神超越和终极关切与安顿。信仰便是这种寻求生命关切和意义、价值安顿的集中表达。从我们对于信仰问题的理论回应和寻求安顿角度看,则明显地与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国家的民族文化有直接的关联。总体上我们认为,人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样式规定了其信仰领域的具体诉求和表达方式,进而也回应着这一信仰本身。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心理便会塑造出不同的信仰理念和行为表现。进一步讲,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本身存在的差异性也使得其在对信仰诉求的内容规定、填充程度以及在对其信仰的最终安顿与回应方面是否充分、得当也明显有别。比如,巫觋文化孕育出的只能是巫觋信仰,宗教文化孕育出的只能是宗教信仰,而德礼文化、人文理性主义思想所孕育出的也自然是理性、人文的信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发展阶段,这种人文理性主义信仰便又具体呈现为共产主义信仰。
具体说来,一个存有信仰需求的人在其努力表达自己的这种需求的过程当中,实际体现的就是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旨在谋求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是如此,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并且随着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认知程度的不断加深,其信仰也会日益明确、清晰起来。也就是说,所谓信仰是从根本上建立在对相应民族文化及其意识观念的理性认同基础之上的。任何未经理性审视过的认知,包括信仰都是无法最终确立和安顿寄放的。盲目地崇信和情感的泛滥不仅有使信仰根基发生动摇,让精神世界陷入无尽空虚与黑暗的可能,而且也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和背反的巨大危险。比如当今社会出现的迷信活动和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普遍存在信仰需求这一客观现实以及在感性理解上的相对便易,从而让信者陷入一种毫无理性辩知,情感和行为表现却极其偏执的危险境地。这样一种对待,不但不能从根本上给人以精神寄托和良性关照,反而会造成让人走火入魔似的人性扭曲和价值、文化的整体性颠覆。所以我们说,良性、健康的信仰观念必须由良性、健康的民族文化来塑造,而民族文化的优劣却又并非先天使然、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沉淀和孕育中不断推陈出新,修正、完善而成的。例如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中国的佛教、道教亦或是其它一些民族的成熟型理性宗教,无不首先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文化形式,并且有着自己的哲学。而这才是信仰成为可能的内在规定。因此说,信仰必是理性的,是文化的,是随着人对于自身文化的理性认知的不断加深而得以确立和建立起来的。而像前文所提及的当下中国社会信仰状况参差不齐的现实囧状,其实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中、在其中国化进程的不断理论推进中,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对接中妥善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既然一定的民族文化孕育和规定了相应的精神信仰,那么是否意味着信仰一旦得以塑造和规定就再不会有丝毫动摇或遗失的可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愚顽死守而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对那些经得起历史筛选和检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发扬和推进,使其不断地适应时代的新变化,以回应和阐释新时代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不同诉求。例如,胡适就主张要以科学代宗教,蔡元培主张要以美育代宗教来安顿信仰,建构体系。但是我们说,诸如民主与科学一类的范畴,其只能称为西方这一根基深厚的文化大树所吐露出来的艳丽之花,而并非此大树本身。即使将其连根拔起,移植于我华夏之内,可否水土足够适宜,开此二花实难确信。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仅表现为一场空前的文化危机,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举凡事物,只要是能够与西方二字占得上边的,就觉得“洋气”“时尚”。任凭什么主义、思想,凡是西方的就应高度重视,进行吸取、效仿。一时间,洋装、洋服、洋酒、洋糖充斥市场,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个人主义粉墨登场。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任何事物特别是思想文化则唯恐弃之不急、弃之不尽。这不但深刻反映了西方文化对我们强势介入的历史事实,也昭示着中国社会曾经历的那场历史空前的文化自卑和信仰迷失境况。可以说,失去精神家园和终极性价值挂搭的中国人的这一自我文化定位和理性寻找信仰的艰难历程时至今日仍在继续。
同时,当今社会道德滑坡、信仰迷失以及迷信活动、邪教组织频出的客观事实也再次映证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的民族文化这“三种资源”的深度融通。只有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融通创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才能确立,而人文理性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方可坚定不移。
如果说文化从根本上说对信仰有着奠基性作用的话,那么反过来信仰又对文化有着坚守、捍卫和成就的作用。一种精神信仰的价值体系一旦确立,那么他就不仅仅具有关照个体生命、寄慰心灵的效能,更能够对整个社会、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其强大的整合力量,成为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内在推手和保证。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和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足以证明,全党上下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下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的全方位的肯定、实现上的贡献巨大。“信仰在一个人则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则为一个社会的元气”[6]8,缺乏信仰不仅会使个体生命得不到终极关切,生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无处安顿,最终使人生颓废、意志消沉、人性异化,而且也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毫无理性和目的可言的混乱失序之中。就像梁启超所认为的“中国人现在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无宗教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6]8时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较之文化、信仰皆未遭受重创的西方则无论是社会成员个体还是整个社会都要显得更为躁动不安一些。坚定的信仰并未完全确立,许多社会规制还不健全,非理性、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物欲的追求与实现成了许多人的精神原则和行为的驱动力。金钱和权力变成了‘世俗上帝’。它的崇拜者变成了一群贪婪的恶狼。投机倒把、杀人越货、买淫贩毒、贪污受贿、弄权谋私、黑道社会、黄色文化……泛滥流行,随处可见”[6]17。一味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吞噬掉的是对于个体生命的迷失和意义、价值的否定,而且也导致着整个社会包括文化的恶化、堕俗。
既然信仰始终是与文化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并且信仰要靠文化来填充内容,表达需求和回应安顿,亦受文化封尘而遗失,因此欲使当下国人精神生活充实起来,使其信仰得以明确、恢复,就必须从文化的自我检讨与革新入手不可。
二、信仰的定义、特征与意义
综上所论,无论我们对于宗教还是文化本身的理解有多么的不同,信仰这一深深植根于人类生命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与宗教、文化却都有着如此莫大的关联。由此也使得我们对于信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性认识。
所为信仰,就是人类通过现实人生的努力经营与创造,对于那个不但具有超越属性,而且能够给人以极其强烈的终极关照和抚慰功能的超越性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信任与持守的精神文化现象。
(一)信仰现象在其不同环节、阶段当中的特征呈现
1.在信仰这一精神文化现象的需求和发生上,有着本根性、普遍性和自发性的特点。荷马说过,像雏鸟张嘴要求食物一样,所有的人都渴望神灵。信仰正是这样,是任何人在其生命存在的精神活动当中本真具有的心理需求和文化现象,并不区分性别、民族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它是属人世界的最高标志,也是生命意识的最终表达。在信仰的世界里,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逐一塑造、先后成就,尽显着为人者当具的荣光和对生命本真的彻悟。
2.人们对于信仰,在其诉求和祈愿方面有着精神皈依性的特点。信仰的发生源于人类对自身有限存在的体认和面对自然、宇宙之人力难及的觉察。这种体认和觉察不但是人类意识的最初萌动,亦是心物二元主动分离,纷纷寻求依靠、安顿的本源动因。对于信仰者而言,在其信仰状态和行为当中,不但在主观认知上表现出了对其所信仰对象的信的一面,而且在情感态度上表现出了敬的一面。这种对待,对于人这一有限界域之中的有限之物来说,便是使其获得生命归属、心灵安顿,对其存在给予终极关切,足以使人安身立命的最终呈现和表达。
3.在信仰对象以及对这一对象的最终设定上,其又呈现出了超越性的特点。为保证信仰诉求的切实落实和有效回应。因此在信仰对象的设定上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由形域之内的有限之物所承担完成。而只能由不受任何规定性所限制的那个创造一切,规定一切的绝对无限本身来承载,“正是在无限的观念中,我们找到了整个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根基”[2]31。而且“从我们个人意识的首次黎明开始,我们就总是面对面地和无限打交道了”[2]32。我们越是远离有限而接近无限,就越能清楚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存在和信仰对于我们内心的回应与关照。
4.具有在内容塑造上的文化属性和民族特性。如果说信仰需求作为一种为人者之精神活动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就其内容、表达而言,则是后天造就的结果,需要有实质的文化传承和价值理念来塑造、填充。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信仰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属性。又因其文化本身固有的民族特性,故而使得信仰相应的具有在内容表达上的民族特性。
5.根据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性,信仰在其表现方式上可以是宗教形态的信仰表达,也可以是人文理性主义的形态表达。
6.具有在确立和最终实现方式上的思辨性、后致性。对于信仰,在我们自觉其需求,明确其属性与特征之余,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便是实现的可能和安顿、挂搭的方式。由上可知,尽管信仰的需求人人具有,时时存在,但信仰的完整呈现乃至最终确立却并非如此。首先,信仰是以文化为基底的,信仰体系的建构和确立要以文化系统的发展、整合为前提。因此,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之事业。其次,信仰的文化属性和生命绑定也决定了信仰者在表达和确信自身信仰上的理性、思辨的方式选择和渐进觉解的后致性特征。因此说,信仰之信实为理性之信,决非感性之信、迷信之信,只有先学而后能达。社会的整体信仰体系需要在文化的建制、发展中去最终成就。个人的信仰也只能在不断的理性思辨和自省中去觉解和安顿。它是以优秀文化为素材,以理性思辨为斧凿,以生命的态度去不断雕琢和造就的。可以说,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其信仰体系的确立和不断修正的历史。人的一生也就是其寻求生命本根,信仰的安顿和最终成就的历程。
(二)信仰对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意义
1.信仰的确立能够给人的个体生命赋予一种意义信托和价值背靠的归属感。提供一种对为人者之尊贵与荣耀的自觉与体认意识。《大学》篇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7]10信仰作为人文世界的最高形式,生命存在的终极表达,一旦确立便能成就个体生命的根本大道,最终所得。
2.信仰的确立能够给人的群体生活赋予一种生命成就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能够营造一种舒展宽和的生命情调和群体氛围。充实的人生就是在坚定信仰的内在支撑下去积极的利用厚生,在修己安民、成己成物的奉行、对待中不断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进而感悟生命的存在提高心灵的境界。
3.信仰的持守能够有力的维系社会的安定秩序。社会的安定需要人心的安定,也需要社会组织的和谐、理性。信仰体系作为文化的着力塑造和集中表达,一旦确立供人持守,自会使人内心充实,知止而定;而供社会奉行,亦能造就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认同,连同信仰本身的理性化特征,进而能够从根本上维系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安定有序。
4.信仰的充实、稳固能够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的人文路向。这不但从根本上是由信仰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人文世界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信仰问题愈加突出的当今社会,我们首先应做的就是弄清这一问题的讨论界域,了解信仰本身的实质内涵和本质特征以及与个人、社会的紧密关系。在这里,我们将信仰与宗教、文化分别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界定出了信仰的本质内涵和效能、特征,以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进一步推进信仰问题的理论思考。
[参 考 文 献]
[1] 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M].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金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 陈博.论中国古代信仰的发生及其人文转向[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4]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5] 陈博.人文信仰的建构是民族复兴的关键[J].人民论坛,2016,(8).
[6] 吕大吉,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卷一 ——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