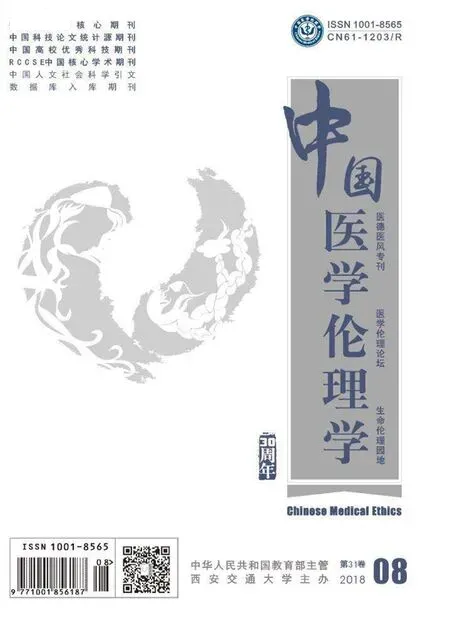整合的医学人类学及其中国实践
程 瑜,胡新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chengyu@mail.sysu.edu.cn)
1 整合的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健康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简而言之,医学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的健康、疾病及其治疗的问题,它的特色在于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2]。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医学人类学立足的理论和视角是人类学。而人类学则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是研究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一门学问,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的研究[3]。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包括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以及文化比较观,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则将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当作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视角,其中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观更是医学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另外,人类学的研究中运用了主位客位的研究策略,这在医学人类学中同样可见。在这些理念和视角的指导下,医学人类学强调整合的概念,即人类的身体健康或者疾病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不仅要求多学科的整合,更要求把人类群体放在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考虑。
1.1 文化整体观
文化整体观指的是人类学不是集中在人类生活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而是强调把人类的体质和行为(包括体质、社会、文化甚至是心理)的所有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整体观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点,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社会文化的广泛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理解其背后深厚的意义[3]。所以医学人类学认为一个群体保持健康或者产生疾病的原因,包括他们对于自身身体状态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保持健康的方法或者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仅是受到自身身体机能的影响,更是和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必须放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理解人们的态度及其选择。相关的经典案例是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田野调查,他来到了湖南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发现医院里面接收了许多神经衰弱的病例,但是在西方,神经衰弱这种疾病名称已经很久都没有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抑郁症等疾病名称。他认为这是一种为了避免中国文化语境中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而采取的策略。另外,很多患者在描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往往强调自己身体上的感受,比如头疼总是感觉很累等,带有躯体化的倾向。这是因为,首先中医话语中本身就有很多躯体性语言的表达,其次患者总是从自己最直接的身体上的感受出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们把身体上的疼痛作为自己生活上失败的借口,通过强化躯体化,人们可以借以掩盖自己的缺点,并且可以获得一些平时享受不到的福利,躯体化的表达成为了一种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因此这种躯体化是社会建构下的产物,需要置身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够解释患者的行为,这种疼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原因,也会产生社会性的后果[4]。
1.2 文化相对观
文化相对观是一种直接涉及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理论,是人类学的核心。它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3]。这指导了医学人类学看待不同医学体系的态度,希望尽量避免西方医学体系的中心主体地位,因为许多地区对于疾病的理解是在民间信仰的指导下形成的,在生物医学体系的逻辑看来这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落后的,但是医学人类学认为生物医学之外的许多医学体系也是一定逻辑的产物,应当放到当时当地的文化体系下才能够理解,不能简单的用原始、低级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集中体现在人类学家对于民族医学的研究之中。在人类学研究的早期,就已经有不少人类学家对于一些部落的宗教仪式治疗方法有过研究。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长期在非洲进行调查研究,他通过对阿赞德人的信仰体系进行研究,发现可以将其区分为巫术、魔法和神谕三个部分。阿赞德人如果身体突然间变得很不舒服,他们会将其归结于有人对自己施加了巫术,然后借助于神谕找出谁是巫师并且进行破解,甚至还会利用复仇魔法来进行报复。生病的时候他们通常求助于巫医,巫医有很多的魔药,会根据症状给予相应的魔药,并且举行仪式进行治疗[5]。这种治疗方式与生物医学体系所追求的科学性相冲突,但是其背后的信仰体系却在阿赞德人的社会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社会解释体系,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具有道德约束作用,起到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社会稳定有极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学家发现了民族医学所拥有的价值,从而能够理解他们的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医疗方式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由此提出了一种多元医疗体系,即不同的医疗体系是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相匹配的,而不是某一种体系一统天下。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相对观并不是绝对的,即认为对所有的文化都无法做出价值判断,对所有的文化都抱有宽容态度,文化相对观也是相对的,要依据其历史文化脉络去把握文化的特点[6]。也就是说,在寻找民族医学的价值的时候,也必须意识到,西方医学具有其鲜明的优势,对现在的卫生健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也不能一味地去为了宣扬民族医学而忽视现代生物医学的价值。
1.3 文化比较观
由于人类学研究范围和群体的广泛,所以一直以来人类学都有比较的传统,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和群体进行比较。一是共时性比较,即对同一时代广大区域内的资料进行比较;二是历时性比较,对同一区域内不同时代的资料进行比较,以揭示变迁的模式;三是跨文化比较,通过对所有收集到的、不同文化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文化比较观不但使研究者免去单一狭窄范围的限制,而且可以使研究者发现更多、更广的人类行为的可能[3]。医学人类学也通过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发现同一类型的疾病在不同区域内的不同表现,或者是不同区域的疾病其实具有某种相似性,并将其放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解释。例如Lock研究的日本女性的停经现象。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停经开始被当成一种疾病,并且基于欧美女性的标准,现代生物医学认为全人类所有的女性停经期间都会有盗汗和潮热的现象。但是从1985年到2005年,Lock跟踪日本45岁到50岁的女性停经现象,发现相比较欧美女性,日本女性发生明显盗汗和潮热症状的比率低很多。更为广泛的是,1988年的全球调查显示,欧美之外的地区只有少量的更年期妇女有盗汗和潮热,且不同地区的症状不同。这种现象使得医生和学者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潮热和盗汗仍然是所有停经期女性的自然身体反应,只是有些社会中的妇女生活中有更加关心的事物,或者母语中缺乏相必要的词汇,所以忽视了这个症状;另一派认为,尽管更年期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变化在全世界环境中都很相似,但是不同地区女性的社会生活、心理变化和生态环境不同,身体对激素水平变化的应变也不同[7]。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文化比较观的指导下,医学人类学家通过对女性停经期间会发生的症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世界上不同地区症状表现并不一样,并且进一步去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从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语言体系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基于地区的特点去分析,最终发现在单一的生物体系之外的世界的多样性。
1.4 主位客位观
主位与客位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策略,主位观点是将焦点放在当地人或者说研究对象的解释方式以及重要意义的判断标准,去发现他们的观点、信念和认知,探究他们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和分类这个世界,以及他们用来解释行为的规则是什么。而客位观点则是一种研究者取向的观点,强调研究者的解释方式、概念范畴以及判断重要性的标准,要求以一种客观以及具有穿透性的观点带到异文化的研究中[3]。主位客位的观点具体是在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时候使用的方法,但是在医学人类学中也有人借助了这种观点发展出相应的理论,即凯博文所主张的区分疾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的概念。疾痛是患者的病患经验,是患者的患病故事,指的是患者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这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解释模式。而疾病如果用有限的生物学词汇来定义,那么它仅仅是一种生物结构或者生理功能的变异,比如说医生需要对患者的体温进行测量,通过具体的数字来判断是否具有发烧的症状,这是一种以医生为中心的解释模式[8]。医学人类学认为现在医患不和谐的深层次原因就来自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造成的冲突,因此他主张要区分不同的解释模式。对于医生来说,为了了解患者的解释模式,应该要理解患者的日常生活,走进他的患病故事,才能够了解他的苦痛。在他的著作《疾痛的故事》中,凯博文尤其强调了慢性病患者的治疗,因为慢性病是长期而难以治愈的,他主张对患者进行疾痛叙述,将自己的患病经历讲述出来,医生在对病患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注重病人的疾痛叙述,甚至可以采用人类学微型民族志的方法,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够理解和整理患者个人生活和社交环境的主要疾痛后果,并对自己习以为常的解释模式作出反思,从而尝试对患者进行合理的治疗[8]。更为具体的凯博文还提出了著名的“凯博文八问”,即“请描述一下你现在的问题?”“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这些问题?”“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影响的?”“它有多严重?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你认为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哪一种是最重要的?”“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9]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医生有效的了解患者的疾痛世界。将医生和患者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区分开来并且加以利用,正是人类学的主位客位观的体现,借助这种方法去寻找更好的治疗手段,这说明主位客位观点不仅仅是医学人类学的研究策略,而且对于目前的医学实践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整合的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利用文化整体观、相对观、比较观以及主位客位观,主张医疗体系不仅要整合其他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更要整合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微观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是一个文化人、社会人,人的健康是身心健康,疾病的治疗更是身心一体的治疗。在宏观上,要看到不同医学体系,不仅包括医患之间不同的解释模式,更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多样的健康知识和医疗方式,跳出西方生物医学的框架,去理解外面的世界。
近些年来,许多医学界人士倡导整合医学的概念,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医学也经历了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以及目前的整合医学时代,整合医学全称是整体整合医学,它需要整体观、发展观、医学观以及整合观的指导。具体来说,整体观要求空间、人和时间的统一;发展观要求医学要纳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并且解决现在面临的新的形势;医学观则强调在传统医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必须要做出一定的改变,比如要关注人文、关注个人心理、注重民族性、更加的灵活多样等;整合观则是医学要和其他的东西结合起来,包括自然、社会、营养、养生等。整合的方法要求全视野、多角度、多因素、立体、可变地去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0]。作为医学人类学来说,它的基本视角和理念正好可以为整合医学提供一个可能路径,因为两者都强调人类的身心一体,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强调不同医学体系的整合。更为重要的是,医学人类学本身就应该成为整合医学发展的一个部分,因为整合医学的发展必定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和合作,而人类学利用其学科独特的价值,可以应用到医学研究和实践之中,解决目前的社会医学问题,适应整合医学发展的时代趋势。
另外,医学人类学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取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罗伯特·汉总结有三种基本理论:①环境进化理论,认为物理环境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否是疾病与治疗的主要决定因素;②文化理论,提出信仰、价值观和习俗组成的文化体系是基本决定因素;③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经济组织和相应的权力关系是控制人类疾病与治疗的主要力量[11]。张实则将医学人类学理论分为五个学派:①结构功能医学人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疾病和治疗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人们的患病认知以及医疗体系的功能就是要满足患者不同的生理、心理需要;②阐释医学人类学,主张从研究对象出发去寻找主观的、深刻的解释,从而认识疾病;③批判医学人类学,关注历史和政治结构对健康和医疗资源不均等的影响,将个人生命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④仪式医学人类学,借助于仪式,从象征、信仰、行为等角度对人的治疗进行研究;⑤生态医学人类学,关注人类的天性和社会环境、行为、疾病以及人类的演化和文化,如何透过回馈的过程,影响行为和疾病[12]。这些分类方法具体上虽有不同,但仍然是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方法指导下发展而成的,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取向,这些在下文中有关医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中也有所体现。
2 医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
一般认为医学人类学进入中国人类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期中国人类学学会编辑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和《人类学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从一开始的局限于生物体质方面的研究,到现在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医学人类学本身就是应用人类学中最为活跃的一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有人类学者介入国际卫生领域,它的应用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公共卫生的防治之中;二是配合临床实践;三是对民族医学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它的应用性在中国的实践中也极为突出,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的一大特点。目前为止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大致包括下列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医学人类学的生物体质性研究;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性研究;医学人类学对民族、传统医学的研究;对公共卫生、临床医学问题的田野调查研究[13]。以往学者大多从这几个方面介绍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和实践,本文从大概的时间顺序梳理医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以求对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历时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且也更能理解其应用性的特点。
2.1 2000年以前,少量研究者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医学人类学
早在1937年,潘光旦先生出版了《民族特性和民族卫生》一书,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取决于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质,后者又取决于人文主义的优生学以及人的适应力或应变能力,他从一种批判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人的健康问题。许烺光则立足于他1942年在云南调查的一场霍乱写成了《云南西部的魔法和科学》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他利用中国的经验讨论了迷信、宗教以及科学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当时出版了一些医学人类学的教材,主要是介绍医学人类学的概念和研究内容,在其中也能发现当时对于人类体质层面的关注,譬如陈华1998年出版的《医学人类学导论》[14],席焕久出版于2004年的《医学人类学》[15],也多是集中在对精神病学、营养学、人种适应上的讨论。陈华在1988年发表的《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总结到当时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生态学研究、医疗体系及其作用、民族医学、民族精神医学、营养人类学、老年人类学、产科人类学、人类的生命周期与疾病、医疗行为、传统医治者的行为及其作用以及文化信仰体系及其对保健的影响[1]。而前面提到的1986年所出版《医学人类学论文集》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专集,它收录的论文多是包括法医、人体结构、人体发育等方面的研究[16],所以说,当时的医学人类学主要是对生物体的研究,多关注人类体质与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即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适应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人类适应环境行为的干预措施从而改善人类的健康[13],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也缺乏实地的调查材料。
2.2 2000—2010年,以艾滋病防控为主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在21世纪初,国内一些在欧美获得人类学学位的学者将西方理念带入国内并且重视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尤其是大规模的介入公共卫生防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艾滋病防治领域。从2000年开始开展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是由英国政府提供1530万英镑来支持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的农村进行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的项目,涉及艾滋病的预防、健康教育、疾病的监测,有不少的人类学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17]。在这个项目的契机之下,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对毒品流动、性产业、生殖健康等领域进行密切关注,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干预,景军、庄孔韶、翁乃群、邵京、兰林友、侯远高、张有春、刘谦、郇建立等学者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中来,由此带动了一大批相关的研究。譬如景军教授展开了一系列的对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血液买卖市场和中国青少年吸毒的研究。他提出一个“泰坦尼克号”定律,认为在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存在着社会等级、风险差异与伤害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即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们在客观意义上受伤害的风险越大,在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中也都带有着类似的社会阶层烙印[17]。2003年清华大学与比尔·盖茨基金会进行合作,该基金会也大力资助中国的艾滋病项目。还有于2002年开始的由张海洋、侯高远在凉山地区所开展的“本土资源与弱势群体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和“凉山腹心地区毒品和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等项目,探讨了本土资源在艾滋病防治中的角色和价值[17]。此外,其他的一些学者,像是翁乃群等人基于在云南四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河南一个村的访问,关注艾滋病和性病在我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认为艾滋病或者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是与毒品、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这显示出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的不协调[18]。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在艾滋病问题的探讨中加入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对于妇女儿童的关注,侯高远在之后就继续在凉山彝族地区创办了“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遭受艾滋病和毒品侵害的妇女儿童的权益进行保护。靳薇在艾滋病防治中就引入了社会性别的视角,认为在相关项目的实施中,需要给女性权利并予以保障[19]。以艾滋病防控为主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不仅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提供了许多的研究机会,而且也使其带有极其明显的应用性取向,带动了之后的大量应用性研究的开展,也使得医学人类学慢慢地进入大众视野之中,为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3 2010年以来,综合的多途径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医学人类学自2010年以来发展到现在,学者们利用不同的视角,利用进入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平台,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进行合作,从不同方面去进行医学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具体来说包括有公共卫生、精神健康、慢性病防治、医患关系、叙事医学、民族医学等方面。首先,整体观视角下艾滋病的干预研究仍在继续,学者们尝试设置出与文化相适应的艾滋病干预研究,例如笔者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进行了“深圳市育龄妇女艾滋病社会网络综合干预模式研究”项目,在笔者的相关文章中,通过对深圳“性工作者”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她们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将性工作者进行分类,从而认为在对她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干预的时候,应该先寻找到合适的社区中介,重视她们在个人网络中的作用,这是考虑到当地文化适宜性得出的结论[20]。在此之前较为著名的是庄孔韶研究的利用传统仪式帮助彝族青年进行戒毒[21],还拍摄了相关的民族志影片《虎日》,他们发现了当地传统民间力量在组织戒毒上的有效性,“虎日模式”甚至被认为是亚洲目前最有效的戒毒模式之一。其次,由于疾病谱系的变化,慢性病也逐渐被社会大众所关注。医学人类学学者也开始关注慢性病相关的话题,余成普利用社会生物学视角来看待1型糖尿病患者所面临的社会苦痛,通过从患者的疾痛叙述出发,结合他们的患病经历,认为他们的苦痛兼具社会性和生物性,患者除了遭受生物性的苦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性压力,因为疾病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饮食进行控制,社会交往和工作受到了限制,婚姻观念也被改变,尤其女性患者还增加了生育风险,最重要的是无法避免的疾病隐喻和社会污名化,社会性力量对于慢性病患者的伤害更为深刻[22]。还有在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对少数民族医学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特色的民族医学。徐义强认为,哈尼族日常生活的各种疾病体验和认知都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神、鬼、灵魂观念息息相关,他将哈尼族信仰中的致病原因进行分类,分析了哈尼族宗教信仰中的疾病理论、治疗实践和神职治疗人员,并且将其与生化医疗模式进行比较,从而对传统与现代,知识与信仰进行比较和思考[23]。乌仁其其格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蒙古族的萨满医疗进行研究,结合当地的社会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变迁等因素,分析当地的萨满教仪式治疗,认为萨满医疗兼具社会功能,并且积淀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探索与经验,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和现代医学、心理学相沟通,因而现代医学可以对这一古老的传统进行借鉴[24]。另外还有大量的基于医学叙事的患者体验研究,医学叙事关注于患者自身的疾痛叙述,不仅是对医务人员的要求,也慢慢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研究方法,例如郇建立通过对内蒙古某家医院的妇产科患者进行个案访谈,调查他们的产后抑郁症相关的情况,发现产后抑郁症的负面影响、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及其局限性很高,最终提出要构建一个有患者、家庭、亲戚朋友、工作单位和医院、社区、社会文化氛围六个层次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从而形成共同防治产后抑郁症的良性环境[25]。涂炯也是基于对患者的访谈和追踪调查,对食管癌患者的病痛体验进行关注,研究食管癌及其治疗对患者身体、自我和身份带来的影响,认为食管癌切除术不仅无法治愈患者痛苦,有时反而使患者身体和生命历程进一步遭到破坏,因此强调癌症的治疗要将身体作为整体来看待,并且提出“以身体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转变[26]。由此可见,医学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仍在延续,并且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图景,从一开始的集中在艾滋病公共卫生领域,到后面扩展到临床实践、民族医学,并且开始关注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慢性病等问题。
除了大量相关的研究之外,一些优秀的国外著作也被引进来并且翻译出版发行,比如哈佛-复旦当代人类学丛书中就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医学人类学著作,如《道德的重量》[27]《疾痛的故事》[8]《全球药物》[28]等,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许多书籍也被翻译出版,前面所提及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4]《疾痛的故事》[8],还有《谈病说痛》[29]等,还有古德的《医学、理性与经验》[30],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31],图姆斯的《病患的意义》[32],布儒瓦的《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33]等大量相关医学人类学作品都被翻译过来,被介绍给更多人了解,对于我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一系列和医学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包括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以及锦州医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室。在2016年的时候于烟台成立了中国医学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置在中山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设立更加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
并且,目前仍有大量的话题值得医学人类学去研究,其中一些已经在进行中。比如基于比较观和批判视角的全球健康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健康问题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开始逐渐地被各界人士所关注,医学人类学家就尝试着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看待全球健康,在《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几位人类学家结合自己的田野工作,提出全球健康并不平等的观点,这具体表现在致病因素和治疗途径上面,他们认为不能离开直接的经验去谈论健康,并且注重国家、各个机构在全球卫生中的联系和角色,利用社会生物的视角,去探求影响人类健康的结构性暴力和社会压迫[34]。另外以往的医学人类学往往关注医生与患者的医疗行为,而以护士为代表的护理人员以及相关的照护行为被忽视,由此也提出了一种基于“照料”(care-giving)的护理人类学研究。凯博文结合自己照顾自己妻子的经历,引发了对照护的思考。他认为,在当今市场经济逻辑侵袭的社会之中,人们忽视了自我的照护体验,在他看来,照护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存在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照护行为的核心是在场,而且是人与人的一种互动,是一种互惠行为,照护者在照护的过程中收获了被照护者的经历和故事,得到了自己的道德体验。所以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也好,都必须重视照护以及思考照护存在的价值和意义[35]。这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医学人类学除了在自身学科领域仍有许多可以延伸的空间之外,它也能为目前医疗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这也符合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实践性特点。首先,随着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医学人文也越来越被重视,对医疗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能够为医学人文的培养提供自己的一分力量。医学人类学所追求的整体观和相对观更是应该成为必备的基本素养,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围的医学世界,保持更佳的健康水平以及获得更好的治疗。另外,在当今的整合医学时代,医学人类学应当成为其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将人类学的基本视角和原则方法运用到医学的发展之中。医学人类学一直带有的极强应用性说明了利用医学人类学去发展整合医学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来说也好,对整合医学的发展来说也好,都将能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