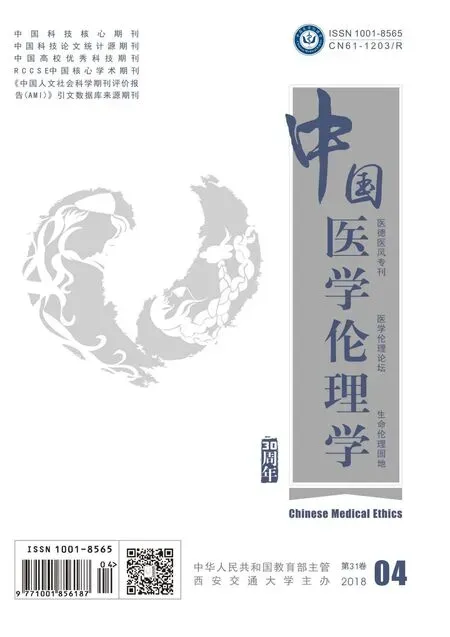生命伦理的内在自生和外部调控
——贺《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30周年
沈铭贤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上海 200042)
1979年底,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广州举办医学伦理研讨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作了国际上医学伦理研究进展的讲演,引起广泛兴趣。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大连的杜治政先生、西安的石大璞先生。
1988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西安医科大学诞生,成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重要阵地之一。之后,伴随着《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的成长、发展、壮大……她在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领域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成为学者们开展思辨、进行交流的学术高地。
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经历了萌芽、发展以及深入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生命伦理学从西方引入后,这一学科就成为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一个学科。[1]生命伦理问题的一大特点是既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又要保护患者和受试者的健康和各项权益。[2]然而,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至今依然是一个在实践中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我常常想,为什么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今生命科学和医学如此发达,还在热切呼唤生命伦理?由此逐渐形成生命伦理的内在自生和外部调控的理念。
1 生命伦理学的内在自生
生命伦理学的内在自生是指生命科学和医学发展必然会遇到、会提出来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谁有意制造出来或强加上去的。生命伦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特点。例如,如何保护基因隐私,防止基因歧视问题;能不能“克隆人”的问题,谁是父亲谁是母亲的问题;器官从何而来,能不能“商品化”[3]等问题。近年来,随着高新医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伦理学问题,如人体冷冻、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伦理、换头术等问题不断产生,这些伦理学问题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愈显密切。因此,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4]
由此观之,生命伦理的形成和发展,确实有其深厚的内在根由。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警诫人类的职业道德圣典,是向医疗界发出的行业道德倡议书。这部流传约2400年前,以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名字命名,规范医生行为的誓言,在医生中代代相传。《希波克拉底誓言》发出强音:“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2017年10月,《希波克拉底誓言》进行了第八次修订,最引人瞩目和称道的地方有三处。这三处修改均与中国医情密切相关。[5]
而我国古代医学道德观念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天然渊源,是在儒、释、道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根据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整体医学观和方法论,形成的关于中医学诊断和治疗的道德根据。[6]生命伦理学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我国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同样谆谆教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至今,《大医精诚》中关于“医德”的思想仍然在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及医疗实践活动中广为传颂,千古不衰,奉为经典。
无论是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东方的《大医精诚》,它们都强调医者要具备高尚的医德,要充满人道主义情怀,认真为患者服务,努力增进患者的健康,保护患者的隐私。医患和谐是医学的本质要求。关于医患关系,宋代医官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说道:“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悦)耳。”清楚地说明医者对患者要仁慈,患者对医者要信任,[7]若能如此,则医患和谐。
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的医患关系不那么和谐,甚至面临某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医患间信任感逐渐缺失,而这种缺失产生的后果不利于医务工作者以及未来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是治病的基本条件。所以,医生要关心患者,有良好的医德;要勤恳钻研,有精湛的医术,“精”和“诚”二者相结合。只有这样,医者才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同时患者也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对自身所患疾病和医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作为杂志忠实的读者,《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创刊之初,就很好地秉承着“促进医德医风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以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为出发点,刊登了一系列有思想、有温度、有感情的文章,读后颇为受益。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本刊物,为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权益发声,让社会大众认识、了解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作用。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杂志今后应该继续保持,并继续努力前进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领域逐步发生着变革。《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紧跟新医改步伐,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发挥凝聚各方力量,以非凡的智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 生命伦理的外部调控
生命伦理学的内在自生关系到医学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当今生命科学和医学极大地发展了,但并没有动摇这一基础。
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突破了事实与价值的樊篱,不由自主地与伦理纠结在一起,提出了诸多两难的伦理问题。[3]生命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总是与时俱进。由此,必然带来科技与伦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带了新的伦理问题。没有约束的科技是危险的。保持科技与伦理的张力,对于新时代生命伦理的发展极为重要。
科学不能背离人道,而要为人道服务。科学是为增进人类的福祉服务的,特别是生命科学和医学,更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是一项充满人性关怀的人道主义事业。[8]
生命伦理学是科学与伦理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学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9]因此,需要伦理学家与科学家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良性互动。
二战期间,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医生的表现又沉痛的昭示我们,科学家和医生也可能走上反人道的歧路,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及相关组织纷纷采取措施,以规范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行为。
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纷纷制订科学家的科研行为规范,以保护受试者造福人类,主要有:1947年纽伦堡法庭制定了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人体试验的伦理——《纽伦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作为国际上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规范;1964年6月第18届世界医学协会(WMA)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制定了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究的道德原则,该准则历经八次修订,比《纽伦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更加全面、具体和完善。它是人体医学研究伦理准则的声明,用以指导医生及其他参与者进行人体医学研究。
2002年国际医学科学理事会(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完成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该准则开宗明义,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论证是希望发现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新途径。[10]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2002年8月修订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旨在规范各国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政策。
生命伦理的外部调控促使伦理与科技两者之间相互平衡,共同发展,以达到有利于社会和社会公众的目的。同时,这也是符合生命伦理发展趋势的。2005年10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4],宣言宗旨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循本宣言所阐述的伦理原则,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
生命伦理的这种外部调控主要表现在: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规范化。科学与伦理携手合作,相辅相成,一方面是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发挥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毫无疑问,这两方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我以为,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伦理的规范的引导作用。[8]
近年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2016年)《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等,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保护医务工作者合法权益,让医学的技术更有温度,更加彰显医学是一门仁学,是一门人学的理念。
生命科学在发展中提出伦理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科技与伦理不断冲撞的过程。[2]促进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生命伦理学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其间会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非常值得为之不懈努力。[11]
近一二十年来,生命伦理学在我国已有长足发展,并初步体制化,这是非常宝贵的。生命伦理学发源于西方,成长于西方,如何在像我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大国生根开花,大有学问。[2]
3 生命伦理学与《中国医学伦理学》
我以为,近三四十年,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也有其深刻的内外原因。而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因素,都离不开社会舆论,离不开专业媒体。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可以比较公正地来评价《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的贡献。这种贡献,是无可取代的。
正因此,我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充满感情和敬意,一直是杂志的忠实读者。我现在80岁了,垂垂老矣,每每收到杂志,总是非常高兴,急不可耐地翻看。在杂志中,我不时看到一些
老朋友,十分宽慰。并开启记忆的闸门。更可喜的是,许多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不仅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观点,而且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2018年,《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走过30年,在我国生命伦理学舞台上,已占据一个重要地位,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取得学界和社会的承认。这殊为不易,可喜可贺!30年,是杂志发展历史长河中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有硕果,也有曲折,意义重大。三十而立,杂志的发展正迎来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新时代,杂志担当的历史使命也更加沉重,但潜力更不可限量。期冀《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更加美好的未来!我相信贵刊一定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办得更出色!
〔参考文献〕
[1] 刘璐.浅谈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与思考[J].才智,2014:271,275.
[2] 沈铭贤.从人文角度来思考科学——读《基因技术之伦理研究》[N].解放日报,2014-04-17(010).
[3] 沈铭贤.医学与伦理能否同行——从生命伦理学的特点探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J].医学与哲学,2012,33(11A):13-16.
[4] 丘祥兴,沈铭贤,胡庆澧.科学家的社会责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6):3-7.
[5] 重磅!“希波克拉底誓言”第八次修改,三处与中国医生最为相关[EB/OL].(2017-11-15)[2018-02-26].http://www.sohu.com/a/204438141_99968779.
[6] 程国斌,新萍.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缺陷及其历史使命[J].新疆社会科学,2008(2):10-13.
[7] 沈铭贤.医者不可不慈仁,病者不可猜鄙——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12):17-19.
[8] 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0(1):11-16.
[9] 沈铭贤.731部队——半个多世纪后的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5,26(6):32-35.
[10] 丘祥兴,沈铭贤,胡庆澧.生命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特征和行为规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1):22-26.
[11] 沈铭贤,张利萍.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