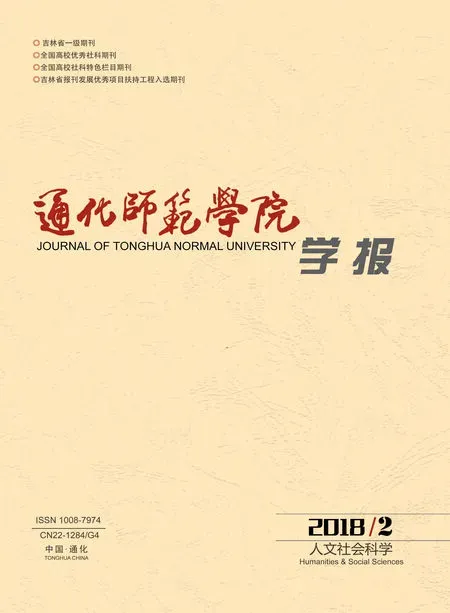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下民间造型艺术的转变
——以关索戏面具为例
薛其龙
关索戏面具是关索戏的“脸壳”。关索戏属于军傩戏的一种,浓缩了地方民众的审美观念和民间宗教信仰,独存于云南阳宗镇小屯村,村落语境下称“关索土戏”“玩关索”,面具表演称“玩脸壳”。关索戏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六期间进行演出,演三年歇三年。开演时要举行祭祀仪式,朝拜药王,演出时头戴面具,边唱边舞。关索戏专演蜀国故事,分生、旦、净三类,有张飞、假张飞、关索、黄三岳、鲍三娘、百花公主、巩固、小军、张邦、张迁、赵云、马超、秦蛟、严颜、肖龙、黄忠、周仓、关羽、诸葛亮、刘备共二十面人物面具。关索戏面具是形态夸张的“神面”,在村落语境中既具有发挥民间宗教的作用,又具有表演娱乐的功能。据田野调查得知,最早的一套关索戏面具在1921年的火灾中被烧毁,至今已无从考究。现有一套1921年版的面具是之后民间艺人进行的仿制,收藏于玉溪市博物馆。另外,在小屯村灵峰寺保存并进行演出的是一套2010年版的面具。2010年关索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Ⅵ-151。自2010年至今,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关索戏面具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而发生了多方面的转变。
一、关索戏面具的造型特点
关索戏面具以竹作框架,面部模型用胶泥做成,用纱布、棉纸和牛胶在模型上层层裱糊,然后上粉磨光,用油彩和金粉勾画线条纹饰,最后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特征装配胡须、绒球、镜面、缨、花等饰物。关索戏面具将头部及头饰连在一起,并留有鼻、眼、嘴洞供演员演出时观看和呼吸。从整体上看,关索戏面具在冠帽或发髻上有绒球、彩花和圆镜等装饰物;上色采用“勾脸”和“揉脸”两种手法,一些角色用红、黄、白等颜色勾绘出蝶纹、云纹和葫芦纹,以此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神态;面具的尺寸是正常脸面的两倍,属于半套头式面具,较戏曲脸谱更为夸张与艳俗。[1]
以2010年版的关索戏面具为分析版本,关索戏面具具有以下艺术造型特点:
(一)典型化的表现手法
关索戏面具在表现人物时参考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外形和性格的刻画鲜明。表演中考虑村落观众的欣赏水平,力求各个层次的人迅速认可并接受角色。关索戏面具的一些图案直接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并成为角色的典型化符号。关羽面具表现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造型虽近似越剧南派的关羽脸谱,同样是大红脸、丹凤眼、卧蚕眉、五绺长须,但关索戏中造型夸张,线条粗放,在额头画云纹与浓密的眉毛,表现关羽的忠心义胆。此外,孔明额头绘有太极图,肖龙画蓝脸,黄忠褐脸白髯,严颜画紫脸,这让观众可以瞬间识别出面具所代表的角色及性格特征。
(二)夸张与装饰的结合
关索戏面具是历史人物的神化,写实的形象难以在民众心中产生宗教的效果,故运用夸张的艺术表现。张飞面具是一张怒面,绘一黑十字形蝴蝶脸,蝴蝶占据整个面孔,蝴蝶有“飞”的意思,意为张“飞”之意。眉眼画于两翅之上,犹如蝶翅的花纹;蝶身画在鼻梁上,触须画在鼻尖上并向两边卷曲;张开的巨口占满整个下颏。张飞面具左右对称,用红、白、黑三色勾画,表现张飞两眼圆睁,张口大吼的骁勇之相。关索戏面具的装饰可分为头饰与胡须两个部分。有胡须的形象包括:张飞、假张飞、马超、严颜、肖龙、黄忠、周仓、关羽、诸葛亮、刘备。胡须多依据人物角色、性格进行艺术装饰,如黄忠的髯、关羽的长须等。头饰除诸葛亮外皆有绒球装饰,个数在5至8个之间,7个绒球的面具最多。绒球颜色丰富、艳丽,以脸面中间为分界,一般呈现左右、大小、颜色的对称。绒球的装饰使面具更加生动、显眼,在配合戏曲表演时,使面具增添了动态的活力。
(三)表演性成分的纳入
关索戏面具在村落空地中表演,考虑让所有人都能观看,面具的外形尺寸大,强调角色的符号特征。为了体现避邪驱鬼的寓意,关索戏面具在注重人物写实的同时更追求造型的神圣性表达,起到一定的宗教恫吓作用。关索戏在演唱的时候自报家门亦是一种表现面具身份的方式,表演成分与面具造型相结合构成了关索戏面具独特的造型特点。
(四)色彩的搭配
关索戏面具的色彩也是重要的艺术造型表现之一,善于运用补色对比,对立色块的拼接,金、白色的分割间隔手法。关索戏面具净角颜色丰富夸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张邦面具为例。以红色为面部基调,额头是深红色,脸颊是大红色,眼睛、胡须是黑色,鼻头与鼻翼是翠绿色,黄色运用在下颚与各个颜色的分界处。张邦戴翠绿色帽子,饰有云纹与圆镜一面,绒球装饰分别是黑色、大红色、灰色。整个面具以红色为基调,再以补色或中性色为填充,以呈现多彩的变化与人物的特征。类似的面具有巩固、假张飞。第二类以大面积强烈而多变的色彩为主。张迁面具以黄色为划分线与装饰线,额头以蓝色与红色组合,脸颊为绿色,嘴巴及下颚为红色,头帽为黑色,黑色、大红、粉红、浅蓝、灰色构成了绒球装饰。这面面具色彩鲜艳强烈,色彩对比度强烈而力求和谐。纯度很高的红、黄、蓝、绿色的运用,使角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得以强化,以至于在表演时非常醒目和吸引观众。第三类采用在各色彩之间插入金、白色进行隔色来勾勒外形轮廓。巩固面具以黑色为主,额头为绿色,下巴为黄色,帽子为墨绿色,各种不同的色彩由装饰性的白色线条进行分割勾勒。
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后关索戏面具的变化
关索戏面具随关索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外在造型到内在文化意义皆有转变。关索戏面具的转变是当前关索戏发展的需求,也是民间造型艺术的时代表征。不足的是,民间宗教面具的神圣性减弱,逐渐疏离艺术存在的语境,地方性知识融合了传统艺术特色与现代商业因素,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倾向。如果把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一个变化的节点,那么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前的关索戏面具倾向于传统的民间宗教艺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关索戏面具倾向于现代的民间大众艺术。
(一)从夸张到概括的造型转变
就1921年版的面具与2010年版的面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随着关索戏面具版本不断地更新,艺术造型由以往复杂的纹饰、丰富的色彩搭配转向抽象性的概括。1921年版的面具造型各异,面具外型差距明显,人物面部颜色丰富,色块面积小,分割线多,绿色运用多。帽饰花纹繁杂,胡须颜色丰富,头饰除了绒球还有纸质花朵。2010年版的面具造型相近,色块面积大,色彩丰富,头饰绒球较多且颜色多样,整体上显得简化,倾向大众化。以肖龙为例,1921年版的帽子两侧靠近头顶,有凹凸起伏的四个帽檐,上有帽翎,绘有丰富的花纹;2010年的帽子到耳朵位置,它由一个整体弧形帽子组成,描绘的图形比较简单且变化较少。最为突出的区别是面部颜色。1921年版以绿色为脸颊、下颚以及额头的色彩,变化丰富;2010年版的面具则由蓝色构成面颊,土红色为额头,黑色为下颚,色彩概括成了几个色块,变化略显单调。此外,张飞的褐色脸变成黑脸;百花公主的花朵被绒球替代;严颜的紫脸变成了棕色脸。
关索戏原生的造型特点主要基于民间宗教的需求,围绕三国人物进行造型的夸张表现,使形象能够有效地表达宗教寓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使1921年版的面具成为供人欣赏的文物,博物馆的保护取代了面具在村落中的应用。2010年版的面具代替先前一套面具的功能,开始在村落语境中表演。小屯村村长陈文强说:“刚拿到面具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画的人物是谁,变得都不认识了……现在的面具和戏服是澄江县文化局做的,做得很粗糙,人物的造型做得很随意,用料也很差。面具和戏服都是用水彩画的,一碰到水就变污了,戏服则从来不敢洗”。此套面具的造型不再以宗教传达为主旨,而是考虑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强调造型的工艺性特点。所以,面具的造型上未见细致的描画,角色特征趋向符号化的概括。关索戏面具从夸张到概括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当前民间造型艺术的普遍转变现象。
(二)从“神面”到“人面”的审美转变
1921年版的面具脸谱化强,面部以竖眉、凤眼为主,形象为非现实生活人物;2010年版的面具面部以粗、横眉,圆眼为主,具有现实生活人物形象的特点。1921年版的面具呈现出“神面”的审美倾向。面具是村落宗教信仰的神灵代表,其形象威严、略带凶相,产生一种恫吓感,发挥庇佑村落的功能。黄忠扮演者龚自成说:“演员戴上面具之后必须变得严肃且不许闲聊,以往的口头禅、骂人的话以及对神灵不敬的行为必须收敛。戴上面具后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不能说话、抽烟,要规规矩矩的。最难熬的是不许上厕所,如果想去厕所必须等到戏曲结束,不可以单独行动,否则就是对神的不敬,违反了会得到厄运”。2010年版的面具整体表现出“人面”的审美倾向。关索戏面具形象源于世俗的人物,剧目源于现实故事的改编,具有民间艺术世俗性的一面。随着宗教教义的减弱,村民更愿意接受民间的世俗化表演,娱乐大众的关索戏面具表演表现出“人面”的世俗审美。在表演性活动中,通过戏曲形式上演有人物、有情节、有冲突、有故事的剧目,踩村、踩街、踩家的表演皆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娱神娱人。
由于依附于关索戏这一戏曲形式,表演性处理是关索戏面具的独特审美表达。关索戏表演不仅是戏曲艺术的完成,同时也包括面具艺术审美活动的完成。但因时代的发展、宗教精神的褪色、外来游客的需求使关索戏趋于大众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1921年版的关索戏曲、面具、服饰成为另一种静态的审美方式。2010年版的面具代替前一版发挥村落的审美功能,更趋于世俗化取向。作为戏曲艺术的关索戏审美的转变一方面保护了面具,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生状态。总之,关索戏面具审美功能的转变不是文化自觉的发展意愿,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促生。
(三)从宗教庇护到娱乐宣传的功能转变
“系统论观点认为,当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异,系统的各个层次核心要素变化和新的结构要素将影响整个子系统的稳定,系统会发生解构,最终形成新的稳定系统。”[2]169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影响到关索戏面具的外在造型,而且影响到面具的深层文化寓意。政府着力打造关索戏成为“地方名片”,神圣性的面具成了地方对外宣传的艺术样板。关索戏面具是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符号,通过仪式表演以及戏曲演出达到驱邪避疫的意愿。村民们崇拜三国历史人物的成就,相信他们的神圣力量有益于村落稳定。村民对关索神灵的崇拜物化为面具的崇拜,戴上面具与摘下面具是两种不同的身份。“面具使用者一旦戴上面具,他与面具所象征的对象便产生了一种生理—心理的认同。通过观众的参与,这个认同又获得普遍的承认和强化,是面具被戴着完成了从一种存在向另一种存在的转换。如果这个面具象征的是神,则这个转变就是从人格向神格的转变。傩面具所具有的象征,正是如此。”[3]156据传承人李本灿所言,“以前看到面具都敬重得不得了,自己都要谨慎一举一动,表演时不能说话,不能干这不能干那,生怕有所冒犯。现今,科学已经推翻了以往的迷信,也没有必要那么刻意地注意了”。无论是对村落的凝聚力还是对外文化渗透,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关索戏面具是庇佑村落的宗教艺术,具有重要的民俗功能。其一,关索戏面具维系和强化着家庭、村落之间的关系。通过关索戏的不同场合的表演,围绕着追忆祖先、供奉药王、演唱戏曲,加强着村落内部的群体认同。在与村落交流过程中,关索戏面具起到了艺术联络的作用。其二,教化功能。在祭祀活动和表演活动中,关索戏面具把村落的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起到认知社会的功能和宣扬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的作用。
神圣不可亵渎的关索戏面具表演还是节日娱乐中增强气氛的艺术活动。在关索戏祭祀仪式唱词中有“药王大将,今年我们大家诚心诚意替你家去玩玩。”“玩”更能贴近村民生活,切合村落的语境。可见,人们对关索戏面具的称呼中有一种世俗娱乐因素。自从关索戏面具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迅速地涌入小屯村,传统语境下的宗教艺术受到了多视角的关注。关索戏面具因满足外来人对异文化的体验而被不断地开箱表演,演三年歇三年的传统被打破。记忆犹新的是,在我第一次踏入小屯村进行考察时,村民执意问我是否需要观看关索戏表演,观看费用一次至少两千块钱。村落中随处可见对关索戏的宣传标语,传统的宗教、民俗功能的面具成了获利、宣传的工具,成了日常生活中经常观看的节目。关索戏面具在越来越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神圣性”的宗教功能,转向地方娱乐宣传乃至获利的工具。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动:关索戏面具转变的原因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些民间艺术正濒临消亡,创作主体正面临着边缘化、老龄化;另外一些民间艺术却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它们皆经历着历史潮流的更迭,当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术。钟敬文对民俗转变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民间艺术。他认为“这种适应着大集体或小集团人们的各种要求的民俗文化功能,虽然是相对稳定的(有的竟延续了两三千年),但一般来说,它并不是长久不变的。社会在或慢或快地变动着,人们的生活和它服务的文化当然也不能永久不变。有的民俗消失了,有的则是随着人们生活、文化和心态的变迁而变了形,乃至变了质——包括机能的转变。”[4]5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民间造型艺术,但是作为其组成部分亦受影响。如果没有关索戏面具的物质造型,非物质的关索戏所演唱、宗教表达、表演技巧、文化知识则无法呈现出来。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作用于关索戏又作用于物质形态的面具。关索戏面具的现代转变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申请,小屯村因此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外来的文化力量改变了艺术的话语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关索戏面具的转变主要集中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多方力量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原因:
(一)研究者的介入
1994年在云南澄江县举办的傩戏傩文化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依据关索戏面具的基本情况进行文字的整理与文化深度的挖掘,不仅增加学术研究的维度,同时在更大范围上传播了这一民间造型艺术。2010年后,更多的学者进入小屯村,他们的书本或文字成了村民对话的一部分,使村落文化在与对外交流、传播中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陈文强说:“我们这个戏,看不懂的人觉得没有意思,看得懂的会着迷。很多专家和外国人都专门跑来看!从傩戏研讨会到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段时间,来看的人比较多,演出也多,从中能赚到些劳务费。专家看戏的比较多,只看看脸壳,他们看完就走了,对村里也没啥帮助。实际上关索戏并不好看,真正对关索戏感兴趣的,只有专家和记者。”先前研究者的话语甚至反作用于后来的研究者,即村民重复着研究者的言论。由此可见,研究者成为主导关索戏面具转变的新的文化精英。在传统村落中,以民间艺人及熟悉村落文化的村民组成的大众群体显然不再具有绝对话语权,而那些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取代传统的民众话语成为新的“发言人”。村民对研究者话语权的接纳与认同是造成关索戏面具转变的推进性原因
(二)商业价值的吸引
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附加值是当前村民普遍的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既体现在对经营各类非遗产品所获得的直接收入上,如通过经营相关产品、纪念品直接获利等;还体现在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所取得的间接经济效益上,如同旅游业、餐饮业的结合。娱神的面具能够赚钱是关索面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有的现象,村民以此为中心展开相关的商业活动。首先,面具的表演者们四处进行关索戏的商演,每次每人能赚得四百到五百块钱。其次,把面具做成工艺品销售也是当前的一种新趋向。第三,旅店、餐饮等因关索戏面具而发展起来,外地的文化公司也参与进关索戏面具的商业活动中。一位旅店老板说:“三年前,这里还没有一家住宿的地方,游客大多当天就回去了,要不就上昆明市里住。后来来看戏的多了,很多还会住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开了一家宾馆。这也算是因为关索戏而赚得到钱”。由此可见,商业价值改变了村民对关索戏面具的观念,成为关索戏面具转变的利益性原因。
之所以吸引商业活动,新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005年《千里走单骑》的热映促使影片中的关索戏及面具成了万众瞩目的艺术焦点,外来的专家学者、游客、戏迷、记者出于对异文化的体验前往小屯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关索戏面具成为了文化资本,各类影视、媒体纷纷拍摄和报道,一时间名声大噪。村民为满足外来人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商业活动,新媒体下的民间造型艺术展示成为了诱发商业活动的因素。
(三)政府的规划
成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味着关索戏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这成为关索戏面具转变的政策性因素。关索戏面具成为了文化瑰宝,由镇政府牵头打造文化品牌,带动村镇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规划下的关索戏扩展了原生的功能,从宏观上调控关索戏面具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政治目的。正如在阳宗镇“十二五”规划中,对于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措施作了特别强调:“抓住旅游二次创业的大好时机,充分挖掘阳宗镇厚重的三国文化历史,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索戏为依托,充分利用农耕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引进大的旅游投资项目,把阳宗镇建设成独具特色的三国文化旅游小镇。”[5]依托关索戏为发展契机,阳宗镇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文化旅游圈,使其成为现代化、商业化的旅游消费地。政府力量的参与与支持使关索戏及面具走向了产业化发展之路,关索戏面具走出了小屯村,面向一个更广阔的社会与群体,加速了文化的交流。
四、结语
关索戏面具在艺术造型、审美特征与文化功能的转变是民间造型艺术在非遗时代所展现的面目。多方力量参与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当前民间造型艺术繁荣发展的机遇。它一方面给予民间造型艺术新的发展契机,那些正在消失的民间造型艺术受益于非物质形态的保护,重新受到重视、保护、应用;另一方面因传播、接受对象面的扩大,各类民间造型艺术不再是传统村落中的存在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政府、学者、商业等力量改变了民间造型艺术发展的自在“话语权”。
2005年,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开始实施,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活动逐渐深入村落,使民间艺术的发展步入一条被“规范化”之路,其保护与发展趋向于物质化形态转变。整体上看,当前关索戏面具与其他民间造型艺术发展模式趋同,转型成工艺商品的形式,成为对外宣传、未来发展的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为关索戏及面具带来了利处,但通过关索戏面具的转变提示我们,一种脱离文化土壤的规范化发展模式也有弊端的存在。我们在大肆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谨慎地反思它带来的转变。
[1]薛其龙.云南关索戏面具艺术的人类学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3.
[2]李炎.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М].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岚.信仰在创造人类学视野中的价值[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研究[М].北京:中央民俗大学出版社,1994.
[5]参见阳宗镇信息网,httр://www.уnszхс.gоv.сn.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