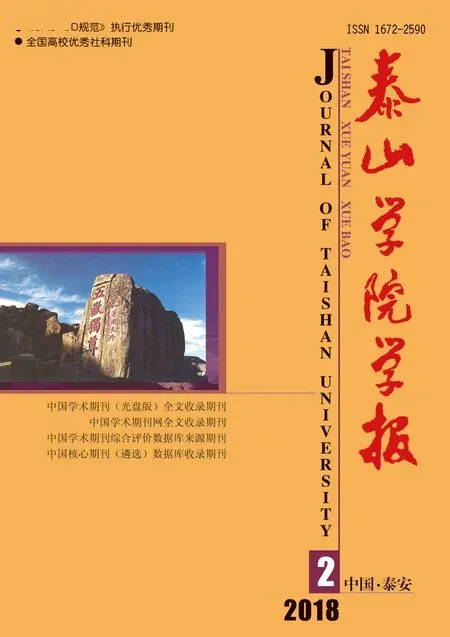泰山经石峪刻经变迁考
丁 武,李泰衡
(1.陕西师范大学 教师干部教育学院;2.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泰山斗母宫东北1公里的山谷中,有一块南北宽40.8米、北部长60米、南部长32米的天然石坪,上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谷因而得名经石峪。经石峪刻经现存1313字(含残字),字径约50厘米,楷隶兼备,书法道劲,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摩崖刻经之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刻经未竟全功、一度荒芜,在明代以前的文献和遗物中记载较少,明代后期以来,人们才逐渐关注到经石峪刻经,在其创作年代和作者等问题上进行了初步研究。近年来,赖非、安廷山、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周郢等国内外学者以及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参与了对经石峪刻经的内容、镌刻工艺和周边题刻等的研究与开发,分析了刻经工程的特征和时代背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经石峪刻经的年代、作者等问题,对其发展流变过程缺少梳理和分析。本文在对历代与经石峪刻经相关的方志、诗词、游记和字帖等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拟探讨经石峪刻经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一、经石峪刻经的起源
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已经形成了摩崖造像和摩崖刻经艺术。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石刻艺术的东传,以及北魏太武帝灭佛运动带来的佛教传承危机,僧人将山崖刻经视为更具永恒性和神圣性的弘法媒介[1],在邺城(今邯郸)和泰峄山区率先开展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经,留下了邯郸中皇山和邹城铁山等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摩崖石刻[2]。泰山经石峪刻经为南北朝佛教石刻艺术兴盛时期的作品之一。
由于经石峪刻经工程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与文物资料,刻经的具体时代和主要参与者目前均不得而知。历代学者对石经进行了考证,根据周边同时期字体相似的石刻,基本确定其形成年代是北齐,推测书写者可能为安道壹、王子椿和唐邕等人[3]。
经石峪刻经工程能够开展,是建立在浓厚的佛教氛围和充足的人力财力保障这两个基础上的。首先,泰山南麓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繁荣,先后出现了光华寺、云台寺和四禅寺等至少七座佛教寺庙[4]。其次,佛教刻经事业也得到了社会的支持,附近邹城铁山、尖山和水牛山等同时期刻经,出资人群体中不乏将军、郡守等官僚[5]。此外,还有学者从石刻本身出发进行研究,指出经石峪刻经镌刻宽而深、字径大,采取了较为特殊的“楷隶”字体,这样的搭配已经远超拓印的要求[6]。从以上特点来看,经石峪刻经最初旨在弘扬信仰,是佛教徒集中表达虔诚的一处圣地。
经石峪刻经工程在尚未完成时便戛然而止了,今天所见的石坪上依然保留着规划好的空白行格和众多双勾待刻的字,对于停工原因,目前认可度较高的解释是北周武帝灭佛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诏令全国灭佛,一切刻经造像活动被迫停止,建德六年(577),北周吞并北齐,灭佛运动在山东地区推行,泰山(北齐属兖州郡)在这次灭佛运动中遭到冲击,经石峪刻经应当就是这一时期被迫停止的。面对灭佛运动,齐地僧人大举逃往南方陈朝,这又解释了齐地灭佛运动短暂但刻经没能复工的原因[7]。
二、经石峪刻经的发展流变
(一)自刻经中断到北宋时期经石峪的衰败状态
自刻经中断到北宋的500余年间,经石峪刻经既没有文献记载,周边石坪附近也没有题刻。乾隆年间修成的《泰安府志》共收录明代以前创作的诗歌100首、赋4篇、记33篇,这些诗词文章中多次提及了泰山的日观峰、南天门、五大夫松和御帐坪等景观,却没有关于经石峪刻经的任何记载[8]。宋人袭庆守、钱伯言的《游览记》是二人登泰山的游记,几乎每至一景必有详细记载,白龙潭、金母洞(吕祖洞)等寻常景点均有介绍,且白龙潭与经石峪相距不远,如果作者看到经石峪刻经应当不会只字不提,推测二人当时有可能不知道经石峪刻经的存在。
北宋政和七年(1117),经石峪刻经周边出现了第一个题刻,上书“莆阳陈国瑞子玉,按学奉高,观石经谷。熟视笔画,字径尺余,非人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岂非神物护持以遗观者?政和丁酉春余一日,丞议郎知县事郑温恭勒石。”这块刻石是已发现最早的提及经石峪刻经的题刻,同一时期陈国瑞还在距经石峪不远的“宋白龙池题名碑”上题名[9],可印证经石峪处题刻的真实性。但自陈国瑞题刻至明代中期的400余年间,经石峪周边再未留下题刻。
宋代题刻的存在,说明经石峪刻经在明代以前并非从未被发现,但是基于周边古迹匮乏、传世文献不载等情况,可以推测经石峪刻经在明代之前基本处于无人问津、长期荒芜的状态。
(二)明代经石峪刻经的观赏和文化功能逐渐强化
明嘉靖年间到明末的约100年间,众多官僚和知识分子来到经石峪题刻,对其景观进行规划设计,并将其运用到文章和诗歌创作中,将经石峪视为风景名胜和文学创作源地。这使经石峪刻经的影响力相比此前的衰落状态发生了显著转变,除新增的大量名士题刻外,有关经石峪刻经的记载还广泛地出现在方志、诗词和文集等文献中。
明嘉靖十二年(1533)修成的《山东通志》是目前所知最早提及经石峪刻经的文献,《山东通志·卷五山川上》“济南府”的“泰山”和“王母池”两条目下以列举的形式提及了经石峪刻经的存在。同一时期还集中涌现出一批关于泰山的文献,主要有汪子卿《泰山志》(1554)、袁禾仓《泰山捜玉集》(1581)、查志隆《岱史》(1587)、宋涛《泰山纪事》(1612)、萧协中《泰山小史》(崇祯年间)和张岱《岱志》六部。除《泰山纪事》外,其余五部书均在泰山地理、遗迹及其他有关章节下对经石峪刻经作了专题介绍,但这一时期对经石峪刻经的介绍普遍比较简略,没有考证刻经的年代、作者以及周边的题刻。这些文献中还大量收录了有关泰山的文学作品,经石峪刻经在嘉靖年间第一次被载入了诗词,自此以后,经石峪刻经时常出现于各类文学作品,还有许多诗文直接以经石峪为题。
经石峪刻经周边的题刻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大量出现。首先,来此题刻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名士,如万恭题词时官至兵部左侍郎、李邦珍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坦、方元焕等人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其次,题刻记叙了万恭等人对经石峪一带进行开发的过程,在漱玉桥和高山流水亭建成后,游人才得以方便地进入经石峪观赏。另外,早期的题刻对经石峪刻经等景观并非都持赞美态度,《诗·般》、《大学》和《经正》等题刻均表达了强烈的重儒排佛观念[10],随着人们对经石峪刻经的关注转移到了审美层面,这种争议才逐步平息。
经石峪刻经石坪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四面群山环围、深谷幽奥,周围松柏葱郁、山溪流经,不但是宏大的刻经遗迹,还是一处巧借自然、浑然天成的隐秘景观。尤其是万恭在石屏旁修建高山流水亭和漱玉桥、镌刻题壁后,该地被赋予了“自然、历史、佛迹”三位一体的独特意义。明代后期,众多重要官员和著名学者的到访、开发、创作和传播使经石峪成为泰山中的重要景点,文人墨客在这一风气的带动下热衷于借经石峪之景题写诗文,争相咏赞其清静和幽深的景致。这样的兴盛持续了约一个世纪,此时的经石峪俨然是一处游览胜地。
(三)清代以来经石峪刻经的艺术研究占据主导
清代以来,经石峪刻经在金石学和书法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成熟,文献中广泛留下了学者对经石峪刻经书法价值的探讨,相关文学创作和题刻的热情则有所减退。
经石峪《金刚经》书法雄豪大气、稳重有力,结构圆润饱满、宽扁伸展,介于隶楷之间的字体有较强的南北朝时代特点[11]。因为审美差异,明代人对其书法评价不高,随着清代碑学兴盛,经石峪刻经的书法艺术价值才得到普遍认可[12]。清代后期的许多著名学者对经石峪刻经的字体和内容进行了研究,由于刻经被山溪流水漫过,石坪边缘被泥沙掩埋,且刻字太大、太多,身处峪中难以细致观察,制作完整的拓片十分不易,因此学者得出的结论常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阮元《山左金石志》载:“刻字径尺余,年久磨灭,存者无几,拓工以一纸拓一字,未详文义,因取《金刚经》覆对,只存二百九十六字。”[13]以此可见清代学者认识经石峪刻经全貌的过程是曲折的,即便如此,经石峪刻经仍收获了学者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包世臣《艺舟双楫》称之“有云鹤海鸥之态”[1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之“榜书之宗”[15],魏源《岱山经石峪歌》称之“雄逸高古”[16]。
经石峪刻经的书法还影响了泰山的碑刻和牌坊。泰山碑刻牌坊无数,在石碑和牌坊的题字中,“中天门”坊(清)、“北天门”坊(1985)、“天柱胜境”坊(现代)以及“树种汉时”碑(现代)采用的是经石峪《金刚经》的书体,天贶殿“东岳泰山之神”牌位和“望吴胜迹”坊(明)带有显著的经石峪《金刚经》书法特点,其书写者应当精心临摹过经石峪刻经。这些书法作品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经石峪刻经书法艺术性的认可。
三、经石峪刻经的文化价值
由于刻经工程意外中断,最初的宗教目的在此后失去传承,这留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明清和部分近代人士也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1988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首个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混合遗产),评审报告以众多儒学和佛教碑铭为例证明其“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17],经石峪刻经正是泰山“双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经石峪刻经具有较高的佛教影响力和历史研究价值,是一处重要的佛教遗迹。经石峪刻经是南北朝时期石刻工艺和佛教信仰的结晶,石坪上镌刻的《金刚经》一直发挥着弘扬佛教和传承经文的功能,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第二,经石峪刻经还是一处游览胜地和重要文学创作源地。明晚期士大夫对经石峪的游览设施和景观进行了改造,在此进行文学创作和摩崖题刻,他们留下的作品已成为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古今游客和文人来到此处观赏、创作。
第三,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和镌刻具有艺术指导的功能。清代的艺术家和学者率先重视到经石峪的艺术价值,结合经石峪刻经的特点总结了多种榜书书法理论和摩崖镌刻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推进。艺术家的推崇还使经石峪《金刚经》字体在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于世,成为书法临习者的必修字体之一。
经石峪刻经的文化价值,是包括历代佛教遗迹、历史遗迹、旅游景观、文学源地、书法名帖和石刻佳作六大元素的集合体,是古今众多一流僧人、工匠、文人和学者所共同铸就的,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因此,应意识到经石峪刻经以及泰山的其它遗迹有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要重视其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在今后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充分体现泰山文化的多元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