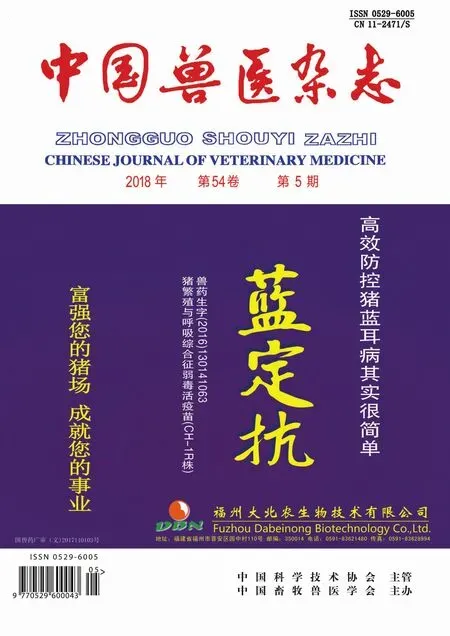牛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牛肺脏脾脏和淋巴结的病理学变化
王振玲,倪家敏,孙 欣,程广宇,刘春法,岳瑞超,王 杰,廖 轶,周向梅
(1.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畜牧兽医系,北京 房山 102442;2.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北京 海淀 100193)
牛结核病是许多国家牛群的主要传染病之一,造成养殖业较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各国之间动物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据世界卫生组织称,牛结核病是一种被忽视的流行性人兽共患病,其在人类中引起的临床症状与结核分枝杆菌相同,如何净化牛结核病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共卫生问题。
自1882年Koch发现结核杆菌以来,人们对结核病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关于牛结核病的文献报道也是层出不穷。但由于天然宿主比较昂贵,还需要专业的设施来进行实验,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是在小鼠、负鼠等易感实验动物中进行的[1]。因为牛结核病多呈隐性感染,难以诊断;而且天然宿主对该病的反应有可能与实验动物的反应不同,因此本试验通过利用牛分枝杆菌致弱株人工感染实验牛,观察并记录其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各器官的病理组织学变化,为研究牛结核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提供参考信息,为牛结核病的诊断提供病理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 本试验所用牛分枝杆菌致弱株(NO.2)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动物海绵状脑病实验室保存。
1.2 实验动物 购自某牛场3~6月的犊牛6头,用PPD和IFN-γ释放试验检测为结核病双阴性,隔离饲养于圈舍。
1.3 试验方法
1.3.1 细菌悬液的制备 将细菌接种在7H9液体培养基中,置于37℃的恒温摇床中培养。6~8周后将菌液倍比稀释接种于7H10固体培养基中进行菌落形成单位(CFU)计数,然后把细菌数量为1×103CFU的菌液保存于-80℃冰箱中待用。
1.3.2 动物的分组及接种方法 将6头犊牛分为两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头,打好耳标。采取鼻腔接种的方法,用5 mL注射器吸取菌液依次向试验组犊牛的鼻孔中缓慢注入菌液,每侧鼻孔注入1 mL,故试验组的感染剂量为2×103CFU。
1.3.3 大体病变的观察 饲养7个月后,颈静脉放血处死试验组和对照组犊牛,将犊牛尸体进行剖检。对比对照组,观察记录试验组的器官或组织的大体病变。
1.3.4 病理组织学观察 对比对照组的犊牛,将试验组犊牛的心、肝、脾、肺、肾、淋巴结、胃、肠等器官有病变或疑似有病变的部位切取下来,放入10%福尔马林中固定。
固定好的样本经常规组织处理,石蜡包埋,2 μm切片,经H.E.染色后置于光学显微镜观察,采集数码图像,记录结果。
2 结果
2.1 剖检病理学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牛只普遍消瘦,皮下及各脏器脂肪较少,肺脏表面散在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粗糙的、灰白色结节,其他器官没有明显的眼观病理变化。
2.2 组织病理学变化
2.2.1 肺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对照组的肺组织无明显异常,可看到正常的气管、血管和肺泡等结构(如中插彩版图1A);高倍镜下可见肺泡隔由薄层结缔组织构成,气管和肺泡中很干净,血管中有较多红细胞聚集,可能是由于放血不良导致(如中插彩版图1B)。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低倍镜下的肺组织结构紊乱,很少看到正常的肺泡和气管结构,肺实质被大量炎性灶所占据,特别地,还可看到试验组的肺组织中有多个坏死灶(如中插彩版图1C);高倍镜下可见坏死灶为明显的肉芽肿结构:中心部分为嗜酸性的干酪样坏死和钙化,中间部分可见上皮样细胞和多核巨细胞以及淋巴细胞,外围部分为成纤维细胞和纤维细胞构成的结缔组织(如中插彩版图1D,由于肉芽肿结构过大,该图未显示外围结缔组织)。
2.2.2 淋巴结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对照组的淋巴结没有明显病变,皮质淋巴窦、淋巴小结和副皮质区界限明显(如中插彩版图2A);高倍镜下可见淋巴小结中的淋巴组织较密集(如中插彩版图2B)。试验组淋巴结中有些淋巴小结可见到蓝紫色的钙化灶(如中插彩版图2C)。在淋巴结组织中还可看到几个明显的肉芽肿结构,肉芽肿的中心部分为蓝紫色的钙化灶和粉染的干酪样坏死灶,中间部分可见上皮样细胞、多核巨细胞和少量淋巴细胞,外围部分为成纤维细胞和纤维细胞构成的结缔组织(如中插彩版图2D)。另外,还可在淋巴结中发现少量的炎性灶(如中插彩版图2E);在高倍镜下可见到炎性灶中的炎性细胞多为嗜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如中插彩版图2F)。有些淋巴小结稀疏、空亮(如中插彩版图2G);高倍镜下可见淋巴小结中的淋巴细胞大量减少(如中插彩版图2H)。
2.2.3 脾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对照组脾组织可见明显的小梁结构,白髓与红髓界限清晰(如中插彩版图3A);高倍镜下可见白髓中淋巴细胞密集分布,红髓中有大量的血窦(如中插彩版图3B)。试验组脾局部可见脾小体结构消失,白髓与红髓界限不清,还可看到出血、淤血的现象(如中插彩版图3C);高倍镜下可见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红细胞混杂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界限(如中插彩版图3D)。镜下还可见较多白髓变得稀疏、空亮,显示其淋巴细胞大量减少,与中插彩版图2G、2H病变相似。
3 讨论
本试验中,试验组的感染牛的特征性病理变化是在肺脏和淋巴结中产生了特异性的肉芽肿结构,其肠道和浆膜没有发生明显的病变,这与牛的结核模型中的病理变化是一样的,可能是由于试验的感染方法是鼻腔接种的呼吸道感染方法,且攻毒剂量不是很高[2]。而在病牛的肺脏和肺门淋巴结中形成局部的炎性灶和坏死,这些病变可能是形成肉芽肿结构的前期变化;病牛的脾脏发生的淋巴细胞相关病变说明牛分枝杆菌感染会引起机体的免疫应答反应。
感染牛结核病的野生动物负鼠、鹿、狮子等一般会在肺脏中发现结核病灶,有时也会在肠道中发现结核病灶,说明其主要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牛分枝杆菌[3]。而小鼠虽然也会在脾脏、肺脏发现类似的结核病灶,但其在光学显微镜下的结构一般看不到干酪样坏死,与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也是小鼠的牛结核病模型的缺陷[4]。
不同的接种方法和不同的接种剂量都会对牛结核病的模型造成不同的病理变化,本试验是对试验牛进行鼻腔接种,感染剂量为2 000 CFU的致弱株,感染牛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在肺和淋巴结形成特异性的肉芽肿结构,而其他器官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病理变化。在小鼠模型中,同样是鼻腔感染,当接种高剂量的牛分枝杆菌时小鼠发生急性死亡,当接种低剂量的牛分枝杆菌时,小鼠则不表现明显的病理变化[5]。而对小鼠进行静脉注射时,相同的剂量在鼻腔感染时小鼠很快死亡,在静脉感染时小鼠能存活很长一段时间;试验还测定了小鼠脾脏和肺脏的荷菌量,发现无论是接种方法还是接种剂量都不影响脾脏中的荷菌量,但鼻腔接种时肺脏的荷菌量呈剂量依赖的趋势且明显高于静脉接种时的荷菌量[6]。在牛模型中,静脉和皮下注射的接种量同样要高于鼻腔和气管的接种量,并且提出呼吸道感染才是最接近于自然感染的接种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对牛结核病免疫应答动力学的理解[7]。这些文献的结果与本试验只在肺和肺门淋巴结中出现典型的病变而脾脏及其他器官中没有这些病变的结果是相符的,还证明了本试验的合理性。
牛结核病的典型病变就是形成特异性的肉芽肿结构,这是机体抵抗牛结核分枝杆菌扩散感染所作出的防御反应,然而分枝杆菌作为一种胞内寄生菌能够存活于肉芽肿中的巨噬细胞中,那么肉芽肿的产生对于患病动物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呢?分枝杆菌感染机体时,进入机体内被巨噬细胞所吞噬,首先就是细菌与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尽管巨噬细胞擅长吞噬和破坏包括死细胞和细菌在内的生物颗粒,但分枝杆菌已经适应了严酷的细胞内环境,进化出了多种方式来抑制巨噬细胞的功能,使其能够逃避巨噬细胞的杀伤作用而在其中存活和复制[8]。虽然在分枝杆菌和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中,机体能够通过促使巨噬细胞凋亡和细胞免疫应答来消灭分枝杆菌,但机体并不能清除全部的分枝杆菌,这些防御机制会使一部分分枝杆菌进入休眠状态,当免疫能力减弱时,分枝杆菌就有可能被再激活,机体就会复发结核病[9]。因此,牛结核病所形成的肉芽肿结构对机体来说是既有利也有弊的,其中的巨噬细胞与牛结核分枝杆菌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研究结核病的新的治疗干预方法以及增强疫苗功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