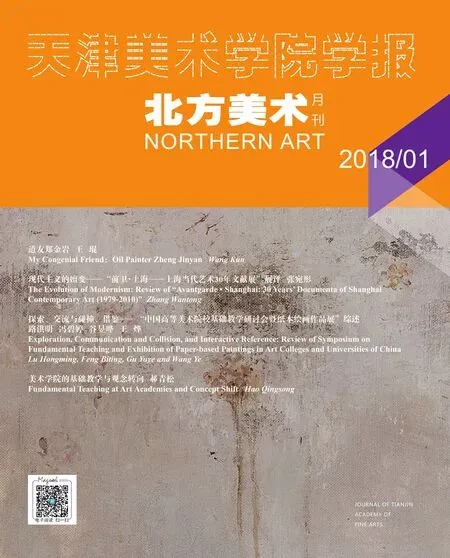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与观念转向
郝青松
近三十年来,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一直在应对当代艺术的挑战。为此,大多数美术学院整合了各个专业系科的基础教学,设立基础教学部,从专业通识的角度切入专业细分之前的准备阶段,希望在宽口径的基础教学之后学生能够不被专业封闭,持续存有当代艺术的跨学科意识。同时,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依然不断提出新问题,对学院基础教学提出新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基础部教师的当代艺术认知。虽然从事基础教学,但每位艺术家教师都出自不同的艺术专业,同时也从事着不同专业的艺术创作。教学计划出自人的理念,某种意义上,基础部教师的当代艺术认知,决定了基础部教学理念的确认和计划的制定。而同时作为艺术家的基础部教师的作品,正像一个镜像,透射出基础部教学的真实面容。
美术学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绘画学院,而是成为以艺术学为一级学科包括造型艺术、设计艺术、实验艺术三大组群的视觉艺术学院,有的美术学院又进而把中国画专业从造型艺术中区分出来独立成章,建筑专业也从设计艺术专业中独立出来而归入建筑学的一级学科。可见,基础部教学远非统而化之那么简单。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语境下基础绘画的意义何在?现代艺术时期绘画最为纯粹,为艺术而艺术,倡导形式主义,几乎剥离了艺术之外的所有附加意义,但这也是艺术最苍白的时候。所以会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说法,那重要的又是什么?当代艺术在方法论上是一种观念形态,自杜尚《小便池》开始,观念形态就超越了古典艺术的模仿论和现代艺术的形式论,成为新的艺术方法论,并在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得以理论确认。自此,绘画不再只是艺术史的遗弃物,而在艺术方式的意义上与装置、行为、影像等等新媒体艺术都站在观念艺术的起跑线上,没有优劣之分。这样就排除了绘画和当代艺术之间的障碍,因为绘画之中观念主体的存在,作为当代艺术的绘画具有了新的生命、新的尺度。
纵观今日美术学院基础部教师的作品面貌,尤其是造型艺术基础部,作为当代艺术的绘画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见证于此次天津美术学院主办的纸上作品展。展览作品以纸上作为媒介,固然不能涵盖参展艺术家的全部艺术面貌,但一斑窥全豹,依然可以透射出目前国内艺术学院基础部教师的艺术思考和创作状态,进而可以了解到国内艺术院校基础教学的普遍状况。
纸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材料,最必要莫过于中国画中的宣纸,因其特别的材料和制作工艺,使得水、墨及矿物、植物颜色在宣纸之上随用笔不同而能千变万化、气象万千。其他类似的还有水彩纸,在西画中也是一种独立表现形式。另有版画,无论石版、木版、铜版还是丝网版、数码版,最后都要在纸上呈现出来。最普及的当属手稿,几乎所有专业的艺术创作,都要先把大脑中的灵感及时记录在手稿之中,以思考和整理,进而创作出完整的作品。纸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可以轻易记录下瞬间即逝的痕迹,纸又具有异常的坚韧性,能够承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的苦心经营。纸是基础部教学中最常使用的绘画材料。在基础部的教学中,深受半个多世纪的西法和苏式教育的影响,即便中国画系也要接受“素描改造中国画”的方法。这种局面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松动起来,每个专业都开始探索自己的基础教学和专业衔接问题。当90年代之后国际艺术语境和当代艺术理念逐步反刍至学院教学,跨专业和跨学科的需要又要求在基础教学阶段淡化专业意识而强化通识基础,兼容或者说独立于各专业的基础部教学应运而生。纸的常用性没有改变,纸上所画的却已大大不同。
不同主要在于后设观念的提前介入,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专业和画种的分类,而成为观念之下的区分。就此而论,对基础部教学的观念意识的强调更能对接之后的专业教学,即便二年级学生依然进入传统的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专业,先入为主的观念教育也会对各个专业本身造成冲击。客观而言,并不是所有艺术院校和基础部的教师都能具备观念意识,更多的是潜在表达。因此,通过展览和研讨活动来推进基础部教学的理论和观念探讨尤为必要。
谈及理论和观念,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当代艺术理论都来自西方,这和现代以来西方人文主义观念的加速推进有关。西方文明主导了现代世界的进程,并影响到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至当代艺术。今日的中国社会依然处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之中,原有的传统艺术理论如“六法论”“南北宗”“天人合一”等等都未走出传统世界,尚需完成古今之变。再者,西方在这里更意味着理论的先导、文明的索引。无论中西都要面对古今之变,期待东方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型。基础部,一年级新生虽然刚刚进入大学,但当代艺术语境已经要求他们直面各种理论话语,并且在纸上尽力表达出来。而这,首先是基础部教师的工作,正如本次展览所呈现的。
吸取美国学者罗伯森和迈克丹尼尔所著《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的部分理论成果,本次纸上作品展既未按院校分类,也未按照专业和画种分类,而是依存于理论话语,将作品分为身份、身体、时间、场所、语言、精神性六个部分:
(一)身份通常指涉一种社会和文化身份,一位热衷于身份问题的当代艺术家不仅会问“作为个体的我到底是谁”,还要问“作为群体成员的我们又是谁”。如果是一张课堂写生,关注的问题并非造型结构而是模特的社会身份,或者对象的模特身份。(二)后现代视野下灵魂虚无,唯有身体。然而本真的身体并不等同于一种生物有机体,诚然身体特征的本质是物质性,但身体的本真背后一定有着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与身份彼此重叠。此外,一件非人体的现成品同样成为身体的隐喻式替代物。(三)时间的意识意味着一种历史意识,从生到死,任何人、任何事件以至整个历史都在时间之中,而我们所在的此刻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与之形成张力的永恒却在记忆与未来之中。(四)自然被现代社会改造为场所,成为人类行为的背景,被赋予记忆、历史和符号意义,汇聚了特定事件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由此,场所成为社会景观。(五)语言、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中心问题,在审美现代性未经充分发育的中国,现代艺术依然有着必要的现实意义。当代艺术中的语言,进而转化为符号、文本和修辞问题。(六)精神性代表着世俗之上的超验存在,对生命源头和死亡时刻的终极追问,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中神秘推动力的无限认知。生命之谜和精神需要,俯身引导着个体和公共行为的道德准则。特别在后现代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精神性越来越成为当代艺术公开表达的复兴主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为观念的潜在或自觉的表达,艺术院校的基础教学虽然还是以纸上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但已呈现了别开生面的异象。美术学院经常被质问是否能培养出当代艺术家,而基础部的教师承担了最开始也是最关键的教学工作。实验性、开放性的教学,首先开始于这些教师艺术家们在纸上的探索,是为本次展览的现实意义。